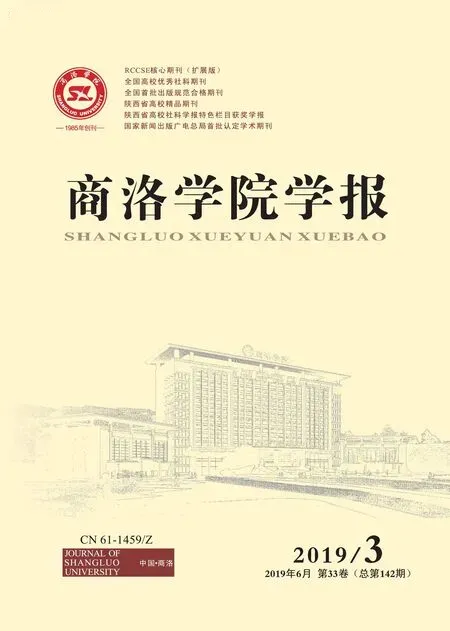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城乡关系叙述
杜薇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书写农民进城、反映城乡关系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出现了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际遇以及他们对城市的认识,同时也寄予了作家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城乡对立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在“十七年”文学中,也有一些小说反映了解放后的农民进城—返乡的无奈与痛苦,初步表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这些小说有箫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康濯的《春种秋收》《水滴石穿》,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卖烟叶》《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等。这些小说反映了一部分农村青年“向城—进城—返乡”的历程,歌颂了那些热爱农村、建设农村的农村青年。它们通过描写一部分“不安分”的农村青年的生存道路,意在告诉读者: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农村同样能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在主流意识形态理论预设下,城乡并不存在差别,城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不同战线,农民、工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与劳动者,并没有高下之分。因而“十七年”的文学对城乡关系的书写迥然不同于当下的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十七年”文学虽然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相对传统农村生活所展具备的优势,但并没有像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那样把城市与农村置于二元对立的位置之上,还是写出了二者的统一之处。目前学界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论文很多,但从城乡关系这个视角切入,探讨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文献尚为稀缺。十七年文学在城乡关系书写方面具有独特的思想与美学特质,形成了独特的写作策略与修辞方式,塑造出了一些不同于社会主义新人的人物形象,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城乡关系书写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在中国现代话语谱系中,城乡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并置关系,还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政治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城乡有不同的文化想象。“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作家都把乡村想象为落后、愚昧、停滞、保守、压抑人性的藩篱,把城市想象为先进自由、开明、发展、开放的世界,出现了一些表现追求个性解放、争取进步的知识分子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小说。三十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了以农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农村成为革命、开放、先进的世界,而城市的革命意义则被怀疑,城乡问题得以政治重构并被赋予不同的符码。“以前,城乡冲突造成现代中国作家的道德困境,现在城乡问题的这种文化基础,逐渐让位于一个城市话语服从于农村话语的新政治结构。”[1]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思维惯性,农村话语或者说农民意识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对城乡关系的定位,进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不断得到体现和表达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形象地把中国共产党进驻北平称为“进城”,言外之意是城市与农村有不同的伦理观念,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好管理城市的知识储备,他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2]箫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就是一部讲述革命胜利后革命干部进城的故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出身贫农的干部张同志在革命胜利后进入了北京城,虽然是第一次来北京,李克却对北京的城市生活很熟悉,感到心情舒畅愉快。从来没有到过城市的张同志本应该更加兴奋,然而她却表现出对城市生活明显的疏离感甚至反感。二人由此发生了矛盾,夫妻感情也出现了裂缝,甚至达到了离婚的边缘,后来二人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达成了和解,重归于好。从话语层面看,这篇小说表现的是解放后普遍存在的革命干部的婚姻危机问题,而在故事层面,却提出了严肃的城乡关系问题、现代生活与前现代生活的关系问题。这篇小说以夫妻二人的和解暗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和解,然而他们二人和解的基础固然有李克在政治上对妻子的认可,更多的则是因为“我”的妻在现代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服装上变得整洁起来了”,粗话没有了,“见了生人也很有礼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到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我”的妻的生活习惯的变化说明了城市文明、现代城市生活对人们极大的影响与渗透。“小说还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以具小资产阶级身份的‘我’为叙事主体,赋予‘我’以优越的话语权,从而可以自由地对其中的人物进行评判,表达自己的见解与声音。”[3]而改造者“我”的妻却处于沉默、被评判的地位,预示了改造者的无力,这篇小说也客观地揭示了现代城市生活与传统农村生活的巨大差距,揭示了城市与农村的矛盾。
小说借李克的感觉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美好与时髦,他对象征城市文明的高楼大厦、丝织的窗帘、地毯、沙发、洁净的街道、闪烁的霓虹灯、爵士乐非常地向往与亲近。
在十七年文学叙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知识分子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且也可以看到城市生活对农民的吸引。康濯的小说《水滴石穿》中的张小柳就是一个对城市生活非常向往的农村青年。张小柳是住在庄上二层楼上的一个苗条白净的姑娘,初中毕业后在社里当会计。她上过初中,她了解了村外世界的精彩,她不甘心做一个农业社社员,一心想通过各种途径去城里当工人,过城里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张小柳,泉头庄上的其他农民也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惊羡与向往,他们对城市生活了解非常少,只能通过张小柳与张小柳的同学了解城市生活。男学生的皮鞋、棉夹克和栽绒帽子以及女学生的紧身小袄与鲜绿的头巾为他们吹来一股清新的城市气息,引得人们像看外国朋友那样指指点点,连他们站立的姿势与走路的姿势在农民眼里都有一种迷人的气派。他们旁若无人的拉手让农民们颇有点难堪,他们说笑的声音简直要盖过连天震动的风箱声。作者通过庄上农民的眼睛形象地写出了现代城市文明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他们并没有认为这几个城市女学生多么伤风败俗,而是充满了惊奇与羡慕。在他们的眼里,只有长相漂亮或者有文化的才能进城过城里人生活。在申玉枝的婚姻问题上,他们表达这样的意见:“我看呀,她最好早早走开。”“赶快找个县区干部,跟人家一走。要不的话呀,你别说这会儿,就是往后她结了婚,咱们见了面怕也要别扭得慌。”“是呀,玉枝少说怕也要找个县区干部,咱村里人们也都这么说的。”申玉枝长得漂亮,他们认为他们农村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申玉枝,申玉枝只有嫁到城里,他们的心理才能平衡。这虽然是一种“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的嫉妒心理的自然流露,可是也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种态度正体现了乡村背后的弱势和被歧视地位。
小说《百炼成钢》中,秦德贵的母亲说有很多农村姑娘都愿意嫁给城市工人。小说《山乡巨变》中,秋丝瓜张贵秋因为自己的妹妹漂亮便撺掇妹妹离婚嫁到城里;盛学文初中毕业后一心想读高中,离开农村去城里工作;盛淑君也想去城里当工人。
和其他进城的女青年不同的是,《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进城不仅仅是为了寻求一份好工作,而且还有寻求人格独立的意味。改霞一开始担心自己年龄大,上不了中学,认为不如趁早参加农业,搞互助合作,而对梁生宝的爱慕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梁生宝对她的误解及冷遇让她下定决心考工厂。考工厂的人特别多,不免让改霞产生一种自卑心理,担心自己考不上。对梁生宝的依恋让她很惶惑,王亚梅的教育让她顺势决定回到农村和梁生宝一起搞合作化。回来后,改霞决心和生宝过了。她决定主动追求生宝,但生宝怕两人的情感影响互助组工作,让改霞等到秋后再说。这让她重新思考二人的关系,最后去了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厂当铸工学徒。改霞之所以进城,不是因为她拈轻怕重、爱慕虚荣,而是要寻求独立人格。改霞担心结婚之后,自己会成为一个做饭、生孩子的家庭主妇,这样的生活是个性要强的她所不希望的。改霞热心社会活动,不甘愿当一个庄稼院的好媳妇,所以她毅然离开了她热爱的农村,离开了她依然挂念的生宝。
建国初期,农村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在中国农村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一家一户的劳动方式,消除小私有者的所有制形式,代之以集体劳动的形式,使农民取得与工人相同的劳动形式。如果合作化运动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机械化水平高的情况下,是可以提高农村的生产力的。问题是当时农村的机械化水平不高,农民们还没有达到集体劳动的觉悟,合作化运动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农业社里,农民们虽然是集体劳动,但劳动内容没有根本的改变,还是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必须消耗大量的体力,这让很多社员吃不消。“另外,在积肥、插秧、收割等重要农事活动中,因为要与单干户比赛,也因为要赶时间赶农时,农业社成员被要求不管刮风下雨都要没日没夜地大干苦干,以至连年轻力壮的民兵也普遍感到睡眠不足。”[4]在合作化初期的新鲜劲头过去之后,社员们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为了保持社员们的积极性,农业社实行高度组织化的管理体制与以劳动竞赛为主要方式的激励机制,这让社员们不但感到疲乏劳累,而且感到不自由。“日常生活充满了革命意味,已沦为残酷而又刻板的范式。不存在什么人类普通的美的标准,只有带有阶级性烙印的美的理解,‘无产阶级或劳动阶层的美才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美,’革命把美学边缘化的同时,实际上把审美从日常生活中给驱逐了。”[5]城市工人为了完成国家订购任务,也是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但他们毕竟还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下班之后,还是有相对宽松的业余时间供自己支配,他们的工资虽然不高,相对于农民的工分毕竟还是丰厚的。他们有时间可以饭后散散步,周末逛逛公园,也有收入以便早餐喝杯豆浆、吃个鸡蛋,周末有时间和家人在餐馆吃饭,也有钱买几件时髦的衣服。这是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这种审美化的现代城市生活无疑会对农民们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二、城乡叙述策略
十七年文学提出了一些值得观察和思考的城乡问题,如“进城”与“返乡”、人物的矛盾与纠结等,这些问题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复杂性。文本的叙述是建立在主体体验或者个体实践之上,虽然说有作家文学想象的成分,但更多可能是细节的相似或者存在,而这恰恰是文学深刻性与普遍性的形象表现。所以,我们观察城乡关系中的特定群体或者特定现象,可以认识作家传达出的诗学与史学的双重意义。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我”是小说的男主人公,“我”虽然有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但作家对“我”持明显的肯定态度。“我”开放、宽容、头脑灵活、乐于接受新事物。“我”对生活的态度是:革命胜利了,应该按照城市生活的习惯规则生活,可以在条件许可的基础上适度地消费。因而“我”想用稿费买双皮鞋、买一条纸烟、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淇淋,闲暇时间跳跳舞。而“我”的妻却是满口脏话、不顾场合大声嚷嚷、多管闲事,走路穿衣土气十足。从现在来看,“我”的妻的行为是一个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在完全陌生的城市文化环境中的自然反应。作者以写实的笔法写出她的种种可笑行为,就形成一种反讽的力量,同时表现了作者本人的城市文化意识。难怪小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有的文章认为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她”,“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是由于作者脱离政治!在本质上,这种创作倾向是一个思想问题,假如发展下去,也就会达到政治问题。”[6]批判者认为作者的政治倾向出了问题,显然是夸大其辞。不过,当时的红色批评家们的确看到了“我”不同于主流小说中塑造的与工农群众结合的知识分子。
最能表现农村知识青年进城艰难、返乡痛苦的是康濯的小说《春种秋收》。这篇小说是新郎新娘所讲、别人补充的、作者认为是绝对真实的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和当时的其它农村题材小说一样,康濯所赞颂的,也是基于服务农村的新时代农村青年献身农村的美好情操。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向城—进城—返乡”的故事。农村姑娘刘玉翠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中学,只好回到农村,她不甘心留在农村,不得不通过找对象的方式进城,但没有成功。在一个书记的帮助和一个农村先进青年的影响下,她回到农村积极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篇小说的主体却展示了农村青年刘玉翠向城、进城、返乡的经历,展现了刘玉翠对城市的向往、进城不得的痛苦以及返乡的艰难,表现了五十年代农村知识青年的理想与愿望。刘玉翠上学期间,当过团干部,觉得自己知识多,长相好。她对城市的向往很执着,城市里的工人妇女、电灯电话、高楼大厦、花衬衫、洋袜子、妇女的卷发等对她充满了无尽的诱惑。她住的小山村非常偏僻,野兽出没,是个荒山野洼。农民虽然翻了身,可是仍然被拴在二亩硬土上,没有俱乐部,赶个会、看个戏,出门得走二十里地。她回到村里,好比住进了监牢,见了人怕笑话,只好躲在家里佯装看书,可是一个字也看不下去,上地里劳动又心不在焉,感到非常无聊。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刘玉翠在农村的尴尬,写出了既向往现代城市生活可是又找不到出路的农村青年的窘态与痛苦。对于农村青年来说,考不上学,就只好靠找个城里对象来进城,但是刘玉翠碰过四五个县区干部都没有谈成。农村不但物质生活贫乏,而且精神生活也非常单调,满足不了刘玉翠想赶会、看戏等愿望。而这是一种正常的消费。“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7]因而,刘玉翠想进城是很正常的,但是她的这种想法却被当地农村人们冠以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而“享受会把消费规定为自为的、自主的和终极性的。”[7]她的思想和行为遭到了同村人的鄙视与嘲讽。在村中人看来,她不配享受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瞧不起妇女,并且风来雨去地造她的谣,纠缠得她情绪不高。小说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刘玉翠进城不得的痛苦,“‘他若是晚一点去省城,’玉翠伤心地想着,‘等跟我谈好了,再让我一块同去,该多好啊……’接着又闪跳出了自己的前途大事:‘城市!学习!建设……莫非就注定了要一辈子困死在这个老山沟里么?’”“这一夜,刘玉翠根本没睡觉。熬到天刚露明的时候,猛一下蹬开被子,爬了起来,扛上镢头就走。她好像发了个狠——倒要看看周昌林是不是还会在坡上的地里等她。”农村那几个青年她看不上,团县委副书记看不上她,这让她的自尊心大受打击,因此她横下心来接受周昌林的爱。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这是小说中最精彩、最生动的一处心理描写,写出了一个颇有点虚荣的农村女青年在自尊受到打击后的真实反应。她美丽、纯洁、有文化,不甘于农村的艰苦生活,追求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这是一个想走出农村却没有找到办法的有代表性的五十年代的农村青年,她的人生道路展示了一个向往现代城市生活却又不得不留在农村的矛盾与痛苦。小说展示了她们不安而又躁动的灵魂。
《山乡巨变》中的盛学文是一个初中生,是盛佑亭的二儿子,他不但勤谨而且功课也好,很有希望考上高中;他也希望自己能上高中摆脱农村的生活。盛学文、张小柳、刘玉翠等人物形象迥然不同于工农兵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们对农业生产缺乏热情,他们不能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动摇、苦闷、彷徨。这种人物塑造具有较多的人性内涵,呈现出立体化的丰姿。无论是张小柳、刘玉翠、盛学文还是向往城市生活的人大都是上过学的农村知识分子,他们见过世面,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把逃离农村、向往城市的农村青年设置为读过书的知识分子,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说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心理。学校在这里充当了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通过学校了解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美好,学校不仅为他们带来了知识,而且带来了想出去的冲动。对他们来说,学校是由农村通往城市的阶梯,清闲的工作、丰富的生活、优越的地位甚至美丽的爱情,都因为学校而变得具体可感。
小说通过人物“向城—进城—返乡”的经历提出了城乡关系这一问题。城乡差距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建国后的工业化战略又加剧了城乡差距。“只要城乡差距还存在,城市化进程仍在进行,城乡一体化没有最终完成,不管是以显性题材或隐性背景出现,城乡关系依然是当前文学创作绕不开的最大现实。”[8]温铁军认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部门垄断的国家资产,供后人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留下了一个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9]五十年代初期,国家不但把大批资金投向城市,而且把农业积累的资金也投向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村的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设施严重不足,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使得农村屈服于城市,造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既然城市与农村存在较大的差距,那么就会产生对城市向往的人们,因为“当社会生产出城市化的空间形态时,同时也就相应生产出人对城市空间的欲望表达形式。”[10]城乡问题的客观存在,引起了文学想象中的一次又一次的“进城”与“返乡”的书写。不过,“十七年”文学的城乡书写还是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通过对人物行为的褒贬,教育农村青年:农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天地,只有扎根农村、脚踏实地,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通过“进城”与“返乡”的书写,十七年文学成功地把农村想象成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园,抚慰了当时人们在城乡之间的巨大情感落差。
三、城乡冲突的想象性解决
在十七年文学中,城乡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一旦把握不好,就有可能逸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遭到严厉批判,最根本的一点是它表现了农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改造的事实,委婉地表现了乡村文明的弱势地位。正如董健所言:“以农村改造城市还是以城市改造农村,这在当时是大是大非的问题。”[11]《创业史》写出了改霞一波三折的进城故事,也没有对改霞的进城进行批判,原因是作者热情地讴歌了农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在作者的描述中,农村同样也是青年人创业、实现自己价值的充满希望的田野,柳青没有把城乡置于二元对立的位置上,没有写出城市对农村的改造与挤压,这篇小说与《我们夫妇之间》的命运也截然不同。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反映出农村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热火朝天的场面,塑造出脚踏实地、克己奉公、锐意进取带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新人形象,表现出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应当反映出城市与乡村互相支援、互相合作的场景来。因而,在“十七年”文学中,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外,其它书写城乡关系的小说都没有把城乡关系作为小说的显性主题来表现,而是作为一个隐性问题来叙述。《春种秋收》的主题是通过讲述农村发生的新鲜事来歌颂农村的光明前途,歌颂那些热爱农村、安心农业生产的农村青年的优秀品质。《水滴石穿》表现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这些小说虽然没有把城乡关系作为显性主题来表现,可是仍然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文本裂缝,让读者体会到城乡问题的严重。
城乡对立有历史原因,而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更加剧了城乡对立,城乡对立问题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在文学中叙述这一问题呢?在“十七年”文学中,反映城乡矛盾的小说都以爱情的形式解决了城乡冲突的问题,以那些不安分的农村青年找到理想爱情的方式来弥合城乡对立。张小柳返回后依然得到了杨吉吉的谅解;刘玉翠赢得了乡村优秀青年周昌林的爱情;清溪乡群众也帮助盛学文找到了幸福的爱情;马有翼赢得了王玉梅的爱;范灵芝与王玉生成了幸福的一对。甜美的爱情稀释了农村枯燥的生活与劳累的体力劳动,增添了农村生活的情趣。然而,这种解决方式只是暂时抚慰了农村青年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刘玉翠们、张小柳们的心灵将会再次苏醒。小说虽然以爱情的甜蜜稀释了农村青年城市梦破灭的痛苦,但小说还是留下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并暴露了城乡问题的严重性。
农村面临知识青年逃离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它从侧面反映出农业合作化改造的凝聚力问题。张小柳的进城引起了村支书以及申玉枝的关注,张德升对申玉枝说:“听永德说,有个什么学生老跟她捎信,可别是她……咳咳,咱们这头一年刚办的农业社可不能留不住人哪!咱们再抓紧说服她和吉吉,该拉扯着他俩结了婚,才稳妥呢!你说是么?”农村人才的出走,不仅使农业社面临劳力短缺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为了回避城乡矛盾,作家们设置了这类情节:农业社为乡村知识分子提供了较清闲的工作。如马有翼和范灵芝当了村里的扫盲老师,张小柳在村里当会计,刘玉翠在村里主要干技术工作。为了让农村知识青年返回农村,作家们设置了来自城市的非硬性的藩篱,目的是让这些知识青年自己的失败阻断他们进城的道路。如张小柳两次考试失败,她不得不回来;刘玉翠也是因为没有考上中学,回到农村;盛学文功课虽好,但他父亲不再支持他考学,他不得不回来。小说并没有设置来自城市本身的障碍,这样的叙述缓解了城乡的对立与矛盾。实际上,由于这些农村知识青年所在学校的基础条件、师资力量、学习气氛与城市学校不可同日而语,而录取分数相同,其中蕴涵着深刻的教育不公,很多农村青年在考试中落榜是必然的。
建国之初,城乡虽然差距明显,但是城市并没有呈现出当下打工文学中那种冰冷、冷漠的印象。“城市所需的豪华经济想象力于此刻依旧是匮乏的,故此,仅在空间的外在性上,城市的形象尚不足以产生令农村不敢奢望的距离。恰恰相反,前者倒是为后者预留了一定的梦想空间。也就是说,对于农村而言,城市并非是不可亲近的。”[12]因为当时城市工厂缺乏工人,通过考学或者城市工厂招工,可以吸收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工厂,其它部门的农民青年只要专心学习技术,同样能成为城市的一员。例如《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本来是一个农民,由于自己刻苦钻研技术、大公无私,成为优秀工人。而当下的打工文学片面渲染城市的冰冷、冷漠,描写农民工与城市文明的不相容,夸大了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疏离。
我们不否认农民工在城市环境中面临诸多的不平等,但这些不平等并不是城市或者农村一方的责任,也不是市民与农民之间有天然的鸿沟,更不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难以融合,而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两种文明之间必然的交融过程。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很多农民工逐渐获得市民身份,而城市也在逐渐改变对农民工的态度。在城乡关系的定位问题上,十七年文学为当下的城乡关系书写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十七年”文学通过农村青年进城的轨迹提出了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应该说,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可以吸纳很多知识分子,农村知识分子也能在农村实现自己的价值。“十七年”文学塑造出了很多扎根农村、踏实苦干、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水滴石穿》中的申玉枝等。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在大多数农村,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在农村并没有发挥出应有价值,反而被作为“干啥啥不行”的红专典型遭到嘲笑。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张小柳、刘玉翠、徐改霞、马有翼等农村青年就经常受到农民的嗤笑,这也是他们要离开农村的原因之一。“事实将会证明,刘玉翠们绝非一个偶然和短暂的现象。这一事实似乎也在提示我们,当一个农民对于土地不再秉持着那种同历史与命运息息相关的本真情怀时,他极有可能转变成的将不是梁生宝或宋东山,而是刘玉翠。”[13]
四、结语
建国之初,农民不但有发家致富的梦想,接触了外界新思想的农村知识分子也有了更多的理想与愿望,而农村承载不了农民日益丰富的生存和生活理想。在“十七年”文学中,农村知识分子以相同的结局回到了农村,城乡矛盾得到了延宕、和解。“十七年”文学反映了农村与农民的矛盾,也反映了城乡对立关系,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但这可能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的城乡叙事,并不是以城市与乡村在现实中的对立为前提,在文化上所造成的想象性补充关系;相反,社会主义的城乡叙事参与到打破城乡对立的实践中去了。”[14]对于那些向往城市而又不得不留在农村的农村青年来说,社会主义的城乡叙事无疑给他们以情感上的慰藉、心灵上的抚慰,可以引导他们在农村实现自己的价值。十七年文学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看似相对简单的文本更能凸显一定的个人想象与文学想象,使文本具备了内涵的丰富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在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下具有特定的思考。同时,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十七年”文学的城乡关系书写无疑会给当下的城乡关系书写以及城乡问题的探讨提供有价值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