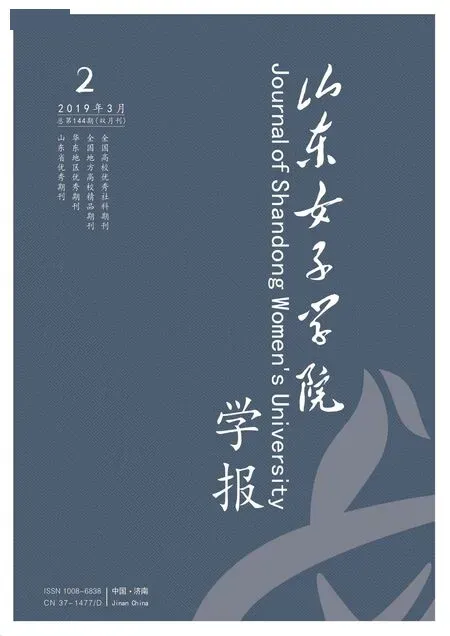影视剧中“白莲花”女主的兴起、反叛与变异回归
——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考察
崔应令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259770)
一、“白莲花”的污名化
“白莲花”并不是新鲜词,但开始具有负面意义大约是从2009年开始,同名泰剧中的女主角如同白莲一样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无休止牺牲,这种过分善良给自己和相关人带来了无穷的坎坷与灾难,让人反感。自此后,“白莲花”原有的善良、无害、纯洁、无辜的正解被取代,成为一个贬义词。百度定义对其这样描述:“她们有娇弱柔媚的外表,一颗善良、脆弱的玻璃心,像圣母一样的博爱情怀,是那种受了委屈都会打碎牙齿和血吞的无害的人,总是泪水盈盈,就算别人插她一刀,只要别人忏悔说声对不起,立刻同情心大发,皆大欢喜地原谅别人。”[1]萌娘百科则这样形容“……一贯偏执地追求自认为的善和爱,且对象泛滥;要求他人遵循她自认为的善和爱;坑且仅坑队友(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坑完队友仍不认为是自认为的善和爱造成的。”网络上有文章界定那些“柔弱善良、清纯高贵、出淤泥而不染,并且同情心泛滥,总是无原则地原谅(或假装原谅)所有伤害过她们的人,并试图以爱和宽容感化敌人”的人为“圣母”“白莲花”。同时也区别两词,认为前者“更多地被用于形容毫无用处的同情心泛滥”,过分善良,力图拯救全世界,是道德圣母;后者“则更强调一种虚伪与自命清高的姿态”。
当“白莲花”被污名化后,人们开始从以往影视作品中寻找其代表。琼瑶小说和其影视剧中的一系列女主都成为其代表:紫薇、白吟霜、紫菱、新月格格等,她们纯洁善良,为了爱可以委屈求全,承受一切羞辱,她们隐忍、美丽,是男人们梦寐以求的爱人、情人。她们的人生目的是爱: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这些曾经代表“完美道德”,“描画着重建道德体系的美好愿景,并以‘承担苦难的命题’许诺她的观众:对道德的坚守和对苦难的忍耐可以通向对自我心灵的救赎”[1]的人物成为攻击对象,不再被人称颂。
白莲花女主成为很多女性公开讨厌并攻击的对象,如玖月晞的《黑女配,绿茶婊,白莲花》(后改名为《怦然心动》)就是完全批判这类女性的。当然白莲花也被用到男性身上,有人认为《琅琊榜》中的“靖王”就是男版的白莲花,靖王完全是“道德”的化身,只做“正义”的事,为他心中的正义甚至冤枉伤害其最好的战友梅长苏[2]。有意思的是,除了专门的分析者,一般观众对男版的“白莲花”并不那么反感,这也说明人们反感的主要还是“白莲花”女主呈现的不平等的性别预设和压迫以及女性的自我奴化。
就这样,“白莲花”一词成为一个负面词,传统女性所代表的形象及其道德观遭到批判并被彻底污名。
二、反“白莲花”背后的女性抗争
21世纪初的影视剧中开始出现反“白莲花”女主形象,这些形象背离传统性别角色的定位,显示出强烈的反抗性。琼瑶笔下的貌美坚贞的女子也遭到批判,如有学者就明确认为琼瑶剧中的女主无不反映“琼瑶对父权社会中男女角色定位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认为琼瑶剧中除了理想的男主和坚贞的女主外,往往伴随着“弃妇”角色和女主爱情背后的“情人”定位,琼瑶宣讲爱情至上的同时,将另一些“主妇”设置成真正爱情的障碍而予以抛弃,这仍是“遵从男权社会规范”的爱情[3]。所以,琼瑶剧中理想爱情的背后,实际上是女性“对男权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度依附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性关系的价值规范一致”[4]。
反“白莲花”女主的代表作是2004年TVB拍摄的《金枝欲孽》和2006~2007年的《后宫·甄嬛传》,前者被称为宫斗剧的鼻祖,是“腹黑”女主上位记;后者则完全是女性抛弃“白莲花”内核的“生命成长史”。两部作品都是对“白莲花”女性的抛弃,都具有强烈的反抗传统男权的意识。具体来说其反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塑造道德上有瑕疵甚至是腹黑的女主,通过揭示她们腹黑背后的不幸遭遇和性别压迫的深层机制达到反抗男权制度的目的。
《金枝欲孽》中的女主玉莹看起来人畜无害、貌美、单纯无邪,实际上却心机无限,为了上位可以出卖爱她的人。她说:“良心?我早就没有了。”而前期一直善良的老好人安茜也发出感叹:“赢的,赢在她们心狠手辣;输的,也未必就正直不阿”;尔淳更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随时出卖姐妹;如玥则更是一出场就心狠手辣:“心甘情愿,俯首称臣这些话,从来都不是用来形容我祜禄如钥的!”每个女性都不是单纯的良善之辈,唯一看起来天真烂漫的人反而最有心机。然而,这些腹黑之人却都有自己的苦衷。对女性形象的去道德化设置并非倡导无德,而是批判导致无德的原因。
《甄嬛传》里的女主一开始还是天真善良、对爱情有期待、对他人友善之人,但后来的发展正如剧情所呈现的,是她一步一步远离“白莲花”之路。在被算计、倾轧、谋害之后,女主用更狠的手段和阴谋回宫复仇,甄嬛的“黑化”不仅合理而且成为众人的期待——期待好人黑化后对坏人的反扑。
其二,通过对女主们宫廷内险恶生存环境的展示,揭示出在一个对女性伤害轻而易举的空间中,女性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自救的道理,粉碎以往女主被动、需他救的形象设置。
“白莲花”女主们在经历坎坷后往往是依靠严格恪守父权社会的品德等待男主们来救,但《金枝欲孽》和《甄嬛传》的女主们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虽然不排除有男性会帮她们),她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手腕和能力而自救。比如《金枝欲孽》中的祜禄如钥说:“我一直没有兴趣做孔雀,因为浴火重生的只有凤凰!”老好人安茜说:“后宫这里,不会有朋友,也不会有亲情,更不会有任何信任可言。在后宫这里,有人奉承你,就代表有人想利用你,有人对你好,就代表有人想害你!”尔淳说:“要得到男人的心,最下乘的方法是千依百顺,这样会让男人觉得索然无味;中乘的方法是若即若离,让男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最上乘的方法就是求而不得。”这强调的是能力和计谋。
《甄嬛传》并无例外。女主甄嬛最初的纯情、眉庄的端庄、安陵容的单纯,都很快淹没在宫廷内的残酷争斗中。甄嬛的丫头浣碧曾说:“且不说利用两个字难听,要是没有利用价值,那才是穷途末路呢”,这说明能力才是后宫生存的第一要诀。敬嫔对甄嬛更是直言生存不是靠心善:“妹妹心善是好事,可是在这宫里,只一味地心善就只能坏事了。唯要牢记一句话,明哲保身才是最要紧的。”端妃说:“华妃若是猛虎,曹琴默就是猛虎上的利爪,不过,你要知道锋刃在谁的手中,就能小心避开,只怕是身受其害,却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呀。”这些论调背后都是对能力的强调,揭示了在一个对女性极为残酷的世界里,女人想要靠“白莲花”般的圣洁及道德自律生存下来几乎不可能,除了锻炼自己的能力,别无他法。在最新的网络剧《媚者无疆》及其同名小说里,这一点更是被无限放大。危局之下,无人来救,主人公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来,再努力改变现实。可谓世事艰难,除了奋斗别无他法。
其三,女人斗女人不再有单纯的赢家,几乎都是双输,女人互斗导致的悲惨结局产生了对男权最大的反抗。
优秀的作品如《金枝欲孽》和《甄嬛传》都写到了女人斗女人的悲,仿佛有输赢,但终究没有真正的赢家,这两部作品看似是对男权的依附实则是对男权社会最大的抗争。悲剧,总是将美撕毁了给人看,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中人物的悲剧就是其抗争性,人物有多美好,其不幸就有多大批判力。就如毕飞宇在《〈水浒传〉的逻辑与〈红楼梦〉的反逻辑》一文里讲到的林冲是如何被一步一步“逼上梁山”的:林冲本是个怂人,只想安安稳稳地过点小日子,但就是这样也不可得,因此“林冲越怂,社会越坏。林冲的怂就是批判性”[5]。
《金枝欲孽》中的女性的结局要么死,要么逃,要么失去生命,要么失去所爱,没有赢家。《甄嬛传》看起来略有不同,因为女主最后斗赢皇后,斗赢皇帝,是有输赢之别的。可是事实是,她爱的人十七爷死了,她最好的挚友沈眉庄也死了,她曾经最好的丫鬟流朱更是早早就为救她而死,她的闺蜜——天真浪漫的淳儿也死了,她有赢吗?没有赢家,真正赢的还是那高高在上的皇权和置女人于死地的男权社会。于是,对“白莲花”女主的反抗以女人互斗之悲惨结局完成了真正的抗争。如《金枝欲孽》中的安茜所说:“离开紫禁城,离开那个四面被红墙围着的鬼地方,那里面只有冤魂以及仇恨,没有的只是自己。在那个地方我已经失去很多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走,你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你可以的。”
离开宫墙,就是控诉,就是抗争;死亡,也是。
三、“玛丽苏”女主的霸屏与“白莲花”的部分回归:女性反抗的削弱或消解
在琼瑶剧被批判,大量宫斗剧开启女性智商上限时,电视剧市场开始出现大量的“玛丽苏”[注]玛丽苏,英文名Mary Sue:最早出现在同人文学作品中,女主人见人爱、高度自恋,高智商、高颜值、善良,无所不能。不同于西方女主无缺陷、无成长的特点,国产影视剧中的“玛丽苏”女主或者“傻白甜”或者“白莲花”,除了绝对的善良和漂亮外,往往有缺点,且后期有成长。作品的共同处是所有男人都爱她,女主光环加身,有难总有人来救。玛丽苏分为“完美型”和“平凡型”,前者主要是能力上的无所不能,后者则多是运气上的无所不能——傻白甜还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而中国影视中的玛丽苏具有各种杂糅性,不变的是人见人爱,总有男人甘愿为其去死,最终女主一定强大到令所有人臣服——走向完美。参见百度词条“玛丽苏”。式伪“大女主”作品[6]。电视剧中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玛丽苏”女主,往往都有一群恶毒“绿茶婊”[注]“绿茶婊”,最初指2013年4月三亚海天盛筵陪睡事件。2015年后,网名“H.H先生”创作了系列漫画,并冠以题目“告诉你什么是绿茶婊”,将绿茶婊予以泛化,泛指外貌清纯脱俗,总是长发飘飘,在大众看来素面朝天,在人前楚楚可怜、人畜无害、岁月静好却多病多灾、多情伤感,背后善于玩心计、玩弄感情的女人。这个词往往是女性对那些假装清纯的心机女性的称呼,有轻蔑、嫉妒和憎恨情绪。参见百度词条“绿茶婊”。女配要加害她们。这些作品部分融合了琼瑶式的爱情至上观,又添加了宫斗元素,但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量“恶毒女配”,她们成为让人憎恨、嫉妒或厌恶的女性代表[7]。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兼带“白莲花”特征的玛丽苏女主和“绿茶婊”元素的女配影视剧形象呢?
其一,无论是拥有百般技能的全能型“玛丽苏”女主,还是本是普通“白莲花”女主但最终成长为赢家的平凡“玛丽苏”女主,都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抗争性,代表了对女性有能力改变命运并能支配命运的向往或梦想。
然而引无数男性折腰的女主形象设计,和现实中女性的真实情况对照,更像是一场意淫。这些作品表达了女性希望自己是中心,是被爱的对象,是能最终胜出的强者的希望或者说梦想。如《醉玲珑》中的凤卿尘会弹琴、懂茶艺、能排兵布阵,还懂术数变化且精通医术,她们拥有现代知识。在《步步惊心》《独步天下》等玛丽苏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前者女主在穿越前就对清史有爱好与研究[6],后者则干脆将历史故事变成为女主的创作作品。这些作品为现实中的人们(主要是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意义与快乐”,事实上“对受支配者来说,快乐源自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对支配结构的抵制……快乐源自所生产的关于世界的意义和关于自我的意义,它给人的感觉是在为读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支配者的利益服务”,因此,受支配者可能是“无权的”,多难的,却因为抵制而获得“力量”[8]。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仍有一定的女性意识。
其二,玛丽苏女主的影视剧中一定会存在的恶毒女配,使得这些作品将此前阶段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反抗变成白莲花女主同道德败坏、相貌丑陋的女配的战争,大大弱化甚至消解了女性对男权制度的抗争力。
如果说反“白莲花”作品中,女人与女人的争斗不过是表,作为整体的女人同男权体制的争斗才是其魂,而玛丽苏女主影视剧里,女人与女人的斗争经由“绿茶婊”的女配彻底“变名为实”了。“绿茶婊”本是对女性的污名,是“多重压制”下“社会阶级关系和性别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9]。然而,所有人对这类女性的厌恶却几乎达成了共识:她们不够漂亮,心机又深,表里不一,手段毒辣,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她们不仅失于外在美,更失了内部美——德行有亏——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内耗和内部瓦解。女配们与女主的争斗因其道德败坏、手段恶劣而失去了对男权制度的批判,纯粹沦为女人对女人不得不展开的绞杀和毁灭。这对消解这类作品中的性别抗争力作用巨大,或者说这种对女配的贬低、对女主的抬高本质就是一场女性内部的内斗和自我瓦解。
其实在反“白莲花”阶段,这类女配已经出现,只是她们往往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总有为了家庭或为生存等方面的无可奈何,如公认的“绿茶婊”代表人物之《甄嬛传》中的安陵容,其行为虽然可恶,可其初衷也不过是护家庭周全和求自己生存,因此她的死也具有抗争性。但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玄女”和“素锦”完全是为了对爱情占有的个人欲望而歹毒,这就叫人几乎无法忍受了。她们的死不仅无法获得同情,反而掀起了全民狂欢——人们痛快于素锦被白浅挖双眼并被贬下凡,遭遇老公出轨、背叛的结局。女人斗女人,合情合理,理所应当。其背后的那些更大的政治抗争命题完全被淹没了。
除了恶毒女配的出现瓦解了这些作品的抗争性外,爱情重新成为重点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减弱了其抗争意味。
“白莲花”女主虽然遭到重创,但变了一个面目(全能玛丽苏或从平凡走向至高之位的玛丽苏)后又回归了,其方式除了女主的人设白莲花、傻白甜外,还有以纯爱、真爱、挚爱为名的爱情主题回归。比如本应该是大气的历史题材的《芈月传》,女主的权力之路如何走?她怎样与各种势力斗智,如何在各种利益纠葛中平衡、取舍?如何发挥自己的才智?对此,作品中几乎没有呈现。她在后宫的各种勾心斗角以及爱情麻辣烫,她与多个男人的情爱纠葛则九曲回肠、动人心魄,以至让那些抱着想了解历史上第一个自称“太后”之人是如何纵横权力的人大失所望。又比如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传奇》,更是彻底将所有有权有势的男人都爱我的意淫无限扩大,李世民、李治、李恪、李牧,这些有权有势且历史留名之人都爱女主,爱的方式各异,但都同样爱得深爱得切。女主武则天则是没有心机的“白莲花”一朵,是被各种外力推到至尊之位,观众在眩晕之中跟着做了一场梦。《独步天下》也是这种作风,且收视率都还不错。以女性观众为主的玛丽苏伪大女主电视剧早已成为麻醉药,与现实却毫无关系。
于是,反“白莲花”影视剧兴起的强烈的反抗性,在玛丽苏女主改头换面的回归中悄悄收起或变更了反抗的对象,女性的抗争之路在一片狂欢中曲折倒退甚至倾覆。
四、女性抗争之路仍在路上
从影视剧中“白莲花”女主的出现到反“白莲花”女主的盛行,词语从褒义变成贬义,包含着对传统父权社会的反抗和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不过这又是以消解“白莲花”作品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反抗意识为前提的。这首先涉及一个问题:怎样看待琼瑶式“白莲花”女主,她们身上是否也有反抗性?
回答是肯定的。琼瑶剧里那些为了爱情而反抗家庭安排、藐视宗族礼法、不惜“败坏”名声的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对当时大陆观众而言具有巨大的“石破天惊”之效,对解除女性身上集体主义的枷锁居功至伟。琼瑶剧中的女主角也有对家庭或家族的个性化的反叛,只是其对传统道德的遵从在女性彻底走向市场、个性突出的时代已经被抛弃,因此开启了对“白莲花”的反叛。
以女性心机和智斗为特征的宫斗剧是对琼瑶剧女主的抛弃,其不仅去除了“白莲花”般女主的道德人设,更抛弃了她们那种为爱情不顾一切的套路,女性在这些剧里或为了生存,或为了复仇,或为了报恩等不择手段上位,然而其上位可以为了任何目的,却很少是为了爱情——“甄嬛”曾有过对皇帝爱情的幻想,但终究绝杀了这样天真的念想,走向为了家庭生存的腹黑之路。我们可以说这种女性的反抗其实又增添了新的女性不自由——她们的反抗有多样化的功利目的,反抗背后其实还是有诸多的不由自主,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对职场女性艰难奋斗的职场之路的写照。无法爱、不能爱也是现实中女性们遭遇到男性不真心、玩弄下的理性选择。因此反“白莲花”女主们的挣扎、痛苦、不由自主,都指向对整个压抑女性的制度的控诉。
按女性主义的理想,影视作品下一步应该指向进一步的反抗和为女性解放提供途径选择和思考——可惜,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影视剧中的“白莲花”女主在一番改装后,以玛丽苏的方式强势回归。依旧是纯洁、美丽、善良、无害,甚至变傻了的女主,不过其人生一路开挂,爱情事业往往大丰收,她们在与恶毒女配的斗争中完胜,她们获得有权有势男性们纯真而浓烈无欺的爱,她们的一生足以让人们永远铭记。女主们与有权有势的男性结盟,将那些政治经济地位低下、道德也低下、长相普通的女配角彻底击倒粉碎。女性的同盟再也没有,有的只有阶级内部的结盟,更或者就是阶层碾压——恶毒女配存在的价值“就是被拉来制造爽点,让代入者在道德上、智力上、政治经济地位上,以及在男人眼中的地位上,获得一种全方位、碾压式的优越感”,“反映了我们时代,在阶级逐渐固化之后,有产阶级对于底层民众的冷漠”[10]。
换言之,影视剧作品中“白莲花”女主、反“白莲花”女主、“玛丽苏”女主都在消费时代被娱乐化、玩笑化,成为夺人眼球、遮蔽现实问题的手段,失去了抗争力。从女性意识消解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大众化、娱乐化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不过是“物质的安全感、思想的解放”的必然,是“人性的本真”的体现,还因其“对各种压制性意识形态的解构,从而实现了思想的再启蒙和人性的解放。”[11]恰恰相反,我们得到的实际是波兹曼“娱乐至死”带来的负面后果:“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2]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彻底异化,一切都终结了,生产、劳动、政治经济学终结,革命也终结了[13]。既如此,我们又怎能指望影视剧中的女性可以成为女性解放的抗争力或帮助构建出“不同于正统的另外一个空间和另外一种生活”[14]?甚至回头再看反“白莲花”女主的时期,仿佛也清晰可见反抗之下的娱乐与消费:如宫斗剧自《金枝欲孽》开始便瞬时成为一种流行,女人与女人的斗争,伴随漂亮的脸蛋、曼妙的身材、邪恶的手段、神算的计谋,没有比这更能刺激人的口味了,特别是剧中总有浪漫真挚的爱情,将观众对情感的个体化需求以浪漫化的方式呈现,从而“将一种隐蔽的政治秩序内化为自身实践的法则”[15],狂欢之下无人自知。
然而,娱乐化的手段、以消费女性(包括以女性成长和反抗男性为包装的消费)为目的的影视剧并非不能继续承载女性抗争的使命,就如同不管其居心如何,我们仍在反“白莲花”女主阶段看到了女性必须抗争的呼唤和力量一样。只是在当前新的情形之下,我们需要厘清几个问题:
其一,在阶层分化严重、阶层间隔膜加深的时代,女性群体内部早已分化,是否还有统一的女性利益?女性的解放指向何处?
女性内部确实分化严重,然而她们因其性别受到的压迫并无根本差异,我们从女性的污名来看其一斑:污称几乎涵盖了女性的各个方面,从女性性特征到其外表、年龄、职业、性格等横扫一切,女性几乎无所逃遁。比如与女性性特征相关的词:波霸(胸部丰满)、太平公主、黑木耳、粉木耳、事业线;与女性外表相关的词:亚美女(长相一般,但有气质)、恐龙(相貌丑陋的女网民)、美眉(漂亮女人);与女性职业相关的词:女司机、小蜜(秘)、家庭煮妇等;与未婚女子相关的词:没女(没长相、没身材、没学历、没钱的女性)、熟女(成熟女性——暗示性经验丰富)、剩女(高学历,高智商、高收入的未婚女);其他如:水母(经常上网发帖子的女性)、作女(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no zuo no die的女性)[18],实在看不到哪个女性群体可以逃过这些污名而单独存在。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女性内部的藩篱和互杀词汇如“大奶和小三”“良家和婊子”“大龄剩女和黄脸婆”“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等——几乎“每一对被男权语境成功创建并对立的符号都足以捉对厮杀,符合男权社会期待者得到奖赏,而不利于其统治者则经由同性之手,被钉死在耻辱柱上。但是何谓胜利者?‘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夸耀和羞辱之间,不过是顺从和反逆的区别。”[17]反抗压迫女性的制度和社会因素,这仍是解放必须达成的目标。
其二,在一个女性被消费、被娱乐的时代,该以怎样的方式让女性重新认识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压迫并作出反抗?
生在消费娱乐时代,想要逃离这样的背景而单独反抗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即便如此女性仍然可以“随时随地地抵抗和反抗”,并挑战“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权力”[18]。既如此,不如好好利用可以找到的武器,重要的其实不是手段,而是思想意识的改变。从女性主义意识看,1995年刘晓庆主演的《武则天》的境界不知比那个一团烂泥的《武媚娘传奇》高多少倍;而对父权当道、女性互戕的批判早在张艺谋1991年拍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就已经充分展现。只是这些精神内核没有被大范围继承发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主义的启蒙课还需要继续普及。当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实在太多了,比如我们要反抗的是压迫性的制度,不是男性——多数时候,男性也是男权制度的受害者;比如我们要明白对待男权意识深藏于心的女性,从改变其思想开始,而不是将其变成敌人。
总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继续完成没有充分完成的女性的思想解放和身体解放,这仍是我们的使命。因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和其他的人权运动内容并无不同,本质上是少数既得利益者和多数被剥削压迫者的冲突。……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割裂自己与其他女性、男性的关系,它必须要走到群众中去,走到女工中去,走到性服务者中去,走到被整个社会侮辱损害的女人中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