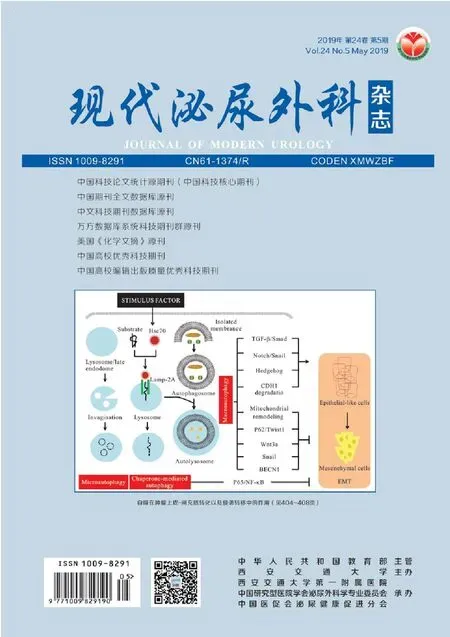膀胱颈部挛缩外科治疗的现状
宋汶雄 综述,撒应龙 审校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上海东方泌尿修复重建研究所,上海 200233)
膀胱颈部挛缩是前列腺良恶性疾病手术治疗后常见的并发症。以前的报道中膀胱颈部挛缩的发病率高达30%,随着手术技术的改进,膀胱颈部挛缩的发病率下降到了1%~5%[1-3],其中以机器人辅助腔镜手术后膀胱颈部挛缩的发病率降低更为显著[4-6]。虽然发病率有所下降,但膀胱颈部挛缩仍然是困扰患者和临床工作者的棘手问题。膀胱颈部挛缩的治疗包括腔内治疗、手术重建和新型顽固性膀胱颈部挛缩的治疗方法等。本文重点围绕膀胱颈部挛缩外科治疗的研究现状展开综述。
1 膀胱颈部挛缩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分型
膀胱颈部挛缩发生发展相关的危险因素分为术前、术中和术后因素。术前因素为小的前列腺容量、糖尿病、吸烟史、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等,术中因素为大的切除环的使用、过度止血、过大的切开深度和广泛膀胱颈部组织切除等,术后因素为出血、长时间尿瘘、吻合口中断等[7-10]。目前研究者们还提出前列腺切除术前无症状前列腺炎和逼尿肌功能不全也是膀胱颈部挛缩的危险因素[11-12]。然而,膀胱颈部挛缩的发生还高度依赖最初治疗的方式及次数,术前的放射治疗和多次失败的手术操作往往导致膀胱颈部挛缩发病率的升高和高度复发,最后衍变为顽固难治性膀胱颈部挛缩[8-9]。
Pansadoro分型[13]自提出以来就受到泌尿科学者们的认可。该分型指出前列腺尿道狭窄可分为三型:Ⅰ型为狭窄局限于膀胱颈口,经典的膀胱颈部挛缩即为此型,常常继发于小的前列腺腺瘤切除术后,此型前列腺窝宽大,直肠指检中前列腺常常是正常的,尿道镜检可见精阜结构正常;Ⅱ型为狭窄局限于前列腺窝内,常发生在开放式前列腺切除术后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感染导致的前列腺窝内纤维组织增生形成瘢痕梗阻,此型膀胱颈口宽大,直肠指检中前列腺可能正常或不规则,尿道镜检中精阜结构是存在的;Ⅲ型为狭窄涉及膀胱颈口和整个前列腺窝,常发生于经耻骨上前列腺切除术后,通常整个前列腺腺体被切除,直肠指检中无法触及前列腺,腺体由瘢痕组织取代,精阜结构完全消失。PANSADORO等[13]通过临床实验还发现通过内镜治疗,Ⅰ型狭窄治疗的成功率为91%(54/59),Ⅱ型狭窄为98%(45/46),Ⅲ型狭窄为76%(13/17),并提出明确狭窄类型的情况下内镜治疗是治疗前列腺尿道狭窄的可靠方法。
2 膀胱颈部挛缩的外科治疗
2.1 腔内治疗尿道是人体与外界相通的天然管道,为内镜手术提供了条件。随着微创理念的提出和普及,腔内治疗成为许多泌尿系疾病首选的治疗法方法。膀胱颈部挛缩的腔内治疗开展得较早且有较高的成功率[9],因其创伤小、操作简便安全,被临床工作者采纳。膀胱颈部挛缩的腔内治疗包括膀胱颈扩张、内镜切开和尿道支架等,以下对这3种治疗方式的研究现状分别展开论述。
2.1.1膀胱颈扩张 膀胱颈扩张创伤小且操作简单,是临床工作者治疗膀胱颈部挛缩的首选方法[14]。软性膀胱镜同轴扩张术及术后间歇性膀胱颈扩张术是常用的治疗膀胱颈吻合口狭窄的方法,并能有效防止膀胱颈部挛缩的复发和进展[8]。如果膀胱颈部挛缩范围小、颈口组织较软且不需要切除,这种扩张治疗在门诊即可进行。HERSCHORN等[14]的一项研究中报道了膀胱颈部挛缩患者经过单次重复球囊扩张获得了83%的成功率。这种治疗方法仅适用于积极配合的患者,因为自我扩张疗法需要良好的医从性和极大的耐受力,许多患者常常因为态度消极而放弃自我扩张疗法[15]。间歇性自我扩张的并发症主要包括尿潴留、肉眼血尿、感染、假道和尿道狭窄,并发症的存在限制了膀胱颈扩张治疗的展开。
2.1.2内镜切开 经尿道膀胱颈部挛缩切开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可采用冷刀、电刀、激光、热刀、环形切除环等多种切开放式[16-17]。泌尿科医生普遍都能操作,但患者随访时间短和研究病例队列少限制了传统内镜下膀胱颈部挛缩切开治疗的普及。
张培新等[18]的研究报告中展示了尿道内窥镜冷刀内切开+电切治疗膀胱颈部挛缩在手术时间、血块堵管、膀胱冲洗时间和患者住院时间上的优势,短期复发率也较低,提出该法是临床治疗膀胱颈部挛缩的可靠方法。BREDE等[17]回顾了他们15年的经验与经尿道切开膀胱颈部挛缩治疗患者顽固膀胱颈部挛缩的效果,他们对63例膀胱颈部挛缩患者使用冷刀,从3个单独的径向切口切开膀胱颈部延伸至周围脂肪,平均随访11个月(1~144个月)后发现后续患者不需或仅需1次经尿道切开膀胱颈部可获得73%(46/63)的膀胱颈部通畅率。
对于1次手术后效果不满意的患者,术后周期性自我扩张对患者的预后有积极作用。BANG等[19]报道初始治疗后行积极的经尿道膀胱颈切开术能带来满意的治疗效果,他们平均随访13.1个月(2~33个月)后发现多次切开膀胱颈部后成功率从最开始的64.%上升到了85.7%。RAMIREZ等[20-21]最近描述了一种治疗顽固性膀胱颈部挛缩的方法,他们初始用24号同轴球囊导管扩张50例患者的膀胱颈部,然后在3点和9点用Collins刀将深侧切口延伸到膀胱周围脂肪,平均随访12.9个月后发现72%(36/50)的患者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另外14%(7/50)患者通过进一步扩张和切开后获得通畅。
2.1.3尿道支架 自从1988年由MILROY[22]介绍尿道支架治疗尿道狭窄以来,尿道支架就被用于治疗顽固的膀胱颈部挛缩。但由于组织增生形成的梗阻、支架移位/结垢、血尿等并发症常常导致手术失败,目前美国已不再流行[8]。MAGERA等[23]报告了25例置入尿道支架的患者中48%的患者要进一步切开等治疗,并且24%的患者置入尿道支架后治疗完全失败,平均随访时间为2.9(2~4)年。同样,ERICKSON等[24]报道了38例尿道支架置入后的患者中47%有初步成功率,但57%的患者需要重复干预,提出尿道支架置入后重复干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一种新的双锥热扩张金属支架(Memokath 045)已在开发和有希望投入临床[25]。Memokath是一种具有形状记忆的镍钛合金线圈,在60 ℃时膨胀,5 ℃时松开线圈。这种支架具有良好的耐压缩性能。由于支架线圈在冷水中打开,所以很容易被取出。WEN等[26]在1例严重的复发性膀胱颈部挛缩患者中进行了试验,通过尿道镜和顺行膀胱镜在膀胱颈闭锁处放置一根贯穿通过的导丝,测量狭窄长度为0.8 mm,狭窄稍微扩张后放置双锥热扩张金属支架(Memokath 045),术后长期随访并通过尿道镜及顺行膀胱颈检测支架的位置,确保近端圆锥在狭窄上方扩张,远端圆锥置于括约肌上方。支架置入术后21个月,患者仍无尿路不适。因此他们提出双锥热扩张金属支架(Memokath 045)可能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症术后复杂性膀胱颈部挛缩症的长期选择。
2.2 手术重建膀胱颈部挛缩需要开放重建的病例不多,多为多次内镜手术失败的顽固难治性膀胱颈部挛缩或伴发尿失禁的膀胱颈部挛缩患者[8-9]。手术重建按手术入路可分为经会阴途径、经腹途径、经腹联合会阴途径和腹腔镜下手术等。已发表的膀胱颈手术重建报道的推广受限于随访时间短、研究规模小和可重复性低等不足。
经腹途径和经会阴途径修复膀胱颈部的研究近期均有报道。REISS等[27]报道了改良TV成形术治疗10例患者,他们通过经会阴途径创建了两个无张力血管皮瓣并行V型缝合,随访平均26个月(3~46个月)后获得了100%的成功率。王林等[28]最近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一种改良YV型膀胱颈部重建方法治疗难治性膀胱颈部挛缩11例,他们在膀胱前壁做T型切口,向下跨过膀胱颈部,截取两侧带蒂的膀胱壁瓣与对应两侧前列腺部尿道切缘做“倒V型”缝合,术后9例患者获得成功,2例术后行膀胱颈部冷刀切开后治愈。REISS等[29]报道了15例经会阴切口治疗膀胱颈部挛缩患者的队列,他们获得了93%(14/15)的成功率,失败患者行1次冷刀切开后治愈。SIMONATO等[30]描述了一种分阶段的方法,在6例患者中最初经会阴切口行后尿道成形术,然后膀胱颈部放置尿道支架,术后6例患者效果均满意。MUNDY等[31]报告了类似的方法,他们在术后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Artificial urethral sphincter,AUS),成功治愈了顽固性膀胱颈部挛缩伴发压力性尿失禁的病例。
通过联合的腹部会阴切口进行膀胱颈部重建,具有组织暴露、游离充分、视野显露清晰等特点。SIMONATO等[32]的报告中17例患者接受了开放膀胱颈部重建术(会阴6例,腹会阴11例),随访6个月,成功率94%(16/17),平均随访时间50.5个月。NIKOLAVSKY等[33]最近回顾了12例经腹联合会阴膀胱尿道吻合翻修术治疗顽固性膀胱颈部挛缩,92%(11/12)的患者膀胱颈部通畅,中位随访时间为75.5个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肯定经腹联合会阴重建膀胱颈部手术的推广价值。
腔镜手术重建膀胱颈部治疗膀胱颈部挛缩的方法也有报道。MUSCH等[34]报道了机器人辅助YV成形术治疗顽固性膀胱颈部挛缩12例,10例获得成功,平均随访时间23.2个月。腔镜技术作为新兴技术,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和更长的随访时间来验证其治疗膀胱颈部挛缩的可重复性。
2.3 新型顽固性膀胱颈部挛缩治疗方法由于传统内镜技术往往需要重复的干预措施才能达到满意效果,有研究者尝试了经尿道膀胱颈部切开辅助药物注射的方法。其中类固醇注射已被用于对抗纤维化、瘢痕化和减少膀胱颈部挛缩复发的治疗中[35],其他联合药物注射如丝裂霉素、曲安奈德和地塞米松等的研究也有报道。
ETAHAMY等[35]通过内镜下钬激光膀胱颈部挛缩松解结合类固醇注射治疗顽固性膀胱颈部挛缩患者24例,获得83%的成功率,随访时间6~72月。ALTAY等[36]报道了在钬激光膀胱颈部挛缩消融后狭窄部位注射曲安奈德,68例患者中成功率为83%。VANNI等[37]报道了经尿道放射状切开膀胱颈部挛缩结合切口注射丝裂霉素C,获得了接近90%的成功率。薛蔚等[38]报道了经尿道膀胱颈部电切结合地塞米松注射治疗52例膀胱颈部挛缩患者,49例获得成功。新的联合注射治疗是有前景的,但其安全性问题已经被提出。REDSHAW等[39]报告了膀胱颈部切口丝裂霉素C注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且预期效果也不如先前报道中的效果。另有研究者提出从类固醇注射会引起生命危险性过敏反应[40]。膀胱颈部药物注射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其安全性及临床价值。
患者成功治疗膀胱颈部挛缩后可能会发生压力性尿失禁且发病率高度可变,所以许多学者建议治疗膀胱颈部挛缩的同时预防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41-42]。BREYOR等[43]报道了膀胱颈部挛缩切除后AUS植入治疗尿失禁获得成功的案例。在膀胱颈部挛缩治疗后,对SUI进行干预的时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SIMHAN等[8]主张在膀胱颈部挛缩治疗后2个月评估AUS植入前的膀胱颈部通畅情况。这种方法减少了再狭窄的风险,也降低了支架植入后进一步膀胱颈部手术的需要。在AUS植入前的延迟时间没有达成共识,一些研究者等待4~6周,而其他人则认为延迟至12个月[37,41]。
3 总 结
在前列腺切除术后,膀胱颈部挛缩仍然是肿瘤和泌尿外科重建研究学者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于膀胱颈部挛缩多种治疗方式的了解认识是必要的。吸烟者和需要复杂手术或放射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患膀胱颈部挛缩的风险较高。内镜治疗中扩张、经尿道切开膀胱颈部和联合纤维化药物注射治疗膀胱颈部挛缩是相对成功的。但在复杂难治性病例中,手术重建是必要的,包括膀胱颈重建和尿流改道,后者常常在所有方法都失败的患者中进行。为达到预期满意的效果,患者膀胱颈部挛缩治疗后尿失禁风险评估同样是重要的。膀胱颈部挛缩的研究进展主要依赖于研究者们的回顾性的或对照性的研究,其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还需要更多的病例数量和更长的随访时间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