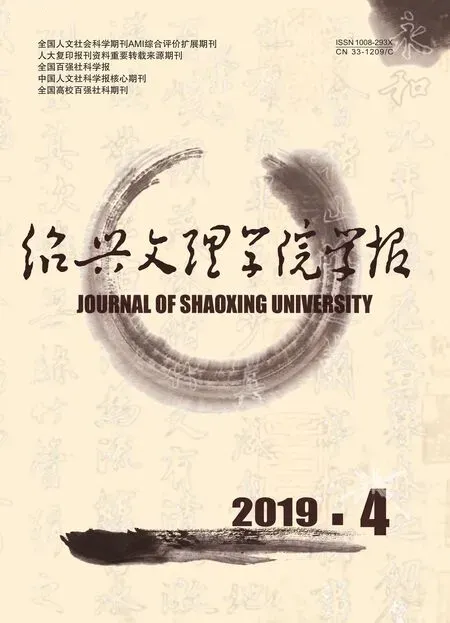从唐宋词接受看清代前中期词之演变
陶友珍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宿迁开放大学 经贸系,江苏 宿迁 223800)
清词号称中兴,学界多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词体自身的发展规律等方面探寻其原因[1][2],虽有学者注意到了清词与唐宋词接受之间的联系,但更倾向于个案研究,而较少从“史”的角度宏观梳理与把握[3]12-16,[4]14-17。毫无疑问,清词的繁荣首先是建立在对“唐宋词”这座文学宝库的传承与接受之基础上的。明末清初至乾隆末年是清王朝从动荡走向平稳进而达到鼎盛又由极盛开始滑向衰弱的时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清人对唐宋词的接受与传承也经历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种演变又给予清词以怎样的影响?本文以时间为序,从唐宋词接受的角度初步解读清代前中期词发展演变的历程。
一、明末至顺治初期:宗花间、南唐、北宋与清词的小令化、艳情化
有明一代,词人学的最多的是《花间集》和《草堂诗余》,正所谓“《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5]1940。这股“花”“草”之风在晚明仍然有着强烈的影响,陈耀文在万历癸未年编的《花草粹编》就是以《花间集》和《草堂诗余》为主要底本。清人王煜在《清十一家词选·自序》中也说:“清初沿习朱明,未离《花》《草》。”[6]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有明一代“花”“草”并行,但对“草”的兴趣要高于“花”,如吴承恩在《花草新编序》中云:“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乎”?[7]118明末清初,词人对花间词要更偏爱。如果说“花间”词风代表的是“艳”,那么草堂代表的就是“俗”,虽说“俗”和“艳”难以截然分开,但毕竟还是有差异。翻阅清代前中期相关文献就会发现,清人对艳词尚能容忍,甚至认为词为艳体在情理之中;对于“俗”,清人则几乎一边倒地口诛笔伐。在清初,除了李渔表达了词应该尚俗、“先要使人可解”[5]553的观点外,极少有人对俗词表示喜好,正如曹尔堪所说“词尚艳冶,亦忌秽恶”(《春芜词》题词)。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早期词主要用于应歌,为了让大众听懂,追求通俗易懂也是应该的,但到了清代,词几乎完全演变为案头文学,词作者多为才人、学人,他们致力于推尊词体,因此反对词的俗几乎是必然选择。虽说在明代词也不应歌,但词的“曲化”非常严重,世俗文学非常发达,加之词体不振,俗词也就大行其道了。
明末清初词坛执牛耳者是云间词派。云间词派活动的时间大概是明崇祯初年至清顺治初年,代表人物是陈子龙,陈子龙最心仪的是晚唐至宋室南渡之前的词,而对南宋词则颇多微词。具体来说,他论词主张“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非常看重南唐北宋词的自然、浑成、本色之美。在《王介人诗余序》中,陈子龙提出了填词的“四难”[8]506,即“用意难”“铸词难”“设色难”“命篇难”,其核心观点仍然是用浅白但含蓄有韵味的语言表达“沉至之思”,再次强调了“天机所启,若出自然”。除了云间词派,其他词人也深受这种唐宋词接受观的影响。陈维崧作为阳羡词派宗主,其词给人感觉踔厉骏发、纵横恣肆,学的是苏、辛一派。其实陈维崧早年曾从大樽学词,其初期的词受云间词派影响较大,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中说他的词“矫丽”[5]659,并说“阮亭既极推云间三子,而谓入室登堂,今惟子山、其年”[5]651。
值得注意的是,从清初如日中天的云间词派提倡的花间、南唐、北宋,到朱彝尊的浙西词派专学南宋,清人的接受取向似乎走了两个极端,且这两个极端之间相隔不过三十多年,这个“乾坤大挪移”似乎有些太突兀了。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转变在明清之际就有了一些征兆。对于明代“花”“草”风行,在晚明就有人表示过担忧与不满,毛晋作为明末著名的词学出版家,他在《花间集跋》中说:“近来填词家辄效柳屯田作闺帷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邪?”[8]635晚明卓人月和徐士俊编选的《古今词统》,所选唐宋词不再局限于《花间集》和《草堂诗余》,而是把选录重心放在了南宋。这些都透露出词学接受转向南宋的端倪。
即使在主学南唐、花间、北宋的云间词人身上,同样也能发现词风转变的蛛丝马迹。以陈子龙为例,陈氏对南宋词并非全无好感,其对南宋《乐府补题》的评价就颇高。《历代词话》卷八引陈子龙云:“唐玉潜与林景熙同为采药之行。潜葬诸陵骨,树以冬青,世人高其义烈。而咏莼、咏莲、咏蝉诸作,巧夺天工,亦宋人所未有。”[5]1260对于宋征壁“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9]2的论断,学界往往关注的是后半句,认为其意是极力贬斥南宋词,却对“词至南宋而繁”往往置而不谈。其实后半句恰恰是对南宋词的肯定,认为词至南宋就到了极盛时期。实际上,宋征壁在《倡和诗余序》中对“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也不无赞许之意。另外,明清之际云间词人虽未提出“雅”的号召,但其词学主张其实是蕴含了“雅”的内涵的,因为无论是表达“沉至之思”还是“不藉粉泽”,无论是追求“含蓄有余不尽”还是“工练”,无形中都包含了“雅”的意蕴。明清之际的其他词人有类似表述,如清初词人李起元在《董澹子诗余小序》中云“盖词取其婉娈而近情也,有景语、快语、情语、浅语、澹语、恒语,而浅、澹、恒尤不易。又用字有雅、丽之分,叶韵有四声之别。字雅为最,丽则亚之”[10]3,明确表达了“雅”的主张。因此可以认为,康熙中期浙西词派的宗南宋尚醇雅在明清之际就埋下了伏笔。
明末清初词坛的这种风尚,无疑是对明后期词风的赓续。但是也必须承认,云间词派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和传统意义上的明词又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认为,云间词派是以对明词振衰起颓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陈子龙对明词是不满的,他在《王介人诗余序》中对明词名家如刘伯温、杨慎、王世贞等人的评价不高,遑论他人。云间诸子虽然学南唐花间,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复古行为,因为云间词派认为“夫风骚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乎闺襜之际”,认为词应该“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8]508。从实际情况来看,陈子龙等人在亡国之后所写的词的确体现了寓国恨家愁于艳词之中的理念。毫无疑问,这些艳词与传统意义上的艳词不太一样,这无形中提升了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明词的救赎,这与后来朱彝尊用南宋的骚雅词来抵御明词的俗艳殊途同归。
受这种接受取向的影响,明清之际的词也深深地打上了花间、南唐、北宋词的烙印:
一是题材的艳情化。总体来看,虽说清初遗民词人也有一些词反映了那段刀光剑影、风雨如晦的惨痛历史,比如金堡和徐籀的词;也有少数词反映了民生疾苦,比如汪价的词,但这类词在明末清初占比不大。受明代词风的影响,清初题材还是偏于传统的闺襜艳情之作,云间词派虽然以挽救明词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主张以南唐和北宋词救明词的芜陋,但从云间词派的创作实际看,其题材以闺情、咏物及个人感怀为主。陈子龙在明亡以后的某些词真正具备了南唐词的自然神韵之美,但他早期的词大都是走花间老路。《幽兰草》中所存陈子龙的55首词,词题多为“春风”“春雨”“画眉”“杨花”以及“闺怨”之类。总体而言,个别遗民词人题材的开拓并不能掩盖整个词坛的艳情化。
二是调式的小令化。词在兴起之际,以小令居多,花间和南唐词也多为小令。云间词派主张复古,词学晚唐。蒋平阶说要“专意小令”,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中也说:“今则短调,必推云间。”[5]653从云间词人的创作来看,大多以小令为主。云间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田茂遇也说:“我乡前辈言词者以花间为宗,几置长调不作。”(《清平词选后集序》)以《倚声初集》为例,其选录明代万历至清顺治年间的词共1914首,其中小令206体1116首,中调102体364首,长调165体434首,分别占比58%、19%和23%。由此可见,小令在明末清初占了绝对优势。
三是艺术风格的婉丽化。明词将豪放词风视为变体,而视婉约为正宗,云间词人完全继承了明词传统。毋庸讳言,题材的女性化和闺阁化,必然导致词风的婉丽。对此,陈子龙在《三子诗余序》中说得很清楚:“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婧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8]507其中“纤刻”“婉娈”“妍绮”等词语都是说词在艺术风格上应该婉约妍丽。实际上,这样的词学观不仅是在云间词人中,甚至在明末清初整个词坛的创作实践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贯彻。
二、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多元化的接受与清词题材及风格的多样化
顺治四年(1647),随着陈子龙抗清失败投水而死,云间词派影响式微。词坛进入群雄逐鹿、百家争鸣的时代。
首先来看“花”“草”艳词在该时期的接受情况。这个时期写艳情词最重要的基地有两个:西陵词人群、广陵词人群。如前所述,西陵词人虽然出自大樽门下,词学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其论词还是更倾向于接受艳词。沈谦曾在《填词杂说》中为黄庭坚好作艳曲辩护:“山谷喜为艳曲,秀法师以泥犁吓之,月痕花影,亦坐深文,吾不知以何罪待谗谄之辈。”[5]634广陵词人群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士禛、邹祗谟、彭孙遹、董以宁等。广陵词人群脱胎于云间词派,但已逐渐跳出云间词派的藩篱。他们的词学主张虽然看起来比云间词派更先进,接受唐宋词的范围似乎更广,但他们念念不忘难以割舍的仍是花间及北宋艳词。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说,“或问《花间》之妙,曰蹙金结绣而无痕迹。问《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远春”[5]675;彭孙遹更是认为,词以艳丽为本色,实乃体制使然。
南唐词在该时期也有一定的受众。清初较好地继承了云间词派陈子龙词学精髓的是纳兰性德,他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11]卷十八。实际上,他是清初学南唐最成功的词人。纳兰性德的好友顾贞观从未标榜自己学南唐,但从他的创作实践来看,其词自然清新,不事雕琢,感情真挚,深得南唐词风之神韵。
北宋词和晚唐五代词关系紧密,北宋词的自然本色、婉丽流畅正是来自晚唐五代,因此,学晚唐五代必然会兼及北宋。这个时期,论词宗北宋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毛先舒就曾说:“北宋词之盛也,其妙处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艳亵,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气取,艳亵可以意工。高健幽咽,则关乎神理骨性,难可强也。”[5]607清初顾贞观也说:“南宋词虽工,然逊于北。”[12]510浙派首领朱彝尊的词学活动大概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其论词主张并非一开始就是宗南宋、尚醇雅,慕姜张的。他在《碧巢词》所附评语中说:“诗馀起于唐人而盛于北宋,诸名家皆以舂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于诗,轻俗不流于曲,此填词之祖也。南渡以后,渐事雕琢。元明以来,竞工鄙俚,故虽以高、杨诸名手为之,而亦间坠时趋。”词“盛于北宋”和“南渡以后,渐事雕琢”这样的言论出自朱彝尊这个浙派宗主口中让人感觉很陌生,但仔细研究,一点也不奇怪,朱彝尊早期也曾学过云间词派。
唐宋词接受在该时期很重要的特色是稼轩词风的回归。稼轩词风的回归和阳羡词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阳羡派是17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词派”[4]296。阳羡词派一开始就是以反对花间草堂闺襜靡曼之音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陈维崧早年师事陈子龙,词风较为艳丽,但后期已经完全走出了明词和云间词派的藩篱。他在《和荔裳先生韵亦得十有二首》的第六首中说“烦君铁绰板,一为洗蓁芜”。陈维崧后期词内容之丰富、风格之恣肆、用调之繁多、用情之沉挚,都说明了他已经不屑于香软词风,而是更多地学习接受苏、辛豪放词风,用追魂沥魄之笔描绘清初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除阳羡词人外,吴绮、冒襄、余怀、尤侗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学辛词。康熙十年(1671),在周在浚和龚鼎孳等人的推动下,稼轩词风随着“秋水轩倡和”而吹遍大江南北。
对姜、张为首的南宋格律词人的接受是浙派词人明确提出来的。汪森在作于康熙十七年的《词综序》中鲜明地提出尊姜、张尚醇雅的主张,认为姜夔的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对于与他词风类似的张炎、史达祖等人也推崇备至[13]2。朱彝尊在不同场合都表达了类似观点,在《词综发凡》中表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13]8先著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所作的《词洁序》中也说:“《词洁》云者,恐词之或即淫鄙秽杂,因而以见宋人之所为,故自有真耳。”[14]1他最心仪的宋代词人是周邦彦和姜夔,和浙西词人也很相似。南宋骚雅词风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学界多有阐释[15]232-235,此不赘述。从词的发展来看,这种词坛接受风气的形成,渊源有自。前面虽然强调了清初词坛接受格局的多元化,但在抵御明词的浅俗、追求雅正上,不同流派的词人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如西陵词人沈谦说,词“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5]635;贺裳在《皱水轩词荃》中提出:“词不嫌秾丽,须要雅洁耳”[5]708;广陵词人彭孙遹虽以艳词闻名,但却主张艳而不俗,认为“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16]卷三七。要追求雅正,自然就会想到南宋词人。以广陵词人群为例,其词学观也是较为宏通的,虽然总体上仍以艳词为尚,但对南宋词也不无赞美,如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说,“宋南渡后梅溪、白石、竹屋、梦窗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李未到者”[5]682。同为广陵词人的彭孙遹也说:“南宋词人,如白石、梅溪、竹屋、梦窗、竹山诸家之中,当以史邦卿为第一。昔人称其分镳清真,平睨方回,纷纷天变行辈,不足比数,非虚言也。”[5]722因此,李康化说“清初阳羡词派推崇辛弃疾,浙西词派推崇姜夔,无不与广陵词坛有关”[17]212是有道理的。
综上可知,该时期的唐宋词接受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种多元化不仅表现在不同词派各自的主流接受取向不同,还表现在同一词派或群体内部的接受取向也不尽相同,如同为西陵词人,沈谦学柳永,毛先舒则认为“柳不足为足下师也”;[18]卷五广陵词人中,相对来说,王士禛、彭孙遹、吴绮等人虽然都倾向于接受唐宋艳词,但对苏、辛豪放词也并不排斥,而董以宁则在专主艳情的路上渐行渐远。再以阳羡词人群为例,陈维崧主要学苏、辛,史惟圆则更多地学习北宋诸家,他曾与陈维崧言:“譬之子,子学庄,余学屈焉”[10]137,而蒋景祁在学辛词的同时对同乡蒋捷更为推崇。这种多元化还体现在同一词人对不同类型的唐宋词表现出来的宽容态度,如毛先舒在《与沈去矜论填词书》中表示:“词句参差,本便旖旎,然雄放磊落,亦属伟观。”[18]卷五吴绮在《范汝受十山楼词序》中也同样表达了非常宽泛的接受视野:“词称两宋,尽乐府之源流。然风雅之所传,不能有王、韦而无温、李;岂声音之道,乃可右周、柳而左苏、辛?”[10]42其实,就是浙派宗主朱彝尊的接受思想也并不是只学南宋姜、张一派,而是明确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10]340。
不过,这种多元化并非是雨露均沾的多元化,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接受取向中艳词和苏、辛豪放词风仍是主流。曹贞吉在康熙初年(1662)为《罗裙草》所作的题辞中就指出:“今天下言词者,非辛、苏则秦、柳。”[10]235究其原因,艳词的影响主要还是源于明代词风的流风所及,虽然清初词人对明词的纤艳多有打压,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赋词尚艳的思想深入人心,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不太现实。即使后来浙西派乃至常州词派全盛时期,艳词仍有相当的市场。豪放词风则主要是由于阳羡词派的鼓吹。毫无疑问,阳羡词派是该时期最有影响的词派,其成员之众、作品之富,足以笑傲群雄。
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清词呈现出以下特色:
一是题材丰富。在这个时期,既能看到西陵词人和广陵词人于花前月下,诗酒流连,也能看到遗民词人对社会民生、百姓冷暖的关注与哀叹;既能看到《静志居琴趣》和《饮水词》对真挚爱情的讴歌和怀念,也能看到《乌丝词》和《江湖载酒集》中所表达的个人漂泊、居无定所的无助与天涯倦旅的彷徨;既有对故国的怀恋,也有对新政权的畏惧以及投入新政权后的羞愧和纠结;有键户吟咏、傲笑烟霞的自得其乐,也有咏物题画的穷形极象、寄托遥深,还有传统词题材绝少涉及的边塞行吟词。
二是艺术风格多姿。西陵词人的绮艳与广陵词人的婉丽是总体而言,从王士禛、彭孙遹的词中也能发现不少“怒目金刚”、骏发踔厉风格的作品。阳羡词人虽然以豪放为主,但也难以完全涵盖其全部面貌。蒋景祁评陈维崧的词就说:“故读先生之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10]93另外,遗民词人反映社会疾苦词的苍凉雄浑,浙西词人崭露头角的清空骚雅,纳兰容若爱情词的清新婉丽、哀感顽艳,边塞词的苍凉清怨,都让人耳目一新。
三是调式多样。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必然会导致词调形式的多样。彭孙遹说:“今人作词,中小调独多,长调寥寥不概见,当由兴寄所成,非专诣耳。唯龚中丞芊绵温丽,无美不臻,直夺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绮,吴祭酒之高旷,曹学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长调之妙,斯叹观止矣。”[5]725他提到的清初擅作长调的四个人是龚鼎孳、吴伟业、熊文举、曹贞吉。龚鼎孳的长调有98首,占其203首全部词作的48.3%;邹祗谟《丽农词》长调63首,占总数的39.9%;陈维崧《乌丝词》266首,长调132首,占比49.6%。相较于明清之际,清初词作中长调的比例有所增加,调式更丰富多样。
要之,这个时期的词坛上风起云涌,各种词学观念碰撞激荡,对宋词的接受和传承也更包容开放,清初词思想内容之丰富、艺术风格之多样、总体成就之高,令人赞叹。
三、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争议中的姜、张独尊与清词内容的贫弱及风格的单一
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基本上是浙派的天下。这段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以厉鹗为代表;乾隆中期至后期,以王昶为代表。康熙三十一年(1692)后,朱彝尊把重心放在经史的考证上,很少再填词了,他的追随者们往往“竞为涩体,务安难字”“抄撮堆砌”[10]444,在字句格律上逞才使气,词坛陷入沉寂,直到厉鹗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厉鹗在这个时期很有影响,在钱塘时与之交往密切的浙派词人有陆培、徐逢吉、吴焯、张云锦、张奕枢等。后迫于生计,厉鹗来到扬州,又有马日琯、马日璐、江昱、江昉、张四科等人与之相互唱和,声势浩大,影响一时无二。厉鹗还与查为仁共同为《绝妙好词》作笺注,借助这部最能代表南宋格律骚雅词风的词选之影响,浙派更是如日中天。如果说厉鹗所表现的是浙派词人在民间的影响,那么王昶则是浙派词人在上层的代表。但王昶在词创作上的成绩有限,其成就主要在于词籍的编选,借助词选来表达对姜、张词的学习与接受。
受浙派词人的影响,“北宋词高未极工,渡江白石启江东”的词学接受思想在该时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昂霄把姜夔比作是散文领域中的韩愈;李调元说“鄱阳姜尧章郁为词宗,一归醇正”[19]2703;时人用“一从白石箫声断,谁倚琼楼最上层”[20]873“千秋白石压词坛”[20]874等来形容和概括白石在词史上的地位。对于张炎,人们的评价也极高,江昱在《山中白云词疏证序》中说“词自白石后,惟玉田不愧大宗,而用意之密,适肖题分,尤称极诣”[20]1187。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张炎评价:“炎生于淳祐戊申,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至其研究声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后劲。宋元之间,亦可谓江东独秀矣。”[20]1194毫无疑问,他们是把张炎当作姜夔的重要羽翼与后劲来定位的。姜、张之外,其他南宋格律派词人也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王昶说“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20]875。词坛上基本都恪守浙派的宗旨,姜、张一派词成为词坛接受的主流,谢章铤曾用“家白石而户梅溪”[5]3458来形容当时的词坛。这一时期除了南宋格律词派之外,清人对其他类型的唐宋词是否不屑一顾呢?下文以苏辛豪放词人、北宋通俗词人和周邦彦为例,考察当时清人对他们的接受态度。
尽管仍有不少人视词为“变调”,非本色和正宗之属,但该时期清人对苏轼和辛弃疾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柯煜在《东斋词序》中说“词莫高于南宋,若稼秆之豪、石帚之雅、玉田之清,皆词苑第一流也”[10]395,他把辛弃疾与姜、张并称,在浙派内部能有此创见实为不易。楼俨则称赞“东坡老人,故自灵气仙才,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不独寓以诗人句法,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20]329。四库馆臣认为辛弃疾“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20]791。当然,清人肯定苏、辛,并非是要摒弃姜、张,而是认为要“一陶并铸、双峡分流”[10]603。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清人对苏轼和辛弃疾以外的其他豪放词人如刘过、刘克庄等则评价不高,这与该时期推崇姜、张但同时对吴文英、周密、史达祖、王沂孙等其他南宋格律派词人赞赏有加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北宋通俗词人,清人的观点颇为复杂。对俚而俗的黄庭坚词意见较为统一,几乎一致予以口诛笔伐。田同之云:“黄山谷时出俚语,未免伧父。”[20]406许田在《屏山词话》中也说,“山谷率皆俚语,全无意味”[20]406。该时期清人对柳永的评价也不高,认为“淫哇”[20]178“俗而腻”[20]331,但作为官方代表的四库馆臣却肯定了其“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20]183,并非全然否定。对其他北宋通俗词人如李清照、秦观等,则总体评价都不低,李调元甚至说李清照“词无一首不工”[20]611,说秦观的词“首首珠玑”[20]408。王初桐《小嫏嬛词话》也说,“李易安元宵《永遇乐》,秋词《声声慢》,妇人有此奇笔,殆间气也”[20]611。汪筠在读《词综》后也称赞“漱玉天才韵最娇”[20]610,楼俨认为淮海词“风骨自高”“能以韵胜”[20]405。
如果说该时期清人对北宋通俗词人的评价有褒有贬,那对周邦彦则更多地予以褒扬。无论是许孙蒥的“周、秦为最”[10]379,还是浙派中期代表厉鹗的“南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20]483;无论是江昱的“词坛领袖”[20]483,还是四库馆臣的“词家之冠”[20]487,都把周邦彦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清真最“识曲”、能“知音”。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浙派推崇姜、张,多认为姜、张一派的鼻祖就是周邦彦。正像江昱所说:“南渡诸贤更青出,却亏蓝本在钱塘。”[20]483但周邦彦是北宋人,与浙派推举南宋的倾向不一致,所以厉鹗才会煞会苦心地避开“南北宋”的提法,而借用绘画中的“南北宗”巧妙地把本属北宋的周邦彦纳入接受的主流中来。
由上可知,虽然说此时期浙派如日中天,姜、张一派词是当时词坛接受的主流,但从实际来看,清人对其他类型的唐宋词并没有一笔抹杀。至少在乾隆中后期,“家白石而户梅溪”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南宋格律派词与其他类型的唐宋词有相通的地方,正所谓“文章能感人,便是可传,何必争洗艳粉香脂与铜琵铁板乎”[20]786;另一方面,独尊姜、张的确产生了很多弊病,这一点,无论是浙派内部还是外部,都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从别的唐宋词中汲取养分来补苴填罅无疑是较好的选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浙派自厉鹗去世以后,缺少真正有创作实绩的大家,号召力有所减弱。
即使对于姜、张词的接受,此时期与清初朱彝尊领导词坛时也不完全一样。如姜、张词的核心是“骚雅清空”,朱崇才在《词话史》中研究发现,朱彝尊论词绝少谈及“清空”,倒是厉鹗在不同的场合提起过“清空”[21]253-254。再如,他评价张龙威词云“清婉深秀”[10]418,评陆南香词云“清丽闲婉”[10]418,批评当时浙派众人的词“大都新绮有余,而深窈空凉之旨,终逊宋贤一筹”[10]419。作为一个身份低微的家庭教师,厉鹗的遭际比之朱彝尊更能贴近姜夔,也许更能领会同样沉沦下僚、终生布衣的姜夔词中的“清空”。就“骚雅”而言,王昶所谓的骚雅与姜夔的雅是不一样的,姜夔的雅带有下层知识分子的孤傲,而王昶身居高位,他理解的雅是“一种清闲幽雅的情趣”[22]322。另外,王昶深刻认识到了南宋词比北宋词优秀的地方,他说“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5]2388,应该说王昶在这一点上比其他浙派词人都要高明。要让大家接受“南宋”词,首先就要抬高南宋词的地位,而之前的浙派词人包括朱彝尊和厉鹗都是从艺术形式上美化南宋词,而王昶则看到了南宋词作思想内容中的“家国之念和经济之怀”[23]290,这无疑会大大提升“南宋词”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受唐宋词接受倾向的影响,这个时期清代词坛总的现状是百川归海,姜、张独尊。这种局面对清词来说不是好事,清初时期百家争鸣、千帆竞发的局面不复存在,词坛陷入了低潮。首先是思想内容的贫弱。这段时期清王朝最为鼎盛,“河海宴清”的所谓“康乾盛世”已经来临,但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清词创作的繁荣。很多浙派词徒具精致的外壳,但缺乏深广的内容和真挚的情思。他们写了大量的咏物词和题画词,被谢章铤斥之为“方物略”和“群芳谱”[5]3415。这些词虽然雅致,但有真情实感的不多。浙派殿军郭麐曾批评浙派:“后之学者,徒仿佛其音节。刻画其规模,浮游惝恍,貌若玄远,试为切而按之,性灵不存,寄托无有。若猿吟于峡,蝉嚖于柳,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10]736可谓一语中的。其次是艺术风格的清雅化。他们大都恪守浙派的宗旨,追求醇雅和清空,清雅成为词坛的主旋律。然而,姜夔和张炎词中的雅和清空是有一定生活遭际积淀的,姜夔终身布衣,在天壤间漂泊,张炎也曾北游;而雍正乾隆年间大多数词人都只是埋头故纸堆,这样往往只能学到姜张词的貌而无法得其神。所以,只能从他们的词中看到堆砌典故,在音律上锱铢必较,乾隆中后期编选的《钦定词谱》让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他们更热衷于在词句上字酌句炼,坠入追求文字游戏的无聊和故作高深的附庸风雅。虽然说郑夑、蒋士铨、黄景仁、姚椿、史承谦等人的词表现了不一样的风貌,但影响有限。最后一点就是长调慢词的兴盛。南宋词人中的大家几乎都是以慢词长调为胜。爱屋及乌,浙西词人学南宋,推尊姜张词,就必然会偏爱长调。笔者对《全清词》(雍乾卷)中所有的追和唐宋词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发现明确可考的追和词有1086首,其中长调642首,占比约为59.1%,超过了小令和中调的总和。虽然说统计的是追和词,但窥一斑而见全豹,长调在清中期的确是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清初偏好小令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结论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前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共同构成的。对前代文学的传承与接受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也必将影响当代的文学。从明清之际的花间、南唐、北宋到清初的百花齐放,再到清中期的姜、张独尊,大体而言清代前中期的唐宋词接受实现了一个由多元接受到单一接受进而又试图拓展的转捩。与之相应,清词创作由重性情的抒发到重艺术手法的锤炼,词风追求由以婉丽为宗到以清雅为宗,调式的选择由好小令到好长调,清词大体走过了一段由复兴到繁荣最后又趋于沉寂的历程。虽说清词中兴的原因、清代前中期词的发展演变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通过上面的分析,就会发现,唐宋词的接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发展走向。所谓清词中兴,严格意义上来说,从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才是清词真正意义上的高峰。毋庸置疑,这个高峰的出现与其接受视野的开阔息息相关。雍乾时期清词的衰微,固然与政治环境的高压、朴学的兴盛、科举的导向有很大关系,但对以姜、张为首的南宋骚雅词的偏爱也不可分。
——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