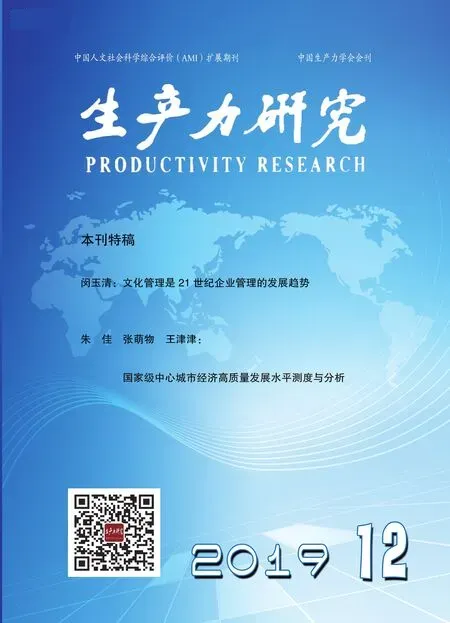关于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思考
——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
刘 蓉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在农业发展政策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土地政策的开端,对改革初期农村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随着农业机械化和新技术的推广,家庭承包经营受限于土地规模小,家庭成员的分工等,其独立经营的落后性和局限性逐渐暴露。改变传统的小规模发展模式一直是几十年农业的探索方向,也是农业经济研究恒久的议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自1987 年首次提出,多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内容。2013—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布局规划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甚至上升到了“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战略高度。然而,小农分散化经营一直是中国农业经营的现状,如何加快规模经营,多少面积方为最适当的经营规模一直是政策当局探究的问题。在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提高粮食产量的议题也是含混不清。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规模经营的“必要性”之争
土地规模的适度扩大对农业生产提高具有正向效应(韩俊,1998[1];夏永祥,2002[2];钱贵霞和李宁辉,2005[3];范红忠和周启良,2014[4];仇焕广等,2017[5])。小规模经营限制农业投资,难以实现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等可变要素投入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营能在生产成本方面占据优势。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实现机械对人工的技术替代和先进工业技术的利用,能有效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机械化耕作便利,从生产、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有助于提高农民收益(董秀茹等,2014)[6]。在当前的生产水平下,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相比,适当扩大经营规模能带来显著的规模效应(朱方林等,2017)[7]。
小农经济是中国历史的选择,现阶段小农经营是有效的,而且必将是未来中国的长期选择(贺雪峰,2011[8];隋福民,2017[9])。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业投入资金短缺、农产品供给短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土地大规模流转对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基本秩序维护相当不利(隋福民,2017)[9],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应摒弃盲目扩大经营规模(罗必良,2000)。限制土地的大规模正式流转,允许农户之间的非正式流转才是正确的制度选择(贺雪峰,2011)。
经营规模的扩大因根据述求而定。从生产中几乎不存在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的结论,经营规模的扩大不能成为粮食增产的充分条件,土地规模经营对单位产量总成本有显著的负效应(许庆等,2011[10];唐轲等,2017[11])。土地规模的增大对土地的生产率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促进作用,却能降低农业投入总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营规模对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逐步减弱(唐轲等,2017)[11]。农场规模超过一台中型拖拉机可管理的范围,规模效应丧失。农地规模并非越大越好,适合我国农户的小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单产的提高(杨春华和李国景,2016)[12]。
(二)规模经营的途径与类型
山东农业大学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查研究指出规模经营土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3.04%;对已经存在规模经营的村,其规模经营程度低,且其实际效果和迫切性落后于理论研究,大部分群众对土地规模经营持不赞成或者反对态度,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主要依赖“行政推进”[13];罗伊-普罗斯特曼(1995)发现一旦村里决定规模经营,土地就通过行政手段而非资源原则集中,部分反对规模经营的农户被“说服”,“自愿”放弃责任田的垦种。
农户间自发行为、土地参股合作社及农业企业土地租赁是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三种途径,前者是流转是主要形式。随着流转市场的发展,流转纽带由亲缘式向租金式转变,主要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主要以土地股份制合作社为主(何秀荣,2016)[14]。土地与劳动力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短板(柳晓倩等,2018)[15],适度经营包含社区型合作社和非社区型合作社组成的合作社(何秀荣,2009)[16],以租赁他人土地自主经营的农业大户,及以企业为主体租赁土地整合后转包给农民经营的形式(汤建尧和曾福生,2014)[17]。
(三)规模经营的“规模”之争
规模经营的规模多大的经营面积最为合适,目前学界暂不存在“普适性”的标准(赵颖文等,2017)[18]。从大部分农户视角,经营规模要扩大到“适度”,还需扩大10 倍以上的规模(何秀荣,2016[14];张磊和罗光强,2018[19])。从保障粮食安全角度,最适宜的耕地规模在80~120 亩;从农民增收入角度,最佳耕地面积在80 亩以上。综合两种目的,最佳的经营标准在80~120 亩左右(李文明等,2015)[20]。从劳动力成本的边际变动来看,无地租成本时最佳规模为30 亩,需支付地租时规模经营面积上升至60 亩,如具备自有机械和农机具修理能力,则最佳经营规模扩大至200~300 亩(周娟,2018)[21]。具体的实证研究也是各执一词。
从全国粮食主产区看,各个学者对各省市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不同粮食产区最优经营规模不同。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实地调查发现,要实现劳均最优土地经营规模,必须增加耕地规模。劳均最低土地面积需在原基础上平均增加22 亩/人(钱贵霞和李宁辉,2004)[22]。侯淑涛等(2017)[23]认为黑龙江省主要平原区劳均最优适度经营规模超过200 亩。第二,不同作物的最优经营规模不同。水稻和小麦的经营规模与单产呈现“U”型特点,玉米呈现倒“U”型,最优经营规模超过大部分农户的实际经营面积。水稻最佳规模经营面积在35~70 亩之间(熊凤水和刘梦兰,2018)[24]。与小麦相比,水稻经营规模扩大会引起要素冗余和生产效率下降(朱方林等,2017)[7],过大或过小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冀县卿等,2019)[25]。玉米最优生产规模为400 亩(陈菁和孔祥智,2016)[26]。通过扩大耕地规模对增加粮食单产意义不大(李谷成等,2010[27];张红梅等,2018[28]),甚至导致实际收入下降,规模报酬递减(赵金国和岳书铭,2017)[29]。
从各个省域看,浙江省生产要素配置经营规模在2 公顷以下时更加合理,但是经营规模超过2 公顷,特别是超过5 公顷时,农户资源配置平衡被打破,每公顷土地的平均纯收入下降(卫新等,2003)[30]。江苏省农户的生产效率随土地经营规模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适度规模范围内,农业的每亩边际收益为31.841 元,生产拐点为14.17亩。适度土地规模与资金、劳动力的配置更优化,并实现全要素的节约(胡初枝和黄贤金,2007)[31]。对于四川省这种人多地少的山地丘陵地区,25~35亩才是最适合的经营规模(王国敏和唐虹,2014)[32]。
(四)适度规模经营的绩效
适度规模经营的绩效可以用实物和货币计量衡量土地的生产率(仇焕广等,2017)[33]、劳动生产率。不同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有所差别,企业以种植蔬菜、花木、瓜果等高效优质农产品为主,人均纯收入最高。农业大户为主体的形式最适合种植粮食,但是“非粮化”种植倾向明显(汤建尧和曾福生,2014)[17]。就粮食单产而言,粮食主产省经营规模与粮食单产呈现反向关系,且这种影响在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区更为明显。规模经营能降低生产成本,但对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弱(唐轲等,2017)[11]。
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制约
(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2017 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口超过3.5 亿,其中农业就业人口约2.6 亿。乡村人口庞大,加之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于企业对知识型或技能型劳动力的综合需求,难以实现农业人口快速非农化。即使已经在城市就业的人口超过一亿,其“市民化”道路也很艰难,随着年龄增长和劳动能力减弱,大部分农民还是会选择回到农村。在社会保险未全方位覆盖之前,农村土地仍是其生存的最低生存保障,也是未来的养老保障。优先解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提高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将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起到积极作用(拜茹,2019)[34]。因此,在国家还不能充分实现农村人均居民收入达到城镇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不能贸然采取强制推行规模经营的手段,而是应该逐步推进。
(二)农业的公平与效率
我国的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步伐不可逆转,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改革,必须把土地流转和农民利益保障相结合。农业比较收益低,农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不断浮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较之前有较大的改变,农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出现契机。但大规模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存在困境:第一,农地流转后难以分享规模经营的利润,使得农民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由于各种原因流转后使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严重。第二,流转后新产业种植品种对土地形态、肥力的破坏严重,如何弥补地力损害成为流转主体新障碍。第三,各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经营的能力不同,国家补贴力度有失公平。2016 年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和各地方政府推出的农业生产经营补贴向规模经营主体补贴的方式,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补助由2016 年126 亿元①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6 年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财发〔2016〕5 号,http://nfb.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606/t20160622_2334393.html.增加至2018 年293 亿元②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8 年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的通知》财发〔2017〕6 号,http://nfb.mof.gov.cn/zxzyzf/nyzhkfbzzj/201711/t20171108_2746103.html.。高额农业补贴激励土地经营户向规模经营转变和增加生产投入的积极性。但是家庭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长期处于小、散、弱的状态,组织化程度低,获取农业补贴的能力明显低于农业大户、产业基地、农业龙头公司。一方面,由于各主体的资金获取能力不同导致农业补贴范围和程度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前者的农业发展能力有限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农业要素资源浪费,制约农业效率提升。上述种种因素使我国推行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可一蹴而就。
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方式
完善农地流转制度。随着多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改革,土地流转愈演愈烈。据农业部公布数据,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由2010 年2.28 亿亩上升至2017 年5.12 亿亩,年均增长率超过12.25%;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4.5%上升至37%。尽管农地流转面积逐渐增大,但当前农业内部存在的问题仍是土地流转困难。要顺利发展规模经营,最主要就是完善土地产权制度。2016 年来,全国土地确权制度推行保障了土地的使用权的稳定性。土地确权解决农民以各种形式流转的后顾之忧,实现土地的快速高效流转。除此之外,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完善流转制度有利于规模经营主体做长短期规划,规避流转后因道德风险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避免经营主体前期投资变成沉没成本。加强司法制度建设,淘汰低效率的经营规模及形式,支持高效率的规模经营主体实现农业规模的帕累托最优。在土地经营权分散,品种选育、生产服务、流通销售等环节统一,实现“统分结合”的创新成为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关键(周振等,2019)[35]。
五、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的“适度”判断
目前各界对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面积尚未形成一致认识。经济规模和技术规模是土地流转“适度”的标准(陈锡文,2017)[36]。中国疆域辽阔,各区域农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应用能力、政府规划等存在差别,因而对于农业的适度经营规模不可一刀切。应根据各个区域的差异实行差异化策略。如对于主要粮食产区和平原地区,可参照美国、欧盟等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土地的规模化的同时达到大型农业机械对人工耕作替代的技术规模。对于四川、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不可盲目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特别是耕地规模,这些地区地形不适宜大型机械作业。可视地形情况借鉴日本、韩两国发展模式,利用丘陵、洼地等相对较平坦的土地资源,以小型农机具耕作为主。通过土地规模化、技术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等多途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要素的充分利用,促进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六、总结
有效规避农业规模经营的多元性风险,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标准是提高农业规模效应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必须与当地的资源禀赋、要素构成、经济水平、政策环境等相适应,要在确保生产率提高、农民社会权益、社会公平效益的基础上有序展开,满足不同经营主体基本利益诉求,因材施教、分类施策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小农经营对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的农业格局中,大规模经营主体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主要力量,但小规模经营主体是主体地位这一现实难以改变,要重视小农户在未来经营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李先德,2017)[37]。推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不可盲目取缔小农户,农户家庭与其他形式规模经营并不冲突。同时,要注重规模土地的连片,避免仅是地块的增多造成的土地细碎化导致“规模陷阱”。要严格限制流转土地的用途,严防农业耕地红线,在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前提下,合理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业“接二连三”步伐,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总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长期的演变的过程,需遵循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进程适时推进。同时,要立足各区域的农业资源禀赋,综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农业人口的转移程度,尊重民众的意愿,因地制宜相机而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实现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