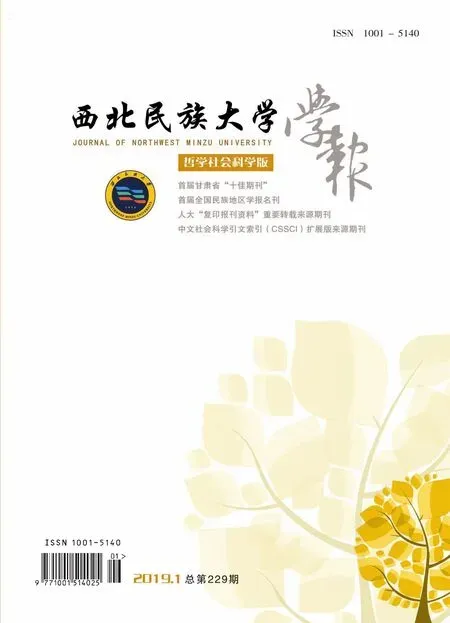互动行为学:戈夫曼社会学的行为主义解读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微观社会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著述对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迄今仍在不断地激发各种学术争鸣。戈夫曼开创了“面对面互动”这一崭新的经验研究领域,他对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研究跨越或综合了不同的研究取向,诸如博弈论、行为学、符号学、社会语言学、功能主义以及拟剧论等,从而摆脱了学科界限的束缚。本文主要探讨戈夫曼社会学的行为主义基础,这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从戈夫曼的著述中可以发现,他在字里行间毫不隐晦地表达出对行为学的推崇,并承认他关于“面对面互动”的基本概念来自动物行为学[1]59。戈夫曼尝试以行为生态学的方法研究共同在场的人际互动,探讨“互动的动物园里能找到什么样的动物”[2]6。在对公共秩序进行微观层次的研究时,戈夫曼曾明确指出若要对“面对面互动”进行自然主义式观察,就应该发展出一门“互动行为学”(interactionethology)[1]x。鉴于此,本文将戈夫曼的行为学研究范式称为互动行为学,并具体展开论述[注]① 戈夫曼通常采用的表述不是Behaviorism,而是Ethology,后者可能翻译成“动物习性学”更为合适,它是在自然条件下对动物行为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并将行为视为进化论意义上的适应性结果。但是,戈夫曼反对行为学的进化论色彩。。
一、戈夫曼思想的行为学渊源
关于戈夫曼的研究文献中,很少有人专门从行为主义的角度进行解读,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成员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Hughes)可能是一个例外。休斯曾是戈夫曼的老师,并对他的影响持续终身。在关于《互动仪式:面对面行为研究论文集》(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一书的书评中,休斯给予戈夫曼极高的评价,称他是“社会学界的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3],同时也表明他认可戈夫曼对“面对面互动”进行的行为学研究。洛伦兹是奥地利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也是动物学的开山鼻祖。在《收容所》里,戈夫曼指出他关于空间的社会使用的探讨深受欧洲动物行为学家的影响,诸如海尼·赫迪杰(Heini Hediger)和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罗伯特·萨默(Robert Sommer)、亨利·埃伦伯格(Henri Ellenberger)等人关于“个人空间”“动物园与精神病院”等研究[4]。戈夫曼在《互动仪式》的前言中认为他对“细小行为”进行严谨而系统性的研究受到当时学术界对动物和语言研究的启发,并且得到关于“小群体”的互动研究和精神疗法的各种学术资源的支持[5]1。
戈夫曼早年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并受到西欧传统社会学思想的熏陶,其中包括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以及迪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等。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术传统中,乔治·米德(G.H.Mead)有很多关于行为学方面的阐述,但经常被人们忽略[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的副标题便是“一位社会行为学家的观点”。。米德的行为主义是一种社会行为主义,比约翰·华生采用的纯粹行为主义更加充分,是“根据个体的行动、特别是(但并非只是)能被他人观察到的行动来研究个体的经验的方法”[6]2。事物具有的特征与个体经验体现在各种动作之中,但该动作部分是在有机体内部并通过后者才表现出来,米德认为华生的纯粹主义论述中忽略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米德的行为主义强调无法被外部观察到的那些动作的重要性,并将它们置于其自然的社会情境中加以研究。米德试图将观念引入行为主义,以挽救华生行为主义的先天不足。米德明确表示,关于低等动物的行为主义的观点也可以转用于人类。而戈夫曼则借鉴了动物行为学的思想,将对动物园里的动物进行的观察运用于人的行为研究。在《性别广告》里,戈夫曼赞同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思想,从而为他的关于面对面互动研究的行为学取向进行辩护[7]1。除了米德的影响之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者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曾强调以有机生态学作为模型来研究城市社会及其生活方式[8],他认为人际沟通是人类群体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而人际沟通正是戈夫曼毕生的研究主题。
此外,对戈夫曼的学术旨趣产生影响的还有雷·伯德威斯特(Ray Birdwhistell)。伯德威斯特仅比戈夫曼年长4岁,1951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其导师之一是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后者也是戈夫曼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导师。20世纪40年代中期,伯德威斯特曾短暂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教学,戈夫曼正是他的学生。伯德威斯特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创立了身势学这门学科,主要研究各种面部表情、手势、姿势、步态以及其他可见的非言语性的身体行为,认为它们承载着人际互动的大部分社会意义。事实上,戈夫曼与伯德威斯特的学术研究是相互影响的。1969年,伯德威斯特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直到退休),而戈夫曼于1968年从加州伯克利分校调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学术接触。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谈话互动行为的研究更加精细化。1956年,在精神分析学家弗里达·弗洛姆—里奇曼(Frieda Fromm-Reichmann)的启发下,包括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诺曼·麦奎恩(Norman McQuown)、雷·伯德威斯特在内的许多研究者聚集在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所,进行一项名为“一场访谈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an Interview)的研究。他们对一个互动短片进行了详尽分析,细致地描绘能被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并确定它在沟通过程中的位置。该计划的参与者中有很多人后来以这种微观的视角研究具体的互动实践。例如,格雷戈里·贝特森等人主要研究互动过程本身以及互动达成的方式,将互动的过程或实践视为一种行为系统,关注互动过程中身体动作的控制、口头表达以及参与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取向的显著特点是对互动过程采取整体主义的视角。学术界这种新的发展动态也为戈夫曼研究“面对面互动”提供了重要参照。1962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关于派生语言学和身体语言学的会议”上,戈夫曼在讨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他后来组织的一些学术会议中,戈夫曼主要关切的是对互动进行结构主义、自然史或“场景分析”等取向的探讨[9]。这一时期,戈夫曼还受到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影响,尤其是诺伯特·魏纳(Norbert Weiner)和冯·诺依曼(von Neumann)的思想。此外,戈夫曼还与精神病学家尤尔根·吕施(Jurgen Ruesch)进行过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戈夫曼关于行为学的思想亦受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影响,这体现在他的框架分析观念。贝特森研究猴子嬉戏行为中的不同框架信号,猴子能够区分本意行为(打斗)与转化行为(嬉戏),他认为猴子将某些行为不是理解为打斗而只是嬉戏而已,这需要一种“元沟通”[注]“元沟通”(metacommunication)又译“元信息传递”,指以比较直观的方式传递信息,诸如人的身势语、猴子等动物通过视听刺激传递信息等。的能力,即它们能够相互交换“这仅是嬉戏”的信号[10]。任何一种沟通行为都具有元沟通的性质,也即“关于沟通的沟通”。戈夫曼的框架概念与格雷戈里·贝特森的这种观念极为相似。格雷戈里·贝特森之后有不少研究者探讨将严肃的、真正的(不是闹着玩的)行动转换成嬉戏行为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和前提条件。20世纪70年代,在汲取动物行为学思想的基础上,戈夫曼还区别了迪尔凯姆意义上的“仪式”(ritual)和达尔文行为学意义上的“仪式化”(ritualization)。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而言,戈夫曼用“仪式”指涉的是神圣而不是惯例,互动秩序之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它创造并维持着社会性自我[11]。而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而言,“仪式”则提供了社会结构常规化的持续必要性。戈夫曼认为,“至少在意图展示的意义上,行为学和仪式的行为学观念如人类学的阐述一样贴切”[2]10。生物行为学的仪式化过程不断地重复行为的本质内容、强化行为的机能和特殊性,物种的沟通通过简化、夸大和程式化的行为而固定化为某种独特的“展现(display)形式”;而在人类社群里,这主要体现在不同性格特征的展现[7]1。仪式化的概念使戈夫曼进一步深化了其已经在拟剧论中提出的关于展演的思想。在后期研究谈话互动的形式时,戈夫曼也是更多地从行为学的意义上使用仪式化术语,而在涉及补救性的行为时,则更多地指向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
二、作为互动行为学家的戈夫曼
20世纪50年代末,行为主义支配着美国的社会科学领域,文化也大多从行为和习性的角度进行定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整个心理学领域是伯尔赫斯·斯金纳(B.F.Skinner)和新行为主义的天下,斯金纳强调对行为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不追究人的脑海里的意识,因为人的意识、情感和动机本身无法进行科学的测量。戈夫曼的社会学探讨行为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外在的行为观察而不是内在的意识反省,尤其是他主张自然主义式观察法,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的基本要素。戈夫曼亦认为自己是一位行为学家,在1971年出版的《公共场合的关系》以及1982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演讲稿中,他都强调行为学对于研究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性[1]xvii。从早期的拟剧论到后期的谈话分析,戈夫曼充分运用了行为主义的要素,而且他关于互动信息的发出、各种形式的应答性行为等阐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刺激—反应”模式为基础的。
人际互动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戈夫曼基于具体可见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阐释来分析“面对面互动”。由于身份、地位和社会声誉等并非实体性的事物,但它们能通过研究拥有者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加以确认。因此,戈夫曼关于互动的研究侧重于表意性,诸如谈话、身体姿势、衣着以及面部表情等。“联结符号”(tie-signs)是个体在公共场所展现的各种姿态,例如手牵着手这一动作,它向旁人表明行动者的亲密关系。不同的行为和身势有意无意地向他人提供了有关个体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戈夫曼关注身体化的社会互动,强调互动过程的生物性特征,这也与行为学密切相关。从拟剧论的视角看来,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大多是身体管理的行家,他们依据情境需要管理外表,通过装扮、修饰自己的身体,恰如其分地掌握身体距离,并运用印象管理技术,策略性地控制自我的形象。戈夫曼关于“太人性的”自我之阐述,也是对生物学感知的强调,太人性的自我更多的是脱离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生物性自我,它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Id)[注]戈夫曼的自我观亦具有两重性,主要表现为生物性和社会性、能动性与情境性等。。品性(character)是表演者信以为真的特征,并且周围的人们也相信它们是关于行为的典型描述[12]。表现生物学个体之品性的东西通常是关于生理外表的一些象征性阐释,对此戈夫曼认为:“为了满足道德与连续性的基本要求,我们在一种根本性的幻觉中受到激励。这正是我们的品性,它是完全属于我们自身不会改变的某种东西,但它多少仍然是不确定的和无常的。”[5]239
戈夫曼从行为学的意义上来阐释互动博弈,强调互动参与者之间“相互考量的无限递归”[13]18。个体在互动过程中会出现无穷递归式地相互揣摩与考量,它使必要的关注从其义务性的目标悄然转移,并出现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这在互动病理学上表现为“局促不安”[13]18-19。在《公共场合的关系》中,一方面,戈夫曼强调社会规则与规范对于社会行动的首要性,正如言语行动中的语法与句法一样。另一方面,戈夫曼又以行为作为基础,对行动者的意图、动机等进行直觉观察和移情式理解。《常态表象》一文的很多例子来源于动物行为学,它描述了动物的蛰伏、追踪、围捕、伪装、潜逃等[1]238,戈夫曼借此表明,表象与事实之间存在差异、断裂、意义的不稳定等。在这种情况下,现实又如何维持有条不紊地运转?戈夫曼透过事物的表层意义探究了其深层的运作机制。在论述全控机构时,他通过被收容者的机构化经验来分析这种“社会性动物”的“解剖学结构及其功能运作”[4]123。戈夫曼关于互动系统中的“运载单元”与“参与单元”的隐喻也具有行为学色彩[1]7。此外,戈夫曼的社会分类学思想也体现了他的行为学旨趣,因为对自然领地中动物的互动实践进行科学分类是行为学的一项基本而核心的分析工具[14]。
戈夫曼关于框架分析的灵感来自1952年他在弗雷肖克动物园(Fleishacker Zoo)对水獭进行的观察。如前文所述,贝特森首先意识到水獭能够区别真正的搏斗和耍闹,尽管这两者在行为方式上类似。水獭能够传递和转变不同的情境定义,它们既会相互攻击,也会相互嬉戏打闹。也就是说,有些信号是表示开玩笑、嬉闹和玩耍,而另一些信号则会终止这种嬉戏行为而引发真正的打斗。因此,一旦脱离具体的情境,行为就其本身而言是无意义的,而且行动的框架也不会使无意义的事件变得有意义。这里涉及行为意义的转录或变换问题,也即打斗行为与嬉戏行动之间的相互转换。戈夫曼认为,即使是最坚实的实在也能进行系统性的转变。人能够提供关于框架的外在表现形式,除了类似于动物的身势语之外,人还能通过述说、书写、绘画、歌唱,甚至创造各类思维象征物进行表达。戈夫曼试图分辨不同框架的“迭片结构”,也即各种框架的复式叠置方式,因此,他的“转换”概念是从几何学而非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意义上而言的。在探讨初级框架时,戈夫曼认为“动物行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训练有素的海豹、善于社交的海豚、跳舞的大象和耍杂技的狮子等。动物行为表明不同性质的能动者能完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导向性行为,动物亦能被训练去完成一些属于人类范畴的“实用主义的任务”。因此,就导向性行为的能力而言,作为人的能动者和作为动物的能动者之间的界限划分是模糊的。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提出了一种关于主体间的阐释与行动如何可能的基本模型。
三、面对面互动的行为学解读
关于“面对面行为”的研究涉及参与者迅速变化的行为展现,因此,搜集个体遵从行为之证据的主要方法是观察行动者与他人共同在场时的表现,但这并不仅局限于狭义的沟通。当个体进入彼此互构的即时性在场时,自我的各种领地也随之进入情境,它犹如设置了许多无形的黄线和禁区,从而导致各种潜在的冒犯性行为的产生。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对自我领地的无形宣称与要求无处不在,许多不经意的事件与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它的威胁和侵犯,因而互动系统时刻需要引入矫正性的补救措施。在情境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禁区,尤为可能发生各种冒犯及具有对话性特征的补救行为。因此,互动参与者不仅需要提供清晰明确的关于自身的信息,当无法令他人信服时,就必须准备忏悔与赎罪、当场提供赔偿并施以补救,以使自己在随后发生的互动过程中能被继续接受。戈夫曼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和犯罪的隐喻来阐述公共场所的互动行为,在这种视野下,犯罪现场、审判大厅、监禁所以及公民社会的公共场所等都处于同一个场景中,犯罪、逮捕、审讯、惩罚以及重返社会等一系列过程都以手势、表情和眼神等方式来完成。
互动卷入的控制与管理包括卷入的具体对象和方向,它主要涉及3个与行为学有着密切关联的方面。第一,“自动卷入”。它最经常地表现为自主性的身体行为,如吃喝、呼吸、打呼噜、睡觉等,当个体专注于自我仪容的整饰时,自动卷入尤为明显。这些对自我身体的关注被认为是附属性的次要卷入。当他人在场时,自动卷入会被视为对支配性卷入的不适当转移。自动卷入的其中一种形式是“生物性释放”,它包含了一个连续或等级序列,一端是从诸如搔痒、咳嗽、揉眼、叹息、哈欠到瞌睡、打嗝、吐痰、掏鼻孔、松腰带再到放屁、大小便失禁等,另一端则是各种情绪性的表达,如未能自抑的爆笑、叫喊、咒骂等[15]68-69。由于个体一直保持某种社会性状态会导致某种紧张,而生物性释放则提供了短暂的放松,同时它也是表明个体是否正在维持情境仪态的重要标志。这些生物性释放表现得很短促,并且可以在“互动防护物”的背后进行,如在打哈欠或大笑时用手遮掩嘴巴。失当的生物性释放通常与情境中个体的“离场状态”相联系。
第二,“离场”。在共同在场的互动情境中,当参与者疏离于某活动时,个体的注意力会从真实或严肃的世界转移,而独自沉浸于类似游戏的世界,这种从聚集场合的转移被称为“离场”[15]69。最重要的离场类型是个体重温过往的经历,或者预演和拟想未来的活动,其形式包括沉思、出神、发呆、白日梦和内向性思维等静态活动,这种“在场的缺席”还包括通过口头言语和身势语进行的自我对话以及撤回当下的情境关注转而利用现实中的材料进行一些想象性的活动。与停留在脑海里的出神和幻想有所不同,个体的这种游离状态对共同在场的他人而言可能是可见的,如剥指甲、随脚踢路边的易拉罐等。在这些不同的时刻,个体会表现出各种无意识的“离心症状”和次要卷入,表明他疏离于当下的情境。
第三,“玄秘卷入”(occult involvements)。不同的互动类型可能出现不同的失当卷入,玄秘卷入是个体没有意识到他正处于“离场状态”,若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表述,这是一种“虚妄状态”或“幻觉”。它既可以伴随着口头言语,也可以有身体性的活动,但对互动情境中的他人而言,这些“非自然的”活动是不可理解或无意义的。玄秘卷入与“离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被发现之后的结果:处于离场状态的人被发现之后,通常会迅速返回或恢复互动的关注点,调整互动状态,使之与情境相适应;而处于玄秘卷入状态下的个体通常不会这么做。玄秘卷入会令他人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并非由于失当行为本身所致,而是由于无法轻易地将个体召回到聚集中,因而难以继续维持互动情境。
在关于“自我的领地”的论述中,戈夫曼也是从行为学的意义上来谈论“领地”“领域性”等,他对领域性的探讨旨在阐述情境性的活动系统。戈夫曼认为,“面对面互动”可以用传统意义上的迪尔凯姆式术语来描述,诸如仪式功能、规范的维持与违反等;同时,面对面互动与动物行为之间的相似性也很明显。因此,戈夫曼试图综合这两种异质性的视角。在戈夫曼看来,思考规范遭受威胁的传统方式通常聚焦于潜在的侵犯者和被侵犯者,而忽略情境的角色。对此,他认为比较理想的研究范式是假定参与者都试图避免公然违反规则,并应对因不同的场景特征而产生的偶然性。参与者的目标和期望是常规化的,而那些能动性的、变化的要素则被视为是当下情境的特质。倘若个体在情境中怡然自得,这表明他已经稳固地建立起应对情境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机会的经验。当个体的获得性能力(包括对他人动机和意图的理解)崩溃时,这种情境便是脆弱的和易遭受攻击的。个体所处的即时性世界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主观的。围绕在个体四周的、存在各种潜在警告源的空间构成了个体的“客观世界”(umwelt)或“环境”,也就是环绕在个体周围发出警告信号,并且个体用以监控、警惕意外侵扰的区域[1]252。戈夫曼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对客观世界加以定义,如根据情境性的警告信号辨别真伪和紧急程度并作出相应的反应、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侦察与反侦察、保持各种临界距离以及避免引起对方警觉等。行动者的客观世界是以自我宣称为中心的区域,但它并非固定在原地静止不动,警告信号及其影响范围会不断地跟随着个人移动,一些潜在的警告信号会移出有效范围,同时之前处于感知范围外的信号(源)则会进入有效范围。就行为及其反应模式而言,人类世界犹如随时可能出现捕猎与反捕猎行为的动物世界。
“社会情境”是指任何在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发现自己处于彼此视觉和听觉范围之内的物理区域[16]。互动参与者需要对整个情境表现出尊重和关切之意,尤其是共同维持的谈话情境,它建立在即时在场的人们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通过行为学意义上的夸大、强度的标准化以及放宽环境要求等,行为和外表被仪式化,这是人类沟通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戈夫曼认为,关于自我对话的分析必须注意那些非言语意义上的嵌入和转换。而且,会话范围并不一定是特定的关联单位,而可能是整个社会情境。在这种情况下,词语的“俘获”是在会话之外,也就是外在于共同认可的谈话状态。语言学的某些话题要求审视行动者与整个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会话之间而已。例如,在路上行走的人被突出物绊了一下趔趄不已,这时他会自言自语、自我嘲讽或以模仿性的夸张动作作为补救措施,以表明他是一个正常的普通行人。这种补救行为与力学定律无甚关联,他将内在的心理状态外显化,以向他人呈现出可以评价他的信息,这是行为学而非语言学意义上的沟通。同时,他也可以通过另一种言语方式来保持脸面和自尊,即突然发出感叹式咒骂,如“该死!”“见鬼!”等。此时,言说者的言语没有为其他言说者确立有义务进行回应的话槽,它也没有正式认可的言说者和接收者,而只有行动者和旁观者。它包含了插入语和感叹词,但它打断的是身体行为的过程,而非言语本身。
四、互动行为学: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
在《公共场合的关系》一书中,戈夫曼关于动物行为学的思想表现得尤为显著。如同动物行为学家依靠敏锐出色的观察技能研究动物的自然习性,戈夫曼认为,社会学家在研究人际互动现象时也应如此。研究者必须对互动进行系统性地详细观察,倚重和关注的不是互动参与者的内在精神状态,而是其外显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本真的、无意识的,抑或故意表演的、矫揉造作的,这与动物行为学的观点相一致。从这种立场出发,戈夫曼的社会学具有明显的反心理学特征。戈夫曼明确承认,他关于面对面互动系统的研究得益于语言学家和行为学家。在他看来,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只有语言学家有能力研究自身社会的各种细微活动,并客观地对待那些习以为常的行为,然而,语言学家的缺憾在于他们的研究视域相对狭窄[1]xvi。也就是说,语言学家能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启迪灵感,但在内容上显得较为薄弱,而行为学家的研究则提供了更为复杂的模式。因此,戈夫曼崇尚行为学家的研究,认为动物行为学家以另一种方式研究着面对面互动。
与拟剧论、框架分析等一样,互动行为学是戈夫曼研究互动组织的重要策略。在他那里,行为学家由动物标本的剥制者转变成了面对面互动的研究者。用戈夫曼的话说,他是挪用“动物社会学”的术语来描述人类的社会行为[15]67。在他看来:
(行为学家)发展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领域,使他们能够详细地研究动物行为,并采取方法控制先入之见。结果,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即能在其接合处打断那些明显随意的动物行为流(flow),并脱离自然模式。一旦向观察者指明这些行为序列,他的理解就会发生变化。因此,行为学家提供一种启示。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很多行为学家迫不及待地运用达尔文式框架、根据其当下的(甚至是退化的)生存价值来解释任何行为惯例,并且这些早期的研究在进行种群归因上显得过于仓促。当这些偏见被带入人类行为研究时,就会导致某些极为粗糙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谨慎地规避行为学的这些特征,那么它对我们而言具有的典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1]xvii
戈夫曼认为,社会学家借助行为学能够更好地研究互动,但是行为学的进化论式解释结构不能运用于人类行为研究。因此,如果适当地忽略和剔除行为学家的达尔文式物种进化论倾向,那么行为学能为面对面互动研究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范式。因此,戈夫曼的行为主义更多的具有米德式社会行为主义的色彩。米德认为,心理学并非是论述意识的学科,“心理学从个体经验与其所由发生的条件的关系来论述这种经验。当这种条件是社会的条件时,它便是社会心理学。通过对行动的研究来探讨经验,这便是行为主义”[6]31-32。通过描述和分析个体外在的、可观察到的行为形式;通过行为来推断个体动机,而不是心理学式内省,这是戈夫曼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取向。他从互动、关系性的视角研究自我尤为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对戈夫曼而言,对自我的分析无法与个体的行为展演相分离。
戈夫曼的社会学还强调情境的重要性,他关于互动礼仪、行为失当的论述都是以行为的情境特征为基础的。戈夫曼从情境互动论的视角看待精神病行为,认为精神病症状是一种“情境失当”[1]355。精神病院将被指控有“精神疾病”的个体从其表现症候性行为的情境中剔除出去,但这是通过医院的高墙而不是医生的治疗技术实现的。戈夫曼的研究试图表明,世俗化世界里的个人具有某种神圣性,这是通过象征性的行为进行展演并得到确证的。现实生活充满着(想象中的)彼此监控、争强好胜的行为,这使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萨特所说的“他人是地狱”的境况,他们需要时刻审视和警惕周围可能造成破坏和进行攻击的人。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平稳有序地运行,个体需要自我控制,包括行动、情感与心理的适当抑制,而社会则需要提供规范性的奖惩手段。戈夫曼的《收容所》《污名》《场所的错乱》(“The Insanity of Place”)和《框架分析》等著述包含了一种“遏制哲学”[17]316,它类似于福柯的权力观念与治理术,用以理解社会生活的不一致、非理性、不可理解、难以忍受以及使社会秩序免遭崩溃和解体的规则。总之,戈夫曼关于社会控制的观念涉及霍布斯式秩序问题,它为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路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虽然戈夫曼经常将他的研究看作是“自然主义式”,但他所说的“自然主义”并非逻辑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戈夫曼指的既是一种观察者的态度,又是一种被观察到的互动实践的特质[18]。戈夫曼以行动为基础来研究意义,他既非主观意志论者,也非结构决定论者。大体而言,戈夫曼的互动行为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之间存在4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戈夫曼没有将行为与意识、意义、动机完全割裂开来,尤其是没有忽略行动的意义。他旨在通过外部行为和表层话语理解真实的感受和深层的意义,但又不同于虔诚的信徒通过解读《圣经》揣摩上帝的旨意。其次,现实是权宜性的,它是个体对经验之相对的、易变的和主观的感知。与之相对应,戈夫曼论述的人并非是平面化的、单一的个体,而是感觉、态度、个性以及各种人际关系。行动者既是表意性的,亦是反身性的。再次,拟剧论不同于行为主义。情境对行为具有制约作用,但是行为并非完全是情境化的产物。大多数角色扮演活动都只需要个体部分地卷入和投入,而不会占据整个人,这一点尤为直接地体现于戈夫曼的“角色距离”概念。最后,戈夫曼通过研究外部行为不仅指向内在的个体意识,而且更是指向外部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戈夫曼与心理学家的根本不同之处。作为社会学家,戈夫曼的社会学实质上阐述了互动秩序是何以可能的,或者说社会互动和生活世界是如何可能的。个体行为及其动机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自我的呈现性本质为遵从行为提供了内在动机,并对互动秩序产生制约。
总之,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戈夫曼的互动行为学强调情境的重要性,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几乎都处于社会性的情境之中,这确保任何特定群体的成员都处于彼此可感知的范围内。他以米德式社会行为主义分析互动秩序,认为规范性秩序并非基于先验的或抽象的价值,而是世俗世界中具体的人际互动的产物。此外,戈夫曼说的信息的“发出”和“流露”类似于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所说的“体化实践”,即以当下的身体举动传达信息,并只有亲身在场才能传达信息,不管这些举动传达的信息是有意还是无意的[19]。戈夫曼的世界观还建立在“动机争胜性行为”(agonism)[注]Agonism是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它指同种动物之间的动机争胜性行为,具体包括攻击、逃避、姑息和防御等敌对行为。的基础上[17]320。通过对外部的行为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戈夫曼探讨了互动秩序的微观动力学机制。尽管互动系统充满各种偶然性,但它在整体上仍然是可预期的,并具有一定的结构稳定性。
戈夫曼主要研究现代都市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模式,他对人类行为进行的自然主义式研究与动物行为学有很大的关联。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不同,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可以被称为“互动行为学”。戈夫曼毕生对那些异质的、陌生的和异乎寻常的事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试图在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揭示出陌生的规则,而这主要是通过互动行为学的研究完成的。戈夫曼阐述了面对面互动的技巧和印象整饰的方式,如污名管理、面子工夫,信息控制、行为监控以及个人领地等,这些都与行为主义密不可分。因此,行为主义构成了戈夫曼社会学的思想基础,他关于策略性互动、互动仪式以及谈话分析的阐述都以行为主义作为其重要的构成。作为社会学家,戈夫曼的互动行为研究是以秩序为导向的,它实质上阐述了以权宜性的自我互动为基础的互动秩序是如何建立的。如果说拟剧论分析展示了戈夫曼社会学静态的理论框架,那么行为主义则提供了动态的分析内容。概而言之,戈夫曼的研究具有浓厚的行为主义色彩。鉴于他早年曾在英国北部的设特兰岛社区进行关于沟通行为的田野调查,后来在美国本土也陆续开展过一些实地经验研究,这使他的著作具有民族志或文化人类学的特质。因此,纵观戈夫曼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认为他的社会学构成了一种“行为主义的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