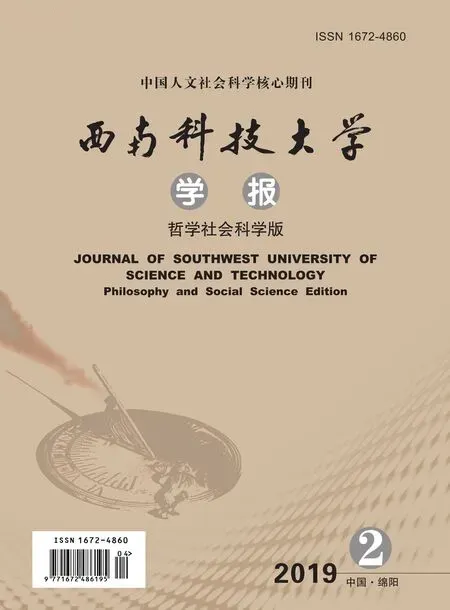跨族际视阈下藏族作家的西藏叙事
杨艳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长期的繁衍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质素的稳定的共同体”[1]。在此过程中逐渐内化于每个社会成员思想与行动中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民俗风情等,是区分同族和他族以及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则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文化“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价值体系、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把单个的个体连接为一个整体、一个群体和团体。文化所形成的认同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认同为人提供集体行动的理论依据,也是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显著标志”[2]。文化认同是藏族作家激发民族认同意识及强化族群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他们确立和定位自身文化视野与创作视角的根本前提。
一、渴求自我阐释的藏族作家
雪域文化、雪域文明早已渗透进藏族作家的灵魂深处,那些世代传承的信仰、人格、语言、服饰、共同祖先、社会经历、饮食习惯等,是他们有别于其他族群的鲜明标识,在渐进的“濡化”(enculturation)过程中实现“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划分。他们自身和同一族群成员被界定为“我们”,其他人则被界定为“他们”。参照民族学实地调查的重要方法,作为“我们”的藏族作家和作为“他们”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作家对雪域文化的认知与阐释,勾连成了自观和他观两种典型路径与方法。站在被调查对象角度,用自身观点解释本民族文化的为自观方法,而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一般观点解释所看到的文化则是他观方法。“明瞭‘自观’,可以克服‘族际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如实地反映真象,不带‘偏见’,但并不能把握本质。”[3]综合运用好自观与他观两种方法方能得出全面深刻的见解。
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文化教育被寺院垄断,“舍寺院外无学校,舍喇嘛外无教师”[4]。1949-1965年,在继续进行寺院教育的同时,新型的教育模式也开始逐渐建立并加以推广,“教育模式的转变是藏族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为根本的转变”[5],教学对象由过去的以僧侣为主演变为以俗人为主,化学、数学等新兴学科以及先进的世界观、方法论等被带进课堂,普通的藏民子弟获得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进而拥有了参与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进程的权利。
正如乌热尔图所言,强烈的述说和自我阐释的渴望,“使生活在人类早期社会的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自我阐释的权利存在于他们之中,存在于他们全身心溶入的部族意识里”[6]。而这样的渴望不仅存在于尚处幼年或童年时期的人们的意识中,同样存在于接受过系统现代文化教育的藏族作家中,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雪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藏族本土作家的书写就兼具文学呈现与文化解读的双重意义。
藏族作家们打破了以往僧侣阶层统领文坛的局面,将汉语作为书面语言进行了一次完美“转身”。但文学本就是语言的艺术,而每种语言都与特定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紧密相关,“每种语言都携带着由认知的、规范的甚至是情感的内涵所构成的文化货物。”[7]语言同时也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只有具备了共同的语言,“才会形成民族的内聚力——民族感和民族的排他性,即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愿望。”[8]语言最深刻地反映民族的特征,也是维系民族内部关系的重要纽带,更能够体现民族的诸多特征,且相较于其他特征而言更具稳定性和恒久性。
用母语之外的汉语,进行跨族际写作的藏族作家,可被看作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所提到的少数族,而少数族的特殊性在于:“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他们总是‘在内’的‘他者’,他们没有确定的民族身份,不可能与某个种群取得完全的认同,而总是站在一条模糊不清的边界上。”[9]对于民族或国家而言,他们又成为了一种“增补”。他们既内在于自己所属的民族,又保持着“之外”“居间”等特征。由于同时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 他们对于文化的解读,“都必须通过一个下意识的‘翻译’过程来完成,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不具有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意义,都是协商的结果。”[9]正因为经过了翻译和协商过程,作为少数族的这些藏族作家对汉藏文化的把握方显与众不同,当他们加入汉语书写阵营的时候,沿袭的已经不只是汉语的书写习惯,因为作者要“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感知,带到汉语创作当中去的时候,必须创造一些表达方式;或者即便是原来的表达方式,也要赋予其新的意义。”[10]这些作家穿行于汉藏文化之间,在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中探寻“藏人生存”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契合及共鸣,并以更宏阔的视角揭示人的生存悖论与现实处境,而非简单地贴上藏地或民族的标签。
与此同时,从事藏地汉语文学创作的藏族作家又不得不面对文化割裂的无奈以及无法归依的疏离之痛,有论者甚至认为不用母语创作的民族作家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族文学的高度,但也有论者认为“只要作家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民族的精神,从民族的心理素质、历史变迁、文化积淀中去洞察民族的深层底蕴,不管你是运用什么样的民族语言都能够真实地、客观地揭示民族的生活本质。”[11]无论评论界如何看待和评说,跨语言、跨文化、跨族际和跨地域写作的藏族作家的确存在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与尴尬,他们因“文化杂糅”“身份模糊”等而成为萨尔曼·拉什迪所界定的从事“边界写作”的“边缘人”或“边际人”,迫切希望以艺术化方式进行自我阐释,阐释所在的地区、所属的部族和所因袭的文化传统。因此,《尘埃落定》的出版对阿来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部小说让人们知道,藏族大家庭中还有嘉绒藏族这样一个特殊文化群落的存在。尽管在血统上会被一些保持正统的同胞视为异数,但丝毫不能减弱阿来对故土的热爱和对部族的认同。
二、呈示文化传承与变迁
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多样性,也具有传承性、创新性和发展性等。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全球化等的影响与冲击,如何既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了解,是每一个作家都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从事藏地汉语文学创作的藏族作家们更要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首先必须意识到母族文化的优势与弱点,要真正懂得扬长避短;其次,应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且对现实生活产生有益启悟;还应该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充分了解世界文化语境的基础上,让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并使其成为世界文化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雪域文化自成体系也不断融合新知新见,藏族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诠释母族文化的精髓和真谛。
藏族作家们穿行于汉藏文化之间,汉语对他们来讲是用于写作的书面语言,而藏语则是口头语言,“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则是与生俱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12],正是藏语里的这些东西内化于作家的记忆和灵魂深处,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即“对某种价值或信念的内化是对社会影响最为持久、也最根深蒂固的反应。……一旦成为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信念就会与它的来源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变得非常不容易改变”[13]。在汉藏两种语言之间不断穿越的过程,两种语言不断对比、转换和翻译的过程,是作家们不断强化母族文化记忆的过程,更是展现和阐释文化交流互渗的过程。相对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作家这些“他观者”,深受雪域文化濡化的藏族作家在主题开掘以及形式探索等方面,都拥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相同的题材内容、汉语言模式及叙事结构,在“他观者”“他们”止步的地方,藏族作家可以继续并深入掘进。
千百年来,藏民族乐观坚强地生活在自然环境封闭隔绝、气候条件严酷恶劣的青藏高原,他们敬畏崇拜自然、善待生命,在与大自然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与信仰。人们将其口耳承传、代代相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全新的形式和价值。以神山圣湖崇拜为例,藏区多山,“十万雪山,十万江河”“前面是雪山,后面是冰川”,藏民族赖以生存、试图改造的是山,最捉摸不定的还是山,遂将其看作神的化身,山神崇拜就成为藏族先民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波光粼粼的湖面、群山雪峰的倒映、湖水拍击两岸的轰鸣、云蒸霞蔚的景色等均能使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思。这些原本属于自然的奇情异景在原始人那里,他们无法作出解释,于是就将这种种现象附会成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创造”[14],圣湖崇拜因此流传至今。朝拜神山圣湖是藏族民众潜心修行的重要方式,也是藏族作家不断运用与诠释的重要母题。
青海作家才旦的长篇小说《安多秘史》以安多部落王转世故事作为主线,与世袭制王位传递方式不同,安多部落王国实行转世习规。勇猛的部落王族族长查朗历经千百次搏杀,建立了强盛的安多部落王国,却不幸染病身亡。出家做高僧的查朗兄弟朗玛被迎请为第一世部落王,朗玛执政38年期间,恪守佛门戒律,终身未行婚娶之事,并留下部落王实行转世制度的遗言。前六世皆合乎仪轨,只有第七世部落王因代行执掌王权的扎登王爷提前偷看六世部落王所留下的寻访证物标志,造成阴差阳错、以假代真的局面。假部落王坎布多杰和真部落王贡巴达杰由挚友变成竞争对手和死敌,二人的两次重大因缘际会皆围绕扎达圣湖展开。首先是二人带着名为“牧家炊烟图”的羊皮画到扎达圣湖验证真伪,坎布多杰在圣湖边被新部落王寻访团认定为第七世部落王,真部落王贡巴达杰流落民间。圣湖与活佛转世习俗之间原本就有着深厚的渊源,在寻访、判断和认定活佛的繁复程序中,圣湖作为元素之一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安多部落王的寻访认定中,圣湖圣景成为了决定性环节,“金盆圣水里的景象又起了变化,金盆里的圣水缓缓地放大成了一泓烟波浩渺的湖水,湖水如天池般盛在一个偌大的山坳里,……金盆圣水的遥远处,两个少年骑着牛朝圣湖走来。”“贡巴达杰这时似乎想起了什么,就对坎布多杰说,我们今天来扎达圣湖是为了验证你的羊皮画的真伪,可现在……坎布多杰于是重新将那羊皮画放到了水里。这时,包括王府外务管家阿嘉丹巴在内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水里的羊皮画,想一睹羊皮画所显现的圣景,可奇怪的是,不仅圣景没有出现,那羊皮画反而像浮物一样沉到水底不见了”[15]。虽然圣湖已经给出明示,是人力遮蔽了真相,才有了之后坎布多杰和贡巴达杰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及命运的跌宕起伏。
第二次圣湖边的交手是在贡巴达杰兄弟勾结马家兵篡夺王位之时。与扎登王爷联手篡位不成后,黔驴技穷的贡巴达杰转而与安多部落王国的仇家马家政府兵合作,却被代表正义的坎布多杰部落武装全歼于扎达圣湖湖畔,此时的扎达圣湖不仅反常地结冰封冻,还在茅草柴枝的掩护下变成了作恶多端的马家政府兵葬身之所。假部落王坎布多杰也经过重重磨砺蜕变成了被人称颂的圣王明君,正可谓天命不可违但后运由己造。扎达圣湖是安多部落王国曲折复杂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成就者。
藏族作家们将本民族宗教与神话、历史与现实等族性文化有机和谐地呈现在汉语文学作品里,同时也会不断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或文化精神,进而展示出时代变迁以及时代风潮中母族文化的各种新变。任何一种文化都会与其他文化相遇、相交,也会发生流转与变迁,“文化演变是其最核心部分的演变,也就是知识和态度的演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行为和行为方式的演变,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成功的演变在于在变迁的过程中,能够始终继续保持对原有文化的认同。”[16]如若文化演变发生在战乱、动荡的非常时期,期间又有各种不可预期的变故出现,原有的文化观念或理念可能会随之出现弱化、偏离或位移。
阿来对漫长历史长河中藏民族蜕变的痛苦和新生的欢乐感同身受的同时,还以强烈的自省意识描摹出了特定时期他们与固有文化传统的疏离或断裂。对于《空山》里连汉语都不怎么懂的村人而言,新社会是一个遥远抽象的存在,对各类政治运动等更是不知所云,就连“运动”“突击队”“错误”之类的新鲜词汇都需要他们穷尽所有想象去理解和领悟。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倍感困惑:“为什么会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势像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心急火燎地往前赶。你跟不上形势了,你跟不上形势了!这个总是急急赶路的形势把所有人都弄得疲惫不堪”。[17]这个形势使得老经验不再被人们奉行和遵从,让沿袭千年的佛教义理部分失却。被形势所迫的人们慌乱地拼凑着对世界的认知,与“文革”前后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他们也经历着旧秩序被打破但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迷茫与困惑。机村人因此忘却了长幼有序,忘却了身为藏家儿女那已经渗入骨髓的佛教慈善悲悯传统,他们可以肆意践踏和欺辱格拉这样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他们会残忍地对与之订立了千年和平共处契约的猴群举起猎枪,他们还会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林木挥动锋利的刀斧。心肠变硬、眼神凶狠的人们因此遭到天谴,他们不得不找寻新的栖息地,但迁徙之路却阻且长,“那条路,不在眼前,而在心上。那条路,不通往地狱,也不通往天堂,通往我们伟大的故乡”[17],不省察自身,迁往何处都不会是真正的心灵皈依之所。
三、西藏祛魅
对大多数人来说,西藏永远都是一个附会了太多想象或猜测的形容词。它是第一个踏上雪域高原的西方人——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eade)的游记《大契丹或西藏王国新发现》里描绘的幽静祥和之地:“西藏到处都是慈眉善目的喇嘛,就是在俗众中间也难听到粗鲁的话语。他们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祈祷,至少早晚两次,每次长达两小时”[18]。或者是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有神圣雪山、幽深峡谷的人间天堂,是远离战争与纷扰的香格里拉,是消弭了时光流逝之忧的圣地净土。
但是,神圣、神奇并不完全等同于神秘或魔幻,“浪漫”的误读背后是对真实西藏的遮蔽。真实的西藏应该是一个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朝圣转山、转经礼佛是藏民生活的一部分,神山、圣湖、寺院、五色经幡、玛尼佛塔是西藏的组成部分,却并不是西藏的全部。因为这里生活着的人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大家有着共同的名字——“人”。现代化生活并非与藏区绝缘,藏区也不是保存人们对过往生活记忆的“博物馆”,藏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丝毫不逊色于内地民众,他们对新事物的适应与接受能力更可与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们相媲美。藏民们迫切希望能够参与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有欢笑、悲伤、获得、失去、甜蜜、酸涩、昂扬、失落等诸种体验。而这些情感诉求或重荷与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并无二致,他们自然有权利享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优秀成果,他们也有资格向往和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
藏族作家要做的就是用传播范围更为广泛的汉语作为书面语言,还原本真的藏区藏民和藏文化,着力于为西藏“祛魅”,不是急于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或呈现某种我有你无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19],更“不以陈腐的浪漫来稀释当代藏地生活的真切性,而以多焦的视点与多重的变奏,理性而全面地审视生活西藏、文化西藏”[20]。唯有如此,他们的作品才不会沦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可能被迅速淘汰的快餐式文化消费品,也不会成为大众文化时代里仅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猎奇心理的单一文本。
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就以藏族村落中普通藏民生活及情感作为叙述对象,自然条件恶劣的普村是离县城最远的村庄,这里因只能种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紫青稞,而被外村人鄙夷地称呼为“吃紫青稞的人”。“‘普村丰收了,全世界都丰收。’普村丰收的年景确实也很少,不是旱了就是涝了,再不然就是虫害、雹灾”[21]。生活如此艰难的普村人固执地认为铁匠永远低人一等,铁匠绝对不能跟村里其他人共用一个酒碗喝酒。但是,铁匠扎西和儿子旺久外出揽工挣钱并让家境殷实的事实又深深地刺激着村里人敏感的神经,其实,他们想出去走走的心早已蠢蠢欲动。尼玛潘多以略带幽默色彩的笔调状写着人们复杂又矛盾的心理状态,同为嘎东县下属村的森格村女人们就生动地演绎着他们对村外生活的强烈向往,尽管从森格村到县城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但县城对森格村女人来说却是个非同一般的存在,“再怎么邋遢的女人在进城前都要洗洗脸上的烟尘污垢,再怎么寒酸的女人也要换件体面的衣服,再怎么忙碌的女人也要梳梳头发,哪怕只是手蘸唾沫往后理理。县城没有仪容检查站,可森格村的女人到了县城会收敛很多,她们对县城怀着一种敬畏心理”[21]。这岂止是对县城的敬畏,分明是对以先进生活方式及价值理念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敬畏和期盼。这些藏族妇女不是一些论者所说的使大都市的中国人感到放心的矛盾存在,即“一方面,她是变化中的中国保存良好的‘传统’文化继续存在的证明;另一方面,她那难以驾驭的他者特征,可以用来强调‘优越的’汉人需要采取开化的办法”[22],她们就是一群迫切希望接近并融入现代文明进程的普通人,她们的期望、诉求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并没有太大不同。
尼玛潘多的叙述是克制平静的,藏地民众渴盼走出世代居住的大山的共同愿望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努力打开城市之门并竭尽全力在城市当中立足,是桑吉、达吉、旺久等青年人的心愿,也是尼玛潘多对本土乡民的殷殷期盼。如果说世代守护一方水土是他们必须恪守的职责,拥有同等发展机遇并获得更优裕的生活质量则是藏地民众应有的权利。
综观当今文坛,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已经构成当代藏族文学的重要一极。尽管没有用母语进行创作,但他们能够运用汉语实现对民族精神和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以“既能入于其内又能出于其外”的创作优势,叙写真实可感的藏民、藏地以及藏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赋予自己的价值判断,用文字叙写藏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用心聆听母族文化的足音,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示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将很多人眼中附会了太多想象的“形容词”化的西藏,还原成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祛魅”后的西藏不再是遥远神秘蛮荒的化外之地,这里有发展,有变革,有进步,有上升,当然也有精神滑坡和道德失范等。他们用实绩证明:“自观者”视阈中的雪域文化有着别具一格的风采与魅力。与此同时,这些藏族作家“在汉语能力越来越娴熟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本民族文化自觉,就是这些人,将对汉语感受能力与审美经验的扩张,做出他们越来越多的贡献”[23]。藏地汉语文学因藏族作家的不懈努力而精彩纷呈,汉语更会因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加入而获得更大的丰富与拓展,成为多元文化共同建构的公共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