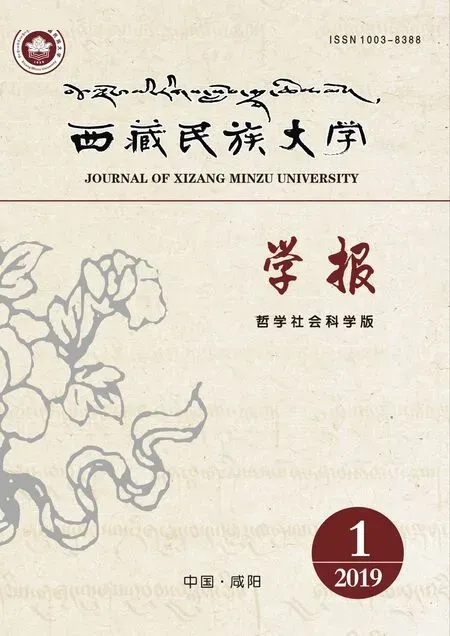和瑛《西藏赋》叙事策略研究
严寅春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赋是中国文学特有的一种文体,由于其“包括宇宙,总览人物”、“铺才摛文,体物写志”等特点,天然具有叙事的因素,因此学者在借用叙事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时,赋也成为关注的重点之一。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把辞赋列为“叙事”的文学,并从虚构故事的叙述框架、叙述描绘客体世界的精细程度、多样化的叙事风格等方面分析了赋体文章对小说文体的影响。[1](P125-138)此后,宁稼雨《诗赋散体化对六朝小说生成的作用》(《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朱迪光《“赋”的含义及其对传奇、话本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陈节《论赋与唐传奇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程毅中《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中国文化》2007年第1期)等则进一步从叙事的角度申述赋体对小说的影响。胡大雷《论赋的叙事功能与中古赋家对事件的参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刘湘兰《论赋的叙事性》(《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傅修延《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等立足赋体的叙事性,具体分析赋的叙事特征,用叙事学的理论分析赋体文本,推进了叙事学的中国化。
和瑛《西藏赋》是清代疆域大赋的代表,也是唯一一部用赋体形式描写西藏情事的文学作品,是中国赋体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本文拟借用叙事学的理论,对《西藏赋》的叙事策略作具体分析
一、创作主旨的叙事指向
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界定叙事的概念时说,“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不外乎是一种传达人生经验本质和意义的文化媒介”[2](P5-6),进而从叙事的功能性入手,分析了抒情诗、戏剧和叙事文的不同。用浦安迪的观点来观照赋,可以发现这种介于诗文之间的独特文体,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抒情诗而非叙事文,具有较强的抒情特性。从赋体生成角度来看,关于赋的起源,尽管众说纷纭,但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不歌而诵谓之赋”[3](P1755)、“古诗之流”[4](P1)、“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5](P43)等,追本溯源,赋体的源头与“诗”密不可分,赋与“言志”密不可分;从赋体流变角度来看,骚体赋、抒情小赋、文赋固不必言,即便是兴于两汉的逞辞大赋,也是寓讽喻于其中,旨在讽喻抒情而非仅仅体物叙事。
赋至清代,特别是舆地大赋的大量出现,赋的讽喻性、抒情性衰弱,取而代之的是叙事性、知识性。徐松跋英和《卜魁城赋》云:“国家抚有六合,尽海隅出日,咸入版籍。康熙、乾隆中,屡测星度,刊定舆图,于是绩学之士,闭户著书,能知宇宙之大。又恭读高宗纯皇帝圣制《盛京赋》,流天苞以阐地符,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泰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独黑龙江界在东北边,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杂诗》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炼京,天则留待我树琴夫子,发摅文章,为封疆增色,升高能赋,山川能说,兼此二难,是足以垂不朽矣。”[6](P517)可以看出,英和创作《卜魁城赋》的直接动机是国家版籍的扩大,旨在“为封疆增色”,进而“润色鸿业”,而讽喻之意荡然无存。
与《卜魁城赋》等一样,和瑛《西藏赋》铺陈西藏疆域,也有“为封疆增色”的一面,但其并不仅仅是“润色鸿业”,更重要的则是在于咨政,在于为后任了解西藏、认识西藏提供第一手文献。西藏虽然地处徼远,政治、经济、文化等迥异于中原,但在“安众蒙古”[7](P98)等事关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性。经过清代初期的治藏实践,清朝中央政府认识到,治理西藏,不仅需要完善的章程,更需要保证治藏方针政策的延续性。第二次驱逐廓尔喀之后,福康安、孙士毅、和琳等大力整顿西藏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后,福康安、孙士毅陆续离藏,而和琳则留藏任钦差办事大臣,具体执行既定的治藏方针政策。乾隆五十八年,“稍谙卫藏情形”的和瑛进藏协助和琳办事;五十九年,又急调松筠进藏,接替和琳。在确定松筠接任和琳后,乾隆特别强调:“卫藏地方经和琳悉心整顿,定立章程,一切驾驭各部落,训练番兵,所办俱有条理。仍著和琳、再向松筠将钜细事宜,面为告知,俾得循照成规经理,倍臻妥协,以副委任。”[8](P432)并将谕旨以五百里加急,分别传给和琳、松筠二人。当天又发谕旨,再次要求“和琳俟松筠抵藏,面行交代,并将应办事宜详悉告知”。[8](P432)嘉庆元年正月,乾隆传谕班禅额尔德尼,又称:“前因藏内事务,噶布伦等措置乖方……命尚书和琳革除积习,酌定章程,一切井然有序。又命松筠等驻彼,循守成规,办理诸事。”[8](P1002)可见在驻藏大臣的人选上,朝廷颇费苦心,考虑良多。而在交代离任一事上,更是反复叮咛,离任者要“钜细事宜,面为告知”,继任者要“循守成规,办理诸事”,保证中央确定的治藏方略的顺利延续。
基于朝廷对驻藏大臣交代及治藏方略延续性的重视,和琳离任之际,可能已经启动了《卫藏通志》的编纂工作,方便“循守成规,办理诸事”,而不只是简单地“面为告知”,口头交代。同样,松筠自驻藏大臣离任时,也曾编纂有《西招图略》,旨在“便于交代,以代口述之未尽者”[9](P673);和瑛嘉庆六年离任时,也曾“将藏内一切应办事宜纂成则例,作为交代”[10]。和瑛编纂的则例已经亡佚不可见,惟其撰著的《西藏赋》广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则例”的作用。嘉庆间,四川官署将《西藏赋》视为入藏必读之书予以刊刻。黄沛翘在《西藏图考》卷八《西藏赋》题下自注中提及文硕进藏任驻藏大臣时途径成都,曾向其出示所携带的《西藏赋》。[11](P488)姚莹《康輶纪行》卷九《〈西藏赋〉言疆域》盛赞《西藏赋》“于藏中山川风俗制度,言之甚详,而疆域要隘,通诸外藩形势,尤为讲边务者所当留意”[12](P26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藏赋》实际上就是一部微型方志,是缩小版的西藏百科全书,是文学形式的交代则例,其创作主旨指向的是叙事而非抒情。
二、自注的叙事功能
《西藏赋》正文4445字,而作者自注则多达24437字,且不少自注都是内容详瞻,事件完整,叙述要素齐备,有较强的叙事功能。如“填海架梁,西开梵宇”句下自注:
《经簿》:拉萨地乃海子也。唐公主卜此地为妖女仰面之形,海子乃妖女心血,是为海眼,须将海眼填塞,上修庙宇如莲花形,乃得吉祥。藏王遂兴工将海子四面用石堆砌。海眼中忽现出石塔三层,用石抛击,然后用木接盖,其空隙处,熔铜淋满,海眼平涸。时有龙王献洋船式样,用石堆之,大招始成。[13](P50)
自注引《经簿》之记载,通过公主相地、湖中涌塔、龙王献宝等情节,叙述了大昭寺修建的缘起与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富有传奇性与神秘色彩的历史故事。唐公主即文成公主,藏王即松赞干布,唐贞观年间,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王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分别带了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和十二岁等身像。为了安置佛像,在文成公主提议下,松赞干布下令修建大、小昭寺来供奉两尊等身像。文成公主亲自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奉十二岁等身像,此寺大门朝东,以示公主悲思汉唐之故。赤尊公主主持修建大昭寺,进展并不顺利,墙一直是修了就倒,根本建不起来。文成公主谙熟星象和五行说,遂夜观天象,日察地形,发现拉萨河谷形如仰卧的罗刹女,而拉萨红山东二里许的卧塘湖正是罗刹女的心脏,池水是罗刹女的血液。于是,文成公主提出只有填平池塘,就地建寺,寺才能建成;填平池塘还必须用山羊驮土,否则永远不能把湖填平。按照文成公主的建议,大昭寺终于建成,其全称为“惹萨噶喜墀囊祖拉康”,意即由山羊驮土而建的佛殿。大昭寺坐东向西,屹立在拉萨一千六百多年,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
又如“挺身缒险,撒手飞绳”句下自注:
正月二日,作飞绳戏,从布达拉最高楼上系长绳四条,斜坠至山下,钉桩栓固。一人在楼角,手执白旗二,唱番歌毕,骑长绳俯身直下。如是者三。绳长三十馀丈。后藏花寨子番民专习此技。岁应一差,免其馀徭。内地缘竿、踏绳,不足观也。[13](P111)
赋文中仅仅用8个字概略地描写西藏高空滑绳表演,而自注中则详细叙述了高空滑绳表演的时间、地点、表演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要素,甚至还将此项表演与内地缘竿、踏绳等杂技表演进行了对比。和瑛在西藏生活了八年,多次观看过此项表演,娓娓道来,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自注这种交代式、说明式叙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赋体等抒情文叙事方面的不足,扩展了抒情文的叙事功能,增强了抒情文的叙事效果。
三、隐寓叙事
隐喻既是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手法,也是一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叙事方式,是“将感知体悟到的事物、思想、情感等投射到与其有质的区别的另一事物、意象、象征或者词语之上的过程”[14](P63)。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强调“寓意的读法是古典小说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层面”,“奇书文体却一定要经常做为寓言来读”[2](P125、126)。其实不只是古典小说,不只是明代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奇书文体,所有艺术形式都是隐喻的,或多或少都具有寓意,中国文学尤其如此。《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5](P621-623)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际上正是一种隐喻思维。和瑛深谙易学,其《西藏赋》亦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产物,字里行间往往隐喻着“微言大义”。
浦安迪说,寓意在贯通运用时,“便成为立意谋篇或立主脑的方法了”,“可以窥见整个故事结构与未曾直接言明的复杂思想模式相契合”。[2](P127)纵观《西藏赋》,和瑛最骨干的寓意便是大一统,便是西藏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西藏赋》开篇先叙西藏之方位,谓:“粤坤维之奥域,实井络之南阡”[13](P1)。《说文解字》谓:“奥,宛也。室之西南隅。”[16](P150)西藏地处中国西南,故和瑛谓之“坤维之奥域”,恰是把中国比之一室,西藏则为“室之西南隅”。此句下和瑛自注又谓:“西藏距京师一万三千里为前藏,由前藏至后藏又千里,由后藏至西南极边又二千馀里,乃坤维极远之地。”[13](P1)在这里,和瑛以京师为坐标,标明前藏、后藏及西南极边之距离,此种地理观念也正是中央政府中心说的一种隐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论及《史记》体例时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17](P3319)池万兴在《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一文中曾指出,《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五体结构是一种司马迁民族思想表述法,形象反映了司马迁的大一统民族思想。[18](P130)和瑛以京师为坐标,叙述西藏方位,正是把西藏视为众星之一拱卫北辰,群辐之一环绕车毂,以此象征君臣之道,隐喻大一统。
隐喻大一统,还表现在对前后藏的铺写上。京师之于中国为中心,则拉萨之于西藏亦为中心,因此,和瑛在铺写西藏情事时,先叙拉萨,再叙周边。《西藏赋》在开篇介绍西藏方位、来历后,笔锋一转,开始着重描写拉萨,谓:“乌斯旧号,拉萨今传。其阳则牛魔僧格,搴云蔽天;札拉罗布,俯麓环川。其阴则浪荡色拉,精金韫其渊;根柏洞噶,神螺现其巅。左脚孜而奔巴,仰青龙于角箕之宿;右登龙而聂党,伏白虎于奎觜之躔。夷庚达乎四维,羌蛮兑矣;铁围周乎百里,城郭天然。藏布衍功德之水,机楮涌智慧之泉。池映禄康插木于后,峰拥磨盘笔洞于前。普陀中突,布达名焉。”[13](P12-21)作者不厌其烦地铺写拉萨山川,甚至不惜与后文铺写西藏山川时有重叠,足见拉萨之中心地位。在描写西藏寺庙时,亦是遵循先拉萨再周边的原则,谓:“其寺则两招建自唐朝,丰碑矗矗;万善兴于公主,古柳娟娟。填海架梁,西开梵宇。背山起阁,东望云天……尔乃桑鸢色拉,别蚌甘丹,垂仲神巫,木鹿经坛。”[13](P48-53)作者不仅先从拉萨城内的大昭寺、小昭寺说起,更是对两寺有着细致的刻画,至于黄教四大寺桑耶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则是一笔带过,只罗列名字。另外,在铺写达赖、班禅及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时,也处处遵循先拉萨后日喀则的原则。由中心辐射四方,由内及外,这正是“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生动体现,是大一统思想的内在要求。
隐喻大一统,亦表现在材料的取舍上。同样是关于西藏寺庙的描写,和瑛选取“丰碑”“古柳”两个意象加以摹画,并在自注中注明“丰碑”即唐蕃会盟碑,“古柳”即唐柳。而对大昭寺、小昭寺则用“填海架梁,西开梵宇”“背山起阁,东望云天”等8字来铺写,“填海架梁”建大昭寺正是文成公主的贡献,小昭寺为文成公主所建;其坐西向东,“东望云天”,也是“公主悲思中国”的缘故。直到今天,一碑一柳一公主依然是做为汉藏一家亲、唐蕃甥舅谊的象征,而和瑛将目光凝聚在一碑一柳之上,也是大有深意之举。再如铺陈西藏东部部落时,谓:“工布、达布、江达,险凭隘口;波密、拉里、边坝,隶属西招。硕板多之么髍,宰桑就获;洛隆宗之孔道,第巴输徭。类伍齐红帽之流,土城寺建;察木多三藏之一,喀木名遥。乍丫多盗,桑艾为枭。”[13](P203-208)在提及各个地方时,多言说其风土人情;唯独在提及硕板多和洛隆宗时,拈出“宰桑就获”和“第巴输徭”二事说事。硕板多也作苏班多、说板多、舒班多、学巴多、硕督、硕板督、硕班多、硕般多、鲜朵、学多,西藏宗卡之一,1960年与洛隆宗合并为洛隆县。宰桑即陀陀宰桑,和瑛自注称“准噶尔占据西藏,遣陀陀宰桑至硕板多一带剥削僧俗。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将军统师进剿,陀陀宰桑潜回藏。遣外委等追索马郎,擒获送京”。洛隆宗也作洛宗、妥宗、路隆、罗隆,西藏宗卡之一,1960年与硕板多宗合并为洛隆县。《西藏图考·程站考》:“洛隆宗在类伍齐西南,为藏、炉通津,亦西海进藏之要隘。原隶西藏部属,委碟巴二员管理。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藏,该地碟巴、番民倾心投诚,采办军粮,挽运无误。”[11](P544)第巴即碟巴,“第巴输徭”即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藏,洛隆宗第巴等采办军粮事。康熙时,大兵进藏,平定准噶尔之乱,是清政府治理新疆、西藏,捍卫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和瑛在叙述风土人情之际特意标榜“宰桑就获”和“第巴输徭”二事,其隐喻之意正是讴歌清王朝捍卫国家大一统。
隐喻大一统,亦表现在典故的使用上。在赋中,和瑛特意提及驻藏大臣与达赖见面礼仪问题,谓“兜罗哈达讯檀越如何,富珠礼翀答兰奢遮莫”。自注:“旧俗:驻藏大臣见达赖喇嘛,以佛礼瞻拜。乾隆五十八年奉旨:‘钦差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系属平等,不必瞻礼,钦此。’以后皆宾主相接也。”[13](P74)富珠礼翀的典故出自《元史》,史载:元文宗时,以年札克喇实为帝师,至京师,敕朝臣一品以下皆白马郊迎,众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国子祭酒富珠礼翀举觞立进,说:“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一饮而尽。众人为之凛然。[19](P4222)和瑛以“孔子之徒”自喻,与达赖“宾主相接”,所坚持的不仅仅是皇帝旨意,而是中央与地方的统属关系。《西藏赋》在叙及作木朗、洛敏汤时,谓:“作木朗唇亡齿寒,洛敏汤皮存毛在。”作木朗、洛敏汤都是后藏西部边界上的小部落,是西藏与廓尔喀的缓冲地带,后来都被廓尔喀吞并,故和瑛用“唇亡齿寒”和“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两个典故形容之,流露出深沉的隐忧。
四、片段式叙事
浦安迪以如何处理“事”来区分叙事文与抒情文,他说:
假定我们将“事”,即人生经验的单元,作为计算的出发点,则在抒情诗、戏剧和叙事文这三种体式之中,以叙事文的构成单元为最大,抒情诗为最小,而戏剧则居于中间地位。抒情诗是一片一片地处理人生的经验,而叙事文则是一块一块地处理人生的经验。当然,我们事实上很难找到纯抒情诗,纯戏剧或者叙事文的作品。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中,同一部作品往往可以同时包含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它们互相包容,互相渗透,难解难分。[2](P7)
在浦安迪看来,小说等叙事文体,一定要通过丰富、完整的事件来构成故事,塑造人物,传递社会生活或历史的经验。赋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特殊文体,既具有诗的抒情特点,又具有文的铺陈特征,其所承载的人生经验,既非一片一片处理,亦非一块一块处理,而是长于片段式处理,通过一个个小片段的联辍,进而传递较为完整的“事”。
《西藏赋》作为疆域大赋,其所处理的人生经验是和瑛对西藏风土人情等的感知,进而为治藏理藏提供鉴戒,这是和瑛创作《西藏赋》的主旨。然而,由于赋体文体的特殊性,其叙事只能通过一些片段和细节来实现。如:“遂有宗喀巴雪窦潜修,金轮忏悔;无上空称,喇嘛繙改。持团堕之盔,披忍辱之铠。紫裓韬光,黄冠耀采。萨迦开第一义天,拉萨涨其三昧海。龙象遴于沙门,衣钵传诸自在。此达赖传宗,班禅分宰。拟北山之二圣,化西土于千载也。”[13]在这一段文字中,和瑛叙述了宗喀巴潜心佛法,倡导宗教改革,壮大黄教的经历,以及宗喀巴圆寂后形成达赖、班禅两大活佛体系的局面。若结合作者自注,其叙事不亚于一篇叙事文。
再如:“刀剑一挥,禅座讵伤乎法济;金衣两设,邪人何畏乎初昌。法嗣横枝,声传绝幕。大师还竺,辉生道场。”[13]此八句叙廓尔喀侵藏之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廓尔喀妄启边衅,侵扰后藏,相继攻占聂拉木、济咙。八月,班禅额尔德尼躲避锋芒,移退拉萨。九月,廓尔喀军队侵入扎什伦布,洗劫一空。清朝中央政府立即从各地抽调兵力,派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兵入藏,驱逐廓尔喀。五十七年五月,廓尔喀纳表称降并归还了在扎什伦布劫掠之物,班禅额尔德尼也从拉萨返回扎什伦布。赋中虽然堆砌了法济大师、六祖慧能、辨才等僧人的典故,但叙事脉络还是清楚完整的。
又如:“哲孟雄,臧曲之千家尚骇。”自注“后藏西南边外一小部落。其地今为廓尔喀所侵,尚有臧曲大河北岸迤东三处寨落也。”[13]哲孟雄即锡金。臧曲,也作藏曲,即提斯塔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干城章嘉峰的泽母冰川,流经印度、孟加拉,汇入贾木纳河。松筠《西招纪行诗》“廓番无敢前”自注:“帕克哩为藏地南门,保障西南,界连哲孟雄部落,其部人户无多,向与唐古忒通好。西有大河名藏曲,唐古忒依为险津要隘。先是河西原有哲孟雄所属人户,后经廓尔喀侵占,以河为界,盖因藏曲水深溜急,不能渡船,仅有索桥数绳,廓番无能逾越,是藏曲既为哲孟雄保障,又为帕克哩屏障。”[9]康熙三十九年(1700),廓尔喀军队入侵锡金,攻占锡金当时的首都拉达孜,锡金国王越境逃亡到西藏,在热日宗的春丕谷避难,作为宗主的达赖喇嘛将此地赐给他使用,这也就是后来的亚东。乾隆末年,清军驱逐廓尔喀后,锡金本欲收复其失土,由于不丹军队突然倒戈攻击锡金,锡金腹背受敌,结果锡金在提斯塔河谷地以西的大片领土仍然沦于廓尔喀之手,而提斯塔河谷地以东的领土则被不丹占领,锡金只保有提斯塔河上游的领土。“千家尚骇”四字,把哲孟雄遭廓尔喀入侵后的现状描写殆尽。
赋中所叙之“事”,往往都是一些片段,一些点画,远远称不上独立叙事,必须借助于史传等叙事文本的辅助才能勾勒出相对完整的一段“人生经验”。
五、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交错
视角“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20](P191)视角有全知、限知之别,全知是作者对作品中的人事、心理和命运拥有全知的权利和资格,并表现在作品叙事之中;限知则是作者在叙述事件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发展链条中出现了限定和隐藏,不作全景式表现。
《西藏赋》所要呈现的是西藏的历史现状、风土人情、山川河流等内容,全景式展示西藏的方方面面,因此和瑛采取了全知视角的叙事策略。开篇先写西藏地理方位,再写拉萨山川,再次写西藏宗教,随后陆续展开设官、治兵、人民疆域、风俗政令、物产、部落、山川等内容,展开了一幅西藏画卷。在具体描写中,也往往采取全知视角,如铺写疆域部分,从西部写起,依次交代其西南、南、东南、东、东北、北、西北之所有,如同扫描仪一般将西藏版图扫描一遍。铺写物产时,则是矿产、草、木、花、果、谷、蔬、禽、兽、鱼、虫等逐一描摹,一一图形,网络殆尽。
与总体上的全知视角不同,在处理细节、局部时,和瑛往往采用限知视角加以描写。如“五百余户之蒙古,驻自丹津;三十九族之吐蕃,分从青海”两句,只是说自丹津起驻扎有五百多户蒙古人,三十九族从青海划分而来,隐去了更多其他信息。赋中隐去的信息,在自注得以弥补,自注谓;“青海蒙古王于五辈达赖喇嘛时带领官兵赴藏护卫,留驻五百三十八户在达木地游牧。协领八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听驻藏大臣调遣。丹津,蒙古王之名也。”“那木称、巴延等处番民共七十九族。其地为吐蕃之旧属,居四川、西宁、西藏之间,昔为青海奴隶。自罗卜藏变乱之后,渐次招抚。雍正九年堪定界址,近西宁者四十族,归西宁都统管辖;近西藏者三十九族,归驻藏大臣管辖,设总百户、散百长,岁纳贡马银两。”[13]又如“乍丫多盗,桑艾为枭”两句,只是点名乍丫、桑艾两地的民风,其馀不再提及。自注则谓:“察木多东五百里,昔为阐教正副胡图克图掌管。康熙五十八年颁给印信,住持乍丫大寺。其地三山环偪,二水交腾,穷僻荒凉。其俗乐劫好斗,婚姻多不由礼。”“阿足塘东北江卡塘,正北名桑艾巴,番部,其人凶狠,好劫夺行旅,俗名夹坝云。”[13]补充说明了乍丫、桑艾两地的方位、自然环境等,更是对其民风作详细介绍,使读者了解其因果原委、来龙去脉。
《西藏赋》的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的视角,在局部上则多采取限知视角;在正文中多采取限知视角,在自注中多采取全知视角,呈现出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交错进行的态势。
六、空间方位叙事
在中国文化中有四方铺叙的传统,如“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的甲骨卜辞已经有了明确的四方铺叙,周易六十四卦也隐含了八方概念,而《山海经》的篇目安排更具有内外、四方的意识。这种按照一定的空间方位叙事的理念,既是观照外部世界的技术方式,也是描绘外部世界的艺术手段。[21]因此,当以铺陈为特点的赋体出现时,按照空间方位叙事也便成了赋体的重要谋篇手段。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谈作赋经验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22](P91)司马相如所云正是以空间方位为序来组织赋文的奥秘。李立曾统计《全汉赋》收录的赋家、赋作中,有23人42篇作品使用了空间方位叙事。[21]朱光潜在谈及诗赋区别时亦云:“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23](P203)抓住“空间”二字,区别诗赋,所言甚为独到。《西藏赋》传承了汉赋,特别是汉大赋的传统,其在运用空间方位叙事方面也是得汉赋真传。其空间叙事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方位叙事,按照一定的方位顺序,依次叙述。如:“乌斯旧号,拉萨今传。其阳则牛魔、僧格,搴云蔽天;札拉、罗布,俯麓环川。其阴则浪荡、色拉,精金韫其渊;根柏、洞噶,神螺现其巅。左脚孜而奔巴,仰青龙于角箕之宿;右登龙而聂党,伏白虎于奎觜之躔。”“人民疆域之殊也……其西……其西南……其南……其东南……其东……其东北……其北羊八井、噶勒丹、噶尔藏骨坌,乃青海属番之界;其西北克里野、纳克产、腾格里诺尔,乃达木游牧之场。左通准噶尔,西达叶尔羌也。”[13]“其部落……其西……其东……”其叙事顺序或阴阳,或左右,或四方,无一不是按照方位顺序,依次铺陈。其在叙述山川一节,虽无明确的方位词出现,但依然是自西向东,梯次铺陈,从最西端的冈底斯山和雅鲁藏布江说起,一路向西,述及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诸山川河流,方位顺序亦是清晰可见。
二是空间叙事,在不同的空间中轮流转换,包括历史空间和区域空间。历史空间中的转换如“乌斯旧号,拉萨今传”,“图伯特其旧名,唐古特其今号”等句,乌斯、拉萨,新旧对举;图伯特、唐古特古今轮换。区域空间的转换如开篇叙写拉萨山川,后文则又写阿里等地的山川;先写达赖之居于布达拉,次写班禅之居于扎什伦布,而写节庆佛事时又回到拉萨,回到布达拉,不同区域交错转换。
三是连类叙事,以空间方位为经,以类别为纬,方位与类别相结合,形成清晰明确的叙述脉络和层级板块结构,从而构成赋作基本的组图框架。[24](P147)整体上来说,《西藏赋》属于连类叙事,依次罗列,以类枚举宗教、设官、治兵、人民疆域、风俗政令、物产、部落、山川等内容。具体到细节上亦是采用类举罗列的方式叙事,如写西藏自然环境谓“风来阊阖,日跃虞渊。斗杓东偃,月竁西联”,从日、月、风、北斗等四个方面来说;写达赖居住在布达拉宫的生活情景,则说:“食则麦屑毡根,饮则鸠盘牛酪,衣则黄毳紫驼,居则彩甍丹雘。优钵净瓶,玉盂金杓。三旛比以离离,百玩灿其愕愕。”罗列了达赖生活中衣、食、居、用等类别。同时,在方位叙事、空间叙事过程中,以空间方位为序,所铺陈对象也往往是连类列举。以空间方位为序,连类列举,这是赋作铺陈的基本方式。
和瑛在《西藏赋》中娴熟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铺陈西藏风土人情,讴歌大一统,既有“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又有资政辅政的功能,相对于汉大赋而言,具有突破与超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