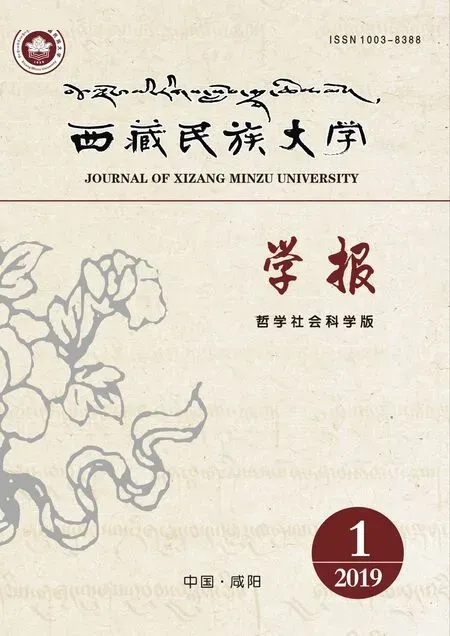试论改革开放40年来西藏城市的精神面貌及其特征
王 川,马正辉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城市的外部体现和内部构造,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城市之精神面貌。中国城市产生起源早,发展历程绵远流长,“十大古都”①和全国各地古代城市考古发现,向后人展示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人类聚居痕迹,及城市发展的漫长历史、灿烂的城市文化、不同的城市精神面貌。“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城市的发展过程又是文明积累、整合、传承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类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动力。’”[1]西藏作为中国版图上整体海拔最高的区域单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高原、民族、宗教”[2](P3)特征明显的城市。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城市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②,西藏城市加快发展,出现了城市群的雏形,城市精神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迄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总结本国不同城市发展经验教训的同时,不断借鉴和引入国外城市研究的经典理论与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发展建设提供参考。在整体中国城市史研究框架下,关于西藏城市史研究,较于东南沿海及内地城市的研究,明显薄弱③,这固然是由于西藏城市发展落后于内地及沿海城市等原因所致,但不能因此忽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城市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文试就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精神面貌做一分析,以更好地认识这一时期的西藏城市发展成就。城市是动态发展的,城市精神面貌更是随之而动态发展,且更多的是一种抽象存在。
一般认为,“塑造引领城市和人发展的城市精神是完善城镇化健康机理的表征”,因此,它表现了一座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建筑风格、形态格局等物质文化形态,还充分体现这个城市的市民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想情操等精神文化底蕴和未来图景。”[3]
1951年和平解放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地区城市的精神,是在“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等引导下,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及藏族自身传统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在吸收区外优秀文化的背景下,所凝聚而成的一种高原城市群精神外显,可归纳为三大特征:现代与传统的消长向渐趋融合发展、民族融合与宗教信仰自由契合共存、城市行政管理与市民自我管理的互补。
一、现代与传统的消长向渐趋融合发展
西藏城市在漫长历史时期的发展,缓慢而不平衡;城市发展更多受政治因素影响,政权中心及后来政教合一的政教中心容易发展为大小城市。整体而言,近代时期之前的西藏城市,在封建农奴制度下,主要服务对象是以“三大领主”为中心,服务设施单一,且数量较少。近代虽有十三世达赖“新政”改革,但受限于其所代表的阶级群体和历史的局限性,现代化城市并没有在西藏形成,现代化的因素对西藏传统城市并没有造成较大冲击。以近代拉萨为例,“新式藏军、警察、电灯、电话、电报等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因素在拉萨的兴起。但也要看到‘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较量,以及在等级森严的西藏地方,并非所有的拉萨人都可以享受‘现代’的内容,他们更多地是为上层人士服务的。”[4]作为当时地方首府的拉萨尚且如此,西藏其他城市现代化因素的影响之小可想而知。如有识者所指出的:“在西藏,现代意义的城镇,是在和平解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5]“从城市社会的性质而言,已经从代表着社会上层利益的封建城市向代表全体藏族民众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转变,从传统的农牧社会城市向现代化城市转化。”[6]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西藏城市得以迅速现代化,同时,现代化的涌入并未完全替代在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西藏城市传统因素,现代与传统在相互碰撞中,渐趋融合。这一特点,在建筑、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一)建筑方面
在西藏传统文化中,寺院经堂、宫殿建筑,“无疑是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7](P1569)西藏城市的发展与藏传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多数城市围绕大的寺院、宗山而形成并发展,在传统城市建设中,寺院建筑最为富丽堂皇,成为传统西藏城市中最为明显的城市标志。进入共和国时期,现代化的建筑随着解放军部分机关单位的设立,而逐渐成为新的城市建筑风格体现。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大规模援藏工程,更是明显改变了西藏城市的建筑格局。
现代化建筑在西藏聚集,与传统的寺院为主的建筑共存。“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更具有了科学性,在城市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老城区、传统建筑文化和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8](P20)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城市建筑特色方面,一些传统的优秀建筑文化并未被丢弃,现代化过程中的西藏城市建筑充分将两者融合。拉萨八廓街、昌都昌庆街、林芝巴宜区等地,城市在新建开发或修缮维护方面,非常注重二者的兼顾。但在未来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目前的经验与作法,应该是必须坚持,以便更好地协调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避免将西藏城市带入“千城一面”之困局。
(二)物质生活
千百年来,青藏高原居民以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为主食。民国时期,内地与西藏之间交流频繁,蔬菜等多种内地物产大量传入西藏[9]。而真正从根本上改变高原上物质生活品种单一、供需失衡的状况则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这是随着川藏、青藏、滇藏、新藏公路的渐次开通及青藏铁路的铺设运营和通往内地与国际航线的开通,“天上西藏”与外界沟通“天堑变通途”,西藏与内地的双向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是来自祖国内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极大地满足了西藏城市居民对于各项物质生活的需求,使得传统物质需求与现代物质需求能够自由选择,并逐渐融合。同时在国家大力开发西藏和培养西藏本土人才的政策支撑下,在西藏地方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各援藏省市无私提供物质、资金、技术、人才的背景下,西藏自我生产、自我满足能力大幅提高,并且将产品销售于内地及出口到欧洲、北美,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饮食服饰与文化艺术
在旧西藏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西藏人而言,饮食和服饰的丰富与充足是很难实现的,一切社会生产资料和资源集中在“三大领主”手中。对此,谭·戈伦夫做了中肯的阐述:“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绝不是‘令人羡慕的’,他们住在‘矮小的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吃的是糌粑、酥油和茶,如果幸运的话,就能吃上一点肉。由于营养不足,生产率低下已经成了一个问题。”[10](P12)及至清末民初,西藏开始出现早期现代化改革,“在服饰、饮食、交通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物质生活出现了现代性的要素。”[2](P530)这一点不可否认,随着英国的入侵及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客观上为古老的西藏注入了一些“现代化的要素”,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些“现代化的要素”是以服务西藏上层为主的,普通居民既无财力更无渠道去享受这些“现代化的要素”。
进入共和国时期,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物质生活逐渐满足,饮食服饰文化在西藏城市居民生活中呈现多样化特征。在精神需求方面,大量现代文化艺术形式与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相融合,共同服务于西藏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如唐卡、藏戏、热巴、弦子等西藏传统艺术形式在民主新西藏的沃土上推陈出新,以蓬勃健康的发展态势服务于西藏人民文化生活。西藏城市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大量本民族艺术工作者成长起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开始建设既是民族的,又是开放的、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既有主体又有多样化的民族新文化。”[11](P369)
二、民族融合与宗教信仰自由契合共存
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西藏是全国藏族居民最集中的地区,人口占95%以上。此外,还包括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怒族、纳西族等民族和僜人、夏尔巴人。④多民族在此聚居,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共存。民族融合与宗教信仰自由在西藏这一多民族、多宗教汇集之地显得极为重要。在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否不打折扣地体现国家《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精神,能否毫不动摇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写入国家《宗教事务条例》,并在《十七条协议》之“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院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明文规定的中央对藏宗教、民族政策,是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是否与西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西藏居民生活、生产相适应,直接影响其城市的稳定,影响国防安全。
纵观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西藏城市的发展历程,党和国家、西藏自治区政府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非常成功,适合中国国情,适合西藏自治区区情,适合西藏城市的发展。成为西藏城市发展精神的一种重要体现,即“民族融合与宗教信仰自由契合共存”。民族融合与宗教信仰自由是西藏城市发展中,区域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融合
顾颉刚于1939年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12]概念后,在当时及后来引发了诸学科学界的大讨论。顾颉刚提出这一理论的背景,固然是他在抗战背景下对民族分裂潜在危机的担忧⑤。而经过抗日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深入民心,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认知。然而在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的各民族之间,是和平与战争相间,以统一为常态,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历史。《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时指出:“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⑥
因此,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是城市内多民族共同合力下的结果。今天西藏城市建设的巨大成绩有其城市内诸民族的巨大贡献,城市建设的成果亦为西藏城市内各民族共享。
(二)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地区民族众多,不同民族多信仰不同宗教,如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等;同一民族内部也会有不同的信仰。西藏的这种宗教信仰格局是在历史时期形成的,并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西藏城市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宗教的影响,其中又以藏传佛教对西藏城市发展影响最大。有学者以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前弘期、后弘期的多座著名寺庙为实例,归纳了西藏寺庙与城市之间衍生出的四种关系:“以寺为中心发展成城;寺庙与城市合二为一,成为区域的政教中心;‘三位一体’的城市格局;寺庙建于城市远郊。”[13]西藏城市发展史上,寺院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影响颇大,围绕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居民大规模聚集,城市基础设施逐渐完备;围绕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形成的日喀则早期城市等。这种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寺院本身作为“三大领主”之一,占有大量生产资料、财富,并将大量劳动力吸收到寺院内有关。同时,它也必然导致劳动力不足等消极影响,限制了西藏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六十多年的磨合与实践,“保障思想、信仰层面的自由,对于国家公民有尊严地生存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宗教信仰自由也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切实保障。”[14]这在西藏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在现今的新西藏,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获得了法律保护,西藏人民真正得到了自己选择信仰的自由。展望未来,西藏城市内法制化框架中宗教信仰自由的健康发展,将会继续服务于西藏城市发展。
三、城市行政管理与市民自我管理的互补
城市发展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城市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要有长远战略布局和持续性的科学管理,同时,城市是人类群体聚居地所在,所以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居于斯地人类群体的共同维护。“清代至民国时期是西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传统西藏与现代西藏的连接点和转折点,它被同时赋予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因素,是西藏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2](绪论P2)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虽然成效较小,但毕竟为西藏注入了一定的现代化因素,“噶厦”新设立的一些政府部门,如“巴细列空”⑦、“扎什电列空”⑧、藏医历算院、邮政局、电信局、水电厂、警察局等或为行政管理部门,或为社会服务部门。它们的出现使得西藏城市行政管理能力和城市功能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作为城市的组成主体,最大多数西藏城市市民并未成为城市的主人,共同参与城市管理,更多的是附属于西藏的三大领主,城市行政管理既没有能力也没形成一种系统的管理模式。直至1959年平息叛乱、民主改革,中央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宣布撤销原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成立相应的政府部门,才开启了西藏现代化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新纪元。西藏现代城市管理开始探索一种规范化、系统化及全体市民作为主体参与并维护西藏城市管理的新格局,即市民自我管理的模式。西藏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政府行政管理与市民自我管理互补的良好发展阶段,使得西藏真正成为“天上人间”,向世人呈现出“天上西藏,大美于行”的现代化高原城市群特征。
(一)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与能力双增长
1959年平叛后,西藏人民获得了管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权利与义务。1951年和平解放后,西藏人民“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才是自己的亲人,才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15](P242)在对比中,西藏人民迎来了民主改革,迎来了真正做西藏主人、做国家主人的历史转折,西藏城市建设进入一种全新的,以西藏人民需求为导向,以国家国防安全⑨为战略考量的新时期。]西藏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开始系统、全面地建立,并大力培养西藏民族干部,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能力。
同时,全国一盘棋思维下的援藏政策对西藏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逐渐显现。对口援藏政策“规模不断扩大”“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援助的结对关系不断稳定”[16]。其中主要从1994年以后的援藏工作以“干部支援为主”[16],包括大量有内地城市建设管理经验的专门人才,内地的城建部门也直接对口西藏城市,这对于规范西藏城市管理体制、提高管理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培养西藏地区的城市管理人才提供了持续性技术支撑。
(二)市民自我管理意识逐渐形成,并向常态化转变
现代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体,既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城市优质生产、生活设施资源及城市发展红利的受惠者,同时市民也应该是城市文明的维护者,是城市精神的代言人。在旧西藏,城市的管理权归于“三大领主”,普通市民作为建设者却难以享有与建设贡献相匹配的城市待遇,参与城市管理更无从提起。进入社会主义新西藏,西藏市民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参与城市建设,享有城市文明的便利,参与城市管理。
在城市现代化大背景下,西藏城市市民构成逐渐多元化,市民数量逐年攀升,“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基础建设的扩张,青藏铁路的通车,以及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藏区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以劳工、技术人员、服务行业从业者、旅游者为主的大量外来人口(以汉人和回民为主)进入藏区。”[17](P130-131)但这种形式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拉萨、日喀则等交通便利,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心城市,且集中于夏秋两季,“并未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改变基本的人口构成。”[17](P131)
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一定时期、一定数量下,有益于城市发展,但也增加了城市管理的复杂程度。这就需要城市居民(包括流动人口)树立自觉参与城市管理,维护城市良好精神风貌的意识。随着西藏城市市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市民自我管理、参与城市管理、维护城市良好精神风貌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
四、结 语
近代以来西藏城市的发展,城市精神面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前所未有。西藏城市市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持续革新,物质精神生活不断满足且丰富,提高了城市的宜居度,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居住幸福指数;愈益和谐共存的民族、宗教关系,成为西藏城市社会稳定的保障,各族市民团结到了社会主义城市现代化文明建设的远景目标下而共同努力;科学、规范、系统、可持续的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与城市居民自我管理、参与城市管理意识的树立和增强互为补充,为西藏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和群众基础。
这种发展态势并未停止,而是仍以蓬勃的生机不断助力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交通环境极大改善和国家政策持续大力支持下,西藏自治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全国援藏省市单位持续、多模式、以“造血”为导向的新型援藏体系建立的大环境下,西藏城市精神面貌日新月异。以大、中、小各级城市为点,将整个西藏地区社会经济联成一个动态的发展整体,现代西藏城市给世人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而愈发引人神往的魅力,并将一直动态、健康、持续发展向未来。
在目前发展的辉煌成就下,西藏城市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继续提升必须面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困境与瓶颈。
其一,传统建筑和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现代化的大规模冲击,民族、地区的建筑特色体现偏弱,有陷入“千城一面”困境的担忧。
西藏城市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建筑文化和高原城市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已落后于时代的因素,限制西藏城市的发展,影响城市市民对更好城市生活的体验。但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是千百年来,西藏人民适应自然、发展民族文化过程中自然形成,自我选择的最优结果,是一种客观的历史遗产和财富。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牧区及区外人口涌入西藏城市,势必会推动城市在空间和布局上的改变,如何满足原有居民与新增人口之间共同的空间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
此外,城市不仅仅是高楼大厦,柏油马路,对于西藏这样有着浓郁宗教文化、高原文化、民族文化的区域,城市应该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其魅力之所在。城市不仅应该有钢筋混凝土的堆砌,这只是文明的外壳,“它还应该有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城市精神”[18],以及西藏诸城市之间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色,如昌都的“卡若文化”、汉藏茶马古道枢纽所蕴藏的茶马文化即为其他城市所无,故而应该借此类文化塑造城市灵魂,打造城市精神。
其二,区域发展不协调日益加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发展动力源单一,现代化的城市管理还有待完善。
西藏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较之祖国东中部差距明显,西藏至今仍有阿里未达到“市”级标准,尚为“地区”;那曲在2018年才撤地设市。同时,西藏城市内部诸城市也是动态发展的,大城市如拉萨,更多的是中小城市,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且因拉萨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发展势必会走在最前列,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这其中有资源分配的差异,也有交通环境的差异,更有城市管理水平的差异。同时,在中国目前“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趋势下,西藏城乡二元结构依旧矛盾突出,应向“城乡统筹发展”,农牧区统筹发展,到农牧区支撑城市繁荣,城市反哺农牧区发展的良性互动转变。
西藏现代化城市管理体制之建立,在时间上晚于祖国内地,且需要处理好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西藏城市的管理体制,也一直在摸索之中,可以说,尚未最终形成一种完备的城市管理体制。“在我国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推动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式,二是自下而上式。”[19]东中部相对成熟的投资环境和活跃的市场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部门作为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和宏观调控者引导、参与城市健康良性发展;而西藏城市则相反,内部经济动力相对较弱,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这样就会导致政府大量资金不得不更加偏向城市,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
处理好上述两个方面的困境与瓶颈,相信在新时代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与奋斗下,在国内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西藏城市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城市的精神面貌将继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注 释]
①2016年10月,中国古都学会主办的“成都古都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致通过了
《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形成包括此前认定的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大同及本次会议所认定的成都之中国“十大古都”格局。
②直至和平解放以前,西藏“全区城镇几乎没有现代化建筑和现代化设施。解放初期,大规模地建设城镇和改造城镇的条件还不具备……民主改革以后,拉萨市人民政府和各地行政公署相继成立,城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及住宅建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化城镇雏形……‘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城镇建设比较混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城镇建设发展较快。”(《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西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4月,下册,第271页)
③近年来,西藏城市社会经济研究也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尤以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何一民教授为首席专家而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研究”已经聚集一批致力于西藏现当代城市史研究的专业研究队伍,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何一民教授团队此前所进行的“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项目,已对限定时间内西藏城市历史时期整体情况做了系统研究。此外,关于西藏城市研究,还有部分“单体城市”研究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研究成果。
④《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4月,第25页。至2017年,西藏人口已达310万人,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33名。(《中国地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8年1月)⑤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载《“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3页。转引自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西藏百年史研究》(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14页。
⑦财源调查办事处,又译作军粮局。
⑧为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近代工业企业的部门和地方财政来源的金融机构。
⑨“西藏的城市发展一直处于缓慢的进程中,城市体系发育迟缓,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形态不完善、分布极不平衡。然而,自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中央管辖,特别是清代以来,城市却发挥了重要的“固边强区”作用。”(何一民:《略论清代以来西藏城市的历史地位》,《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