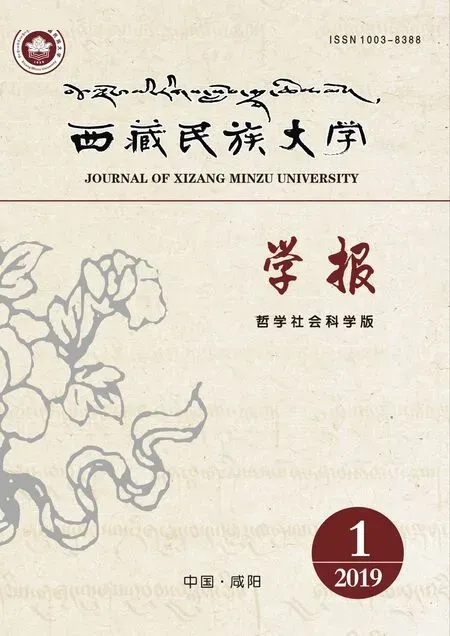清代西藏地方志的撰修、类型及特点
杨学东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清朝建立后,基于开拓疆土及有效管理的需要,大力提倡各地撰修地方志。清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无论数量与质量都超越前代。西藏地处青藏高原,与内地往来交通不便,在地方志修撰方面要比内地逊色很多。在内地方志发展进入高潮之时,西藏地方志才开始产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合目录》)统计,撰修于1949年以前的西藏地方志计48种。其中,清代撰修17种,民国撰修31种。①然而,《联合目录》所收西藏地方志并不完全,今人曾做过一些补遗工作:赵心愚补遗10种,[1](P343)刘凤强补遗1种。[2]这11种均为清代西藏地方志。这样,《联合目录》著录的17种加上补遗的11种,目前所见清代西藏地方志共有28种②。就编撰质量来说,民国所修西藏地方志远不如清代高。
清代西藏地方志是中国清代地方志的一部分,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发生、发展、类型及特点与内地方志相比又有许多不同。目前有关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个案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成果,但将西藏地方志作为整体进行的考察则相对薄弱。本文旨在梳理清修西藏地方志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其特点。
一、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修撰
考察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全过程,可以看出其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初始期、快速发展期、发展缓慢期以及再度发展期。如此划分,是基于西藏地方志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独特阶段性:快速发展期与再度发展期是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的两个高峰,产生的方志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其余两个时期则为发展相对缓慢的低谷,产生的方志数量少,影响也不大。
(一)初始期:雍正至乾隆初期
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应为成书于雍正初年李凤彩的《藏纪概》。该志除了记进藏途程,还有“天异”“土则”“附国”“种类”“产作”及“招迹”等内容,涉及西藏的气候、地理、物产、风俗等各方面。虽然该志类目设置与内容均较简略,却对后来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与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等志书的编撰产生了一定影响。
《藏纪概》是私人修撰最早的清代西藏地方志,成书于雍正十三年的《四川通志·西域志》则是官方修撰最早的清代西藏地方志。《四川通志》之“西域志”其实就是“西藏志”。虽然将打箭炉、里塘、巴塘等地也纳入,但主要记今西藏地区。“西域志”尽管存在于《四川通志》之中,体例尚欠完备,内容也显简略,但开创了清代官方修撰西藏地方志的先河。
成书于乾隆元年的《西域全书》可以说是“清代西藏第一部成熟的方志”。[3](P149)该志根据传统方志的编写方法,首列以图,再述史实,继之介绍山川、物产、风俗等。不仅介绍西藏一域,还涉及各条进藏路线、台站粮务以及从拉萨到各边隘的路程。由于该志成书较早,体例完善,内容丰富,在汉文藏学文献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西域全书》之前,具有西藏方志性质的仅有《藏纪概》一书。但《藏纪概》内容简略,体例不纯,在清代西藏方志方面虽有开创之功,却有很大局限性。相比于《藏纪概》,《西域全书》不仅类目划分更加详明,内容也更为广泛细致。与同一时期的《四川通志·西域志》相比,《西域全书》记载的内容也更全面,有些类目如“人物图形”“文书征调”等为《四川通志·西域志》所无。且《四川通志·西域志》撰修于成都,因作者对西藏情况了解甚少,有些类目下的内容过于简单。而《西域全书》作者久居藏地,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无论是记述的丰富性还是可靠性都远非《四川通志·西域志》可比。书成流传后,很快在当时入藏人员中产生了影响,其内容被同样成书于乾隆初年的《西藏志考》《西藏志》等传抄,致使各方志内容重复性很高。
初始期是西藏地方志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产生的方志数量不多,只有5部,体例不够完善,内容亦稍嫌简略,只是粗具地方志的特征,但对后来西藏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快速发展期:乾隆初至嘉庆时期
在前一阶段几部方志的影响下,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西藏记述》《西藏见闻录》、乾隆《西宁府新志·西藏》《西藏记》及《西域遗闻》等一批西藏地方志先后出现。这些方志或模仿前几种志书的体例,或从中大量选取材料,但创新不多。乾隆末年,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的出现标志着西藏地方志发展的巨大进步。
该志突出了图在方志中的地位。乾隆初年的《西域全书》已经列有地图及人物像,但所绘地图非常简略,史学价值并不高。《卫藏图识》所列地图、人物像较《西域全书》有了较大发展。全书共列出10幅地图,18幅人物像,地图部分标注地名已经非常详细,人物像部分有些并不见于《皇清职贡图》,可补其缺。这些内容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另,该书很多类目前都有一小序,叙类目设置的缘由,言简意赅。这是较以往西藏志书在体例上进步的地方。
在乾隆时期发展基础上,西藏地方志于嘉庆时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出现了《卫藏通志》《西藏赋》《西招图略》以及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等多种方志,其中《西招图略》与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对其后西藏地方志的编撰影响较大。《西招图略》作者松筠作为驻藏大臣,留意总结治藏经验,于巡边之际,绘制地图,记述边地形势、关隘要塞。该书刊行后,不仅对其后驻藏官员安边、守边和清代西藏方志的编纂产生了影响,还对民国西藏方志的编纂和研究西藏问题产生了积极作用。民国陈观浔《西藏志·西藏关隘考》几乎全部抄录《西招图略》“审隘”条的内容。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较之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其记述的内容更为全面、详细。它将西藏分为“前藏”“江孜”“后藏”“定日”“阿里”等五个地区分别记述,专门设立“后藏”篇目与“前藏”并列记载,纠正了以前的失误,反映了清中期时人对西藏认识进一步深化。体例方面,嘉庆《西域志》新设“国朝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西域职官忠节”“西域蕃酋”“西域喇嘛”等五部分,以内地方志惯用的“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载自唐代以来汉藏重要人物的活动,扩大了方志记述的内容。不仅为雍正朝《四川通志·西域志》所无,在西藏方志史上也属首例,是对西藏地方志的创新。
乾嘉时期共产生西藏地方志12种,不仅数量多,质量相对也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乾隆皇帝本人十分重视修志事业,在位期间继续修纂一统志,推动了全国各地志书的修纂。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与乾隆前期准噶尔的威胁仍然存在和乾隆后期廓尔喀侵藏及对西藏的威胁有关。”[1](P11)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败亡后,准噶尔的威胁才算彻底解除。反映在地方志的编纂上,乾隆十九年以前一共产生了《西域遗闻》等6种西藏地方志。此后一段时间里则没有新的西藏地方志出现。及至乾隆末期,廓尔喀侵入西藏,清军再次入藏戡乱,“内地又涌起研究西藏史地文化的热潮”[4]新的西藏地方志著作又不断出现,一直持续到嘉庆中期。
(三)发展缓慢期:道光至同治时期
经过乾嘉时期的快速发展,至道光年间,西藏地方志发展放缓,不仅新出方志数量少,也未产生有影响力的方志著作。郑光祖《西藏纪闻》、管庭芬《西藏记闻》均为辑前一时期西藏地方志中的材料而成,没有新的材料,体例也无创新。李梦皋《拉萨厅志》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唯一的一部厅志,由于记载过于简略,反不如《西藏志》对拉萨地区记载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两次刻印松筠《西招图略》,说明此书在后世的影响力。道光之后,咸丰、同治几十年间,西藏地方志既无新出,也未重刻。
(四)再度发展期:光绪至宣统时期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光绪、宣统时期西藏地方志又恢复了发展。光绪十二年成书刊行的《西藏图考》是晚清一部重要的地方志,是从传统文献向近代著作转变的作品。
此书第一个特点就是将古今有关西藏的地形地貌、山川河道、交通道路加以融会贯通,择善而从,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藏区地理志。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借鉴了诸多西藏地图的优点,又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以全新的计里开方的方法绘制出前所未有的西藏全图。较之《卫藏图识》《西藏图说》之地图不标经纬甚至比例尺也不标明是一个明显进步。该志重视西藏战略地位,针对英国侵藏野心,关注西藏南部的边防险要,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初刻之后,仅光绪年间就翻刻过三次以上。《西藏图考》既是传统西藏方志的一次总结,同时也开启了西藏新方志的编纂,在西藏方志编纂史上是传统与近代的分水岭,是继往开来之作。
除此之外,此一时期还有《卫藏图识》《西藏记述》以及《雅州府志·西域志》的补刻与重刻。宣统三年间,又相继出现了《杂瑜地理》《门空图说》《乍丫图说》及《西藏新志》等多部地方志。其中,《西藏新志》体例为章节体,而且不少材料直接采自国外相关文献,反映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这一时期共产生了10种西藏地方志,数量较多,质量也佳。究其原因,与西方势力侵藏密切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俄加紧了对西藏的争夺,加之驻藏大臣腐败无能,致使西藏问题日益严峻。一批有志学者投入到西藏史地的研究中,就如何筹边、加强西藏地区的防卫等纷纷建言献策。如《西藏图考·序》多次提到英圭黎,英圭黎即英国。指出“今日之藏卫,其关系中外利害数倍于昔。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之急务也。”[5]此语道出了黄沛翘编撰《西藏图考》的目的。不仅《西藏图考》,《杂瑜地理》《门空图说》《乍丫图说》等的编撰也莫不如此,都是有为而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类别与特点
就内地方志而言,居于主流地位的是各基层政权所修府志、州志、县志,且基本由官方主持撰修,私撰志书比例很小,只是作为官修方志的有益补充。西藏地方志则不然,通志多而府县志少且通志多为私撰是其重要特色。
(一)通志多府县志少
与内地省份不同,西藏的府志、县志极少,这与其长期以来的藩属地位有很大关系。元代,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元中央设宣政院,总领全国佛教及西藏地方事务。在藏区设立3个互不统摄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再辖13个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及若干千户所。明朝基本沿袭元朝的划置方式,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甘青川藏区、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指挥使司及军民元帅府下再实行宗本(相当于县长)制,划西藏为13个大宗进行管理。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统领西藏地方行政。此外,继续设置数十个宗溪(相当于县级设置)管理西藏地区。有清一代,西藏不曾设立行省,更没有建立起府县制。只是在历史上曾属西藏辖区一部分的东藏(西康)地区,出现了个别府县制地区。清末,赵尔丰被委派进入川边,并在川、滇、藏交界地带成立川边特区,把清朝时期赏给西藏的察木多、察隅、乍丫等地纷纷收归,实施改土归流,设县任官,将这些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些地区也成为后来西康省的一部分。
清代西藏的这种行政建置,自然影响到了与其关系密切的地方志的编纂。西藏地方志中,府县志只有《拉萨厅志》《乍丫图说》《杂瑜地理》及《门空图说》等4种。这4种方志,除《拉萨厅志》疑为伪作外③,其余3种均出现于东藏(西康)地区。而其余23种皆为通志,通记西藏全域的情况。
(二)官修少私撰多
除了《西藏志》《西藏记》、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乾隆《西宁府新志·西藏》《卫藏通志》、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等7种为官修外,其余21种皆为私人编撰,私撰比例极高,这与“清代大部分方志属官修”[6]的内地恰恰相反。这些私撰藏志的作者多为随军进藏人员、入藏公务人员以及驻藏大员,他们有感于对西藏史地知识的欠缺,于是有意识地编撰图籍,记录西藏的地理、历史、民情等,以供行军、治藏之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将这些著作视为西藏地方志,当时作者或许并不这样认为。萧腾麟在《西藏见闻录》自序中谈了他搜集材料与撰写此书的经过:“凡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躬之所践履者,辄笔之于纸,以志无忘。”[7](P1)萧腾麟写作此书也许是为了纪念在察木多五年督理台站的难忘经历。又如,《西招图略·序》称,“因书二十有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其方舆,名之曰《西招图略》,庶便于交代以口述之未尽者。”[8](P2)作为驻藏大臣,松筠编撰此书是为了将来就如何安边、固边等事宜向上级述职之用。再如,《卫藏图识》作者在凡例中明确指出“俾从军者便于检阅”,“未敢妄附志书之例”[9](P22),作者希望编撰该书能有助于行军,但不敢声称是方志之作。另外,从这些方志的命名上也可以看出些端倪。内地方志无论官修还是私修,基本上是以“通志”冠于“省”之上或以“志”冠以“府、县”之上的方式命名,如《河南通志》《曲阜县志》等,较为整齐划一。西藏地方志除个别官修志书称“通志”“志”外,绝大多数称名都比较自由,如“纪概”“记 述”“见闻录”“考”“记”“遗闻”“图说”“图略”“图识”“全书”等等,各有千秋。如果不是为了避嫌④,那就是作者本人并没有将其视为方志。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清代西藏地方志全部由内地学者编撰。藏族学者也曾编撰类似于地方志的著作,主要是寺庙志、佛塔志、地理志及朝圣行路指南[3](P92),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类志书在记录地方史料广度方面较内地传统地方志逊色很多。西藏自元代起就纳入中央的管辖下,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西藏之于统一的中华帝国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首先需要知悉西藏的地理、历史、民情等情况。藏族学者只是致力于与佛教相关专志的编撰,将西藏看作一个整体从大一统全局出发全面记录西藏的任务,只能由内地学者来完成。
(三)军事色彩深厚
首部西藏地方志《藏纪概》的产生即与清廷用兵西藏有关,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所经历的两次高峰,也正值西藏的多事之秋。可见,藏事起则藏志出。西藏地方志的发生、发展与西藏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西藏地方志的军事色彩还体现在作者成分与类目设置上。首先,方志的编撰者基本上是随军进藏人员、长期活动于进藏路途及台站粮务官员以及驻藏大臣。如《藏纪概》作者李凤彩康熙末年随从山东登州总兵李麟护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由塔尔寺进藏。《西藏见闻录》作者萧腾麟乾隆初年统领官兵驻守察木多,督理西藏台站,前后历五年。《西藏图说》与《西招图略》的作者松筠乾隆末年出任驻藏大臣,前后亦五年,后又出任伊犁将军。他不仅治边有方,也留意编撰边疆文献。这些人于公务之余,记录在藏经历见闻,甚至有条件对西藏史地做长期考察。其次,方志类目的设置最能体现军事色彩。很多西藏地方志都设有“程站”“粮台”这一类目。自内地进入西藏的路线,有南北三路:由青海西宁入藏、自四川成都入藏、从云南昆明入藏。“程站”所记为清军入藏沿途所设驿站,并标明各站点间里程以及山川形势特点,“粮台”所记为清军入藏途中所设粮草补给站。这些类目的设置都反映着现实的军事目的。此外,像“兵制”“设隘边防”“镇抚”等类目所记更是与军事活动直接相关。
(四)大多属于简志
与内地方志相比,西藏地方志总体上都比较简略。表现之一是卷数基本很少。内地方志少则十数卷,多则上百卷,而西藏地方志卷数最多的《卫藏通志》也仅16卷,卷数最少的只有1卷,且这一类简志数量最多,几乎占到全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一半,其余则2至8卷不等。表现之二是大多采用平目体。除《西藏新志》采用章节体外,西藏地方志基本上都是平目体。这种结构形式将志书内容分为若干类目,各类目间平行独立,互不统摄。平目体是一种不成书的篇目形式,因其结构简单,比较适合内容单一、字数较少的志书。宋元以前应用较为普遍,直至清初仍较为流行,此后这类体式逐渐减少。西藏地方志普遍采用平目体,与其卷数大都很少密切相关。
西藏地方志的主体是私修志书,而私人修志受制于财力、人力,在材料搜集与编撰质量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张之浚为《西域遗闻》所作序曾转述作者陈克绳所言云:“此余转馕时,所身历之途,目击之事,于风饕雪虐中,呵冻手录者。”[10](P1)以“呵冻手录”方式搜集的材料必然是杂乱零散的,不成系统,这个特点也直接决定了此书的体例只能选择平目体,而不适合讲求首尾贯通的纲目体。相较而言,官修西藏地方志因为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支持,就有可能搜罗更为全面、详细的材料,编出的志书质量也有保证,《卫藏通志》就是明证。
[注 释]
①民国所修31种西藏地方志中,刘赞廷以一人之力修了17种,且皆为县志。
②本文所讨论的西藏地方志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通记西藏全境的方志,这是主体。二是毗邻西藏的青海、四川等地的方志涉及西藏的部分,如《西宁府新志·西藏》《四川通志·西域志》等;三是清代曾属于西藏后又脱离出去的地区的方志,如《乍丫图说》《杂瑜地理》及《门空图说》。
③关于《拉萨厅志》为伪作的讨论可参考赵心愚《道光<拉萨厅志·杂记>的有关问题及作伪证据》(《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1期),房建昌《伪造的吴丰培先生所藏<道光拉萨厅志>手抄本》(《西藏研究》2010年6期)二文。
④清代统治者一方面倡导修撰地方志,另一方面又对各地方志严加审查。乾隆三十一年,还诏令严禁私修志书。由于文网严密,文字狱盛行,“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