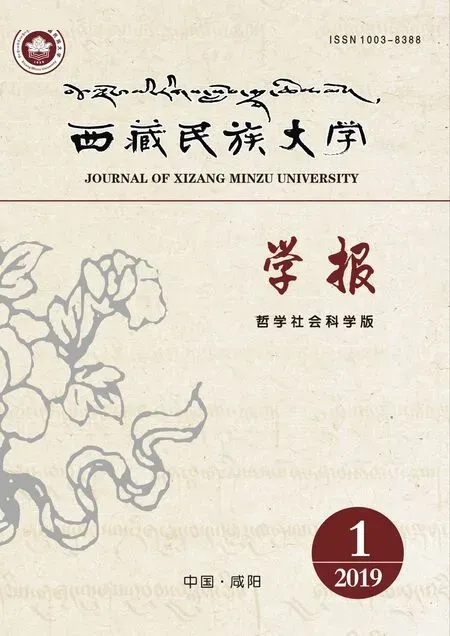从历史交通路线看唐代吐蕃与南诏的关系
李晨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唐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原政权的扩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原文化对周边区域的影响逐渐加深。同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本地文化,其中的一些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性政权并向周边拓展自己的影响,发生了族群间的互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吐蕃和南诏是唐代在中国西南地区崛起的两大少数民族政权,各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除了与唐朝中原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外,吐蕃和南诏也曾有长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考察吐蕃与南诏的交通道路入手,借助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探讨唐代两地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
一、吐蕃与南诏的交通路线与政治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吐蕃通往南诏的交通路线有东道和西道两条。东道自藏东的昌都至云南大理,但是对昌都往南入滇道路的具体走向存在争议:一说由中甸渡金沙江至剑川,如《云南志》的校释者赵吕甫;一说经维西直接到剑川而不过金沙江,如《唐代交通图考》的作者严耕望。这两种看法分歧的关键在于确定历史记载中“神川铁桥”的位置。唐人樊绰说:“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1](P232)吐蕃军队进入滇西北后,曾在此设置神川都督府作为统治中心。史载公元787年南诏攻取吐蕃铁桥以东16城,擒其王5人,降民众10万余口,可见当时吐蕃对神川都督府的苦心经营。既然如此,那么铁桥城一定是吐蕃通往南诏交通道路的要冲,只要确定了它的位置,自然就可以明确东道的走向。
神川铁桥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历来说法有异。严耕望认为铁桥在剑川以北3日程,约在今丽江西北400余里,虽然靠近金沙江,但并不过金沙江干流,有可能横跨的是她的一条支流,因为“若渡金沙江至中甸地区,则该区山最高峻,恐非大道所宜”,而“剑川向北有大道循金沙江西岸至巨甸,乃离开金沙江河谷,折而西北经维西,再循澜沧江东岸北行入西康境。”[2](P1271-1274)他坚持认为,吐蕃入滇是经维西直接到剑川,并不过金沙江。但是横断山脉为南北走向,虽有高山峻岭阻隔,在两山之间的河谷地带往往是宽阔的平川,吐蕃的军队当时就是沿着这些河谷一路南下。再则史载吐蕃铁桥以东的16城中相当一部分在云南中甸。可见这里是吐蕃政治经营的中心,也是交通的必经之路。
赵吕甫说铁桥遗址在“在今丽江县塔城公社塔城村北四里许之金沙江岸,东西两铁桥城,大抵分立于金沙江渡口东西两岸,为守护铁桥而设。”[1](P233)支撑他这个观点的还有对“神川”词源的考察,“神川”是藏语“腊普”的意译,就是指塔城。[3]实地考古证据也认定铁桥遗址在丽江塔城关下的塔城村,下游不远处金沙江中的笔架石就是固定铁桥的地方。其东岸的石梯与平台是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应曾经建有吐蕃铁桥城堡的军事设施。东岸往北的石门关和结布崖亦为通向南诏军事设施的设置处。[4]由此可见,唐代吐蕃通南诏的东道确实应由中甸渡金沙江至剑川。
铁桥城是吐蕃在滇西北统治的中心区域,曾设有神川都督府,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迪庆、丽江、兰坪、剑川、鹤庆及四川盐源一带,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族群被称为磨些蛮、施蛮和顺蛮。1992年初在云南丽江金庄区格子村的金沙江边发现了一块古藏文石碑,碑文载“洱海腹地之弄部的首领,最初,唐朝由百姓委任管民官。因与长官不睦,衷心亲近于赞普神子,向大臣结桑顶礼因男告身铜的国多赐大金告身。弄部首领自被享赐最诰告身后,享年九十岁时寿终于坟墓。”大臣桑杰是吐蕃任命的神川都督兵马使,为吐蕃在滇西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告身原本是吐蕃官员等级标志。碑文反映了吐蕃设立神川都督府后对归顺的部落予以赏赐,分授官职,推行军政制度的历史事实。经初步考证,此碑与金沙江铁桥遗址属同一时代,都是吐蕃统治滇西北地区的遗留物。[5]
由铁桥城向南至剑川,就到了神川都督府的南境。在唐代剑川是吐蕃与南诏的交汇处,彼此的势力在这里数度进退消长,加上唐政府的介入,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剑川城周边居住着所谓“三浪”部落:浪穹,邓赕和施浪。最初“三浪”在龙首关以北居住,南诏首领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兼并五诏,这些部落被迫北迁,浪穹诏“退保剑川”,邓赕诏“退居野共川”,施浪诏“归于剑川”,纷纷降服吐蕃。[1](P104-105)他们在吐蕃的庇护下仍保存了相当的实力,继续与南诏对抗。公元794年南诏进攻剑川和野共川,控制了三浪部落,设置剑川节度。
由剑川向南入龙口城就进入西洱河地区,这是南诏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本土后开始向外扩展。公元678年吐蕃大相悉若多布帅兵攻打西洱河,降服诸“蛮部”,应该就是沿着上述线路经剑川而来。苍山与洱海之间是狭长的谷地,南北两端分别有龙尾关和龙首关,易守难攻。吐蕃军队绕道苍山侧翼,修建铁索桥,翻越苍山直插西洱河地区。《大唐新语》卷十一记载“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戍之。”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说:“漾濞江南流经点苍山背,至合江铺与洱海之水(龙尾江)合,又南流四十里,与备胜江合。则所谓濞水者,或即备胜江,而漾水即漾濞江也”。[6](P560)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唐代的漾水是今天漾濞江的上游,流经苍山西,前后分别有龙尾江(此江为洱海出口,流经龙尾城下)和顺濞江(即备胜江)两条支流汇入,最后流入澜沧江。冯智认为,当时吐蕃军队修筑铁索桥的具体位置在现今大理炼铁街与平坡之间的地方靠近“洱河尾”的地方。[4]
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初,在唐与吐蕃的博弈中,双方都希望将南诏作为自己能够倚靠的犄角。公元688年唐朝复置姚州都督府,第二年原本归附吐蕃的“浪穹诏蛮”首领谤时昔带领25个部落一起降唐。为了扭转局面,公元703年吐蕃赞普亲征西洱河地区。藏文史籍《弟吴教法源流》记载悉都松赞“在南诏被霍尔人所弑。觉热·空悉与江格尔·索域二人拼死只将赞普之右大腿带回,其余均未得”。[7](P4)公元707年唐灵武监军右都御使唐九征毁吐蕃漾濞江铁桥,夷其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吐蕃企图通过漾濞江铁桥进入苍洱地区,进而直接控制南诏,取得战略优势。但是在唐朝的积极干预下,它没能实现这一战略目的,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吐蕃只好退居剑川以北,依靠神川都督府来控制周边部落,间接对南诏施加政治影响。唐朝、吐蕃和南诏在西南地区的三角均势由此确立。
吐蕃与南诏交通路线的西道又称高黎贡山道,因在途中要翻越高黎贡山而得名,是吐蕃经云南通往缅甸的贸易通道。相比东道,西道的情况比较复杂,经过的地区主要位于横断山脉,地形特征两山夹一江、两江夹一山。高大的山脉间往往是开阔的谷地,相互交错。横断山脉主要呈南北走向,因此西道也多南北向的道路。
西道主线自南诏永昌城(云南保山)开始。公元743年南诏首领皮罗阁在此筑城,作为南诏永昌节度府的治所。永昌是西南地区通往印度和缅甸国际商路上的重要城镇。由此向西渡过怒江至穹赕就要翻越高黎贡山,路途非常艰险。《云南志》记载过高黎贡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赕,汤浪毒暑酷热”,[1](P65)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形容“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6](P475)
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现今的腾冲地区,南诏曾在这里设立软化府。腾冲盛产马匹,滇马在北宋曾是中原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云南志》记载“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有泉地美草,宜马……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也称越赕聪……腾充及申赕亦出马”。[1](P276)这里的越赕、藤充和申赕等地名经方国瑜考证均位于腾冲地区。从腾冲向北、向西均有道路通吐蕃,向北南诏曾建有越礼城和长傍城,由长傍城沿南北走向的恩梅开江即可进入吐蕃。从腾冲向西经宝山城可以到丽水城(又称寻传城),公元762年阁罗凤“西开寻传”,当地“裸形”、“祁鲜”等部落相继归附,南诏设磨零都督府管理这些部落。[8](P82)由丽水城折向北到金宝城(缅甸密支那)。金宝城向南向西分别通往骠国(缅甸)和大小婆罗门(印度)。向北沿着南北走向的迈立开江而上,就到了《云南志》中记载的“大赕”。《云南志》记载“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1](P293)可见阁罗凤在征服寻传后沿着这条通道一度占领过大赕,但最后由于气候条件恶劣而放弃。方国瑜认为“大赕”就是今天的坎底,是横断山脉地区中最广大的平川,多瘴气。“大赕周回百余里……三面皆大雪山,其高处迭天。往往有吐蕃至赕的贸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1](P67-68)翻越雪山后就进入西藏的察隅地区。
除了这条干线之外,西道上还有许多民间贸易往来自发形成的小道,这也是西道的一个特点,错综复杂。总的来看,因为西道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比较恶劣,而且距离南诏核心区域较远,所以东道成为吐蕃与南诏交通的主线,不仅是双方政治角力的战场,还留下了许多文化和经济交往的痕迹。
二、藏传佛教对南诏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南诏的时间约是8世纪末到9世纪初,应该不会早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公元755至797年)。虽然在7世纪初的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吐蕃,但是遭到了本土宗教苯教及贵族集团的强烈抵制,他们趁年幼的赤松德赞即位,发动了吐蕃历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9](P7)此时佛教在吐蕃本土尚未扎根,更不可能向外传播。公元763年成年的赤松德赞亲政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他举行大议事会,任用亲信为大论、元帅,实际行使权力。藏文史籍《贤者喜筵》说赤松德赞年届20岁时手臂麻痹,经苯教师实施各种祈福禳灾的仪轨都没有效果,于是废除禁佛法令,诏谕吐蕃臣民像以前一样信奉三宝,赞普的病情开始好转。记载虽然有一些传奇色彩,但赤德祖赞亲政后确实重兴佛法:迎请莲花生、建桑耶寺、选吐蕃贵族子弟出家、组织翻译佛经,建立起完整的僧伽制度,确立佛教在吐蕃的地位,才具备了对外传播的内部条件。
吐蕃控制滇西北后,与南诏的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唐天宝战争后,南诏更是投向吐蕃,接受“赞普钟”的封号。双方经济和文化交往大大增加。藏语中称云南丽江为Sa-Tham,唐代史料记载“磨些蛮”的居住区名为“三探觅”,即为Sa-Tham的对音,是为当时这种紧密关系的历史痕迹。[10](P179)这为吐蕃佛教文化传入南诏创造了便利。
藏传佛教进入南诏的情况与佛教初传吐蕃很相似,先在南诏统治集团内部流行,对民间的影响不大。一直到劝丰佑时期(826-859年),他和当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兴佛一样,大力提倡密教,在洱海地区普遍建立庙宇,迎请僧人。云南石宝山石窟的开凿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其石窟和摩崖造像强烈的藏传佛教印记,为研究吐蕃宗教文化对南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线索。
石宝山石窟距剑川城约20余公里,分布着16处石窟和摩崖造像,包括石钟寺区8处(第1-8窟)、狮子关区3处(第9-11窟)、沙登村区5处(第12-16窟)。较早的沙登村区第16窟第2龛的两尊雕佛下的题记中有“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的字样。天启为南诏王丰佑的年号,天启十一年应为公元850年。较晚的石宝山区第1窟“阿泱白”龛顶的墨书题记末尾有“盛德四年作□己亥□八月三日记”,经研究认为是造像时所题。这是大理国王段智兴年号,盛德四年为公元1179年。由此大致可以确定石窟开凿的时间段。在石钟山区石窟中还发现了两个藏文题记,为来自藏地朝拜的佛教徒之手,说明当时南诏的石宝山石窟也得到藏人的认同与尊奉。[11](P188)
石宝山石窟造像中以观音造像最多,分布在各区,是观音崇拜的体现。观音早期不过是阿弥陀佛的二胁侍菩萨之一,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大力提倡佛教,抬高了观音的地位,将其奉为至尊菩萨单独供养。南诏地区的密教受到吐蕃崇尚观音风气的影响,才会出现这么多的观音造像。现存《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第1-6段的内容是观音幻化的故事,中兴二年是公元899年南诏王舜化贞时期,进一步说明观音崇拜早在南诏国时期就在大理地区流行了。[11](P198)
整个石宝山石窟,特别是石钟寺区8个窟的具体内容和整体布局都体现了浓厚的藏传佛教密宗文化特色,如石钟寺区第6窟(明王堂)中的八大明王、天王、力士等造像秉承藏地密教造像夸张变形的风格。第1窟的“阿泱白”经研究最初实际上是藏密护法神怖畏金刚雕像,后来被凿毁。虽然唐宋时期中原地区亦有密宗流传,当时在四川地区开凿的佛教石窟中供养的密教尊像也不少,但并不是按曼陀罗法组织,而是显密并弘,为当时中原佛教信仰的主流。[12]所以石宝山石窟应该更多是受到来自藏传佛教的影响。
纳西族的东巴教源于南诏时期云南的本土宗教,也受到了包括苯教和藏传佛教在内的吐蕃宗教文化的影响。东巴教徒认为,祖师丁巴罗什来自西藏阿里古象雄,那是苯教的发源地。在东巴教的3尊大神里,有两位是苯教和藏传佛教的神灵。许多东巴教的咒语也使用藏语词汇,法器也大都与苯教和藏传佛教类似。东巴作法事戴的法帽“五佛冠”也是来自藏传佛教。现存近二万册的东巴经都是用象形文字写成的,有学者认为纳西族使用象形文字应当从唐初开始,至宋已经流行,这些经书的成书年代应当在宋初[13](P231)
三、吐蕃与南诏的经济交流
唐代吐蕃着力经营滇西北地区,除了要在侧翼对唐朝形成军事压力之外,还有自身的经济需求。在吐蕃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游牧经济结构单一且不稳定,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牲畜大批死亡,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因此吐蕃总是周期性向邻近的农耕地区扩展,以取得本族群生存所需的资源。[14](P14)南诏地区物产丰富,《西洱河风土记》云“其地有稻,麦,粟,豆,种获一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日为岁首。菜则葱,韭,蒜,箐,果则桃,杏,李,奈。有丝麻蚕织之事,出绢,丝,布,,幅广七寸以下染色有绯帛;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畜则有牛,马,猪,羊,鸡,犬。”这些都是地处高寒的吐蕃需要的。
吐蕃与南诏的经济交流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后者缴纳贡赋的形式来实现的。史载悉都松赞“推行政令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于制下”。《旧唐书·南诏传》说“吐蕃役赋,南蛮重数……牟寻益苦之”。可见在吐蕃统治时期,南诏的贡赋负担是比较沉重的,这也是南诏后来复归于唐朝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双方还有相当规模的贸易,东道的铁桥城就是主要的商品集散地,《云南志》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前来博易”。[1](P284)
从文献记载来看,南诏运往吐蕃的物资有盐和丝绸。吐蕃时期藏地制盐水平不高,“蕃中不解煮(盐)法,以咸池水沃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这种盐不仅产量低,质量也很差,因此吐蕃对周边地区盐的需求量很大。唐朝政府曾想以川西丰富的盐井资源作为手段来控制吐蕃,为争夺盐井吐蕃与唐朝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南诏也有盐井,史载“剑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为溺井。剑川有细诺邓井。”方国瑜考证这些盐井的位置在现今云龙,兰坪和剑川交界。吐蕃之所以要努力控制这些地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盐供应。当时就有人指出了这一点,“吐蕃唯利是贪,数沦盐井……今知其将兵拟侵蛮落,兼拟取盐井,事似不虚。”[16]
南诏的丝织品也是输出吐蕃的重要物资之一。南诏的丝织业发展得比较早,公元829年南诏攻占成都,掳掠了大量内地纺织工匠,用来提高自身的纺织工艺。《云南志》记载“精者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
吐蕃向南诏输出的物资,除了前面提到在铁桥城的牲畜之外,还有相关产品。《南诏德化碑》碑文记载南诏首领阁罗凤投降吐蕃时赞普“命宰相倚详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账床,金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鞍等,赐为兄弟之国。”[11](P155)这里的毯是一种毛织物,即藏地的氆氇。
吐蕃发迹于青藏高原的雅隆河谷,统一西藏本土后,经过长期的对外扩展,至赞普悉松德赞时期势力范围涵盖现在的青海、甘肃南部、川西高原、滇西北高原和新疆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原有族群大都属于氐羌文化圈。吐蕃实施军事征服后,在这些地区建立政治机构,征收赋税,也带动了文化和经济的扩散与交流。吐蕃的扩展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因为吐蕃的军事组织以部落为单位,这些军事化的部落长期驻守在被征服地区,没有吐蕃赞普的命令不能返回本土。吐蕃政权瓦解后,他们就永远留了下来,与本地氐羌文化的族群融合,逐渐演变成现在青藏高原上藏族的各个群体。因此吐蕃的对外扩展是青藏高原藏化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吐蕃的中勇部驻扎在贝囊隆山上、恰贡和佩以下,任务就是攻取和控制南诏。[16]吐蕃解体后,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法返回,遂与当地人融合在一起,成为现今滇西北藏人的起源。当然文化的影响永远是相互的,滇西北藏族独特的祭天习俗不见于其他藏区,却与东巴教存在亲源性,当地藏语方言中大量的纳西语借词,这些现象都体现了吐蕃和南诏文化关系另外一个面向。[17]研究吐蕃与当时周边族群的互动,对理解藏族和藏文化圈的演变进程,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