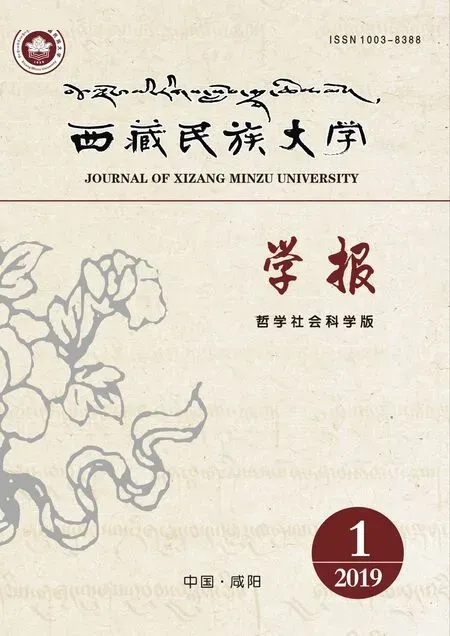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趋势
刘再营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陕西西安710062)
从历史上的“华夷之辩”到“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由近代以来的“五族共和”思想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转变,标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确立。新时期以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要求。
一、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然
(一)从“华夷之辩”到“华夷一家”,确立“华夏”族融合的基础
“华夷之辩”,亦称“夷夏之辩”,是先秦以来关于民族争论的思想源泉,经过后世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何谓“诸夏”,最初指周王室及诸侯封国等血缘关系为纽带,“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1]进而延伸到王畿地区,则表现为五服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2]华夷之辩的发展的最后,主要在文化上的区分。“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3]
早期的夷夏观念认为,“夷”和“夏”之间是对立、不可逾越的。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后汉书》“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4]江统在《徙戎论》“《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5]
遵循“华夷之辩”的义理关系,“华夏”与“夷狄”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对立、静止不动的固化,是可以进退、可以转化。“夷狄”可以德化为中国,诸夏亦可沦为夷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孟子认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6]而《全唐文》收录的《内夷檄》中道,“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唐太宗进一步发展了“夷夏之辩”思想,使“夷夏”融合、一体同视,不分你我的大民族观。“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正如父母。”[7]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帝国版图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有的“华夷之辩”。秦汉帝国内生活的各族人民,不再是之前的“诸夏”和“四夷”,而是有新的时代称谓,即“秦人”或者“汉人”。自此,“华夷一家”逐渐取代“华夷之辩”。
(二)“大一统”的思想,促成封建王朝体系政治统一体的形成
“大一统”表述源于《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揭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王正月?大一统也。”所谓的“大一统”,政令皆出于周天子。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思想的精华,在于其“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政治宣教,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子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司马迁最早提出夷夏皆是同宗思想,丰富了“大一统”的种族来源,《史记》“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孙,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是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8](P341)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急想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一直以“大一统”的后继者自称。如匈奴人自称为大禹的后裔。“匈奴人与汉人本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后篡,匈奴亦出兵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汗,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9]鲜卑人也自认为是黄帝苗裔,据《慕容廆载记》“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10]
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接受,并自称华夏先王之后,以符合“大一统”政权的合法身份。匈奴人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代之苗裔”,“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微赫实为天连,令改姓为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人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11]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更是具有“大一统”的合法性。《魏书·帝纪第一》,“黄帝以土为德,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延至孝文帝时,更是采取大规模的汉化进程,在行动上符合“华夏”之礼,进而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北魏以汉魏正统的继承者自居,重用汉族士人,依靠鲜卑族的武力和汉族的文化”,完成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这一时期的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密不可分的一体性。”[12]
隋唐时期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使“大一统”的实践得到充分的发展。宋朝建立之后,常面临强敌入侵,根本无法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宋、辽、金、西夏政权的相继并存,宋人只能强调自身政权的“正统”地位取代“大一统”理想。而隋唐之后的大一统”,只能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来完成。1260年,忽必烈在大都即位,次月颁布《即位诏》,“朕惟祖宗,肇造宇内,庵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宣布新政权采取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的不足。次月,改国号为“元”,“朕获瓒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盖取《易经》乾元之义。”雍正帝认为,“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人也;所施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夫满汉色,犹直隶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13](P696)
(三)交往、交流与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与交融,共同铸就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形成。这一进程主要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如互市、和亲等形式的进行,有时候是战争情形下进行,不管是和平往来还是战争融合,客观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发展融合。
互市贸易。主要由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往来互动。互动的前提是经济上的互补,处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与草原地区的匈奴、突厥、契丹、吐蕃、蒙古等游牧民族之间进行,前者以农业生产为生,后者以牧业为主,在互市交往的基础上,情感上得到了交流,经济上增强了依赖。自汉朝开始就与匈奴进行贸易,延至明、清,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属茶马互市。茶马互市起源于唐朝,盛行于宋、明。黄庭坚诗云,“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原地区的茶等生活必需品,与吐蕃的马、骡、羊毛、麝香、药材等互换,达到共赢的目的。
和亲政策。和亲是古代民族关系中的重要方面,一般发生在政治集团上层人物之间,以达到特有的政治目的。历史上的和亲,主要发生在汉与匈奴之间、唐与吐蕃之间、清朝的蒙满联姻时期。以文成公主入吐蕃为例,带去了丰厚的嫁妆,还有大批的手工艺者、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纺织、建筑、冶金等生产技术传入吐蕃,促进吐蕃经济社会的发展。清朝奉行的蒙满联姻的政策,“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的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无一不以王公额附对清廷效忠程度为转移。”[14](P55)和亲在客观上促进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推动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发展。
民族战争。马克思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野蛮的征服者总是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自秦汉以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时有发生,延续数千年。其中汉与匈奴之间,唐朝与突厥、吐蕃之间,宋与辽、金、西夏及后面崛起的蒙古之间的民族战争,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大集团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游牧文明集团战争胜利后,进入生产力比较先进的农耕地区,受农耕文明的影响而仰慕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农耕文明集团胜利后,通过“归顺”、“降服”的措施,同化大量的游牧民族,丰富了人种和文化的多元性。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促进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融合,加速了“汉”族主体的扩大,提升了“汉”族的文明水平。
二、近代以来的民族思潮,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时代必然
(一)鸦片战争以来民族思潮,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条件
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思想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其中,最具代表的是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争论。立宪派领袖的康有为其“民族”意识深受春秋公羊派大同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所谓的“大同”是华夷间区别在文化上差异,随着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华夷之间的差别趋于消失,会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华”族。“黄种”各族之间的纷争造成种族意识蔓延,必然造成“大同”社会的障碍。他认为中国是黄种之国,包括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不要将他们进行区分,“满族和汉族原本宗教是相同的。曾文定公以来汉人一直高居政权之位,同治以来总督巡抚几乎都是汉人,汉满之间没有什么芥蒂。”[15](P44)“满洲种族字黄帝、夏、殷之时就有了,以后其政教、礼数全同化于中华。”[15](P44)他认为所谓的“汉族”和“排满”思潮,只不过是革命派的工具而已。
1896年,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中提到,只有变法,才能“保国保种”。他所指代的“种”,包括了生活在中华帝国版图内的所有人,因为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分为不同的“种”,因为进化迟缓,有些“种族”制度低下,有“今之蒙古、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谓的由“多君”向“一君”转变的“小康”阶段。他认为,由“汉种”的高度进化,带动满洲,蒙古将来达到“汉种”进化的程度。梁启超针对革命派的“排满”主义,则主张将诸民族统一为一体,组建融合统一为一个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统一的国家。“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其他民族是也,大民族者何,合国内的本部属之诸侯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全球的三分有一之人类,……此者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者,必成于汉人之手。”[15](P63)
上述三种方法中,最简单用时最少的是方法3,根据要解决的问题的要求,通过观察、比较和分析,找出规律,从而迅速解决问题,体现的是综合应用能力。其次是方法2,它是化学学科思想中整体思想和化学学科观念中守恒观的有机结合的应用。方法1,是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应用。
(二)“五族共和”思想,初步铸成中华民族自觉联合的雏形
五族共和的提出。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思想,主张“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这些思想建议,还强调满汉民族之间的一体性。“时至今日,竟言和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行,言语同声。”[16](P234)与此一致,一批留日满族学生在东京创办《大同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宣传“五族大同”。
宣统三年,清廷颁布退位诏书,“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展示出清政府对“五族共和”民族思想的认可。1912年4月,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6](P240)后来,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以法律形式确定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6](P240)在《五族国民合进会启》一文中,“五族国民,固同一血统,同一支派,同是父子兄弟”“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冶之,成为一大民族;即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豪杰之才识知能,成为一大政党,”“五族国民果能终成一大民族,一大政党,并此汉、满、蒙、回、藏之名词且将消弭而浑化之。”[16](P80-81)
1913年,《庸言》杂志刊载了吴贯因的《五族同化论》,“汉、满、蒙、回、藏五民族,起初固非单纯之种族,而实由混合而成之民族也。夫人种相接近,由种族之事故,二融合交通,世界史上实数见不鲜,而非独中国而已。……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五族人民负担平等之义务,亦享受平等之权利,既已无所偏重,以启种族之猜嫌,自可消灭鸿沟,以使种族之同化。则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当非不可能之事。”[16](P243)吴氏认为,“今后全国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可称中国国民也亦可。”[16](P243)民国初年的历史环境,他没有使用“中华民族”称谓中国国民,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已经在他的思想中的得以体现。
(三)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观的初步形成。
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文化已渐趋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刑典,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17](P302-303)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族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8](P393-394)表明了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立场。1922年,在中共“二大”宣言中,正式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民族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理论。1927年4月18日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中宣称,“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言语口音之歧义,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19](P54)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日本人为加强殖民统治,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积极鼓动内蒙古地区自治,企图利用民族问题,从思想上分化和瓦解中国。而此时,传诵广泛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16](P262)更加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抗战信心。
顾颉刚先生对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深表担忧,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往后大家应当留神适用这“民族”二字。”[16](P3)通过论述,得出“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然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往后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6](P43)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大讨论。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几千年的密切交往中,共同的地理疆域、共同的历史使命、共同的传统文化使56个民族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型民族——中华民族,因此也必然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成意义重大。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现实必然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的形成、融合与消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民族的形成,“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部落发展成立民族和国家”。语言、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必备条件。”“部落联盟及后来这些部落联盟的融合,使各个部落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民族的交流,必然导致民族的同化,“民族自然同化是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自然地、自由地发生的必然现象,是有利于民族交往和接近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现象。”[20](P151)关于民族的消亡,“在共产主义阶段各民族在公有制基础上通过民族融合走向民族消亡的一般规律,说明民族消亡是各民族在共产主义阶段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共产党人强制取消的结果。”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要是各民族融为一体。”“各民族融为一体,是要在消灭了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以后才能实现的,因为民族差别,“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斯大林指出,“列宁不是把民族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而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后形成的。在抗日战争,“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同时,“中国境内的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蒙、回、朝、藏、苗、瑶、黎等)和汉族一起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21](P306、307、301)解放战争时期,“团结国内各民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22](P1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发展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确定民族平等。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任何民族歧视、压迫和分裂团结的行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同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二是做好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毛泽东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是地方民族主义,又不利于给民族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23](P145)三是发展民族经济。毛泽东认为,“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24](P214)1963年,在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要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放在民族工作的第一位,以加快缩小和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不平等的差距。”[25](P124-125)在谈西藏共工作方针时,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否则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3](P8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时代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党对民族地区的工作也有新的要求。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工作,提出“两个离不开”,即“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亲密关系的科学总结。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能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1987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实际,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致富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民族工作。1990年,他在新疆考察时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50多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23](P237-238)“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是新时期民族关系的科学总结。同时,对民族工作的长期性、重要性也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民族差别、民族问题将存在很长很长时间”从历史上进行梳理,“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26](P2、30)在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他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27](P73)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理论的同时,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现实,提出新的定义。他认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27](P83)同时,对“民族”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描述,不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把宗教作为一些民族形成和构成的因素,对于正确处理新时期的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7](P83)
(三)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的指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时代条件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抓紧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探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经验,创造性的提出来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27](P100)2014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全面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必须做好八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23](P101)
2014年,习近平在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23](P99)2015年,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他强调,“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定不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27](P103)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8](P32)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