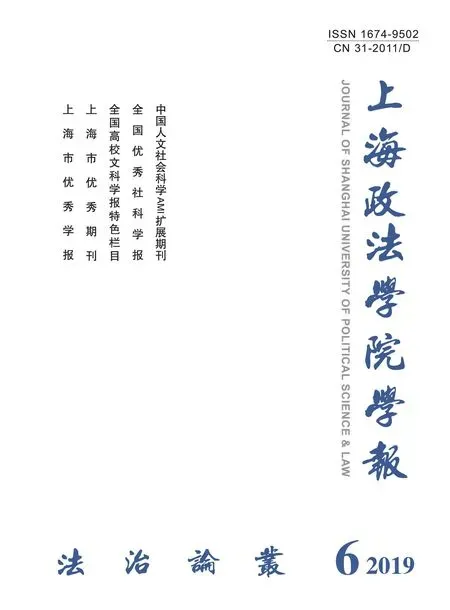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两大基本原则
范进学
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是由国家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与政党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共同构成的,即在我国,存在着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与国家层面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审查制度。鉴于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殊性,在现阶段,从我国国情、政情与现实出发,要真正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不断发展,必须首先确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基本法律不予审查原则;二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予审查原则。
一、基本法律不予审查原则
“基本法律”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是在1980年8月30日彭真同志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他谈到民法和民事诉讼法时称“是很重要的基本法律”①参见彭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0年第5期。。1982年宪法文本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基本法律”这一术语,《宪法》第62 条第3 款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宪法》第67 条第2 款、第3 款规定:常委会行使“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职权,以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2000年 3月由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第7 条又重申了1982年宪法的上述规定。①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然而,《宪法》《立法法》以及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其他正式文件,均未对“基本法律”的内涵如标准、位阶效力等作出权威性解释。目前,学者仅仅从学术研究与探讨的角度,对“基本法律”进行了分析与阐释②具体文章可参见: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2003年第4 期;薛佐文:《论 “基本法律”和 “法律” 的性质和地位》,《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 “法律”的涵义》,《法学》2005年第2期;薛佐文:《对立法权限度的法理思考——专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莫纪宏:《论宪法与基本法律的效力关系》,《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马英娟:《再论全国人大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的位阶判断》,《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 期;李克杰:《中国 “基本法律”概念的流变及其规范化》,《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3 期,等等。,譬如,韩大元与刘松山在《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一文中认为:“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
从宪法的规定分析,1982年宪法第一次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的职权,在此之前,全国人大是“唯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③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制定法律”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法律”和“制定法令”的职权。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该决议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的权力;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 进一步明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的需要对现行法律中的一些不再适用的条文, 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1978年宪法第一次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1982年宪法之所以赋予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宪者的考量是:“由于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较多,不便经常进行工作、行使职权,……因此,草案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更好地发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④1982年4月22日,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 页。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的立法权是由全国人大立法权派生出来的。⑤参见薛佐文:《论“ 基本法律” 和“ 法律” 的性质和地位》,《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 期。结合1982年《宪法》第62 条和第67 条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之规定与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笔者认为,立宪的基本意图是划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即全国人大制定哪些法律,常委会制定哪些法律,而不是对“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进行定义上的界分。从全国人大制定包括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全部法律,到常委会也制定一部分法律,这部分法律就是除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因此,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权的划分规定,表达了5 层含义:一是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二是全国人大也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⑥有学者认为,从法理上讲,1982年宪法实施后,全国人大就只能制定 “基本法律”而不能再制定 “其他法律”了(参见薛佐文:《论“ 基本法律” 和“ 法律” 的性质和地位》)。这一观点不符合《宪法》第67 条第2 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的立法意图,宪法文本的字词不是可有可无的,这里之所以使用“法律”而非“基本法律”,就清楚地表明立宪者心中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而且这一理解与解释也符合宪法条款的体系解释。;三是第67 条第2 款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也就是说,常委会可以制定除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以外的(非基本)法律;五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在不得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从1982年宪法的上述规定看,宪法只是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分享全国人大的国家立法权的职权,换言之,在1982年之前,所有的国家法律均由全国人大制定,其中就包括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1982 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共享“国家立法权”的权力,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自然就可以制定“除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然而,由于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由此可推知,“基本法律”制定主体只能为全国人大,而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常委会不能制定“基本法律”,而只能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全国人大不制定的“非基本法律”。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从属于全国人大的创设机关,其立法权是由全国人大立法权派生而来的,要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也有可能制定或通过“不适当”的决定,所以,《宪法》第62 条第11 款又赋予了全国人大对其常设机关即常委会制定或通过的“不适当”的决定予以“改变”或“撤销”的审查监督权,从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全国人大进行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宪法依据。而对于全国人大自身制定的“基本法律”,除了《宪法》第5 条要求“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外,宪法并未规定具体由谁进行审查监督。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否定了西方国家那种权力制衡式的、由全国人大(议会)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对全国人大(议会)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审查的可能性。所以,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不可能受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与审查,即使另设一个独立于全国人大的机构如“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的制度构建,也不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并将与之背道而驰。如此看来,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具有不可审查性。如若审查,也只能由全国人大自己进行自我审查。然而,这种自我审查应当不属于合宪性审查范畴,自己针对自己起草或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照“宪法”进行自我审查,使自己制定的基本法律不与宪法相抵触,这是立法者的基本要求。问题是制定出来的“基本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由谁进行合宪性审查?由于该问题在现行宪法中没有规定,《立法法》也未对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作出规定,所以,从学理上推论,基本法律的违宪问题属于自我审查的问题,而不应当由全国人大之外的其他机关予以审查。
合宪性审查的目的在于通过审查宪法以外的一切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此确保宪法的正确实施,确保宪法的权威。在我国,由于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全部法律体系中,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截至2017年9月,共有252 部①参见《我国现行有效法律目录(253 部)》,http://jlfxhw.com/flmlnew/index.jhtml,吉林省法学会网,2019年7月20日访问。;截至2014年9月底,我国已经制定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37 件,国务院部门规章2856 件,地方政府规章8909 件。截至2016年7月底,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经济特区法规共9915 件。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法规5701 件,设区的市、自治州地方性法规2936 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967 件,经济特区法规311 件。②参见第二十二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之五:《我国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的数量》,http://www.npc.gov.cn/npc/lfzt/rlyw/2016-09/20/content_1997847.htm,中国人大网,2019年8月10日访问。
从我国法律体系的法律数量看,最庞大的是法规群与规章群,违宪或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多属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在“孙志刚事件”①2003年3月17日晚上,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这一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的2003年5月1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腾文彪,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的许志永3 人以公民个人的名义,针对国务院1982年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了合宪性审查建议书,3 位博士认为,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正是该建议,开启了中国普通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合宪性审查建议的先河。此后,公民个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合宪性审查建议的对象几乎都是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几乎没有针对基本法律的,近年来针对普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仅有1 起。2003年6月21日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针对《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2004年1月,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2007年11月29日,江平、茅于轼、贺卫方、胡星斗等69 名学界专家以公民名义,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针对劳教制度的“违宪审查建议书”。2012年,1 份由15 位国内法学、人口学学者联名签署的修法建议书曾寄送至全国人大,建议审查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废止生育审批制度,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诸如此类的公民提起合宪性审查的建议案,几乎都是针对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的,针对普通法律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仅有1 起。因此,在我国,只要普通法律、法规或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解决了,违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基本法律不予审查原则确立的意义就在于:第一,避免了全国人大对自己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自我审查的批评与指责。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制定的基本法律具有“基础规范”的作用与功能,在实践上对其不予审查,是充分相信基本法律不会违反宪法,即便违宪,也相信凭借全国人大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定程序与自我完善机制得以妥当处理。第二,避免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关监督全国人大的权力逻辑上的悖论。在宪法设计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自身隶属于全国人大,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若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由常委会审查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否违宪?在权力逻辑上是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第三,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点放在法律之外的法规、规章与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上,就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只要法律外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得以解决,宪法的权威就能够树立起来,公民的宪法权利或人权就能够得以保障。
二、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予审查原则
目前,我国合宪性审查体制采取的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归党审查、国家法律规范性文件归国家审查”的党国审查制度分离模式。我国《宪法》《立法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以及《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皆把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局限于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等,而没有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纳入到国家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范围之中。国家意义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均遵循不予审查的原则。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尽管不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范围之内,但却由党的机构负责审查。根据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规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式合宪性审查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承办,具体事务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办理。所谓“备案式”合宪性审查,是指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主动对其收到的报送机关需要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否同宪法不一致”进行审查的活动。
事实上,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归党的机构审查而国家机关对其不予审查原则是一个既定事实,也就是说,这一原则事实上为国家立法者与国家层面的合宪性审查主体所遵循。这里的问题是:人大机关为何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采取不予审查的原则?
第一,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属于中国共产党内部规范性文件,是党治理自身事务的基本规范。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党内法规是指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其他党内法规是党章有关规定的具体化。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第2 条规定:“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文件,包括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文件。”因此,包括《党章》在内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共产党治理自身事务和工作的基本准绳与规范,对于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各项工作和党内生活的制度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规党法的效力只对党内事务和党的组织及其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对党外其他组织或公民个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领导党,共产党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之列。实践中,国家宪法和法律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交由执政党自身进行审查,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不予审查是有法定依据的。
第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由党内审查机制能够得以保证。执政党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从制定到通过之后都有相关机构进行合宪性审查,以确保党内法规文件与宪法相一致,不会出现违宪情形。《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6 条规定:制定党内法规应“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原则;同时,该条例还规定了审定程序,即党内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应履行审定手续,报送中央审议;具体承办机构(中央办公厅)负责校核并向中央提出校核报告。这样的规定,就确保了党内法规在制定过程中不出现违宪。同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按照《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由制定机关报送中央备案,再由中央负责合宪性审查的中央办公厅对报送中央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合宪性审查。通过中央办公厅主动性备案式合宪性审查,就基本确保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会出现违宪现象。所以,在此前提下,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就显得没有必要。
第三,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在人民法院案件受理范围之内。如果说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是主动性合宪性审查,那么由利害关系人针对党的规范性文件提起合法性或合宪性审查则属于被动性审查。对于当事人提起的这种被动性审查,党的文件或国家法律、法规等法律文件皆未规定此种情况。从理论上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譬如,1988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查受理“水利电力部第十四工程局诉云南省机电设备公司房屋产权纠纷”一案时,遇到了中共云南省委的1 份文件即批转了云南省经委《关于统一管理物资和设置省物资管理总局的请示》,而这份文件引发了产权纠纷,于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请示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党委发文调整引起的房产纠纷不属法院主管范围的批复》中指出:“经研究认为,水电部第十四工程局要求收回的房屋是经云南省委发文件批转调整给云南省机电公司使用的,不属法院主管范围,不应受理,可告知当事人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党委发文调整引起的房产纠纷不属法院主管范围的批复》,(88)民他字第62 号。这是由当事人针对党的文件提起的唯一一起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批复,此类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因此,关于党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或合宪性被动审查在目前既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之内,也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之内。
第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无权审查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党中央出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之考量,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各部门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可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对党中央作出的决议和制定的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向党组织提出保留意见,也可以按组织程序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提出。”②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61 页。该规定是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的解释主体第一次作出的明确规定,无疑向世人表明,凡是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党外国家机关均无权作出决定和解释。最引以人们瞩目的是,依据《准则》规定,党的方针政策是否与宪法相一致的合宪性解释权只能由党中央行使,党外的任何国家机关均无权解释,如此一来,等于完全否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解释党内法规文件的可能,从而为“党内法规审查归党管、国家法规审查归国家”的二元型混合制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并为党内法规审查与国家法规审查两种不同的制度划定了疆界领域。③参见范进学:《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色与风格》,《政法论丛》2018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