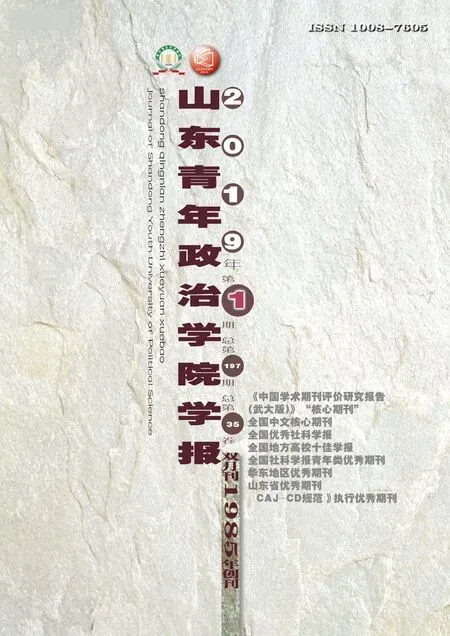爱情·死亡·命运
——艾丽丝·门罗的小说《机缘》《匆匆》《沉寂》主题分析
李淑霞
(山东交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济南 250357)
一、爱情——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
“爱”与“死”是自古至今文学创作的两大永恒主题,贯穿于所有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中,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同样,这两大主题也蕴含在门罗的女性命运三部曲《机缘》《匆匆》《沉寂》之中。这三部曲实际上就是以主人公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生活为线索,演绎出一首完整的关于女性生命轨迹的交响乐,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
像门罗的小说代表作《逃离》中的女主人公卡拉一样,朱丽叶也是门罗小说中的典型的女性人物——一个出生、成长于加拿大城郊小镇的年轻女孩。她长大后,离开家乡小镇来到大城市多伦多进入大学学习。二十一岁的时候,她就已经获得古典文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她抽出一段时间到温哥华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托伦斯寄宿学校做代课老师,教授拉丁文。在从多伦多去往温哥华的火车上,朱丽叶邂逅了一个来自温哥华城郊小镇鲸鱼湾的男子埃里克。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已经结婚,依靠出海打鱼为生,他太太在八年前的一次车祸中受了伤,一直瘫痪在床,由小镇上邻家的女人帮忙照料。因为火车上那个趁着火车停车的间隙下车卧轨身亡的男子,朱丽叶和埃里克之间发生了一场对话,并逐渐萌生出了爱意。朱丽叶代课结束之后,没有回多伦多的大学继续做博士论文,而是跟随着爱情的指引,来到了鲸鱼湾,开始了与埃里克的同居生活。
朱丽叶与埃里克的邂逅,可以说是她与爱情的邂逅。这次邂逅改变了朱丽叶此后的生命轨迹。如果没有这次在火车上与埃里克的偶遇,朱丽叶的生命轨迹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态。那么,爱情到底是什么呢?究竟何为爱情呢?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爱情,在本质上意味着两性之间的永恒战争:施爱者希望占有受爱者,但是,这受爱者的自由(这是他或者她的人的本质)是无法占有的;因此,这施爱者便倾向于把这受爱者变成一个对象以便占有它;这受爱者为了维护其作为人的本质,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占有;正是因为这一点,爱情,特别是性爱,最终变成了不断的紧张,乃至事实上的战争。[1]
这种紧张的气氛和战争的硝烟充斥、弥漫于朱丽叶与埃里克的爱情生活的始终。他们在火车上邂逅,互生爱意,然后深情吻别。数月之后,朱丽叶收到了埃里克的一封信。信的结尾写道:“我时常会想起你。我时常会想起你。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2]这种话语分明是毫无遮拦的十分露骨的爱情表达了。朱丽叶跟随着爱情的召唤,来到埃里克的小镇鲸鱼湾。这一天,刚好是埃里克为他的亡妻安举行葬礼的日子。葬礼结束后,埃里克并没后回家,而是去了他的情人克里斯塔的家。朱丽叶在埃里克的家里遇到的是他家的帮佣艾罗。艾罗表面上对朱丽叶客气礼貌,朱丽叶实际上感受到了她骨子里的排斥和拒绝,她还明确表示希望朱丽叶可以乘坐末班长途车回温哥华去。艾罗就好像是埃里克的替身和代言人。朱丽叶却坚持留下来,在埃里克家里等待。埃里克知道朱丽叶在家里等他,没有回温哥华,可是他并没有回家去,也没有做出其他回应,好像是欲擒故纵。此时,朱丽叶感到:埃里克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只是个自己可以与之调调情的人;然后,在某一天的早晨,她会一走了之的。[3]但是,当埃里克回到家里后,惊喜地拥吻抚触她,她感到全身沉浸在轻松之中,都快乐得不知怎么才好了。[4]朱丽叶与埃里克之间的爱情关系就在这种时紧时缓的张力中向前推进。
朱丽叶与埃里克共同生活了十六年之后,她发现了一件摧毁她爱情信念的事情:在十二年之前,在她带着他们的小女儿佩内洛普回到故乡小镇看望父母的一段时间里,埃里克去与他的旧情人克里斯塔重续旧欢了。这个发现使得朱丽叶与埃里克的爱情关系由紧张升级成了激烈的战争。朱丽叶感到:对埃里克来说,性爱问题,根本不是值得认真看待的事情,至少不像是对她自己来说那么重要;谁恰好近在身边,他就跟谁玩儿。她觉得:埃里克不爱她,而且从来都没有爱过她;他和她在一起十六年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是一场骗局。这种感觉激起了朱丽叶对埃里克的深仇大恨,燃起了她对埃里克无法压抑的炽烈怒火;这种感觉伤透了她的心,摧毁了她赖以生存的一切,她觉得自己周围的一切全都坍塌了。可是,埃里克却觉得他在十多年前跟一个旧情人发生性爱关系,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不能理解朱丽叶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有时候甚至认为她是在装腔作势。于是,两个人之间互相指摘怨怼,战争愈演愈烈。最终,这场战争以埃里克出海时遭遇暴风雨遇难身亡落下了帷幕。[5]
男女两性在爱情关系之中的紧张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男女两性爱情观念的差异和错位引起的,正如朱丽叶和埃里克对爱情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感受。埃里克认为,在朱丽叶离开家的一段时间里,他与旧情人爱情复燃,鸳梦重温,并不是很要紧的事情,不会减少他对朱丽叶的爱,也不应该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朱丽叶也没有必要对此耿耿于怀。而朱丽叶却觉得,埃里克的出轨行为是对他们在一起十六年爱情生活的全盘否定,不仅深深地伤害了她的感情,而且还摧毁了她赖以生存的所有生命支撑。埃里克认为,他只不过是与一个旧女友在干草堆里打了几个滚而已;而朱丽叶觉得,他不仅背叛了他们的爱情,而且颠覆了她整个生命的凭依与价值。由此可见,朱丽叶的爱情观念与埃里克的爱情认知存着深刻的差异和深度的错位。这就决定了她的爱情理想最终必然会走向幻灭。
作家王安忆认为:爱情是人性为孤独求救。在生命的漂流中,爱情好像是带有岸的面目,可是后来,我们渐渐明白,它也只不过是一条船,同样也要随波逐流。我们都希望它既能度己也能度人,可是,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同样的渺小无助,谁能拯救谁呢?[6]确如其所言,男女两性谁也不能成为另一方的拯救者。女性的拯救者,既不是她们依据幻想构建出来的完美有力的男性,也不是她们依靠憧憬想象出来的乌托邦性质的爱情,而是她们具有主体性和独立性的自身。在两性之间的爱情关系中,女性应该成为诗人舒婷笔下的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橡树并肩站在一起。也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权理论中的“独立的女人”,在与男性的平等关系中求得与其有差别的共存。在现实世界中,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之间的独特的、挑战传统观念的、具有创造性的爱情关系,正是实践了这种“在平等中有差别的共存”的两性关系理论。正如波伏娃所言:在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战争中,“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7]
二、死亡——偶然性与有限性的显现
死亡是艾丽丝·门罗的女性命运三部曲《机缘》《匆匆》《沉寂》所蕴涵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三部短篇小说中充满了密集的死亡叙述和死亡意象。《机缘》中,朱丽叶在火车上邂逅的陌生男子在火车停车的间隙下车去卧轨身亡,埃里克最终为他因为车祸瘫痪在床八年的太太安举行了葬礼。《匆匆》中,朱丽叶父母家的帮工艾琳的丈夫在他干活的养鸡场的一次事故中丧生,朱丽叶的母亲萨拉在朱丽叶回去探望她并陪伴她一段时间之后离开人世。《沉寂》中,埃里克驾驶小船出海检查他捕大虾的网是否有问题时在暴风雨中遇难,埃里克的旧情人朱丽叶的情敌兼密友克里斯塔在某一年的一月也非常突然地死去了。
关于死亡的严格的形式定义可以为:“死亡意味着一个有生命的实体状态的全然改变,这种改变是这些具有某些特性的生命实体,对其有本质意义的特性之不可复原地丧失。”[8]人类比较理想的比较容易接受的死亡方式是寿终正寝。但是,正如帕斯卡尔所言,死亡并非总是按照约定正点降临,而是具有一种偶然性,一种处于人类存在核心的基本偶然性,一种随时都可能把我们意想不到地猛抛掷进非存在之中的偶然性。[9]朱丽叶在火车上并不知道那个向她搭讪的陌生男子将会蓄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也全然没有料到她到达鲸鱼湾的那天正是埃里克为太太举行葬礼的日子。艾琳的丈夫就在她过二十一岁生日的那一天,在养鸡场丧生,仿佛厄运从天而降。朱丽叶的母亲萨拉中年辞世,我们只是从他父亲山姆和家里的帮工艾琳口中了解萨拉发病的时候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常常搞得家里一团糟,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萨拉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埃里克出海的时候海面上几乎是风平浪静,可是,下午稍晚时候突然遭遇到了暴风雨,他的渔船被海浪吞噬,他的遗体第三天才被找到。后来,某年的一月,克里斯塔也非常突然地死去了,没有任何病症,没有任何预兆。门罗小说中的这种浓墨重彩的死亡叙述正显现了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世界包含着偶然性和非连续性。
同时,另一方面,门罗小说中的死亡叙述,不仅显现了死亡的偶然性,也彰显了死亡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她的女性命运三部曲《机缘》《匆匆》《沉寂》实质上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女性的完整的生命流程:朱丽叶出生、求学、恋爱、结婚、受苦、走向死亡。她先后经历了火车上陌生人的死亡、母亲萨拉的死亡、爱人埃里克的死亡、密友克里斯塔的死亡,以及女儿佩内洛普的失踪;最后,她仅仅是怀着一线“能够从佩内洛普那里得到只言片语”的希望,孤寂地看着死亡的脚步一步一步逐渐靠近她。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所言:一个完整的人,如果没有死亡、焦虑、罪过、恐惧和颤抖以及绝望之类的人生体验,那么,他也就不再完整了。[10]赫拉克利特曾经教导说:万物皆流,无论何处都逃脱不了死亡和变化。[11]柏拉图也曾经说过,人体是坟墓,哲学思考就是学习死亡。[12]托尔斯泰也曾经对高尔基说过,如果一个人已经学会了思想,那么,不管他可能思考什么,他都总是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所有的哲学家也都是如此。[13]因此,死亡问题始终位于哲学意识的中心,同时它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死亡是我们人类各种可能性中最个人和最内在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我们必须自己去经受的,任何他人都无法代替我们自己去死。接受死亡,并认为它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这就透露了我们存在的彻底的有限性。[14]火车上的陌生人、埃里克的太太、朱丽叶的母亲萨拉、埃里克以及克里斯塔,所有这些人的死亡意味着朱丽叶的过去都已“不再”。这是人的有限性在时间上的显现。人的有限性也要在空间中显露它自己。朱丽叶和她周围的人都生活和活动在有限的存在领域之内。同时,人的有限性更要鲜明地表现在认知能力上:我们并不能够同时认知一切事物,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其他事物为代价的。朱丽叶不知道那个火车上的陌生男人为什么会结自己的生命,不明白埃里克的性爱观念为什么会跟自己有着巨大的差异和错位,不清楚为什么女儿会突然离家出走而且多年杳无音讯……这一切都揭示了我们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甚至,帕斯卡尔断言,人就是他的有限性。[15]
关于死亡的存在主义观点认为,死亡不仅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偶然性和有限性,而且也内蕴着一种终极的肯定:面对死亡,生命具有绝对的价值。死的意义就在于它对这种绝对价值的启示。[16]因此,在埃里克出海遇难身亡就地火化之后,面对着必然要到来的死亡命运:面对着浩瀚的延伸到生前死后的虚无,朱丽叶自觉而坚定地选择了她自己的生活:她卖掉了在鲸鱼湾与埃里克一起居住了十六年的那座房子和埃里克的卡车,把埃里克的工具都送了人,给鲸鱼湾的生活落下了帷幕画上了句号;然后,她搬到温哥华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找到了一个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的职位,后来又到某电视台做访谈栏目……她的面向死亡的存在体现了作为反叛的、有尊严的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三、命运——理性与非理性的合奏
艾丽丝·门罗的三篇小说《机缘》《匆匆》《沉寂》是关于一个女性命运的三部曲。世间万物都有某种内驱力,以便不断地向前运动。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在这种内驱力推动下不断向前运动的结果。它像一条看不见的时急时缓的地下河流,最终流向大海;也像一股缓慢而盲目地向前流动的波涛,最终趋向死寂;它就是一支由理性与非理性交织而成的合奏曲。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理性是我们人格中最高贵的部分:人,真正说来就是理性。因此,一个人的理性,就是他的真正自我,他个人身份的中心。这是以最严格最强有力的措辞表达出来的理性主义——一个人的理性就是他的真正自我——这种理性主义迄今为止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家的观点。即使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在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时,也没有撤换掉他的这条原则。[17]圣托马斯以理性来区别人与动物,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动物”[18]这个传统定义。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理性的地位都是不容质疑的。
当今时代,理性文化衰颓而非理性文化崛起。非理性主义凸现人的自由、个体性、主体性和实践性等人类特性,认为所谓的“理性”只不过是人借以实现其欲望和意志的手段或者工具而已,主张感情、意志或者本能比理性更有价值,也更为实在。帕斯卡尔早就看到:人本身是个具有矛盾和两重心理的生物,纯粹逻辑是永远理解不了的。[19]柏格森认为,抽象的理智不足以把握经验的丰富性。[20]萨特则无情地断定:在一个无神的宇宙里,人是荒谬的,不合理的,而且也是没有理性的,一如存在本身。[21]
美国当代哲学家威廉·巴雷特则认为:“本真的人”既不完全是“理性的人”,也不完全是“非理性的人”,因为无论是“理性的人”还是“非理性的人”都只是一种“片面的人”,一种“不完全的人”,因而也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本真的人”应当是“完全的人”或者“完整的人”,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体,应当是既有血有肉又有头脑有思维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22]
门罗的小说《机缘》《匆匆》《沉寂》中的女主人公朱丽叶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体。她在托伦斯寄宿学校代课结束后,本来是应该动身回家的,可是,她却打算去兜个小圈圈,去探望一位住在海边的朋友——那位六个月之前在开往温哥华的火车上邂逅的男子埃里克。可以说,朱丽叶此行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同时也是跟着非理性的感觉前行。正当她在是否继续古典文学研究并完成博士学位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在火车上邂逅了埃里克,好像是看到了爱情的曙光,听到了爱情的召唤。埃里克跟她谈论那个卧轨身亡的陌生人,缓解了她内心深处深深的负罪感,然后他们一起吃了晚餐,还一起在星空下辨认星座。最后,他们深情吻别。六个月之后,朱丽叶收到了一封埃里克表达相思的信件。理智上,朱丽叶知道她爱上的是一个已婚男子,而且,他不可能离婚,因为他的妻子瘫痪在床,她的爱情好像并没有生长的余地和空间,可是,她还是身不由已地踏上了开往鲸鱼湾的大巴车,尽管在路途中她依然疑虑重重——她怀疑埃里克的感情是否真诚,她不确定自己是否真要见他一面。到达鲸鱼湾之后,在跟着司机去埃里克家的路上,她还在犹豫,心里想着“我不如就回去吧。”到了埃里克的家里,埃里克从太太的葬礼上没有回去,在帮工艾罗的暗示下,朱丽叶又要起身离开;可是,接着,她又坐下不走了,决心等待埃里克回家。本来,她是想着就在鲸鱼湾待一个晚上,甚至只给埃里克打一个电话,可是最终的结果是,她在那里开始了与埃里克长达十六年的同居生活,直到埃里克出海遇难身亡。纵观朱丽叶的一生命运,好像并不完全是她明确的理性判断和选择,而是有一股隐秘的生命力量在推动着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行动。
此外,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命运也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神秘性和可疑性。朱丽叶在从多伦多开往温哥华的火车上邂逅的那个陌生男子,看起来是理性地自主地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可能就某个方面而言,生命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可是,他的死到底是蓄意已久还是一时之念, 他究竟为什么选择卧轨身亡,他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生命经历,我们都无从知晓。朱丽叶的母亲萨拉最终应该是患病而死,可是,我们不知道她患的是一种什么病,只知道她经常会把家里搞得一团糟,然后大哭一场,有时候说话也仿佛是在尖叫。还有,朱丽叶的女儿佩内洛普在二十一岁那年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至于她离开母亲的缘由和后来的归宿,佩内洛普没有向朱丽叶做出任何说明,小说也没有向读者做出任何交代。我们只能在一团团疑云中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推断:她决绝地切断跟母亲的所有关联,肯定会有着她自己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和理由。
纵观门罗的这三部小说,可以说几乎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由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合力促成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人”的合体。
结语
艾丽丝·门罗自从1952年21岁时写出第一篇短篇小说《蝴蝶的日子》开始,至2012年81岁时出版最后一部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后宣布封笔,一生经历了从20个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年整整六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在这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虽然门罗并不喜欢追逐文学潮流,也不喜欢那些在当时看来时髦的花哨的文学创作,甚至主动选择远离所有的主流圈子,但是,她毕竟不能完全与时代隔绝,不能完全身处潮流之外。而且,她一生酷爱阅读,如她自己所言,直到她三十岁,阅读都如同她的生命。她不仅特别喜欢美国南方女性作家的作品,而且也很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威廉·马克斯韦尔的《再见,明天见》等作品。一个作家的文学阅读会潜移默化于其文学创作之中。因此,她的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和潮流的印记。正如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所言,她自己读她早期的小说时发现了一些流行于50年代的写法。所以,我们从她的这三篇小说《机缘》《匆匆》《沉寂》中解读出存在主义的意味,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文学潮流。她在关于女性命运的三部曲小说中对爱情的书写——爱情是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对死亡的叙述——死亡是人的偶然性和有限性的显现,对命运的思考——命运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合奏,都渗透着一种浓厚的存在主义意蕴,因为人类的偶然性、有限性和非理性以及两性之间的对立关系,毋庸置疑都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