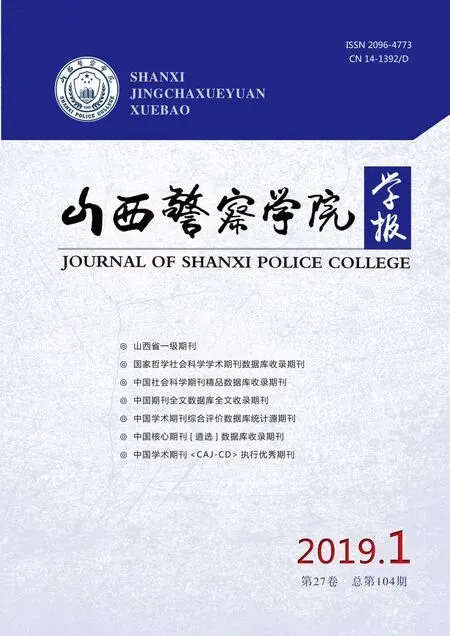“套路贷”犯罪行为及涉黑化问题研究
□潘若喆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套路贷”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违法犯罪模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8月1日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中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套路贷”是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犯罪行为。此类案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犯罪分子往往持有形式上合法的合同、借条等文件,并结合对受害人威逼恐吓甚至非法拘禁等暴力讨债行为,使得受害人惧于也难以维权。最高院及浙江、上海等地纷纷出台了有关通知,对“套路贷”案件的定性及处理方式做出了规定,但都较为原则性,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来明晰“套路贷”犯罪的本质。
一、典型案例——朱某团伙共同诈骗案
2015年起,被告人朱某纠集被告人李某某、程某、袁某某、吴某某、汪某某、顾某某等七人,形成较为固定的团伙,租用上海市中山北路某处房屋,以个人名义对外从事资金借贷业务。朱某系团伙实际负责人,其他被告人均听从其安排和指挥。李某某、程某根据朱某安排充当资金出借方和讨债等,袁某某、吴某某、汪某某主要负责为借款客户拉征信情况、办理信用卡、陪同借款客户看房、上门讨债,顾某某根据朱某授意对借款人名下房产进行非法网签锁定、协助签订借条、房屋租赁协议、看房和陪同讨债等。该团伙与天甘公司、怡智公司一起从事类似的非法放贷业务。
2016年1月,被害人丁某向天甘公司实际借款9万元,但是被要求签订了价格虚高的借款合同,称签订虚高借条是民间借贷的行规,是将不还款之后的违约金等数额一并算入,如果按约还款则无须偿还多余部分,最后签订的借款金额达到28万元。签订合同后,天甘公司遂派人与丁某前往银行走账28万元,丁某取出28万元现金后当场交还19万元给天甘公司。之后丁某正常还款2个月共计2.34万元,2016年4月因逾期未还被认定违约并被索款20万元,丁某无力偿还,于是在2016年5月,被害人丁某被带至怡智公司,怡智公司向天甘公司虚假平账20万元,丁某再一次被骗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并走银行流水70万元。2016年6月因逾期未还而被认定违约并被再次虚高并走银行流水50万元。2016年6月13日,怡智公司将被害人丁某120万元虚高金额债务转单给朱某团伙,朱某团伙向怡智公司表面平账120万元(朱某团伙实际参单42.5万元),丁某被骗签订151万元虚高金额借条并银行走账151万元。2016年7月12日,丁某被朱某团伙逼债还款130万元,但无力偿还,又不堪忍受朱某团伙的威逼恐吓,最后答应出售自己名下的房产来用于还债。
而在朱某团伙的另一起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陈某某也是因同样的“套路”被迫签下虚高金额借条而无力偿还,朱某团伙最终为达犯罪目的而采取了诉讼的方式,企图用这种方法合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但被法院识破,出具民事裁定书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犯罪因此未能得逞。[注]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案号:(2017)沪0101刑初919号。
“套路贷”的“套路”模式可以简要概括为:借贷人来借贷——虚高借条——银行走流水——上门看房或其他租房担保、担保人担保、签订担保合同——故意放少量的款或不放款——故意制造违约——要求再提供担保借钱或强行平账(上述流程再走一遍)——强行讨债或提起民事诉讼或占有房屋或给房子办网签阻止被害人交易——获得非法所得。[1]
二、“套路贷”的行为特征
上述案件一审法院最终认定朱某团伙系犯罪集团,所判处的罪名是诈骗罪,其他相似案件均以诈骗为主罪判刑。然而上述犯罪是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虚假诉讼等系列犯罪行为的集合体,在“套路贷”这种犯罪模式下,究竟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还是有多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还是多个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以一罪论处,这就需要先对“套路贷”的行为特征进行剖析解读。
“套路贷”中,首先可以将相关人员的相关行为划分为相同行为人实施的不同行为与不同行为人实施的独立行为。前者主要会涉及到同一行为人不同行为之间的情形,后者主要解决犯罪集团中共同犯罪将如何处理的问题。对于前者而言,首先必须处理以下两个问题:其一,这两个以上的行为是否都有必要纳入刑法的判断范围中;其二,各个行为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性。[2]
从整体行为上来看,“套路贷”中的犯罪团伙从犯罪伊始便是以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为目的的,这与高利贷行为是不同的。高利贷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而实施的放贷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借款人能及时按约定支付本金和利息来获取利益,因此放贷人不会故意制造违约的情形,借贷人对于自己应还金额都有明确的认识。而“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之实,因此被害人对所约定的高额虚增数额部分是持不用归还的主观认识,但犯罪团伙会用各种手段方式制造违约的情形来达到自己非法的目的。因此,“套路贷”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
从各个行为上来看,整个“套路贷”犯罪过程中有许多细化的行为,如欺骗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去银行取流水、故意制造违约情形、看房担保网签等等,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诈骗行为。但是在不同的案件中又会出现其他不同的犯罪行为,如有的案件中犯罪分子会在制造违约情形后对被害人实施人身上的威胁或限制迫使其变卖资产还款,可能会涉及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等犯罪行为。
(一)诈骗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并存
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同属侵犯财产罪一章,两者中,被告人的主观目的都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侵害的法益均是他人的财产权。其区别在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主观认识不同。从被告人的角度而言,两种行为类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欺诈行为,后者则是威胁恐吓,带有一定的暴力色彩;而从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前者是基于自己错误认识而给付财产,后者则是基于自己的恐惧心理。
例如,在陈寅岗、韩世平等诈骗案[注]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案号:(2017)沪0106刑初892号。中,陈寅岗等人在被害人吕某签订虚高合同后又对吕某实施殴打并以自己持有被害人借条及相关证件为由进行敲诈勒索,未果后进一步采取虚假诉讼的方式来谋取非法利益。在此案中,被告人虽然实施了诈骗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但两种行为均指向同一法益侵害事实,因此不能以数罪论,以避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这两种行为单独分离来看都是独立的犯罪行为,无法概述为事实上的一种行为,因此不属于想象竞合犯在内的实质的一罪。同时这两罪之间没有规定相通,自然也不能评价为法定的一罪。本案中,涉案金额约为25万元,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属于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中“数额巨大”的一档,法定刑幅度相同,因此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重行为与轻行为之分,不成立吸收犯。
因此争议焦点在于两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有观点认为,“套路贷”有相对固定的运作模式,犯罪嫌疑人对该行业的操作手法应有较强的心理预期,其使用每种手法虽不具有必然性,但必定为常用的手段。虽然普通群众没有对“套路贷”形成深刻的认识,但民间借贷市场内对该类型借贷的“底细”十分清楚,知道“套路贷”不以单纯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套路贷”的作案手法已经达到“类型化”的特征,达到了牵连关系的通常性和伴随性,[3]因此认定两者为牵连犯。但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这种观点避开了对于“套路贷”犯罪的实行行为的认定。若本案中被害人吕某签订的虚高金额合同为1000万元,其在被被告人敲诈勒索后基于恐惧心理给付了这笔财产,这种情形下,被害人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有着清楚的认识,也知道自己并不实际欠款那么多,但他为了自身安全考量不得不给付了这么多的财产,因此被告人的实行行为应当是敲诈勒索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论处。但如果认为构成牵连犯,依照牵连犯“从一重从重”处罚规则,本案应当选取法定刑幅度更高的诈骗罪为最终罪名,由此会出现相悖的情况,牵连犯的观点难以成立。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套路贷”中被告人选取的犯罪实行行为比较随意,只要能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会去区分什么是目的行为什么是手段行为,同时也因为诈骗与敲诈勒索两罪处于互斥关系,对于欺骗与胁迫兼有的场合,只能构成诈骗罪或勒索罪一罪,而不可能出现任何竞合,[4]因此需要结合具体事实加以认定。在兼具“欺诈”与“敲诈勒索”两种行为的“套路贷”案件中,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欺诈——胁迫”型,二是“欺诈——胁迫——诉讼诈骗”型。前者以敲诈勒索为实行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签订虚高合同的诈骗行为为敲诈勒索罪的预备行为;后者以诉讼诈骗为实行行为,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单独评价为未遂犯罪,但因为指向同一法益侵害事实,不作另罪定性评价,只作为量刑的参考事实之一。
(二)虚假诉讼行为的判定
在上述陈寅岗、韩世平等系列诈骗案中,被告人也曾多次使用虚假诉讼的方式意图通过法律程序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满足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同时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诉讼诈骗的模式,也构成诈骗罪,依据《刑法》307条之一虚假诉讼罪第三款规定,以处罚较重的诈骗罪为判处罪名从重处罚。
但值得探究的便是中途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代理人应当如何界定的问题。在陈寅岗案中,律师曹某某因为在多次诉讼中均担任陈寅岗犯罪团伙的诉讼代理人并为之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被认定为是诈骗行为的共犯,即一种承继的共同正犯。那这种情形是否适用于所有“套路贷”案件?
首先要明确诉讼代理人是否属于犯罪集团的一份子。依据《刑法》第26条第二款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因此,若诉讼代理人是在中途被聘请,而非开始即合谋,则不满足犯罪集团的组织固定性。但如果同一诉讼代理人多次被同一团伙聘用,那么可以推定其对于此类犯罪的模式和流程比较熟知,并且主观上并不抗拒,视为默认加入。
其次有诉讼代理人参与的“套路贷”案件中,最后的诉讼诈骗行为往往才是整个犯罪的主行为,被害人所遭受侵害的财产法益与律师的虚假诉讼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但这里需要对诉讼代理人的犯罪目的进行界分,因为如果认定诉讼代理人构成承继的共犯,那么就需要满足其与其他犯罪分子的犯罪目的相一致的要求,这也是成立共犯的基本条件之一,即诉讼代理人应当持以诈骗为方式来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主观故意,而非单纯完成委托人委托为目的。在如何判定的问题上,最高法解释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但上海以及浙江有关“套路贷”的解释意见中列举了多项成为“套路贷”共犯的具体情形,其中一项均为:“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的,具有以下情形之一,以共同犯罪论处……4.协助以虚假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从这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对于此种情形的判定是主观明知+客观行为的模式,此处的明知,笔者认为,不能严格从文义上来解释,必须要求诉讼代理人明确知道所代理的是“套路贷”案件,而是只要对相关文书中记载内容的虚假性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委托人是利用这份虚高金额的合同来谋求非法利益即可。这样有利于打击诉讼代理人的不法行为,减少犯意出现的可能性,符合现在对于严厉打击“套路贷”犯罪的刑事政策要求。
(三)其他类型犯罪行为
在“套路贷”的犯罪中,往往会伴随着其他类型的犯罪,如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依照上海与浙江两地出台的指导意见来看,实践上对于这种情形往往是以数罪或依照重罪来处罚,但如何区分一罪与数罪并没有明确说明。
从行为外观上来看,这些行为各自具有一定的形式独立性,往往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实施的,因此并不具有连贯性,并且行为侵害的法益也各不相同,如果这些行为造成的结果达到了刑法标准似乎应当以数罪论处为妥。然而行为内核上来看,这些行为都是指向同一个犯罪目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此彼此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但这些行为难以概而括之地评价为一行为,因此仍然属于多行为侵犯多法益的情况并且刑法上并没有对这些行为进行结合,即使构成一罪也只可能构成牵连犯。
要判断是否构成牵连犯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来判定牵连关系存在与否。[5]从客观方面而言,牵连犯中的数行为之间应当有主从之分,这样才能进一步区分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在“套路贷”中,多数情况下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侵害后果都是较为轻微的,是为了激起被害人的恐惧心理或迫使其接受虚高合同而实行的伴随行为,但如果某一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过于严重,如致人重伤等,则原本的从行为升格为另一独立的主行为,以数罪论处。从主观方面而言,需要各个行为都是出于同一犯罪目的而实施的。如果在案件过程中,另起犯意而为的犯罪行为应当视为独立的犯罪。
综上而言,如果在“套路贷”犯罪中,某一行为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从属于“套路贷”诈骗行为,那么可以将其视为手段行为,从而将整体评价为牵连犯一罪进行评价,反之则数罪并罚。
三、“套路贷”犯罪组织与黑社会的关系界分
在“套路贷”犯罪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到许多暴力的因素,再加上其分工明确、层级鲜明的组织特征,似乎这种组织类型与黑社会组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笔者翻阅相关的判例,并没有一个判例将“套路贷”犯罪定性为黑社会组织犯罪。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司法实践并不将这种犯罪模式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呢?下面将从四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一)组织特征
《刑法》第294条第五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这一条是成立黑社会组织的基础条件。“套路贷”犯罪团伙具有自己较为稳定的组织结构——往往是以设立的借贷公司为根基,日常经营活动的场所固定,人数较多且分工明确,办事流程较为固定清晰,并且所属成员都听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安排,人事变动也并不具有随意性,因此在组织特征上基本符合黑社会组织的要求。
唯一会有差别的地方是在于人数具体数量的界定上。2015年最高院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座谈会纪要》)中,对黑社会组织的人数限定为“一般在10人以上”。同时,在确定人数时应当明确组织中的人对于组织实施的犯罪行为有统一明确的认识。如果是被雇佣来处理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并不知晓组织的犯罪行为则不应纳入人数计量。
(二)经济特征
《刑法》第294条第五款第二项规定:“(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而2015《座谈会纪要》中,将一定经济实力解释为“20-50万幅度内依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自行划定一般掌握的最低数额标准”。“套路贷”的犯罪团伙是以借贷后签订虚高金额合同来谋求非法利益,往往在签订合同后即前往银行取现走流水,这部分涉及的金额往往超过上述最低数额标准要求,因此“套路贷”团伙满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三)行为特征
《刑法》第294条第五款第三项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首先是行为性质,要求具有一定的暴力性。在“套路贷”犯罪中,并非所有的犯罪类型都参有暴力因素,有一些仅靠欺诈签订虚高金额合同以及诉讼诈骗的方式即完成了犯罪活动。2015《座谈会纪要》中提及:“因此,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有一部分能够较明显地体现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本特征,否则定性时应当特别慎重。”所以如果“套路贷”团伙并没有很明显的暴力特征,那么在行为性质上难以评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其次是行为数量,要求“多次”性。这里的“多次”不仅要求犯罪次数多,也要求犯罪种类也要多。2015《座谈会纪要》中即写明“涉案犯罪组织仅触犯少量具体罪名的,应结合其他特征综合判断,严格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往往会涉及到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涉及到财产性利益纠纷,还包括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等其他类型的犯罪,犯罪行为复杂性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大特征。而“套路贷”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涉及其他罪名,但大多数情况下仍以诈骗罪为主要犯罪类型,因此如果犯罪行为种类过于单一则需要审慎考虑。
(四)危害性特征
《刑法》第294条第五款第四项规定:“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着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危害性特征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要有一定的行业控制力或影响力,而这一点是“套路贷”团伙所不具备的。第一,“套路贷”是被害人主动找上门寻求借贷,而后犯罪团伙再实施相关犯罪行为的犯罪类型,犯罪团伙并没有强制迫使他人进行借贷的行为与能力。第二,“套路贷”团伙本质上是民间的小额借贷公司,这些公司在借贷行业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所涉及的案件金额对于个体而言并不算小数,但就金融借贷行业来看并不达到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地步,因此危害性程度并达不到构罪条件。第三,“套路贷”犯罪往往针对的是单个借贷个体,彼此之间并没有一定的联系,因此针对的对象具有分散性的特点,难以形成区域范围性的影响力。综上而言,“套路贷”难以满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性特征要求。
“套路贷”犯罪本质上还是以诈骗为核心要素,可能伴随的暴力行为大多是为了帮助诈骗行为的实现为目的的。因此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主动寻求暴力并以暴力为首要谋求利益的形式有着本质区别。但“套路贷”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套路贷”团伙犯罪已经有涉黑化的倾向,因此需要对于这一变化额外重视。
四、结语
“套路贷”犯罪是近几年新兴的犯罪类型,在具体定性时要注意对不同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分。在诈骗与敲诈勒索行为并存且指向同一犯罪目标时,因为这两种行为有互斥的特点,因此需要结合事实具体认定,确定犯罪的实行行为,而后依照该行为进行定性。在诉讼代理人进行虚假诉讼时,如果对案件的犯罪性有一定认识,即可依照有关规定以“套路贷”的共犯论处。而其他犯罪行为则需要考虑是否与诈骗行为有牵连关系,如不满足则以数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