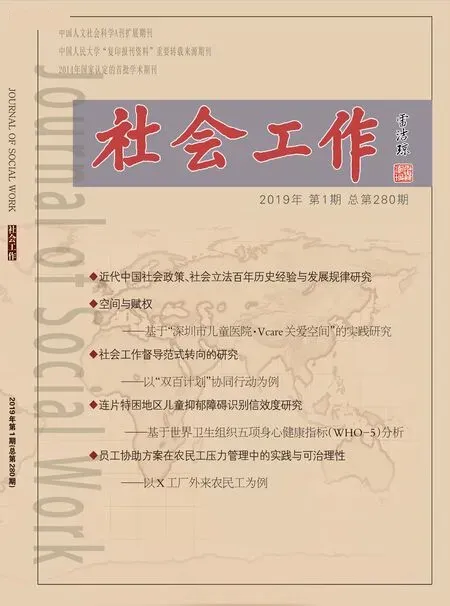社会工作督导范式转向研究
——以“双百计划”协同行动为例
廖其能 张和清
“双百计划”①“双百计划”的全称:粤东西北地区“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2017年至2021年)。“双百计划”在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山、开平、恩平等地建设运营200个镇(街)社工服务站,开发近1000个专业社会工作岗位,孵化200个志愿服务组织,培育10000名志愿者。详见:2017.3,《省民政厅王长胜副厅长在潮州市第六届”岭南社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双百计划”宣讲会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shuangbai-plan.org/protal/5559/。是广东省民政厅促进广东省社会工作区域均衡发展②截至2016年底,广东省持证社工近6万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1254家,社会工作投入总金额超过60多亿元,这些指标都居全国第一,然而粤东西北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数1104个,仅占全省7%;年度资金投入2330万,不足全省2%。”详见:2017.6,《广东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卓志强同志在广东社工“双百计划”推进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shuangbai-plan.org/protal/5771/。的重要举措。为保障“双百计划”专业性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广东省民政厅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双百计划”督导和培育发展社工与志愿组织,在粤东西北15个地市分别建立督导中心(卓志强,2017),形成“‘双百计划’项目办-15个地市督导中心-200个镇街社工站”三级网络支持系统。
被视为社会工作的“助产士”的督导,因其致力于专业化,深深地融入社会工作自身专业项目的结构中,作为发展的基本实践和配置(Liz Beddoe,2015),社会工作督导作为在社会工作实践上的重要性一直备受国际重视(Kieran O’Donoghue,2015)。
然而,“双百计划”专业共同体(三级网络)更偏向将“督导”称为“协同行动的‘督导’”,将“督导者”称为“协同行动者”或“同行者”(张和清,2017)。“协同行动”的概念在“双百计划”的脉络里由项目总督导、中山大学教授张和清提出,自项目启动以来,“双百计划”的督导团队一直践行和探索这种“协同行动”的理念。然而,“协同行动”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被系统地阐释和研究。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传统的社会工作督导范式是否适用于“双百计划”所探索的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双百计划”提出的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范式的意涵是什么及其可能性如何?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社会工作督导从美国早年的慈善组织会社以行政督导起家。20世纪初开始,社会工作督导从机构的训练转入大学的教育,开始有了自身的理论和文献。在30至50年代心理分析等个案工作流派盛行时,社会工作督导的形式与结构以个案工作为取向。从50年代社会工作发展为成熟专业开始,社会工作者争取摆脱长期个案工作式的督导,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在80年代起愈来愈要求责信的时代,督导又回复其最初的行政取向,确保社会福利资源的有效运用(Tsui,2008)。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受专业化力量及外在经费资助环境所左右。然而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不同专业化发展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对专业化和督导范式的看法截然不同。
作为美国慈善组织会社运动代表人物,玛丽·里士曼(Mary Richmond)推动科学化的慈善,基于其在慈善组织会社20多年工作和研究的经验,开创了社会工作个案工作方法,推动社会工作迈向了符合实证科学要求的专业发展道路(童敏,2009;何雪松,2004)。社会工作督导根源于慈善组织会社,从行政督导开始,逐渐发展出行政性、教育性和支持性的传统社会工作督导的三大功能,督导成为了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一项公认的制度。在实证科学潮流下,个案工作的督导以及个案工作式的督导成为了发展的主流甚至是一种传统,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督导主要指的就是个案工作的督导”(Kadushin&Harkness,2002:15)。
然而,在传统的社会工作督导范式中①所谓传统社会工作督导是指:督导者的三重功能,即在层级机构背景下每次为一个人提供教育性的督导(也称为临床督导)(Tsui,2005),支持性督导和行政督导(J.HAIR&O’DONOGHUE,2009),带有治疗性质的督导过程被许多社会工作员拒绝,他们认为“对个案工作者进行个案工作的作法侵犯被督导者的隐私”(Kadushin,1992b等,转引Tsui,2008)。
与此相反,美国睦邻组织运动代表人物简·亚当斯(Jane Addams)对科学、理性的专业化并不热衷,认为专业化只会导致社工与民众的疏离,主张采取“非科学”的直接融入(immersion)的方式,建立平等而非指导性的关系,站在平民的立场,运用民众文化的力量,促进社会改变(童敏,2009)。有学者研究发现,文献中很少看到督导在睦邻组织运动中的运用,这一方面是因为睦邻组织运动的社区工作者难以接受“督导”这一沾染了等级色彩的观念。这正如库兹克(Kutzik,1977:37)所言:对于睦邻组织运动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要的“是协商,而不是督导”。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工作处境的难以界定以及探索性的性质,使得传统的督导模式难以奏效。Kadushin(2002)指出,实际上社区工作者的督导需求相比个案社会工作者更甚,只是传统督导文献以个案工作为主流,难以为小组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提供任何可资效法的互动模式。
特别是到了强调责信的时代,社会工作督导有时被看作对一线社工的一种监控机制,这会降低社工的自发性与创造力(Tsui,2008),对于富于平等主义精神的社区工作者来说,更加难以接受。Tsui认为社会工作督导不该只是“指导”还应“鼓舞”社工,社会工作督导最重要的工作是:传承其对社会工作使命与愿景的热情(passion)给被督导者,如此一来,社会工作督导就成为资深社会工作员与社会工作新生代之间使命感的共享,那么,社会工作督导也就不仅仅是专业实践(professional practice),更是道德实践(moral practice)。
那么,社会工作督导到底是如个案工作督导那样强调自我完善和专业技巧,还是如责信时代所强调的行政问责和情绪处理(回应职业倦怠的问题),还是一种使命感共享以及愿景热情传递的道德实践?不同社会工作实践范式或许会有不同的偏好。
“双百计划”倡导回归社会工作的“初心”,效仿睦邻组织运动扎根贫民社区,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下简介“三同”),探寻个人困扰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发掘、利用社区的优势和资产,与社区民众共创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最终实现社区自治与善治(张和清,2017)。既然期待“双百社工”与民众平等地互动并且相伴同行,那么“双百”的督导是否也应该与社工平等地互动,共同成长,相伴同行?笔者认为,所谓“道德实践”,简单来说就是将相信的东西做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下的督导应该偏向于一种道德实践。
我国内地关于社会工作督导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主要聚焦于对ITP(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赋权、AGIL模型以及叙事治疗等理论在督导中应用的探讨(张洪英,2017)。与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相关性较大的赋权理论,在督导中的应用分为两个研究脉络。一个是以严樨(2013)为代表,侧重于建构赋权视角下社会工作督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虽然强调督导者与受督导者建立协同伙伴关系,有意识地为受督导者消除无力感,但在赋权的过程中(包括辨别无力感和培养各种能力)依然强调督导者的中心角色。另一个研究脉络是姚进忠(2010)尝试将批判教育学的理念引入社会工作实习督导中,倡导民主的督导关系、对话式督导的教学模式以及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能力视角。然而,在职督导与实习督导却有所不同,实习督导以教育为首要任务,在职督导更加突出对社工的全面支持,以应对工作难题,保持士气,完成服务目标(马丽庄等,2013)。总的来说,两位学者都对赋权相关理论在社会工作督导实践上的应用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探索,然而两种模式依然只是传统个体督导、团体督导等“面对面”谈话的方式,但并未强调督导者进入行动的脉络中,与受督导者的相伴同行。由此可见,在我国内地,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仍然缺乏可资效法的、“协同行动”的督导范式。
既然睦邻组织运动的社区工作者要的“是协商,而不是督导”,那么,倡导回归初心、重拾睦邻组织运动扎根社区传统的“双百计划”,将“督导”称作“协同行动”则不足为奇。而且,“协同行动”的意涵不仅仅是“协商”,更重视共同的行动,推崇的是一种道德实践。
总而言之,在采取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实践范式的“双百计划”脉络里,“协同行动”的社会工作督导范式转向,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督导范式多样性探索的一种新尝试。
在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的文化敏感非常重要。文化敏感不仅要求社工对在地的文化敏感,因为“发现文化差异不难,难的是如何将自我先从社会和教育建制的专家里解放出来,真正以一种非专家的身份与村民进行对话,促成彼此之间的意识提升,发掘我们彼此的能力”(古学斌等,2007:177)。更重要的是,社工还要察觉社会工作的实践正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一样,是在文化负载(cultural laden)和理论负载(theoretical laden)下进行的,如果不审视文化识盲和专业限制的陷阱问题,将会对民众造成伤害(古学斌等,2007)。社会工作督导(以下将“社会工作督导”统称为“协同行动”)作为社会工作实践者的重要角色之一,具备文化敏感显得尤为重要,协同行动者对其文化负载和理论负载时刻保持自省精神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否则容易陷进与社工“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和自上而下单向的教学或管理过程,影响到协同行动的成效。
保罗·傅雷罗(Paulo Friere)用囤积(banking)的概念来描述传统的教育和师生关系。而在囤积教育概念中,知识是一种由自认为博学的人赋予给他们认为一无所知之人们的恩赐,他们否认教育与知识是一种探究的历程。传统师生关系是一种“主客二元”的讲述(narrative)性质,学生被视为一个容器,教师可在其中“塞满”东西,“塞得越多”和“装得越多”分别被看作是否为“好老师”和“好学生”的标志(Paulo Friere,2003:107-108)。古学斌(2011)进一步指出,这种教育方法压抑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如创造力、思考能力、反思能力等),使得学生变得缺乏社会改变的想象力,也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
Paulo Friere(2003:117)认为“提问式的教育”可以打破囤积式教育中自上而下的模式,透过对话的发生,打破师生的“主客二元”对立,师生成为:同时身为学生的教师(teacher-student)与同时身为教师的学生(students-teachers)……教师与学生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同负责任。
刘晓春和古学斌(2007)引用批判教育学将教育视为文化政治实践场域,提出社区发展是文化政治实践的说法,并将它称为能力建设的社区发展模式,提倡在能力建设社区发展中,以社区民众意识觉醒为实践目标。能力建设想象的社区发展里,能力建设被看作是“三向”的,是教育者、学生/社工、民众从对话式教/学情境中,知觉自己的主体,认清各种社会知识/权力关系对知识建构的影响,在彼此对话中建构社区发展的实践知识,三者以主体身份共同参与社区转化的行动。
“双百计划”将社区发展视为其中一项很重要的专业目标来追求,因此,能力建设的社区发展模式对“双百计划”的督导模式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协同行动者推动下的能力建设中,要注重主体性的知觉,以及共同行动、对话和反思这些关键元素的运用,以最终促进社区的转化。
笔者认同社区发展过程中最终应该实现“协同行动者—社工—民众”三重能力建设的状态,然而要达致三重能力建设,需要先进行“协同行动者—社工”的双重能力建设,当社工的能力建设起来后,他/她同样能够与民众进行双重能力建设,最终实现三重能力建设。因此,本文主要是指“协同行动者-社工”的双重能力建设。
总而言之,在“双百计划”扎根社区的实践范式下,在粤东西北15个地市、200个镇(街)多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田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要求协同行动者应该具备文化敏感,审视文化识盲和专业限制的陷阱问题。在价值层面上,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应该成为资深社工与社工新手之间对使命感的共享和对愿景热情传递的一种道德实践。而在知识层面上,协同行动者应该保持对知识生产和教/学权力关系及其后果的警觉,“互为师生”,与社工一起共同生产社区发展的实践知识。而在实践层面,协同行动者必须进入行动者的脉络里,与社工一起开展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并通过行动、提问式的教与学、对话和反思,知觉相互的主体性,在行动与反思的循环往复中实现“协同行动者-社工”的双重能力建设。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中的“实践者行动研究”(实践者与研究者“合二为一”)。行动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集研究、教育和实践于一身,是指“行动者对自我,对自我所处之社会位置、情境、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结构,对自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或实践,以及或对自己行动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主研究”(古学斌,2017:73)。由于本文研究的议题具有探索性,而且笔者既作为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行动者,更是一位协同行动者,透过对自身行动的自主研究与本文研究主题最为贴切,因此最适合运用行动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以笔者协同行动的HC社工站为例,对一年半以来协同行动该站点的完整过程进行行动研究。笔者平均每月对站点进行1-2天实地“过夜式”(即留在当地吃和住)的协同行动,另外还包括“线上”和电话协同。本研究的材料包括田野笔记、协同行动记录表、协同行动反馈表、社工的总结报告、社区研究报告等一手材料。出于匿名性考虑,本文对研究中出现的名称进行了化名。
本文案例选取的“双百计划”社工站位于广东省西北部、与广西省接壤的Z市H县,站点实践场域属于传统的城乡社区,既保留着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习俗,当地民众使用其本土语言进行日常交流。同时也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表现为传统行业的衰落,生计的不可持续,以及守望相助等文化价值难以为继等。
社工站配有7名社工。从社工上岗前的专业结构来看,有5名社工来自社会工作相关专业,1名来自外语专业,1名来自汉语专业。其中2名社工持有中级社会工作师证书,4名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从社工上岗前的经验结构来看,3名社工有6年珠三角社会工作经验(属于返乡资深社会工作者),1名社工有2年社会工作经验,1名社工应届毕业,1名社工在残联从事康复工作8年,另外1名社工从事残联办公室工作4年。总的来说,站点属于资深社工与社工新手混合的团队。
关于行动研究者在实践中的角色和位置。本文的第一作者是:HC社工站的协同行动者,但对当地的文化和方言并不熟悉;虽有农村生活经验以及在珠三角城乡结合部开展青少年社区社会工作的经验,但缺乏真正驻村的社会工作经验:从事社会工作一线、管理和督导工作10年后,2018年考取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与此同时保持每月1-2天对HC社工站的实地协同行动。而本文的第二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具有20年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践与研究的经验,是“双百计划”项目总督导,同时也是本文第一作者的硕士导师。在“双百计划”一年半的探索历程里,我们对“协同行动”的理论概念有着较多的深入交流与探讨,并共同完成本行动研究论文的构思与撰写。
三、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过程分析
基于笔者针对HC社工站一年半以来协同行动过程的梳理与观察,下文将论述在面对经验结构与专业成长需求多元的社工团队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区处境时,笔者是如何寻找到协同行动的方向,并“深描”协同行动以实现双重能力建设和社会工作目标的过程。最后,从案例经验中反思协同行动的特色与难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寻找协同行动的方向
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模式对于站点所有社工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尝试,社工们表现得既兴奋又迷惘。社工L表示“我加入‘双百社工’之前在残联从事康复教育已经八年了,……初转换社工,充满了新鲜感,处于兴奋状态,很投入有激情。”社工们在走访中“看到村民在拔草、掰玉米粒等,主动协助提供帮助,一边倾谈一边劳动”,开启了驻村的工作模式。而有着多年城市社区综合服务经验的返乡资深社工Y却分享:“双百入职初期,驻村模式跟综合服务运营模式的区别在哪里等等一系列的困惑一直难以理顺辨别清楚”。另一位资深社工C也说“因为现在的工作方式与之前在珠三角做社工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很多工作做得还不足,我感觉还达不到‘双百’的专业角色要求,怎么说呢,就是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张教授(张和清教授)说的‘有温度’”。看到社工们既兴奋又迷惘的情况,而且团队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结构差异性较大,那么协同行动的方向是什么?应该如何协同?是笔者急需考量的首要问题。
在前期的协同行动中,笔者发现社工团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社工,特别是资深社工受固有经验和思维定势影响,没有充分投入到扎根社区的驻村、“三同”中,而是很希望站点能够尽快步入规范化的“清晰”管理。社工C在研究报告中的反思清晰地道出了这种困境:
那时原有固化的工作思维和方式限制了自己:首先是情不自禁就开始找规范找套路,搜索各种管理条例和文书表格,几个人更多地说以前的服务怎样,没有切实按照项目办的指引去践行探索本地的社会工作;其次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模式,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进村入户走访,但是欠缺‘三同’,村民叫吃饭,也不好意思去吃,总就是外来人的感觉。
资深社工来到一个新的工作情境中,他/她们的前置专业经验既是项目前期工作的优势,有助于站点管理的规范和团队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如果缺乏文化敏感性,不对其知识和经验加以审视、反思和转化的话,也可能成为影响其继续成长、探索专业新的可能性的“绊脚石”,尤其是在对待与当地政府互动关系及社会正义等议题时变得过于谨慎。在2018年7月下旬第一次协同行动的时候,社工们向笔者说起社区内居住着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水上人家”,表示这个群体里面存在很多问题,比较“敏感”,不清楚是否应该继续关注和跟进。笔者通过提问继续了解更多的信息:据社工了解,随着水上运输业的衰落,2001年H县水运公司宣布解体,船队职工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上岸后的”水上人家”面临生活习惯改变的适应问题、再择业问题和社区管理及卫生治理等问题。笔者问社工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群体“敏感”。社工们表示因为刚刚入职“双百计划”来到社区,需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认可才能立足,如果社工对此群体的关注和介入激起了更大的矛盾,将会影响社工能否“站稳脚跟”。笔者很能明白社工们的担心,他/她们是为社工站的“大局”和长远利益考虑。虽然笔者并不清楚船队解体带给”水上人家”的冲击是什么,以及目前是否已经缓解或妥善解决。但是听社工们的初步描述,这个群体很值得关注,从社会正义的价值和“弱势优先”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社会工作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对象。如果还没深入了解便畏惧是否“太敏感”而却步(更谈不上介入)的话,是否为时过早?
第二个特点是:资深社工在站点前期工作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而非社会工作专业背景和刚毕业的社工(下称“社工新手”)则显得较为被动,专业自信不足(或称专业“自卑”),更希望资深社工的带动和指引。社工L回忆说:“刚开始在GT村搞活动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参与者的角色,不敢提出意见,就怕说错了,同事分配我什么工作就做什么。”然而,这些社工新手虽然缺乏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经验,并显得被动,但笔者发现她们有着很高的可塑性。在2017年9月,社工要去村里了解祠堂文化,由两位社工新手来主导访谈过程,她们表示很迷惘:“头脑一片空白”。于是笔者先跟她们讨论了访谈提纲,并陪伴她们一起进村访谈。过程中,笔者鼓励社工成为访谈主角,而笔者从旁协助,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不懂当地语言,另一方面笔者也不希望成为主导的角色。笔者发现她们能用流利的当地语言与村中“达人”交流,谈笑风生之余,不忘回归访谈主线。笔者发现这些社工新手如果有相对充足的准备,并有人给她们鼓励且一起同行,能够取得不错的行动效果。后面笔者及时跟她们做行动的总结和反思,她们很快就领悟到访谈的要义。
通过前期协同的参与式观察,笔者寻找到未来协同的方向:培养资深社工的文化敏感性,协助他/她们审视和觉察自身的文化负载和理论负载对工作开展的影响,将前置经验进行合适的转化,并在新的实务情境下继续成长,建立契合本土脉络的专业知识体系。而对于社工新手,则是鼓舞其保持情怀和“初心”,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和经验,培养其专业能力,增强专业认同和自信。
1.社工的转变
笔者一直尝试探索一种“行动-提问-对话-反思”的协同行动策略,以期带动社工们以及笔者自身的专业成长。关于是否需要介入“水上人家”群体的探讨,成为笔者在HC社工站协同行动的一次不错的开始。
当共同讨论决定继续关注这个群体后,笔者便与社工们一起来到“水上人家”聚居社区,成功地与巷口的阿姨“搭讪”,并在阿姨的带领下走到巷子深处,以竹编文化为切入点与其他阿姨打开话题。这位阿姨还邀请我们到她家作客,介绍”水上人家”的历史文化和社区问题。这次社区走访完,我们一起反思行动经验,社工M反思到自己存在“自我设限”,认识到不能一开始就假设和判断这个群体“敏感”不能介入,而是要先行动和感受。
但社工们真正大的转变,是从他/她们阅读笔者在2017年9月4日撰写的一篇以HC社工站为其中例子的行动研究文章①文章题目为《社工的起步:社会情怀与专业能力,孰轻孰重?——“双百”协同行动的观察》,2017年9月4日发表于“双百计划”公众号,主要论述如何看待上岗时资深社工的前置经验和社工新手的情怀在项目起步中的作用。开始。社工们表示:“(文章)使我们受到了冲击,……我们开始进行了自我反身性研究,才发现急于展示专业性,进行规范化的站点管理运作,反而忽视了用心和耐心去融入所在的社区,也使我们自己的心碰了壁。我们决心改变……”而在社工们改变和成长中,“双百计划”专业课程,笔者发起的对相关理论概念的探讨,以及身体力行地一起驻村、相伴同行,成为重要的“催化剂”。从2017年10月份开始,社工们开始尝试突破“自我设限”,调整“上班”和“下乡”的模式,放下身段,走进田野,践行“三同”的精神,很快便与村民打成一片:社工在协同记录中表示“通过与廖sir②社工对本文第一作者的称呼一起和村民同劳动(与三婆同劳动,一同拔青菜,并搬菜回其家),更易融入村民的生活当中,用心的陪伴,村民也会热情对待。”因此,社工们对“双百”驻村工作越来越有认同感,社工L在上岗半年总结中分享到“进到村庄有回家见到亲人的感觉!”,并且自称变得更有自信:“恢复自信了,变得比较主动,能给出很多的建议”。
除了对驻村的认同度和投入度的转变外,社工们对于解决社区问题中自身的角色定位也有很大的理念转变。“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环卫工囤积废品遭邻居投诉)做的有些事情有点过于着急,在这次的囤积垃圾的问题当中,我们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处理这个问题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在笔者的协同下,社工领会到不能一厢情愿地把解决社区问题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而忽略了其他主体的参与,开始扭转作为问题解决的唯一主体的“主客二元”的思维,从而降低自身在社区工作中时有的无力感。
正是因为资深社工从过去工作经验和思维定势中转换过来,发扬过去经验的优势的同时,真正投入到驻村工作中,而社工新手也在团队的鼓励和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增强了信心,才能够更好地与村民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对村庄/社区更容易做到“知根知底”。社工们在笔者建议下,一边行动一边整理和反思行动信息,从而推动新一轮的行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社区评估的行动研究。经过笔者持续一年的现场跟进,以及与社工5、6次的网络批注和修改,2018年8月,社工站最终撰写了一份接近8万字厚重的行动研究报告,并据此与当地政府、村/居委、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商讨制订出站点的“五年愿景、三年规划、年度计划、月计划和周计划”(简称“53111”)。
而令人欣喜的是,社工经过一年对”水上人家”群体持续介入,与”水上人家”“打成一片”,挖掘出”
(二)协同行动与“我们”的转变
水上人家”的独特文化(饮食、船歌对唱、竹编等),并在元宵节通过船歌对唱和传统小吃的制作、试吃等活动将整体社区激活了,“活动现场围观居民纷纷用手机拍小视频分享给远方的亲友”。与此同时,社工也摸清了居民“怕出头”、没有社区领袖的社区治理困境。最后,“水上人家”的介入方案成为社工站“53111”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各利益相关方(包括住建局、镇社会事务办、居委和船队等)的高度认可。负责“水上人家”版块工作的社工M告诉笔者,社工站联同相关部门一起向H县住建局成功争取到“水上人家”廉租房一楼尚未出租的铺位作为水上居民公共活动空间,社工与水上居民商量决定将公共空间起名为“水上文化活动室”,使其具备展览室功能,以后会将运输船模型(居民在社工鼓励下新做的)、船队老照片等展览出来。同时,“水上人家”妇女将用其独特的竹编工艺把活动室牌匾和社工站的名字编织出来挂上活动室墙上。
由此可见,通过一年半的驻村、“三同”和行动研究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认可,赢得了较大的专业自主空间,社工团队也实现了较快的成长,HC社工站被评选为“双百计划”省级核心示范建设点和Z市年度的优秀站点。
2.协同行动者的转变
那么,既然称作双重能力建设,一年半的协同行动到底给笔者带来了什么收获呢?笔者主要从两大方面来分享自己的成长。第一,笔者从社工们的工作中更深刻地理解了扎根社区的社会工作的具体策略、方法和效果。刚开始接触“双百计划”的扎根社区的实践模式时,笔者虽然认同其理念,但对应该如何具体操作,以及这一模式在粤东西北地区实践的效果将会怎样,还不够确信。因此一直以来,笔者是抱着一种共同探索的心态与社工们相伴同行。然而,随着社工们的逐步投入与适应,并渐入佳境,笔者体会到社会工作实践范式的多元性,逐渐认识到扎根社区和文化行动的重要性,并总结出一条清晰的从文化切入到社区社会关系重建的介入路径。
第二方面的成长是,笔者也逐渐清晰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应该如何进行,“行动-提问-对话-反思”的协同行动策略是笔者最大的领悟。笔者反思自己以往在珠三角地区虽然也秉持着一种“启发式”督导的理念:通过有目的性提问的方式促进受督导者的自我导向的学习,即扶助受督导者善用其人生经验,从实践经验中学习(马丽庄等,2013)。但由于受项目评估要求等种种因素的影响,笔者最终甚少能够走进社工们的行动脉络里面,跟社工们一起协同行动,更多只能通过面谈和文书反馈的方式给予社工们支持。而在HC社工站一年半的协同行动探索,让笔者对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理念和操作方法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确信。
(三)协同行动反思
资深社工从城市转到农村,社工新手从其他专业或行业转到社工领域,确实需要经历一个调适和转化的过程。但他/她们的前置经验和思维定势的转化并非易事。在这种背景下,他/她们需要的并不是专业知识的“囤积”,而是在本土实践的基础上与专业理论对话,从而建立起契合本土脉络的专业知识体系,这正如张和清所称的“本土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强调立足本土的优先性和专业发展的内生性。
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范式,是文化敏感的,并且采取“行动-提问-对话-反思”的协同行动策略。虽然笔者有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但并没有预设可以将已有的知识体系和过往的实践经验直接照搬到“水上人家”的介入,直接告诉社工应该如何做,而是提议要向社区学习,充分考虑社区的社会处境和文化脉络。而除了协同行动者应该具备文化敏感外,笔者更会通过共同行动及反思,引导资深社工们保持文化敏感性,审视自身的文化和经验对其行动的影响。资深社工Y在年度总结中反思道“以往的服务经验是把双刃剑,很容易就会把服务思维带偏离驻村模式的轨道。……正是由于有十多年对于社会工作的认识,容易使自己在社会工作层面有‘我很厉害’的错觉。所以我要时时提醒自己笃实基础……而且要学以致用,不要眼高于顶”。可见,这位资深社工从一开始受固有经验和思维定势的束缚到能够时刻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学习与调整。而“行动-提问-对话-反思”的协同行动策略很注重在行动与反思的循环往复中共同寻找解决实践困境的有效方法,生产出契合本土情境的专业实践知识,很好地回应到社工们的实践困境和成长需要。面对上述”水上人家”这个弱势群体的种种困境,社工一开始由于“自我设限”的原因而想“知难而退”,但直到协同行动者身体力行地带领社工们一起走进”水上人家”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协助社工理解和解读弱势群体的困境,体会到行动带来改变的可能性,才能辨别到这种“自我设限”和“知难而退”。通过行动与反思有了意识的觉醒之后,社工们积极关注弱势群体,重拾社会工作社会关怀和公平正义的价值使命,并通过一年半的持续介入和探索,摸索出一条契合本土文化脉络的社会工作路径。然而,要践行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理念实际上并不容易。
首先,协同行动者要改变文化习性,放下专家身段并不容易。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习性”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机制,集体历史的产品(客观结构)需要进行反复灌输和据为已有的工作,“将它的特殊逻辑施加于身体化(incorporation),行为人则通过这种身体化使自己从属于制度中客观化了的历史”(Pierre·Bourdieu,2012:81)。由此可见,习性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历史文化产物,习性对实践活动施加影响具有“既无意识又无意志的自发性”(Pierre·Bourdieu,2012:80)。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协同行动(督导),免不了会受到习性的影响。虽然有学者认为督导者应该接受“知不知”(informed notknowing)①意即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知识或完全理解。的立场,承认学习是一种与受督导者的“共同的冒险”,因此鼓励督导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探索,并对受督导者的知识充满好奇(J.Hair&O’Donoghue,2009)。然而,“尊师重道”是华人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习性,“传道、授业、解惑”是对师者的传统角色期待,协同行动者要改变这种文化习性,放下师者的身段,知道并承认自己的“不知”,与一线社工“互为师生”,一起进行学习的“冒险”,并不容易。在实践中,虽然笔者常常向社工们澄清协同行动者并不是“专家”,而是与社工们一起行动、互相学习,但是社工常常因遇到挫折而习惯性向笔者“求助”,例如社工们遇到“闭门羹”就期望笔者传授或示范一些入户方法技巧给他/她们。面对社工们的“求助”,笔者虽懂“互为师生”的道理,但迫于社工们对协同者(笔者)传统师者的角色期待,笔者最终会不自觉地提供自认为合适的建议,特别是协同行动的前期。但笔者后来会发现,社工在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中也能够寻找到“答案”,他/她们缺乏的,只是一些启发、鼓励和相伴同行。后来,笔者就找到了直接给予建议与通过共同行动来寻找解惑方法之间的平衡点。
其次,社工在协同行动关系中看到自己的主体性也并不容易。受到“囤积式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社工一方面把自身定位为问题解决的唯一主体,依赖协同行动者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从而通过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当他/她们在实践中感觉到自身的知识和方法不足以解决面对的问题时,助人和解决问题的主体责任感便使社工倍感焦虑,甚至否定自身的价值,从而要向比自己拥有更多知识和方法的“老师”寻求帮助。如果社工能够放下助人者、解决问题者的“专家”身段,尝试从问题和事实的表象寻找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根源,将问题“外化”,社工是否会减少“无力感”,有更多的耐性和包容,从而能够忍受这种所谓的“不成功介入”?虽然笔者也时常与社工们探讨“问题外化”的议题,但社工们在实践中时而不自觉地又会出现这种因难以解决社区问题而带来的苦恼。因此,社工们“问题外化”的意识也需要经过一个反复和漫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养成,这需要协同行动者持续的相伴同行。
四、结语
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范式采取“提问式教育”的理念,推崇“互为师生”的关系状态,通过“行动-提问-对话-反思”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协同行动策略,达到“协同行动者-社工”双重能力建设。通过在“双百计划”一年半的行动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社会工作督导范式的转向是可能的。虽然,双重能力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但笔者相信运用“行动-提问-对话-反思”的协同行动策略,有助于克服传统“囤积式教育”师生的角色定型对协同行动关系的束缚,协同行动者在与社工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共担责任,成为协同行动共同体,最终推动社会工作使命和愿景的实现。
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初步探讨了双重能力建设的协同行动的内涵及其可能性,但并未能展开论述笔者协同行动的成效,更未研究“双百计划”其他协同行动者对这一范式转向的实践成效。因此,对于其是否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