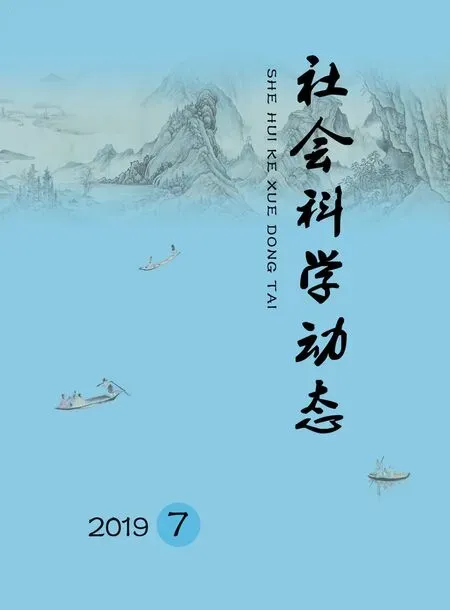影中影:软体社会与灰色人性的窒息地带
——评曹军庆小说《影子大厦》
方亚男
曹军庆的《影子大厦》通过讲述幸福县龙贵集团由兴到衰、由衰到灭的过程,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绝望、阴暗与人性的灰暗、复杂。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相比,《影子大厦》看似以批判现实主义为落脚点,实则是一种夸大了的现实主义,是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为介质,揭示“软体社会”与灰色人性中的典型问题,并试图在具有高度典型性的小说张力中,开出一剂“济世救人”的“药方”。表面看来,“影子大厦”指的是龙贵大厦这一“经济怪物”,“影子”是指与龙贵大厦相关的“影子经济”(高利贷)、“影子员工”(小混混、麻将馆的老头老太太们),甚至“影子县城”(幸福县)。实际上,在这些“影子”深处,还有更缥缈的“影中影”,它们直逼现实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灰色地带,其中蕴含着作者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忧虑。
一
有研究者将曹军庆的小说称为“世情小说”,认为“如果要对当下中国的人间世象进行关照,曹军庆的作品是可以参照的文本”。①然而反映“当下中国的人间世象”的作品何其多,曹军庆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就《影子大厦》而言,曹军庆小说中反映的并非浮光掠影式的表面现实,也非机械复制的原版现实,而是一种被集中扭曲、夸大后的怪诞、阴暗的“软体”现实,此为“影中影”的第一层指向。在《影子大厦》中,曹军庆借王月白对“软体音乐”的痛斥指出“软体社会”的真实面目:“软体是什么?比如蚯蚓那一类的软体虫子就是,还有鳝鱼泥鳅或蛇一类的东西。总之就是那种东西,阴暗、潮湿。”②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皆置身于这种阴暗、潮湿的“软体社会”环境里,他们或走向生命的终点,或显出道德的污点。曹军庆并非在谱写一曲引人积极向善的华丽赞歌,而是在抽丝剥茧中揭露现实社会的残酷、阴暗面。这种阴暗,是繁华背后的虚空,是奉迎背后的算计,是看似光明的背后所隐藏的阴冷、黑暗的“影子”。
“软体社会”阴暗面之一表现为底层人物奋斗之无效。《影子大厦》揭示了底层人物的悲苦命运,但这种悲苦并非止步于一般作家所描写的生活苦难,而是以奋斗之无效的叙事套路,揭示或预示着底层人物在经历无数苦难后依旧难以善终的悲剧命运。李贵书、王永年、徐小丽、王月白、蔡枭龙等人,都曾是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普通人。然而,底层人物如何挣扎求生?他们的求生方式能否带来善果?底层与高层之间如何嫁接?在这嫁接之中隐含了哪些社会痼疾与人性弱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影子大厦》皆有所涉及。在“死鬼”向徐小丽讲述蔡枭龙的故事时,曹军庆借叙事者之口讲出了“乡下孩子”的三条出路:求学、打工、混入黑道。③这三条道路,代表着社会底层人奋斗的三大方向。然而,这三条道路是否都能走通呢?被乡下人寄予莫大希望的“孩子”,果真能通过这三条道路改变自己、家人乃至家庭的命运吗?脑力、苦力、暴力,真是独立发展、截然不同的三条道路吗?它们是否会交叉?若交叉,又会有怎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经久不衰的传奇,还是引人自省的悲剧?诸如此类,曹军庆通过《影子大厦》表达了自己的严肃思考。小王、徐小丽、王月白是走第一条路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高校研究生。小王将训诂方法用于社会人际关系的潜心摸索中,以窥探和掌握他人秘密为自己铺路、谋利,变得愈发工于心计、自私冷酷。龙贵大厦的沉没,实则也为小王的平林新城敲响了丧钟。小王成长为另一个李贵书,也终将走向“李贵书式”的倾覆和沉没。徐小丽则在一次工作面试中失了贞洁,也失了爱情,最后嫁给一名死者,落得个与儿子在乡下相依为命、战战兢兢过日子的凄凉结局。王月白在销售工作中备尝艰辛,在女友失身后愈发自卑,最终走上以行骗换取金钱的道路。假使不发生任何变故,徐小丽和王月白依旧恩爱如初,这两名研究生在北京大概也只能成为工作、为住房发愁的“鼠族”。可见,求学之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修得圆满。那么,打工之路呢?如小说中所述:“老老实实去南方打工,也是穷途末路,挣到的钱和存下的积蓄,或许还不够治疗得的职业病,更别说买房。”④蔡枭龙的打工之路,还未开始就悄然结束,更讽刺的是,那张去广州打工的火车票,本是蔡枭龙决心重新生活的开始,最后却成了坐实他杀人罪名的强有力物证。而如小王父亲般老实敦厚的农村普通劳动者,也要面临自己病痛缠身、妻子出轨、儿子变得陌生的家庭变故。可见,打工之路亦可能得不偿失。而李贵书则是走第三条道路的典型,但显然这条道路也铺满鲜血,失败者如徐飞虎般死于非命,活下来的李贵书也并不能真正将“黑”洗“白”。在自身的虚荣、膨胀、失察和小王的精心算计下,李贵书只能绝望地与龙贵大厦一起沉至地下。由此看来,曹军庆在《影子大厦》中似乎堵死了底层人挣扎求生的三条道路,走这三条道路的人,皆未得到真正圆满的结局。
相反,怎样的人才能活得更舒适、更安全、更持久呢?是胡家轩那样擅作表面文章、谄媚唯上,且对危险有着高度敏锐性的官场“候鸟”。他们历经磨炼,懂得趋利避害,在位之时用尽手段为自己谋取最大化的利益,一旦“气候”有变,他们又洞若观火,提前规避风险。龙贵大厦濒临拆毁之时,胡家轩已全身远害;李贵书忧心忡忡之时,胡家轩却在公园悠闲地遛狗。“洗牌”风波之后,胡家轩除龙贵集团的工作外几乎无所失,反倒有所得——虽然历经波折,他的侄女终究还是被调入了团县委工作。两相对照,“胡家轩们”在谈笑间便活得游刃有余,这不仅是对底层人物奋斗意义的讽刺和消解,也是对错综复杂的生存之道的追问和反思:底层人物如何真正走出底层?正气为何就被歪风压过?诸如此类,都是小说留给读者的思想空白。
除了奋斗之无效,现实之苦悲也是“软体社会”较为突出的一面。《影子大厦》既揭示出“这世界的表里互为倒影”⑤,又将这“倒影”的性质提炼出来回归现实,进一步强化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苦悲。在《影子大厦》中,苦悲现实多是通过直接描写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即“以苦写苦”。对小王来说,现实“只是古代的影子,或者只是墙壁的影子”⑥,他不甘心复制老师曾崇德的人生道路,在母亲出轨烧烤王老朱后才“猛地回到现实”,而他“回到现实”的第一件事,便是责怪父亲为何不去杀了老朱。对徐小丽来说,进入龙贵集团之前,现实是不再有爱情的颓废之地;进入龙贵集团(成为蔡枭龙的妻子)后,现实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丝笼、一张隐形的网。衣食无忧、收入颇丰的现实如同“地狱”,从前吃苦、骂人、吵架的日子反倒成为“人间”的日子。“人间在哪里?”⑦这不仅是徐小丽对现实的痛苦诘问,更饱含着作者对尚存一丝正气的“徐小丽们”的无限同情。对王月白而言,现实则是他童年时就认定的一种严重的不公,是被无数“软体”充斥的阴暗社会,是依靠正当途径只能“穴居”和依靠诈骗却能获取财富的生存谬论。在这些人物的境遇中,现实并非指向完满、幸福的一面。与徐小丽、王月白等人遭遇的苦难现实略有不同,对李贵书来说,现实看似是以龙贵大厦、香格里拉公寓为代表的物质成就,是来自幸福县、龙贵集团内外的阿谀颂歌,是活成了“大人物”的虚荣与骄傲。然而龙贵集团内部和气友爱的烟雾之下,掩藏着各自的利益算计;顺从与夸耀背后,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谄媚套路。李贵书的“当局者迷”,一方面是身居高位后的“被迷”,另一方面也是当局者潜意识里“愿迷”——活在龙贵集团上上下下营造的龙贵神话中,多么“幸福”呵!但随着徐小丽的“告密”、陈灯山的失踪、欧阳老师造城运动的失败,李贵书逐渐看清了这些“影子”背后的真相,却再也无法阻止“影子大厦”覆灭的趋势。在这“实”的苦难与“虚”的繁华之间,现实世界变得缥缈闪烁,真假难辨。不仅如此,《影子大厦》突破了当代底层写作中较为普遍的苦难叙事模式,它不是单纯描写底层人物生活的困顿,而是将奋斗之无效与现实之苦悲进行深度杂糅,以二者的恶性循环强化了这种令人绝望和窒息的压抑感,使读者不仅对“软体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对当下的社会现实产生自然而然的严肃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龙贵集团濒临倒塌之时,小说中多次出现“骨头”这一意象。一定意义上讲,“软体社会”之所以“软”,与缺少“骨头”的支撑有着必然的联系。李贵书肋骨断裂后便开始怀疑自己的“骨头”,实际上也是怀疑小王——小王对李贵书而言,正如身体的骨头那般重要。然而,这些“骨头”却在不知不觉中“脆化”,一旦受到撞击,便被轻而易举地折断。“骨头”之断裂不仅预示着小王的背叛、龙贵集团的覆灭、“软体社会”的持续“软化”,而且昭示着人性的“软化”——灰色人性的力量正在逐渐扩大。
二
如前所述,对“软体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物而言,奋斗无效、现实苦悲似是难以摆脱的宿命,也正是这一“宿命”,迫使人性的弱点集中爆发。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曹军庆写“软体社会”,并非止步于社会表层,而是深挖至构成社会的“人”。换言之,“影中影”的第二层,亦是最深层,指向人性。与许多颂歌式的作品截然不同,《影子大厦》更多展现的是人性的灰色地带。
具体而言,灰色人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人物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强化:人们为巩固自己的成就、扩大自己的利益或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损人利己,常以双面孔或多面孔的方式立世。首先,在虚实相交的现实世界辗转求生的李贵书是具有双面孔的典型。一方面,李贵书表现出仁、义、智的正面形象:对向秀琴,他百般纵容讨好;对公司下属,他总是报以宽厚的微笑。但另一方面,在成功者的宽厚笑容背后,掩藏着阴冷和决绝、凶残和霸道、冷酷和自私。相比李贵书的双面孔,小王的面孔更为复杂一些。在小说叙述之初,小王的多面孔便已显出端倪,“别看他只是李贵书的司机,在工人面前他却跟个老板似的大呼小叫”。⑧面对李贵书时的沉默内敛和面对他人时的冷漠戾气,已然暗示小王决非泛泛之辈。随着故事高潮的到来,小王的多面孔亦逐渐显露。他一面视李贵书为“先生”,努力为其奔走,另一面却暗中布局将龙贵集团的财政一步步掏空。此外,他还以网友“死鬼”的身份接近徐小丽,为她出谋划策取其信任的同时,又悄无声息地为自己套取关于李贵书的消息。不仅如此,他还不事声张地求娶了欧阳老师的私生女。《影子大厦》看似只重点表现了小王在龙贵集团的“司机”面孔,实则已将他的“死鬼”面孔、“丈夫”面孔隐藏在字里行间,人心之复杂、面具之多样,已非小说文字本身所能尽述。
同时,在双面孔与多面孔的背后,隐藏着人性中更复杂的“受虐—施虐”倾向。《影子大厦》并非简单地以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如“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为叙事逻辑,严格说来,小说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真正“善”的“正面人物”或真正“恶”的“反面人物”,他们大多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养成多元性格,各自徘徊在受虐与施虐之间。这种“受虐—施虐”倾向,显示出人性的复杂与贫弱。以看似为受害人的徐小丽为例:在征集“龙贵之歌”的工作中,徐小丽最初是在“死鬼”的指导下被动地置办购物卡以此作为办理公事的“润滑剂”,随后她却能细心地为办公室主任也准备一张。这种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迎合的行为,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表明徐小丽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龙贵集团的工作氛围,至少在实际行动中遵循了这一“潜规则”。而在面对生活的孤寂、压抑时,徐小丽不惜以自慰来解决生理需求,她一方面难以自抑,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洁、可耻,最终患上抑郁症,进而自我嫌弃。仅从这个角度来说,徐小丽的心理亦是“非健康的”(至少也是“亚健康”的)。显然,徐小丽在李贵书的监控范围内是受虐者。自从“选择”嫁给蔡枭龙后,她便只能生活在李贵书的安排中,反抗无效,求情无效。然而,在对卖鸽子的男主人“打情骂俏”和对何总的“告密”行为中,徐小丽又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施虐者。结果是卖鸽子的男子被剁掉三根手指头,何总在家上吊自杀。此二人的悲剧虽非徐小丽直接造成,却与徐小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徐小丽外,其他人物的“受虐—施虐”倾向一样存在。李贵书虽是杀人犯,是禁锢者、施虐者,但他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的仁义者、受虐者。无论是出于内疚、虚荣还是其他,至少在行为上,李贵书始终对向秀琴表现得宽厚孝顺,的确履行了自己对蔡枭龙的承诺。但即便如此,李贵书也在自身的失察、膨胀以及小王的精心算计下走向倾覆,在施虐的同时亦摆脱不了受虐的命运。同样,面对母亲出轨的事实,作为儿子的小王亦是心理上的受虐者,但在击垮李贵书的行动中他又是难辞其咎的施虐者。在这种“受虐—施虐”的命运怪圈里,人性的灰色地带逐渐扩大。
除“受虐—施虐”倾向外,作者还揭示了人对权威的有意识反抗和无意识依附的矛盾心理。如果说李贵书在龙贵集团所享受的权威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他对徐小丽的束缚、强迫则是一种抑制性权威。如弗洛姆所言,在抑制性权威关系里,关系双方如同奴隶主与奴隶,“充满了对剥削者的憎恨和敌视,臣服的是与自己利益相左的人。但就奴隶而言,这种仇恨常常只能导致冲突,只能使其受苦受难,根本没有赢的机会。因此,奴隶常常压抑这种仇恨,甚至有时用一种盲目的崇拜之情取代它”。⑨在《影子大厦》中,与其说李贵书与徐小丽之间是哥哥与弟媳的关系,不如说是更为隐秘的、牢固的契约关系。在这契约关系中,李贵书是新的“奴隶主”,徐小丽则是履行契约义务的“奴隶”(或工具)。站在人性的角度,所谓恪守妇道、孝顺母亲、传宗接代,皆是以徐小丽的牺牲来满足李贵书的狭隘要求。在性苦闷与恐惧感齐头并进时,徐小丽甚至主动要求与温柔、亲切的李贵书“偷鸡摸狗”。⑩此后,当徐小丽察觉到龙贵集团无处不在的“造神”运动时,便毫不犹豫地直言“进谏”,也是真心为李贵书和龙贵集团着想。徐小丽一方面埋怨李贵书,另一方面却认可他、维护他,甚至对他衍生了一种不自觉的崇拜、关爱和依赖之情。受虐者爱上施虐者,这与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颇有相似之处。徐小丽由有意识反抗到无意识依附地悄然转变,将人性面对权威时的“进退两难”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见,在“软体社会”中,人物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防御机制不断强化,双面孔或多面孔的立世哲学、“受虐—施虐”倾向、反抗权威和依附权威的矛盾心理等,皆表现着人性的灰色地带。社会变“软”,人性趋“灰”,这既是通过《影子大厦》折射出的社会现实与人性侦查报告,亦体现着曹军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情怀。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曹军庆虽然通过《影子大厦》揭示了人性中的灰色地带,但他并非一味贬斥这种灰色人性,相反,对于这种灰色人性他给予了较大程度的理解和同情。
如前所述,“软体社会”阴暗、潮湿。在错综复杂、充满自卑与苦难的“软体社会”中,人物往往变得谨慎而敏感,人性的灰色地带也愈发彰显。对于经历了“初入城市→逃回乡下→再次被接入城→被迫重回乡下”波折的向秀琴来说,现实生活变故导致的心理变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人性特征可能更具代表性。大体说来,向秀琴的性格特点具有两个不甚相同的时期特征:前期的向秀琴心理上颇有一些张爱玲笔下曹七巧式的心理扭曲印记,后期则逐渐回归到中国传统乡妇的朴素心理。向秀琴初入香格里拉公寓时的偷窃行为和她对徐小丽“莫名其妙的敌意”⑪,并不是简单的患得患失或年龄代沟造成的。徐小丽的昼夜颠倒、冷淡寡言、香艳美丽,不仅招惹向秀琴怀疑,更令其畏惧。况且徐小丽年纪轻轻,在“没有作任何牺牲”的情况下搬到香格里拉公寓来,享受着向秀琴牺牲了唯一的亲生儿子才换来的舒适生活,这种“不公”更加引发了向秀琴内心强烈的自卑、不平和恨意。但在得到李贵书和城里老头老太太们的充分“尊重”后,自卑与恨意逐渐淡化,她逐渐从被人嘲笑的“乡下人”转变为人人追捧的“城里人”(实际上只是“半城半乡”的中间人物),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徐小丽怀孕后,朴素的“传宗接代”思想使向秀琴更清醒地认识到徐小丽的价值:“因为有了后代,她向秀琴也跟着有指望。蔡家的根在她这儿没有断掉,向秀琴因此对徐小丽怀着感激。”⑫由憎恶到认可,由认可到感激,向秀琴对徐小丽态度转变的原因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丰富、细腻的思想变化过程。同样,李贵书、徐小丽、王月白等人物大抵如此。命悬一线的李贵书杀掉徐飞虎和蔡枭龙,何尝不是人性中求生本能的反应?徐小丽选择嫁一亡人,除了高额薪资的诱惑,与其自身失去爱情想要“遁世”的心理又何尝没有关系?王月白通过诈骗成为“谷飞”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逆袭”?正因如此,《影子大厦》中的人物才显得多面立体、更加鲜活。
基于此,曹军庆尝试性地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小说中,违章建设既是龙贵大厦被炸毁的直接原因,亦是具有釜底抽薪式意义的最有力的反击。显然,若无违章事件,龙贵大厦也如强弩之末,终将腐朽。然而曹军庆并不甘心放任这一“经济怪物”苟延残喘,他意在将其逼入穷途,以摧枯拉朽之势使其瞬间崩塌、彻底没落。“违章”二字,直接从源头、法规上否定了龙贵大厦存在的合理性。那么,能从源头上断绝“软体社会”与灰色人性的“致命点”又在哪儿呢?曹军庆似在告诉我们:善恶自有因,善恶终有果。参透人性,克服人性中的弱点,重视人自身的心理问题,或许才是摧毁“影子大厦”真正有效的途径。
三
综上所述,《影子大厦》虽有对灰色人性的理解和同情,但曹军庆着重表现的依旧是“软体社会”与灰色人性的窒息地带。之所以“窒息”,是因为几乎看不到“希望”。徐小丽等人虽暂时逃脱了小王的怀疑,但她与虎子真能相依为命度过余生?长大后的虎子又将如何走出白龙村?哪里才是底层百姓真正的出路?算计者、背叛者活成了新一代的“大人物”,软弱者、良善者退居乡村还得战战兢兢,这种不公究竟是谁造成的?又该如何摆脱?这般灰色结局,遗留给读者的自是无尽的思索和叹息。一方面,“软体社会”的种种不公和阴暗加剧了人性弱点的集中爆发,李贵书、小王、王月白等人皆选择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取更直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这类人物的选择又进一步强化了现实的苦悲,道德逐渐滑坡,悲剧持续上演,陷入社会非正当竞争与人性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就此而言,《影子大厦》所反映的问题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较强代表性。
这种揭露社会阴暗与灰色人性的强度与鲁迅有一定相似之处。学者林贤治曾言:“鲁迅的存在,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这不仅仅因为他揭露了为人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世界的真实,而且还在于他总是以一种与人们相悖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这真实。”⑬可以说,在揭露那“为人们所不乐于接受的世界的真实”方面,曹军庆的《影子大厦》是颇为成功的。但如何对待这种“软体社会”与灰色人性的长期恶性交融与循环,改变“软体社会”的现状,摧毁社会与人性层面的“影子大厦”,恐亦需要更加强有力的体制机制。至于机制究竟如何建成、运作,则非一部小说本身所能完全承载的了。同时,《影子大厦》表现的是一种被集中扭曲和夸大了的“软体社会”现实,这种现实趋近“真实”却又并非完全真实,极易落入批判现实主义的格局。整个小说叙述文本是一种新锐的先锋叙事套路,还是处于萌芽阶段的寓言革命?《影子大厦》看似已入尾声,实则故事未了,余音犹在。而在“影子大厦”的倾覆中,我们已然看到,曹军庆的小说创作有其独特的思想底蕴与潜在能力,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新的突破!
注释:
①汪政:《道不尽的现实与讲不完的故事——略论曹军庆的小说创作》,《文艺报》2017年6月30日。
②③④⑥⑦⑧⑩⑪⑫ 曹军庆:《影子大厦》,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 83—84、149、149、63、153、8、127、110、207 页。
⑤ 杨晓帆:《“影子大厦”:这世界的表里互为倒影——读曹军庆长篇小说新作〈影子大厦〉》,《湖北日报》2015年10月11日。
⑨ 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110页。
⑬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