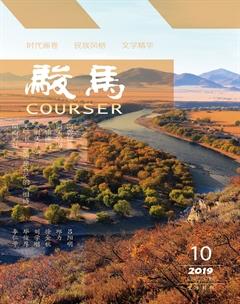绿萼
她七十五六岁,也可能有八十岁吧,跟我的家乡众多这个年龄段的老太太一般,短发整齐地梳向耳后,头顶箍一只黑发卡。蓝布褂子外面,五冬六夏的喜欢罩一件坎肩,黑底的牡丹大花或者蓝底的夸张的大白菊图案。
牡丹大花坎肩是前些年带她去草原,途中的小商铺里淘来的,她非常喜欢。她的身体还算健康,可以远行。
照片上,她笑得眯眯着眼,比坎肩上的牡丹大花还耐看。
我回家,她在迷迷瞪瞪的小睡里睁开眼睛,我伸出双手,她立刻眉开眼笑,我们轻轻地拥抱。很多时候,我会在她蓝布褂子的衣袋里放一些小零嘴儿。
她每次都能发现并且拒绝收下。她摸索着把我给她的一小袋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辗转捎回来的牛肉粒或者是几块花锡纸包着的软绵绵的糖果,掏出来推到我手里,我握着她的手再给她送回衣袋里,她便不再执意不收。
我妈妈帮她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她居住的房里,风想从窗外进来,都要先认真地在长着黄菖蒲的池塘里洗个澡,披挂一些白蔷薇的香气,然后才站在她的窗台上观望思考,是在她的抽屉里歇脚呢,还是在她的针线箩里打个盹?
她的针线箩里没有针线,她已经过了拿针线的年纪。妈妈说,老太太越来越糊涂了,看见跟你差不多身个的女子她便要冲上去抱人家,也不知道去看看人家的脸对也不对。
我说我就知道嘛,这个小老太,她喜欢我。
院里的紫藤落了一地花朵,我摘下一串,别在她的衣襟上,她拿下来,呶着嘴好像吹走上面的灰尘,然后把花放在我头发上。
顶着头上的紫藤花串,我抱着她的肩,春天又来了,我想请她去人民公园看花,大片的郁李,榆叶梅,都开了,天空抹上了一层粉红的颜色,仙境一般。
妈妈说,好好带着她。我说,好。
人民公园对过,是一家遮阳伞店,飘飘摇摇的小花伞撑开着,满眼都是,她看看我头上,再看看日头。我明白她的意思。她看上了一顶粉色的小伞,不舍得放手。我掏钱包时,她就伏在我的肩上喜笑颜开。她喜欢看钱,妈妈在她的针线箩里放了厚厚一沓。
我带她进洗手间,她摇头不去,只站在门口认真地打量玻璃窗上映出来的她举着小伞的样子。我告诉她,不要乱走,等我。她点头。
及至我赶出来,却不见她的踪影。
喷水池边围了些人,有人大声地嚷嚷,嗬,看,看哪,又抱住一个!
嗬嗬,真是个搞笑的老太太!
人们笑作一團。
我扒开人群,一眼就认出是她。她正抱住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女人一边尖叫一边推她,她的小伞掉在地上,她跌跌撞撞地对着女人伸出双手,女人厌恶地躲开她。
我冲过去,把她揽在我的臂弯里,把我的脸靠近她的脸颊,她认出我后,激动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抱着我的肩膀。
我帮她捡起小伞,替她擦净眼泪。
我紧紧地攥着她的手再也不敢松开。
妈妈哭着要我再一次发誓,外出时候,千万不要撒手,千万不要撒手。
而这时候,她正安静地坐在她的房间里,翻看她的那沓钱,然后把玩她收藏在衣袋里或者是针线箩里的那些小东西——一张梅花鹿拉着木头车的旧旧的卡片,几枚原本放在花盆里的白色小贝壳,我用过的破了一角的背面是两行桃花诗的小镜子。有时还能翻出一两粒上回吃落下的盐渍过的葡萄干,小心地拈到嘴里,甜滋滋的,她半闭着眼睛,像是品尝着她从此以后恬静的人生岁月……
她无名无姓,半聋又哑。十年前,她流落至此乞讨,妈妈跟在她身后走了五条街,悲从中来,掩面而泣。
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终要到哪儿去。
妈妈收留了她,为她取名绿萼。
据说,我的外婆,六十岁时因病失去记忆而意外走失,寻多年至今未果,旧时书家门户之女,闺字绿萼。
【作者简介】高沧海,本名刘秀玲,女,70后。作品散见《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大观》《天池小小说》《小小说月刊》《小说月刊》等,《天池小小说》2018年度专栏作家,2015-2017年度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