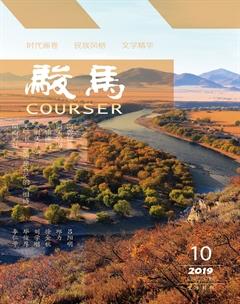消失的湖
邱力
薄暮时分,落日的余晖从山那边射向栖霞苑,被密集高耸的楼盘一挡,光线如强弩之末,顿时弱了。洒向栖霞湖的阳光稀稀拉拉,全无往日辉煌。先是闻到浓烈的鱼腥味,跟着就看见湖面上漂浮了一片死鱼。好大的一片,简直要把整个湖面覆盖。鱼肚一律仰面朝天,反射出白花花的光,仿佛鱼们统一约好以仰泳的姿态迎接这个最后的傍晚。湖边围了一群人。吴青松和母亲停了脚步,朝湖边走去。有人用树枝扒拉死鱼到岸上,更多的人在议论鱼的死因。一会儿,两个保安也赶了过来。一个胖保安见状当即振作起来,取下腰间对讲机,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通。另一个矮保安说了句,“大家退后些,要保护好现场。”张开双手把众人向后阻挡。在警察尚未到来前,两个保安充当了临时警察。吴青松还想凑近看个究竟,母亲向后拉了拉他的胳膊。他们离开人群,继续沿湖边散步。自从母亲和吴青松一家三口住在了一起,晚饭后陪母亲绕湖行走就成了吴青松每日的必修课。儿子和老婆说是有事,其实是没有耐心。谁愿意陪着一个老人边散步边听唠叨呢?但吴青松必须得陪,母亲一个人不敢独自坐电梯,附近也没有认识的老友,像坐牢似的待在21楼的家中一整天,绕湖行走相当于放风。吴青松上班再忙,回来也要满足母亲这个唯一的喜好。再说,吴青松自己也想去湖边走走。
这个湖现在叫栖霞湖,从前叫鸭池湖。听上去,就如同一个人所拥有的学名和乳名。学名是政府取的,乳名是市民取的。瓮城市民特别是上了点儿年纪的老市民始终坚持叫这个湖为鸭池湖,对栖霞湖这个洋里洋气的名字嗤之以鼻。全城人民都管鸭池湖叫水库而非公园,可那么多年,鸭池湖的的确确是在承担着公园的职责和功能。就这样叫来叫去叫了好些年,直到这个城市的第X任管理者发现城里竟没有一座公园时,才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指出,“太不像话了,城不在小,有园则灵嘛。建一座公园就那么难吗?”要建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城市公园还真就不容易,不仅财政捉襟见肘,也耗时耗力啊。政府毕竟是政府,灵光一闪,便临时抱佛脚就地取材,推出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将鸭池湖水库改造为城市公园的实施方案”。还面向全社会搞了个“征集园名活动”。活动结束后,鸭池湖水库于是变成了栖霞湖公园。那一年,新公园正式面向大众开放时,吴青松正在读高一。他瘦长身子,上唇冒出点稀松的胡子茬,成绩中下,除了耽于幻想班上那位立定跳远时胸脯隆重耸动的女同学外,还在心中树立了成为一名“尼斯湖水怪研究专家”的远大志向。这样的状况,使少年吴青松看上去双眼迷茫心事重重,大家无不同情这个背着沉重书包的忧郁少年。
说起来,远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大峡谷里的尼斯湖和贵州东南部小城山区的鸭池湖八竿子打不着,可因为在吴青松童年时代发生了一起“鸭池湖龙吟事件”,而将两个湖串连在了一起。
那天,晚饭桌上,父亲和母亲聊起白天众说纷纭的鸭池湖里有龙在吼叫一事。听得吴青松和弟弟抓耳挠腮,忍不住打断父亲的话头问这问那。父亲眉头一皱,“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瞎咋呼!”呷了口自泡的枸杞酒,又道,“等明天下班我带你们去看个究竟。”父亲不像其他家的大人一样,老爱摆出一副权威的臭架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人。父亲在家中是个“妻管严”,在政府部门任个闲职。印象中,父亲的腰背从没挺直过,好像随时准备对世间所有的一切点头哈腰。“你倒是学学人家老李啊,两个娃儿都安排了好单位。唉,倒了八辈子霉,吃干饭屙稀屎的!”这是母亲责骂父亲最多的一句话。父亲最大的爱好是下棋喝酒。下棋从不悔棋,喝酒喝出了酒糟鼻,红红的,泛着油光。直到患病去世,父亲都保持了“红鼻子老吴”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形象。第二天,父亲带着兄弟俩来到鸭池湖时,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围在湖边。竟然有人燃起了香蜡纸烛,面朝湖水,喃喃念叨。吴青松学着别人的模样,俯身在地,侧耳倾听。他听到了一阵接一阵低沉的吼声,从幽深的湖底传来,又像是从群山之间大地之下传来。吴青松被震慑住了。瞥眼看见父亲在晚风中阖着双目,红红的酒糟鼻微微翕动。当晚,从父亲口中,吴青松第一次听到了尼斯湖水怪的传说。“地球上本来就存在许多无法破解的谜,那也不足为奇。只是硬说小小一个鸭池湖里藏着一条龙,鬼才相信哩。不过这样瞎胡闹一气也蛮有意思的啊。”父亲冲着听得津津有味的吴青松哥俩一笑,又干了一杯。吴青松打心底里希望鸭池湖里有龙,起码也要有一头像尼斯湖水怪一般大小的水怪。要不活着真他妈的没劲,既没马戏团光临小城又没新电影上映,每天上学放学写作业熄灯睡觉,闷都要把人闷死了。吴青松失眠了,他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胡思乱想。长大了最好是亲自去一趟英国苏格兰,去看看那座大名鼎鼎的尼斯湖,在湖边住下守着,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够亲眼见到水怪从湖里冒出来。几天后,鸭池湖被抽干了,真相暴露出来。原来是一对重达三斤四两的雌雄牛蛙在水库底的管道内交配时发出的欢鸣,这声音在管道内无形中被放大了数倍,成了“仿真版龙吟”。湖水在人们的咒骂嬉笑声中被重新灌满。吴青松放学后,独自来到湖边。踏着地上狼籍的香蜡纸烛残骸,对眼前的景象怅然若失。鸭池湖里的龙不复存在,但尼斯湖里的水怪却烙在了吴青松的心里。从小学到高中,吴青松俨然成了一个尼斯湖水怪迷。
班上成立有“课外兴趣小组”,有书法绘画组、诗歌朗诵组什么的。吴青松和另一名叫袁远航的同学加入了生物课老师成立的野外考察小组。該小组的活动有点儿类似郊游,主要是去野外采集一些植物的叶片和五颜六色的蝴蝶制作成标本,用大头针别在纸板上,再放置于玻璃框中,供大家参观识别。但吴青松和袁远航的兴趣和志向不在树叶和蝴蝶上面,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是尼斯湖水怪,一个是百慕大魔鬼三角。小组成员在老师带领下去鸭池湖水库开展活动时,吴青松和袁远航跑到湖边,捡起石块比赛打。石块斜斜地射向湖面,轻盈地跳跃,嗤嗤有声。吴青松最好的成绩是能打出八个水漂,袁远航始终比吴青松少两三个水漂。两人玩累了就聊起各自的理想,一个说要成为尼斯湖水怪研究专家,亲自揭开水怪之谜。一个说要去百慕大三角走一遭,看看这个号称魔鬼三角的海域到底有多么恐怖。他们伫立湖畔,双眼迷茫呆呆地望着鸭池湖静静的湖面。湖面上偶尔掠过几只水鸟,有风吹过,吹皱的湖水一层一层地随风翻卷,像是他们手里翻阅的《世界未解之谜》图书。两人不无惋惜地认为这个湖实在太平静,缺乏像尼斯湖和百慕大那种让世人神经为之一振的东西。袁远航看得乏味,躺在草地,嘴里衔了根草。吴青松仍在看湖。袁远航说,“一个破湖有啥看头?”吴青松说,“你看的时候,尽量把它想象成你想要看的湖不就得了?”说完两人都傻笑起来。吴青松说自己将来要是住在湖边就好了,可以天天看着这个湖发呆。袁远航说自己将来最好是在湖边上班,又能拿工资又能看湖。
湖里的鱼是被人毒死的。
承包栖霞湖渔场的那个老板少说也要损失四十来万,而栖霞苑房开商损失的是楼盘的信誉度。警方已介入调查。人们猜测,投毒者恐怕是报复,要么和鱼老板有仇,要么和房开商有怨。栖霞湖尽管变成了钓鱼场,可它毕竟还是目前瓮城人民唯一的一座城中湖啊。投毒的人实在可恶,母亲每天散步的地方看来得调整一下。吴青松站在21楼的阳台上,俯瞰着被群楼环伺的栖霞湖。现在,沿着湖边已经竖起了一圈蓝色的施工隔板,五台大功率水泵正在发出巨大的轰鸣。水里有毒,自然是先要把湖水抽干,排毒养湖。可到底如何养法,目前尚无定论。一说是重造新湖,一说是填湖移址。栖霞湖的命运让居住在此的业主们担心,也备受全城人关注。
吴青松今年46岁,半辈子光阴倏忽而逝。当初许下的诸多愿望,掐着指头盘算,大概就只有“在鸭池湖边居住”这一样终于实现了。五年前,父亲去世,谁来陪同母亲成了问题。弟弟在政府部门任主管领导,经常出差开会,媳妇又对婆婆不待见。兄弟俩一商量,决定由吴青松陪同母亲安度晚年。征得母亲同意,卖了老房子,卖房款拿出一部分,去刚刚封顶大吉的栖霞苑楼盘交了首付。待交房后装修完毕入住新居,看着房产证上赫然写着的吴青松三个字,吴青松想到总算是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长吁一口气。老婆张唤霞也首次做小鸟依人状,对奚落了半辈子的丈夫俯首贴耳。两口子当时从停产倒闭的造纸厂双双下岗。吴青松在一所大专学校后勤处当水电工,张唤霞在一家中医院当保洁员。儿子吴青云正在读高一,样子简直就是少年吴青松的翻版。唇上也冒出了一圈胡子茬,只是热衷于玩网游打老怪,对于尼斯湖水怪什么的从小就不感兴趣。三岁看到老,看见儿子一副不成器的样子,吴青松觉得当初给儿子取名“青云”真是好高骛远头脑发热。
不管怎么的,城市的确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那会儿,吴青云学会了走路,一家人喜气洋洋地牵着手,随着人流走进造型华美的栖霞湖公园大门,顿时感到有点儿身为城市人的自豪。公园比水库丰富多彩多了,用“与日俱新”来形容一点儿不过分。进园子往里走,一路修了长廊凉亭,小桥流水,各种花卉点缀其间。你可以流连驻足多拍几张相,照出来,如果跟人吹嘘是到国内的某个大城市景区旅游保准没人会怀疑。园区的核心游乐点以湖为中心,玩的有过山车、海盗船、大钟摆、碰碰车,吃的有烧烤、风味小吃、酸汤鱼饭馆。但水库变成公园后,也有新问题出现,进公园大门免费,进去后如果要玩园区内的娱乐项目就要掏腰包,偏偏吴青松两口子的腰包从来就没有鼓起来过。所以每次进来游玩,吴青松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请君入瓮这个成语。可又没法,全城就只有这一座公园,独家买卖,别无分店。吴青云小学三年级暑假期间,一家人进了园子。吴青松两口子故意避开那些热闹的高消费场所,拖着吴青云径直朝僻静的地方冲。冷不丁看去,两口子好像是半路上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去公园管理处买了张15元一小时的“合家欢”游湖船票。上船前,吴青松看着湖面,忽然童趣大发。拾了两块石片,一块递给儿子,一块自己先朝湖面斜斜地射了开去,“来,咱们来比赛打水漂。”儿子听见不远处过山车和海盗船区域不时传来阵阵惊叫欢呼声,满脸不高兴。懒懒地将石块扔进湖面,拍了拍小手。张唤霞过来拉儿子上船,“谁还有闲心去跟你玩这些小儿科啊?游湖是计时收费的,再耽误时间,我们的船票钱真要被你打水漂了!”三个人坐一辆脚踏式动力小船,向湖里奋力踏去。踏到湖心,就让小船随波漂浮。吴青松说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有点自豪地称自己是个“水怪迷”,把这个鸭池湖当作是大名鼎鼎的尼斯湖,幻想湖里躲藏着一头大水怪。本以为儿子会感到害怕或者至少是好奇,可儿子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鼻子一哼,“我们老师说的,你讲的这些都是迷信。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妖魔鬼怪。爸爸小时候肯定是个大笨蛋。”老婆在旁直夸儿子聪明。吴青松忽然有点伤感,看着紧挨在身边的老婆儿子,再环顾四周,感觉整个湖面仿佛比从前缩小了好几倍,凭一己之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来到湖心。学生时代的无限豪情和理想早已灰飞烟灭。回到家中,张唤霞念叨这次逛公园又花去了35元钱,以后如果实在要去就不能由着儿子性子,吃喝玩乐过够。吴青松没有吭声,躲到卫生间去抽烟。
吴青松中专毕业,考进造纸厂,和张唤霞在同一个车间。两人结婚后,在厂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两室一厅小屋。吴青松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对生活没有什么高要求。只希望能够稳稳的上班下班和老婆做做爱跟工友喝喝酒,只希望日子就像厂区前的乌拉河水一般平缓地向前,再向前。这一点很让张唤霞瞧不上眼。好不容易攀上一个来自城中心的干部子弟,离开厂区到市区的梦想又死灰复燃。自己想要逃出厂区,丈夫却在厂区过得蛮滋润。两口子一吵架,张唤霞就边哭边骂自己真是看走了眼上了贼船,把自己好端端的处女身白白送给了吴青松这个窝囊废,这辈子要老死在这个山坳坳里的臭厂区了。他们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把吵架当作了柴米油盐般的生活必需品,也像所有的家庭一样热火朝天地吵完后又夹着尾巴繼续生活。
吴青松在造纸厂待了整整十年。原以为能够如愿以偿地终老于斯的造纸厂,在国家环保政策的严厉处罚下,这家有着五十余年光荣历史的重度污染企业宣布倒闭。吴青松一家搬出了厂区。
下岗那段时间,吴青松一家三口跟吴青松父母挤在一起住。晚饭后,父亲经常让吴青松陪自己去夜游栖霞湖公园。
那天,吴青松又推着父亲去了栖霞湖公园。父亲已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的活头。晚霞的光芒照在两人身上和轮椅上,涂抹了一层金色的油彩。父亲的酒糟鼻黯淡无光,生命的血色正从他的鼻尖一点一点褪去。上了堤岸,父亲示意停留下来。他举起右手向原来水库的大坝指着,吴青松顺着他所指方向望去,看见大坝上原先用水泥灌注而成的“鸭池湖”三个魏碑体大字,被萋萋荒草遮盖得几近于无。对面山坡上有座全木结构的七层塔楼,吴青松小时候就见到的,少说也有三十余年了。檐下灰黑色的风铃在晚风中不住摇晃,却听不见铃声。也许檐下只是一只倒悬的蝙蝠或者一个废弃的鸟巢?从堤岸下来,父亲让吴青松一直推向湖边。呆呆地站了好一阵,一些落叶在湖面漂浮着,湖风吹得吴青松起了凉意。正要推父亲离开湖边,父亲突然说了一句话,让吴青松忍不住流下泪来。
父亲死后,吴青松好长时间没来栖霞湖公园。直到他在学校后勤处正式上班,张唤霞在中医院也找到了事做。
栖霞湖的水被抽干了,工人师傅们都撤走了。机器停止喧嚣,施工场地忽然冷清下来。大概这个湖的何去何从成了个新问题?湖的命运掌握者们正在商讨中?母亲仍然要在湖边散步。沿着蓝色的隔板慢慢地绕着圈走。吴青松劝说无效,只得陪着母亲。吴青松探头去观察这个干涸的湖,见到空洞的湖底还残留着黑绿色的水,散乱地分布着水草淤泥石块,如同母亲卸掉假牙套后的嘴。这种绕湖一周的散步,让吴青松想起不久前去殡仪馆参加一位老友的葬礼时,大家绕灵柩一周的情景。吴青松想,这哪里是在散步呢,这是在告别啊。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那个投毒者是谁?动机何在?吴青松在学校里成天和管道水泵保险丝打交道,跟外界接触得少,社会上的消息自然就不太灵通。从厂里到学校,换了个新岗位,过去是和大老粗们厮混,现在伸向自己的全部是软绵绵的知识分子的手。吴青松恪守少说话多做事的原则,随时随地给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留下好印象。后勤处水电班共三个人,平时就人少活路多,逢开学季就像打仗一样,忙得屁股上冒烟。可是再忙,吴青松一听说后勤处长或者学生处长家的下水道堵塞电表烧坏了,便二话不说,放下手中活,赶紧跑去修好。这样做自然有好处。比如学校临时租给其他单位作为考场使用,学生处长就会通知吴青松来充当监考老师。轻轻松松一天下来,每人有一百元左右的监考费,中午还有免费午餐,下午运气好的话,大家会嘻嘻哈哈地顺便邀约吴青松下馆子。走在一伙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旁边,吴青松按按胸口上别着的监考证,仿佛自己也成为了知识分子行列中的一员。再比如学生公寓的宿管员最近缺人手,后勤处长就对吴青松说了,只要张唤霞愿意,四栋的宿管员位子给她留着。张唤霞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在医院当保洁员早已腻烦。回到家中就发牢骚,数落吴青松的无能。吴青松暂时不想告诉张唤霞宿管员这个有油水的差事(可以经常得到学生们淘汰的九成新物品),一是对张唤霞长期以来的恶劣态度心存怨怒,二是五栋的宿管员屡次三番向自己示好。吴青松对那个五栋宿管员也颇有好感,人不仅长得像自己高中时代心仪的那个女同学,而且韭菜饺子包得很好,一口咬下去,韭菜的滋味会幸福地溢满口腔。与五栋宿管员四目相视一笑,会让自己心潮澎湃,下腹处似有久违的阳气急遽上升。但关键时刻,一想到张唤霞每天在医院拖地洗衣,儿子脸带菜色背着书包上学的样子。阳气便立马下降,冷气从脚底冉冉升起。
几天后,吴青松在一次同学会上意外地听到了有关投毒者的消息。告诉他消息的是昔日的同学袁远航。
那次同学会上见到的袁远航还是像从前一样瘦,只是脸色不如从前那么红润,衣着也不怎么光鲜,跟大家咋呼他的什么袁总袁老板名不副实。一个气质不凡的女人向大家挥了挥手,“我们家老袁是糖尿病,上午还在医院治疗,今天参加聚会是带病前来啊。请各位饶他一次吧。”吴青松坐的位置离袁远航较远,正在为是否主动上前打招呼举棋不定。袁远航一抬眼看见了吴青松,十分高兴地拉着吴青松坐在自己身边。酒菜一会儿热气腾腾地上了桌,袁远航离座去了趟洗手间,一会儿回座,侧身在吴青松耳边道,“咱们兄弟俩八年没见面了,今天当然是要痛快喝一场。”捏了捏吴青松的手又道,“没事的,刚刚打了胰岛素。”吴青松心头一热,想起了八年前那个炎热的下午。吴青松刚进纸厂工作时,袁远航专程前来找他玩耍。那时候,袁远航也找到了工作,单位是市自来水公司。袁远航本来是坐办公室,给领导写点材料拟个文件什么的,多么有前途的差事。袁远航却执意要去鸭池湖水库管理所。清闲是清闲,可大好青春就要在青山绿水的陪伴下清闲掉了。当天,吴青松请了半天假,一个下午的时间两人全都耗在了厂区一家小饭馆里。吴青松举杯祝贺袁远航实现了“在湖边上班”的愿望,自己“在湖边居住”的愿望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实现。袁远航趁饭馆里的食客不注意,从怀里取出两本色彩艳丽的杂志塞在吴青松腿上,“我爸去香港出差搞来的,被我偷来了。你在厂里无聊就翻翻看,解闷。”说完捏了捏吴青松的手。吴青松低眸一看,杂志封面竟是些衣着暴露的女人做出挑逗的姿态,知道是眼下急需的精神食粮,使劲握住了袁远航的手。第二年春,听说袁远航已辞职下海,至于在哪片海域遨游就失了音信。
酒过三巡,气氛渐热。袁远航带来的那个女人被几个女同学围着叫嚷剪刀石头布,没空再来关照袁远航。袁远航两颊也泛起了红光,说话声音变得激动起来,“……什么他妈的狗屁理想!我如果不从自来水公司辞职,混得不会比老杜强到哪里。”众人都停下酒杯,听袁远航继续说,“老杜是我在鸭池湖水库上班的同事,一个老光棍,守了一辈子湖,退休好几年了。最近也不知是发哪股神经,拿几包毒药把那个湖的鱼全都毒死了。那么老实窝囊的一个人,真是让人想不到啊。”吴青松说,“老杜是报复鱼老板或者房开商吗?”袁远航笑道,“老杜要是有这胆子,我倒是佩服他了。老杜的年龄和我老爹差不多,又是我同事。我就想法子去看守所看他。问他咋个这样蠢,你猜他咋个说,他说他看着湖难受,和以前不一样了,不如让它去死。”大家都哦了一声,都觉得不过瘾,不刺激。跟想象中的惊险情节和复杂背景大相径庭。但又不得不信。谜底一旦揭开,猜谜前的一切努力都变得那么荒唐可笑。聚会是在几个喝醉了酒的男女同学相继倒下后提前结束的,都奔五十的人了,还这么硬撑着假装年少轻狂。
回到栖霞苑,那座模仿巴黎凯旋门的大门口站着个高大的保安。自从发生“毒鱼事件”后,保安对进出栖霞苑的人有了戒备,来栖霞湖玩的人都要接受保安审视的目光扫描。吴青松每次走进这座大门都有一种陌生感。到了家中,脑袋仍然晕乎乎的。看见母亲老婆儿子围在小飯桌边吃饭,属于自己的那一角空着,一副空碗筷放在桌边。张唤霞抬起头,用筷子敲打着空饭碗,“啧啧啧!你倒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和女同学在一起怀旧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吴青松把挂在嘴边的脏话吞进了肚里,想学校四栋宿管员位子空缺的信息决不能告诉张唤霞。五栋宿管员如果下次再煮韭菜饺子来给他,他是不是也要送点儿什么东西给人家呢?饭后,张唤霞照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儿子进了自己的小房间,母亲在厨房收拾碗筷。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吴青松忽然感到厌倦,冲张唤霞道:“你过来收拾一下。我陪妈散步去了。”说完,他拉了母亲的手,用干毛巾擦干,也不顾张唤霞在身后发出的牢骚,和母亲下了楼。
围湖的蓝色隔板已经拆除,被抽干的的湖底让人看了心头越发空虚。有几个人在湖边焚烧枯枝败叶,烟雾在空中弥散,吴青松和母亲被呛了几口,就在一张油漆斑驳的休闲木椅上坐下来。坐了会儿,母亲叹了口气,“以后你多让着点唤霞,她不容易。你爸不也让了我一辈子。”说到父亲,吴青松想告诉母亲一件事。但想了想,还是算了。这件事如果母亲知道的话,说不定就不会再来湖边散步了。许多年前的那个傍晚,下岗在家的吴青松陪同病重的父亲站在湖边时,父亲说:“这个湖老了,我也老了。我连跳进湖里的力气也没有了。”吴青松听后吃了一惊。暮色中,湖里隐约可见自己和父亲的倒影,像一张老胶片,漾在显影液中,却怎么也显现不出清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