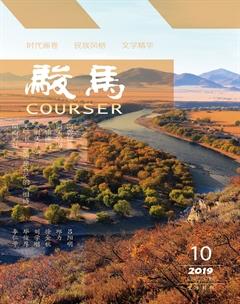大路朝天
朱斌
1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感都是在攀比中失落的。譬如,私家车在我们这座三线城市里没有普及之前,我走路的感觉还是蛮好的。可是,待到私家车普及后,我则是越走越憋屈了。
我本来压根儿就不想开车,内心深处、潜意识里,我都不爱车。而且在这座小城里中速步行,从城南走到城北用不了两小时,从城东走到城西也用不了一百二十分钟,公交也很方便,私家车真的不是刚需。可现在不管开公车还是开私车,几乎人人有车了,我也被逼决定要去买车,而且打定主意要买一部好车。老话是“人靠衣装、马靠鞍装”,现在还需要接上一句“没有车子道儿不畅”。我这可不是吃饱了撑得慌特意弄条狗尾巴来续貂。其实,车多了路堵。
现在这年头,若是没私家车,恐怕连丈母娘家的门都不大好进的。
我丈母娘家在地地道道的苏南农村的深处,并不在肥得流油的地方,那儿连像样的马路都没有,可是我的阿舅和阿舅的阿舅们统统都有私家车了。每回逢年过节我去“丈母娘”家,他们就来陪我喝酒吃饭,各式各样的车呼啦啦地停满了我丈母娘家门前的晒谷场。而且我那丈母娘也很能来事体,她并不跟我多啰嗦,只盯着她女儿我老婆一个劲儿地问:“你们什么时候也置部车啊?”
虽然,我们每回回去皆是礼物多多红包厚厚,但因为没有私家车开回去,腰杆子就不能硬硬的。别看那帮小子的车老了点,有的四个轮子的胎纹都磨平了,下雨的时候在泥地里开起来直打滑,可人家是有车族,跟我有本质区别,所以说话硬当。
他们七嘴八舌地叫嚷:“您下次要回来时吱一声,我们开车去接您。甭坐农公车了,挤,这且不说,还跟电兔子似的,起来一蹿,停下一扑,中间蹦蹦跳跳的。不适合您,您好歹也是个有级别的干部,坐它真不合适,您吱一声,我们中的随便哪一位去接您好了。”
他们“您”来“您”去的,“您”得我满脸红热红热的,就跟桌上盘里煮熟了的大江虾一样。非但脸上颜色,连身条儿也曲得跟煮熟了的大江虾一样。
其实,他们那车根本就进不了城,等我回城的时候,还得醉醺醺地骑电兔子去,可没人理会这茬,人人在乎的是有没有车。连远在外地的父母亲要来我家时,都在电话里跟我这样说:“……行了,你就在家里候着吧。让你姐夫去车站接我们,他有车……”
弄得我心里这个窝囊啊!没处说。
我反反复复地做着同样的一个怪梦:一辆黑色轿车的四个黑轱辘忽然间变成了四个黑衣人,他们先是背对着我蹲在地上,后来立起来转过身冲我好不尴尬地笑着。那个铁壳子也在他们身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一顶歇在地上的轿子,轿子里抑扬顿挫地飘出一句话来,我清清楚楚记的是:“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好像是很古的时候哪个圣贤说的?具体是谁?叫啥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只能想得起来:大夫就是官儿,徒行就是用脚走路。本来脚就是为走路而生的,但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旦当了官儿,就不可以扇打着大脚板子亲自在外面走大路了。可我能算作是个官儿吗?应该算是吧,至少在我目前所供职的这个单位里,可以确定无疑俺是“从大夫之后”的。
兄弟我供职于一家肥得流油的单位——市里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但不幸的是,我在这肥得流油的小衙门里得了一份清汤光水的差事。
这差事好不好的,可不能光听名头。虽然我也被封为办公室主任,但和其他十一位正副科长真的没法比,和一正三副外加一个享受副职待遇的领导们就更没法比了。甚至连普通的能管着工程质量的职工也不如。我们党支部书记兼站长经常拿来吓唬人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愿干?那就到办公室搞内勤去!”
由此可以窥见我治下的这个办公室的地位了吧。我手下也就五个人:两个会计,一个聘用的司机、一个聘用的打字员、一个聘用的勤杂工。
不错,按常规办公室是管车辆的,但我这个办公室并没有能供我调配的车辆,因为我们都是搞内勤的。除了办公室,其他科室都是管工程质量的外勤部门,都有专属车辆。说起来更为尴尬的是,全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二十多号人,就我一个没车——没有专门用来上下班以及到别处耀武扬威的小轿车。而且,敝人确实是从大夫之后的呀!这恐怕也正是我的父亲母亲丈人丈母娘和阿舅及阿舅的阿舅等众人想不明白的地方。
话说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恨起了三句儿。我之所以从大夫后却没车完全是三句儿一手造成的。三句儿就是我们单位那个党支部书记兼站长的双肩挑一把手。
咋叫单位一把手这名号呢?一是因为他年轻,还不到三十,对于我们这帮老家伙来讲,他的确是属于儿辈的人;二是因为他喜欢如此这般地办事,就算是你的办公室在他的对面,他也从不主动走过来。要么是电话要么是QQ,提你没商量:“你来一下。”
我就得赶紧过去。
“这事你看怎么办?”
做属下的怎敢怠慢,连忙搜肠刮肚地把对策奏上去。但后来我凭直感觉得:很多时候,他没听明白抑或根本就没听。等我说完了,他就往外吐第三句话:“那就你去办吧。”
做领导,尤其是一把手,原来可以如此简便!久而久之,三句儿的雅号不胫而走。后来,我们几个老家伙很是发挥了一把阿Q精神,认为他在家里也是如此这般使唤他娘老子的,心里也就稍微平静了些许。现在不都是爹娘围着儿子忙得团团转的么。
在他的主持下,我们站里按级别解决交通问题:三句儿是老大,乘坐极配的黑色别克君越;副站长们统一配银灰色帕萨特,那个享受副职待遇的则是豪华版的桑塔纳;接下来十一位正副科长是一色的锃光瓦蓝的普通桑塔纳。一下子各就其位各开其车,唯独我,按行政级别是中层正职——绝对是从大夫之后的,却啥也没捞到。凭啥呀?不蒸馒头还争口气呢,不会开车也应享受个该坐车的待遇吧,任命文件上,我排在第一位,压着那些科长副科长的,怎么也应该给我的办公室配一部车吧?要不,面子往哪儿搁?
没车可不是小事儿,你看,出入单位大门时,保安只冲开车的敬礼。因没车而吃的亏也接踵而来,站里為了调和公车私用私车公用之间的矛盾,又出台了一项配套政策:开私车的每年报销六千元的汽油费和四千元的其它费用。毋须赘言,肯定又是没我的份儿。这一来一去的,等于是我又白丢了一万元。嘿,真是气死个人儿了。
我怒火冲天地去找三句儿评理。我说:
“你把我给免了吧!”
“这是为什么呀?”他两只眼睛倒是瞪得有鸟蛋般大,显现出真心真意的吃惊来。
“车呀!”
“哦,那呀。不就是个车么,至于吗?”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说办公室都是搞内勤的,没必要配车。还说我是一名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要发扬风格。听听,这哪跟哪啊?谁不知道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工作需要是一方面,享受待遇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该享受而没享受,这是多么没面子的事啊?真是欺你没商量。而正好在一旁的邵科长帮腔的三言两语差点没让我的眼泪掉下来,他说:“主任,你可以去买部山地自行车,一千来块钱,经济又实惠,骑着上下班很好玩的。”
真是岂有此理!到底是谁好玩?那时站里开公车无望的普通职工也都买了私家车。你说满院的汽车中间停一辆自行车,还是那个从大夫之后的老家伙的,是不是很好玩?咱可丢不起那人,也咽不下这口气。那咋办呢?
要车?没要着。买车?不甘心。骑自行车?嫌丢人。坐公交?更不对路了,公交车上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
“嫌挤,你开私家车去啊。”
走路。咱接着走自己的路还不行么?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么。好在我家离单位不远不近,急行军般步行只要半个来小时。好像我过去一直都是走路上下班的,挺好的。咋等到三句儿分车后,这路就不那么好走了呢?
过去好像没人在意我是走路上下班的,咋现在就这么惹人眼目了呢?连三句儿都找我到他站长室去又谈了一次。
“你为什么要走路呀?”
问得我是气不打一处来,反问他:
“不走路,我咋上班?”
我想他对于这句反问的弦外音是心知肚明的。果然,沉默了一会,他像下了决心似的说道:
“我不能给你或者说是你的办公室也配部车,没额度了。但我能保证你今后在这里干得很开心。”
“哦,咋个开心法?”
“别急,来日方长嘛。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会碰到一些需要组织上帮忙解决的私事,到那时再说嘛。”
真是屁话,糊弄谁呀?但我记住了他这些话。
2
我有一小哥们,买了房正勒紧裤腰带还房贷呢,可他在前不久,又再刹刹裤腰带,贷款买了部中档小轿车。我很不解,私下问他顶着巨大金融压力买车的原因,他苦笑了一下说:
“送儿子上幼儿园啊。没车送,他就不去。而且车还不能差了,那帮小坏种还在互相比着呢。”
小哥们望望我,郑重其事地建议:
“主任,你也不要再走路了,就买部车开了呗。”
我嘴上没说啥,心里想的是:你开你的车,我走我的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不能碍着谁吧?难道没有车,我还就不上班了?
但我发现,自从三句儿分车之后,看似平坦的大马路好像不再是给我这从大夫之后的人的两只脚预备的。特别是临近建管大楼的一段宽阔的大马路尤其如此。
这条路上车流不息,两侧店铺林立,十分繁华。我常在这儿遇见分管我们站的陈副局长。
若是后来不出事的话,他是一个公认的很好的领导,年轻且极平易近人的局领导。他给我们留下了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句话,这也是他在不同会议和工作场合重复说的一句话:
“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脑子围绕工作高速运转,不给任何腐化堕落的意识留任何思想空间。”
陈副局长毫无疑问有专车,但他一直是走路上下班的。一度给了我一种工作上雷厉风行,生活上从容淡定的感觉。我曾帮他起草过两三回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工作方面的讲话稿,所以彼此相熟。
以前在路上碰着也只是简单打个招呼,一切都很正常。三句儿分车后,我们再在上班的路上遇见,陈副局长就显得很吃惊地问我:
“今天咋没开车?”
“我啥时开过车?我连开车的本本还没有呢。”
“那你怎么上下班?”他更加吃惊地问我。
“我不一直是走路上下班的么?”我小声反问陈副局长。奇怪,这时候我的脸颊莫名其妙地发起热来。
“你为什么非要走路上下班呢?”好像我的反问使陈副局长更加不解,他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感到震惊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回答他呢?说三句儿不给我配车,那不显得我小鸡肚肠,不顾大局打小报告了吗?我只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领导不也走路上下班么,向领导学习呗。”
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望我。好在已经到单位了,我们没再继续谈下去。
我和陈副局长在步行上班的路上再次相遇时,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你打个报告给我,我来想办法解决。犯不着走路嘛!”
我一时犯糊涂了:走路和生活困难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再说了,他不也是步行上下班吗?
哦,对了,他那步行和我这步行咋能相提并论呢?人家有专门的司机专门的小车,那车虽则我叫不上名儿来,但肯定要比三句儿的高档,要不,三句儿怎敢在他手下开黑色极配别克君越。我恍然大悟,原来,首先要真有车,然后把车放在一边的步行才能叫做“安步当车”,才是一种姿态和品位。连个车都没有,你走得再安又能当个啥呀?像我这般从大夫之后的步行法,在似乎知我者的眼里不过是斗气罢了。可我这是在跟谁斗气呢?跟三句儿还是自己,还是跟车或者面子叫劲呢?
他们或许是认为我要不到车也买不起车吧?啊,呸。
恍然大悟后,我就怕再在路上碰见陈副局长,怕又要话不由衷地跟他解释我为什么走路,怕他再那么真心实意的要扶我的贫。那很伤我的自尊心。你可能不能够理解,那确实特填堵的。有一阵儿,我在路上走得慌慌张张甚至鬼鬼祟祟的,就是为了不再遇见他。
好在沒过多久,陈副局长就因经济问题进去了。起因是他收了一个楼盘的开发商送的一部宝马,他又把那宝马送给了一个二奶还是小三什么的,另一个二奶还是小三什么的没有,心里不平衡,到处瞎闹,闹来闹去的就出事了。
谁知,路上虽则不见了爱嘘寒问暖的陈副局长,回家的电梯里偏又冒出了个爱管闲事的女邻居。我这女邻居胖得像个超大号的猪肉狮子头,连到不上五分钟脚程的小区附近的菜市场去都要开车,我估计,她找车位停车的时间都好用脚走一个来回了。回回在电梯里遭遇着了,这个说起话来眉飞色舞的“狮子头”都要大惊小怪地问我:
“还走路呢?”
她这一问也给我一种我好像还没脱贫的感觉,好像我还没有攒够买车的钱似的。奇怪的是我自己,明明心里憋着一股火,脸上偏偏就露出两道忸怩的羞涩来。
路越修越宽阔越修越平坦,但我咋就越走越憋屈了呢?
那一天,我好好地在路上走着,一条穿戴花里胡哨的小卷毛狗追着我叫个不停。俗话说狗仗人势,我心里想本来就给这追着脚后跟叫的小畜牲搞得很是烦躁了,跟在卷毛狗后面那个同样穿戴花里胡哨的女主人偏偏又很会说话,她的几句话差点把我的肺给气炸了:
“汪汪,你就是叫得凶,真让你咬你敢咬么?”
啥意思呀?她这是在鼓励它咬我呢咬我呢还是咬我呢?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即便它不敢咬,我也该给她点颜色看看了。昨天雨天走这儿,被一辆飞驰而过的小轿车溅了一身脏水,我无可奈何,只好冲那车恨恨两句。今天,我再怎么地,也不能被这小畜生和后面的主子撵着欺负吧?老子抬腿一脚,踢得那卷毛狗儿像团毛毛球一样地飞起来落进了路边的灌木丛里。
这一下闯祸了。这小畜生的女主人看着花枝招展,实则是个泼妇。踢了会叫的狗,后面那不会说话的女子几步抢上前来,一把揪住我的后衣领子大吵大嚷不依不饶。
一时狗吠人叫的,我顾得了上面就顾不了下边,人同狗一样的张牙舞爪。卷毛狗的女主人原本涂得鲜红的长指甲被我的血染得更红了。
最后连110都给叫来了。警察拉我到一边小声劝道:
“你就赔她一张吧,好男不跟赖女斗。”
咋要我赔她钱?原来,那畜牲被我一脚踢进了灌木丛,出来时不但灰头土脸,而且还衣衫褴褛的,看上去是吃了大苦头的。本来那狗妈当着警察的面和我纠缠不清,定要我带她的宝贝儿去宠物医院查一查,看有没有受内伤。后来在警察的再三劝说下,才稍稍作了点让步,让我赔她一件狗背心,因为狗儿身上的那件给灌木条子扯破了。她一口价要一百元。
“这不是明摆着宰人呢吗?老子身上的背心才十几块钱。”
“好啊,那你去给它弄一件一模一样的来。”
汪、汪汪、汪……
该死的小卷毛狗紧偎在她脚边帮衬着主子。
我去哪儿给那畜牲弄件一模一样的来?
“要不,警察同志,我把我的背心脱下来赔她,好么?”我真不是调侃警察,我是在真诚地向他提建议。
谁知那警察居然换了一副严肃的专政面孔对着我说道:
“别开玩笑了,我没工夫陪你们在这玩儿。你一个大老爷们,就爽快点吧。”
我忽然想起,单位上、小区里的保安都是只给开车的主儿敬礼对着牵狗的主儿赔笑脸。我这甩打着手呱嗒着大脚板子的,在警察叔叔那里也就能落得个和城市盲流差不离的待遇。
没办法,只好自认倒霉,我抽一张红票子交给警察,然后眼睁睁看着警察把我的百元大钞交到卷毛狗的女主子手里。
拿到钱后,那女的咧嘴一笑,不谢警察更不谢我,只冲她的狗儿来了一句:
“走喽,汪汪,我们买好吃的去喽。”
汪、汪汪、汪……
人领着狗兴高采烈地扬长而去。
望着女人扭饬着的屁股和狗儿高举着的尾巴,我气得浑身哆嗦。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只许狗欺负人,不许人教训狗?
这路还咋走么?你说这警察也真是的,我转身去找警察,可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3
我去五台山的时候,在尊胜寺负责讲解的和尚突然发问:
“众生平等吗?”
随着他这一问,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三句儿分车的事儿上,脱口答那和尚:
“众生在制造不平等。”
业已有些年纪的和尚目光炯炯地盯了我好一会儿,微笑着说:
“施主原来有慧根。”
“有也都已烂在心底了,呵呵呵。”
“不晚不晚不——晚。”和尚冲我很郑重地点了三下头。好像有些意思。
更有意思的还在俗世。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站里流传起两句顺口溜来:
三句儿专欺三种人,无影腿只踢无心人。
三种人是指没后台的、新来的和老实人。这好理解。无心人也好理解,至于无影腿嘛,却要费一番口舌了。
三句儿不但给自个儿搞了一部好车,还专门聘了一个姓刘的师傅供他使唤,主要是帮他料理加油、洗车、维修、年检等等的一应杂事,他只管开不管别的。若是在路上和别人碰撞摩擦产生麻烦了,也是一个电话把刘师傅招来替他处理,他则溜之大吉。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才换的那新车就偏不让三句儿舒心。他回回下车关车门时,背后都好像是有人暗中踢他一脚。刘师傅去试的时候就没有。开到4S店去查,人家分析可能是静电作祟,就在车底拖了一条铁链子帮着跑静电,就像是藏不好的一条狐狸尾巴,但还是没用。那车还是隔三差五地踢他,不轻不重的。有人说那叫无影腿。于是,单位上就传开了这么两句顺口溜。
新买的车,而且从定点选车谈价到提车,都是三句儿一个人一手操办的,也赖不到别人身上。再者,刚买的新车,又实在没有马上更换的理由。没办法,他回回下车后都不敢如人家般潇洒地一碰车门了事,只好慢慢地、轻轻地、做贼似的合上车门。
我说他这是活该是合情合理的,怎么后来连刘师傅私底下也说起他活该来了?
这刘师傅和我一个办公室,烟是我一根他一根地越抽越多,话是他一句我一句地越说越近乎。
我从他口中得知,作为一站之主的三句儿竟然沒心没肺到了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有一次,他从外地出差回来,正下着瓢泼大雨,刘师傅开车去高铁站接了他一路把他送到家后,浑身一滴雨水都没沾着的三句儿一个谢字都没有,就冲刘师傅摆摆手说:“你回去吧。”
三句儿说完,拿着车钥匙拎着包自顾自地上楼去了。刘师傅当时就愣怔在车库里了。天又黑又下着大雨,不给车,连把伞也不给,就这么的让人家自己回去,有这么无心的人么?
刘师傅站在三句儿住的那个小区的冷冰冰的车库里翻江倒海地酸楚了一场,最终无可奈何地冒雨摸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回到了家里,整得落汤鸡样的。连气带累加上淋雨,刘师傅当夜就感冒发烧了。第二天,老伴陪着他到医院挂水,刘师傅是个细心的人,他一边打点滴,一边打电话给三句儿请假,结果还被他数落了一顿:
“咋搞得?怎么这么不小心。现在单位这么忙,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你不来,万一车子上有什么问题了,我找谁去?雨淋一下就病,你咋就这么娇气呢……”
把刘师傅气得当时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幸亏老伴在旁给劝住了。说是找个活儿不容易,忍着吧。
刘师傅挂完盐水就硬撑着去上班了。
听完,我愤愤不平地说:“这领导也真是的,就不能让你把车开回去,第二天一早你再去接他,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刘师傅哼哼了两声,摇了摇头。
然而我们和三句儿因车而生的气却是越来越大。
我原盼望着车改,心想车改后,我这从大夫之后的就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地一块儿享受一份车贴了。谁知,在我们这座三四线的小城里,车改只推进到处级机关事业单位。财政算了一笔账,说如果再往下改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削减公车费用来得实在。得,我这从大夫之后的是甭想拿车贴了。而在科级事业单位中混的如鱼得水的他们才不怕财政削减公车费用呢。
邵科长开着他的那辆桑塔纳去他监管的一处工地上发整改通知书,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车身被另一辆车给擦了一下。发完整改通知出来的邵科长一看,正待发作时,只见那工程的项目经理跟个胖弥勒似的满脸堆笑地迎上来,他一边连连赔不是,一边跳出两根肉乎乎的手指头说:“两万块、两万块,够不够你修车的?”
邵科长一听,立马转怒为喜。自己开着车到修车场兜底弄得跟新车似的,还不到一万元。他想了想,正好自己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就在修车场又搞了一套高级电动按摩椅,一共是一万七千元,全部以维修费的名义由那个工程的项目部给报销了。
就这样,邵科长还说便宜他狗日的了。
至于整改嘛,自然是不了了之了。
此事在我那个站里传为美谈,有好事者顺嘴问我:“怎么样?主任,看看人家,再想想你自个儿吧?”
把我气得脱口说道:“我怎么了?走路有什么不好?真是的,大路朝天,你开你的车,我走我的路,走路又环保又廉洁,多好啊。”
真是祸从口出,我这话不仅把邵科长给得罪了,恐怕把三句儿也给得罪了。没过多久,他就给厉害让我尝了。
这年夏天赶上了百年一遇的高温。报纸上说有个老人不慎摔倒在路边,等人发现扶起来时,半边脸都烤熟了。偏偏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中午都必须赶回去给放暑假在家的孩子做午饭。
刘师傅看我赶来赶去的实在辛苦,就把本已废置不用的面包车鼓捣好后开着送我。
我知道三句儿的为人,怕给刘师傅找麻烦,所以一开始并不肯让他送。是刘师傅执意要送的,他说:“他们大大小小头头脑脑的,哪一个不是开着公车回家睡午觉的?”
说的也是,他们是天天如此,我不过是难得几回,而且我也是从大夫之后的响当当的办公室主任耶,他三句儿应该不至于不讲这个情理吧?
我忽然想起三句儿曾信誓旦旦地保证让我今后很开心之类的话,就对好心的刘师傅说:“如果他问起这事来,你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他不會连这事都管吧?那也太不讲究了。”善良的刘师傅天真无邪地说道。
“你以为他是个讲究的人吗?他要稍微有点讲究,就不会让你冒雨徒步回家了。”
“哦。”
听我这么一说,刘师傅的心好像往下一沉,没精打采起来。
事后,我们才反应过来,三句儿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们。到第三天中午,刘师傅开着面包车载着我刚出单位大门,他的电话就响了。还真是三句儿,他一上来就问刘师傅在哪儿?刘师傅望望我,眼神里透出点紧张,不知如何回答。我指着自己的鼻尖算是提了个醒,他于是说:“我在送主任回家呢。”
三句儿在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全乎也听不清楚。但我肯定他的话又多又难听。刘师傅最后说的是:“随你的便吧。”
等挂了电话,我再次叮嘱刘师傅:“你一定要咬住说是我要你这么做的。我可是你的顶头上司啊,让他冲我来。”
他苦笑了一下,调侃我:“你以为他会讲究这个吗?”
这回是我太天真了,我想三句儿曾对我信誓旦旦:“我保证你今后在这里干得很开心。”再怎么地,也会给我个面子,不会太难为刘师傅吧。就是有气也应该冲我撒呀。可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三句儿不容分说就把刘师傅给开了,反正刘师傅是他口头聘用的,连一纸合同都没有。三句儿说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这儿是三句儿的领地,他说了算,开个刘师傅,简直是哈气吹蝼蚁。
我又气又悔又无可奈何,能做的似乎也就是尽快买车,咬牙买部比他坐的极配的黑色别克君越好的车以示抗议。
夜里,我又做了一遍那个怪梦。不过这次我看清了四个黑衣人中有一个是刘师傅,他冲我拱了拱手,转身和其他三个人一起抬起了那顶黑轿子,越抬越快、越抬越快,直到“嗖嗖”地奔驰起来,变成了一辆现代高级轿车,并从尾气管里喷出了那句话:“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我终于听出来是大圣人孔子说的。第二天,我在《论语》“先进篇”中找到了原文。不由得感叹道:
圣人就是圣人啊,即便是牛拉的车,也不可一时或缺。更何况我等落于纸醉金迷的红尘里的凡夫俗子呢?
我随手还翻着了下面这一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我说:“车不车,车啊!车啊!”
大路朝天,没车难行。我这就买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