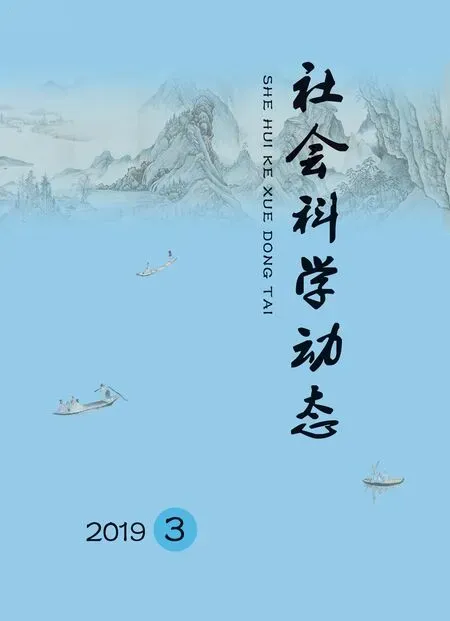20世纪以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综述
徐 威
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急剧变革的时期,而体现在赋役制度上尤为深刻。明初尤其是洪武一朝,绘制鱼鳞册,颁行户帖、黄册,遍行里甲,强行佥役,军匠分籍等,在有明一代的赋役制度创设上具有奠基意义,王朝统驭经济的超强制色彩十分浓重。正统以后,财政规模难以应付繁多国事,尤其在战事频繁、宫廷超额支出、宗藩食禄等问题上愈发困难,因此改革成为中晚明赋役制度的主要线索。目前学界在对明史的研究在整体上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但就赋役制度一项进行梳理评析的文章不多。本文在通过较系统地收录近百年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探寻其发展脉络,以期求正于方家。
一、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阶段
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分离于明史的总体研究,自成一系,得益于20世纪初新史学观念的引入。发展至今,共有70余年的学术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奠基阶段(20世纪30—40年代)
从整体而言,系统的明代赋役制度史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实为奠基人。其陆续发表的《明代鱼鳞图册考》、《明代粮长制度》系列论文、《明代的黄册》以及围绕一条鞭法展开的论著等,明确把握住了若干最为核心的研究问题,并框定了基本研究语境。同时,梁方仲尤其重视地方志资料和计量方法的利用,从中国各地以及日、美等国收录了1000余种以上的方志材料,与官书相补充,从侧面反映了各种赋役制度在地方实行的真实情况。此外,日本学者清水泰次译入国内的《明初田赋考》、《明初之夏税秋粮》、《明代田土的估计》等若干论文,质疑明清文献中的田额、地亩数字和税目记载的准确性并引入援证,推动了一批辨析具体赋役数目论著的出现,成为三四十年代的又一种研究趋势。
此20年的研究开始步入正途,出现了新的论题与方法,但就总体而言,缺憾仍然不少。专力研究此项课题的学者稀少,研究力量略显单薄,相当数量的成果仍拘泥于辨析与介绍,受传统史学的影响程度较深,因而研究水平整体上仍受很大限制。
2.发展阶段(50—70年代)
进入60年代后,明代赋役制度课题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全国各大高校开始着力培养相关研究人才,特别是史学界对所谓“五朵金花”等问题的热烈论讨①,成为积极的推动力。
在粮长制度、黄册、一条鞭法等主要课题的研究方面,梁方仲增补出版了《明代粮长制度》、《明代的黄册》及《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等论著,使其研究达到系统化高度。同时,一批青年学者加入研究队伍,尤以韦庆远最具代表性,他于1961年出版的《明代黄册制度》一书更注重黄册制度与其他典章制度之间关系的探讨,诸如分籍、里甲、鱼鳞册等,均有一定突破意义。此外,对粮长制度推行原因、里甲作用、一条鞭法推行后的丁徭与社会状况等,此时期都有新的阐释。
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激烈批判明朝封建统治阶层对劳动人民的压榨,江南重赋问题成为了研究的一大热点。伍丹戈、林金树等学者系统梳理了江南官民田的由来、种类、科则、数量及各占比例等几个问题,提出了官田居多导致赋重的观点。
本阶段主要的特征是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面进一步铺开。
3.交流与繁荣阶段(80年代至今)
80年代后,随着与西方及日本学界的交流与互动,明代赋役制度研究进入大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三:
一是对“分流”观点和白银流动这一因素的重视。美国加州学派的“分流”观点以及弗兰克等人的白银理论对国内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如樊树志、万明等以世界史观、白银输入等视角考察晚明的财政赋役变革,尤其是与一条鞭法推行的相互关系,成果颇丰。
二是新出史料大量运用于学术研究。中国社科院于80年代开始整理的徽州文书,包含大量关于家谱、地契、供单等一手史料,栾成显、周绍泉等学者加以充分利用,对明代鱼鳞图册、黄册、里甲等制度的实行情况提出不同看法。地方省市博物馆、档案馆珍藏的鱼鳞图、亲供长单等实物公布,对研究明代不同地域情况有所贡献。
三是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与深化。明代役制方面,唐文基、左云鹏等学者对里甲正役、各种杂泛的由来、编佥、负担状况、优免等都作了充分的研究,填补了长期以来的诸多空白。
二、主要研究议题概述
以下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个人阅读与体会,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议题进行简要归纳与总结。
1.赋役制度与赋役文书
本文探讨的赋役制度,仅就有明一代长期存续的基本田赋力役的征调制度而言,而文书则是随之定期编修的赋役文册。从20世纪初以来,相关的论著发表数量占各类明代经济史著述之首,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重点。对这一方面的长期延续性研究,逐步揭示了明代赋役制度全面而真实的情况,意义重大。
(1)明建国前的赋役制度。明代文献中关于明建国以前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洪武实录》、刘辰《国初事迹》和宋濂《大明日历》等几部书中,因材料缺乏,研究成果较少。最早论及此题的是方中1933年发表的《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一文,首次探讨了朱元璋起兵之初的“寨粮”问题,即临时征收、无固定税率、带有军事强制性的军粮收集制度,结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胡大海之奏②。关于明开国前赋额问题,也有探讨。赵其芳《明代之赋役制度》,认为明太祖为吴王时的赋额为十取其一,役是按田佥派③。畏人《明开国前后赋率》指出,明开国以前的赋率大约在什一到什二之间,并且明初在四川推行的十取其二的赋率是承自明夏政权④。
(2)鱼鳞图册。鱼鳞图册是有明一代记载户口实在田亩数量的基本册籍。鱼鳞册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的《明代鱼鳞图册考》可以视为开山之作。全文第一次较全面地论证了鱼鳞册的内容、与黄册之间的关系、名称之由来、与前代的沿袭情况、攒造经过五个问题⑤,基本框定了明代鱼鳞册研究的范围与范式。同时,大量征引地方志作为史料支撑,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此后鱼鳞册的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沉寂,直至60年代才出现了具有推进意义的成果。1961年韦庆远出版《明代黄册制度》一书,从黄册制度的角度凸显出作为土地管理办法——鱼鳞图册制度的作用,并认为“两者是互相补充和互相配合的关系”⑥,充分肯定了鱼鳞册的史料价值及其研究意义。80年代以后,鱼鳞册研究的重点在于明代鱼鳞册首次攒造的时间及其起源等相关问题。唐文基《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洪武元年》一文中即指出,建国后的一些通史和专著将明代绘制鱼鳞册定在洪武二十年的说法明显有误,并在梁方仲基础上将始造时间提前至洪武元年⑦。刘敏在《明代“鱼鳞图册”考源》一文中探讨了鱼鳞册在两浙首先出现的原因,他认为至少在元顺帝至正年间,浙江绍兴路、衢州路、婺州路、处州路等很多州县就已经实行了鱼鳞图册,其中尤以婺州路最为普遍。明初赋役制度尚未建立之时,两浙地区依然承袭了元代的旧制,并且后来得到明中央的认可,得以向全国推广⑧。
90年代,鱼鳞册研究的突出进步体现在与原始材料的结合上,栾成显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学者。其《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册考》一文,查证各册所载字号“民”,推断出地点应在祁门县十西都九保。又利用册籍有“金户”这一属于元代诸色户的名称,结合朱元璋在龙凤十一年(1365年)在徽州实行废除金课的“已巳改科”的具体情况,确定该册攒造时间为龙凤三年(1357年) 至十年(1364年) 之间。栾成显据此认为,作为明朝开国的首次土地经理及攒造的鱼鳞册,发生在龙凤时期,提出了龙凤说的观点⑨。还有《洪武鱼鳞图册考实》等,重点也在质疑与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颇,如税亩数低于实亩数的通行观点等等⑩。
(3)粮长制度。明代粮长制的研究仍由梁方仲发端,其系列论文《明代粮长制度》 (初探)、《明代粮长制度》和《明代粮长制述要》可以视为奠基之作。其详细考察了明代粮长设立的用意、区域、职责、催收解运税粮的程序、编佥粮长的原则及其后期转为轮充、朋充的变化等问题⑪,宏观上架构了研究粮长制度的框架。
50年代以后,粮长制研究一度中断。80年代以后,粮长制研究开始由从宏观整体向关注具体地域、府县为单位转化,相继有部分论著问世,颇有价值。洪沼的《明初的迁徙富户与粮长制》,以江南区域为中心,重新审视了明太祖建立粮长制度的目的,认为以往谈到的免除胥吏侵渔百姓并非主要原因,以及优待南方富民,争取对新朝的支持也不尽然。相反,粮长制是明太祖对江南富民采取强硬经济政策的手段,体现了明初地主阶级内部之争⑫。蒋兆成的《明末清初杭嘉湖的里役改革》考察了浙江杭嘉湖三府从嘉靖末年到雍正初年里长、粮长等里役的变革情况⑬。周绍泉利用徽州文书所作《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一文,对学界长期认为的明代的粮长制和老人制,在嘉靖年间就已经废弛,以里甲制为核心的基层体系也因万历均田均役而消亡的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列举94条从嘉靖十三年到道光二十九年有关粮长、里长和老人行使地方职役的材料,证明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徽州的里甲、粮长等并未废除⑭。
21世纪后延续了90年代以来利用文书资料辨析旧有观点的研究思路。如汪庆元的《明代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施》,就利用新发现的《新安蠹状》等资料考察了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行情况和演变过程⑮。谢湜的《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与以往考察粮长的视角不同,着重粮长在地方上的积极作用⑯。
另外,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唐文基先生的《明代赋役制度史》,这是国内第一部明代赋役史专著。其中“粮长制度的建立”部分,较为完整地梳理了明初粮长制的源流,并且广采宋濂《朝京稿》、吴宽《匏翁家藏集》等明代时人的文集笔记,翔实可靠,具有史料价值⑰。
(4)杂役和均工夫。明代的役法研究,起步比赋税研究晚的多,80年代之后才有相关论著出现。除去里甲正役(另述),此处拟从明代杂役及其种类、佥派原则和程序、均工夫、徭役优免四个方面论之。
在明代杂役及其种类方面,左云鹏、唐文基等学者作了充分的研究。左云鹏的《明代徭役制度散论》认为明代杂役应始于洪武二十七年,是里甲正役难以承担驿差的结果,内容包括马夫、水夫等项目⑱。唐文基的《明初的杂役和均工夫》⑲,把杂役分为各地普遍性的杂役和地区性、临时性的杂役两类,普遍性杂役有隶卒、铺兵、馆夫、驿夫、斗级、库子等,地区性、临时性杂役有仓脚夫、抬柴夫、砍柴夫等等,并对各种杂役的编佥、职责都作了详细探讨。同时,也有几篇文章专门就杂役中的驿役进行研究。李长弓的《试论明代驿传役由永充向轮充的转化》从整体上论述了明代驿传役由永充转变为轮充的过程。他的《试论明代驿传役编佥“唯粮是论”》提出了明代驿传役的编佥不同于里甲、均徭等役“必验民丁粮多寡,产业厚薄”的特点,而是唯民户岁纳粮赋是论这样一种一元化的编佥标准,这在明代役法中独一无二。其关键在于驿传役在明代徭役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地要求役夫在出身手服役外,还要承担应役所需各种财费的标准,实行自备当差⑳。陈京的《明驿的组织管理及其特点》一文提及了陆驿、水驿、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等不同组织形式的驿役情况㉑。吕景琳等《论明代驿传之役》则着重关注了明中后期乘驿之滥的弊病,由此导致驿夫难以负担而大量逃亡的情况。并且指出在正德出现改驿传役力差为银差之后,驿传役折银大致在313万172两(《明会典》载万历以前),要比太仓银库年入200万两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半有余,可见驿传之重,苛剥之深㉒。关于铺户,有唐文基的《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赵毅的《铺户、商役与明代城市经济》等几篇文章。探讨的问题在于,铺户的身分或者含义,铺户的负担及其演变(当行买办、招商买办、佥商买办三种形式以此演变),铺役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等几个方面㉓。
关于役的佥派原则和程序,明代杂役的佥派,大都采取按粮佥派的原则,这可能是出于均民赋役的需要。左云鹏的《明代徭役制度散论》,秦佩洐的《明代赋役制度考释》,王毓铨的《户役田述略》和《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两篇论文等,大致持相同的观点㉔。而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一书中则提到了除按粮佥役外,明初还存在一部分杂役采用雇募办法的观点。
均工夫这种役制,创始于洪武元年二月,因为只在直隶应天周边18府州(也有17府州说)佥派,推行范围较小,因而关注的人并不多。就笔者所见,仅有伍跃《均工夫役浅析》㉕和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相关章节有专门探讨。伍、唐两文主要阐明了洪武初佥派均工夫的地域范围集中在直隶附近17府州、佥派原则为验田出夫,大造黄册后仍然存在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均工夫这种杂役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徭役的优免方面,有伍丹戈的《明代徭役的优免》、张显清的《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等论文,概述了明代各种专业户优免徭役的条件,平民反抗徭役的斗争等情况㉖。
2.赋役征调与基层治理
明代的赋役征调,包括以田土为中心的田赋征纳和以里甲为核心的徭役摊派两个方面。涉及到的问题,涵盖了明代国家对田土的掌握程度、田制、科则、征收实物类型、解运存留以及蠲缓、黄册攒造和里甲等内容。这也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研究热点,在动态过程中揭示赋役征发的具体情况。
(1)明代田额、田制及科则。对明代不同时期田额的考察,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对明代田赋资料的汇编和整理。《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文,以《实录》和《会典》的各种版本为基础,统计出明代自洪武至天启(无建文)14朝的全国分区田地面积数,提供了直观准确的田地数字㉗。日本学者清水泰次《明代田土的估计》一文首次对明代文献中有关田数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从洪武到弘治的田额有400万之差,但税粮总额并没有明显差异,故洪武初的田额存在问题,并且推断有明一代土田的面积大致在400万顷上下,连山塘合起来是800万顷左右㉘。此后,这种认为明代文献记载失实的观点逐渐被学界接受,出现了许多分析性论著。1980年马小鹤等《明代耕地面积析疑》一文,对洪武二十六年857余万顷、弘治十五年422万余顷、万历六年697万余顷三个数字进行分析,认为《会典》所载洪武数字有误,因为各分省土田数字有所夸大,尤其是湖广高达220余万顷,超出实际数字10倍,所以明初的实际田额应为400余万顷㉙。王业键则认为万历二十九年实际田额应为773万余顷左右,比较准确。1981年,王其榘发表《明初全国土田面积考》一文,指出明代田土面积错误源自洪武二十六年成书的《诸司职掌》一书,其统计的田额849万余顷的数字被《会典》、《明史》等继承,几经流传,成为错局。王文通过考证,认为《诸司职掌》在湖广、河南二布政司和南直隶凤阳府三处数字都是错的,得出洪武时土田的最高额当为450万顷上下㉚。田培栋《明代耕地面积的考察》认为从洪武二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180余年间田额始终维持在400万顷上下,但这是纳税熟田的数字。同时由于明朝永不起科和垦田归己的政策,有大量荒田被开辟,从嘉靖开始的清丈直至一条鞭法,明代的田额达到了700万顷上下,并一直到明末㉛。樊树志《万历清丈述论——兼论明代耕地面积统计》通过考证,提出了万历六年清丈后,全国耕地面积比明初增加了80%左右,比万历六年清丈前增加了50%的观点㉜。总体而言,这些观点都普遍认为《实录》、《会典》、《明史》及《后湖志》的洪武年间部分所载全国田额都是失实的,明初田额实际数字应为400万顷以上,至万历时增至700万顷左右,总体上田额是逐渐增加的。
关于明代的田制和科则,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研究一度盛行的影响,论著颇多,成果丰盛。上世纪30年代即有方中的《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一文,明初田赋制定的时间应当在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到吴元年十二月之间,但文末又提出未免过迟的疑问。其后戴博荣的《明代的田赋制度与垦荒政策》将明代田制分为官、民两类,并对官田的各种类型如旧有官田、还官、没官、断入富、学田、皇庄、官庄、屯田等都作了简略介绍,对田赋科则、江南重赋等问题也有论及㉝。日本学者清水泰次的《明初田赋考》,认为《明史》所载“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存在很大缺陷,其中各种田制纷繁复杂,不可视为一般性法则㉞。总体上,这个时期仍处于初步的介绍和质疑层面上。
建国以后,在阶级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史观下,注重土地制度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研究,专门针对明代田制及科则考察的论著不多。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赖家度的《明代土地占有关系和赋税制度的演变》、伍丹戈的《论明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清田制札记》、《明代的官田和民田》等㉟。其中伍丹戈的《明代的官田和民田》一文,系统梳理了明代官民田的由来、种类、科则、数量及各占比例等几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㊱。也有少部分讨论江南田赋独重原因的文章,如王仲荦的《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和江南纺织业》认为,苏松嘉湖四府的布缕之征是造成江南超额田赋的原因,江南重赋是以变相手段剥削纺织机的结果㊲。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则认为大量官田的存在和江南地主阶级为兼并官田而着力渲染和批评“重赋”,这两点才是江南重赋现象产生的原因㊳。
80年代以后,对该问题的研究集中到江南区域,尤其以林金树等学者为代表。林氏的系列论文《明代江南官田的由来、种类和科则》、《关于明代江南官田的几个问题》、《明代江南民田的数量和科则》等,具体分析了苏州等个别府县的官田科则繁重,民田科则轻少的现象,并指出民田粮轻而大大刺激了官田的买卖,加快了官田的私有化进程㊴。
(2)田赋征收与蠲缓。明代两税的税目,每年税额及征解方式等问题受到关注较早,但成果不多。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对明代两税征收的具体实物进行过讨论。梁方仲发表的《明初夏税本色考》,总括史籍记载的夏税本色的5种说法,即农桑丝、丝绵、布、钞、麦,认为夏税本色就是麦无疑㊵。清水泰次《明初之夏税秋粮》也持同样的观点㊶。此外,梁方仲的另一篇论文《明代“两税”税目》,列举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十五年和万历六年三个时期的两税税目,发现夏税税目由洪武时期3项一直增至万历时期31项,税目日趋繁杂,还考察了各项税目输纳地域的分配情况㊷。
关于上供、物料的研究,相关论著不多。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上供和物料作了区分,也是由里甲负担。但是刘志伟的《关于明代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目前尚无材料能反映明初里甲需要承担上供物料的情况㊸。高寿仙的《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认为明初实行按月时估制度,凡遇买办物料等项,即以此作为价格依据。后来时估制度废弛不行,遇到买办物料等项,便采用随时估价的方式㊹。
税粮的征解,最早的研究见于梁方仲的《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和《田赋输纳的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两篇论文,侧重阐述了各地方距京师路程与税粮起运存留划分之间的关系,认为起运存留的分配情形,以距离和贫富为依据,越远或贫瘠的省份,起运的田赋就越轻㊺。肖立军的《明代财政中的起运与存留》,认为起运、存留是明代财政的核心内容,对明代起运、存留的来源、种类、用途及变化等作了详实论述,并特别强调了“羡余”这样一种具有地方财政萌芽意义的财政现象㊻。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则从整体上对明代起运、存留的大致数字进行了估算,并进行了比例划分,突出了明代宗禄支出在地方存留之中的弊端。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江南白粮和漕粮的问题。吴智和的《明代江南五府北差白粮》,初步对明代苏州、松江、嘉兴、湖州、通州5府州的白粮负担予以研究,阐明了5府白粮总额、征解过程、运输路线、白粮船编制以及白粮差解所受的盘剥5个方面的问题㊼。鲍彦邦的两篇文章《明代漕粮制度》和《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除概述白粮的来源、用途、特点,白粮解运的组织形式,白粮解纳遭到的盘剥等问题外,更指出白粮只是部分府县承担的实际情况㊽。
明代实行田赋蠲缓政策的研究,数量较少,起步时间也较晚。上世纪80年代有田培栋的《论明代的“永不起科”政策》一文,比较有价值的是作者整理了自洪武到嘉靖各朝有关“永不起科”的诏令,并推算出明前期北直隶、山东、河南因“永不起科”增加的田额㊾。风良的《明代永不起科令实施时间的地域差异》认为明代“永不起科”这一政令主要实施于北直隶、山东和河南三地,并且三省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都不尽相同㊿。除此之外,还有着眼于特殊原因实行蠲免的考察,比如周致元的《明代永免凤阳临淮二县徭赋考辨》,辨析了明代文献中凤阳府赋役永免记载的错误;《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一文探讨了明代救灾的程序、频率、对象,蠲免的内容、数额,漕粮改折的办法,以及由皇帝个人决定和以保障国税为核心的救灾措施的局限性[51]。
(3)户帖、黄册与里甲制。户帖制度是明代基本的户籍制度,其雏形在明朝建国之前就已存在。冯尔康的《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一文,认为户帖来源于建国之前朱元璋政权的“给民户由”,并且由朱本人亲自“花押”,反映了明代对户籍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朱元璋政权支持贫苦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态度[52]。
对于户帖的研究,学界一直置于明代整个户籍制度进行考察。张志斌的《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一文详细探讨了户帖、均工夫图册和黄册三种赋役册籍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以洪武十四年作为分界点,前期是户帖、均工夫图册和小黄册三种文书并行,户帖给各户收执,小黄册存于官府,并且由于户帖只颁行过一次,无法反映人户变动情况,而均工夫仅行于直隶周边,实际上小黄册才是征赋依据。洪武十四年之后,明政府正式确立以黄册为中心的赋役征发体系,黄册每10年一造,户帖一年一造,逐渐废止[53]。卞利的《明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社会的稳定》就农村中户等的划分,户帖制,黄册制度,逃、流民籍等问题作了探讨[54]。陈学文的《明代户帖制度的建立和户帖格式》考察了户帖的格式、内容及相关问题[55]。栾成显的《明清户籍制度的演变及其所造文书》系统考察从户帖到黄册的演变过程,并指出这种长期实行的户籍与赋役合二为一的制度,是导致明代中后期人口统计严重失实的主要原因[56]。
黄册研究,最早有梁方仲的《明代的黄册》一文。全文分11个子题,梳理了黄册由来、作用、内容格式、编制申解的手续、大造及其费用、黄册库架及黄册数目、造册及监造人员、黄册与鱼鳞册之间的关系、后湖查册管册晒册人员、造册失实处罚等问题,具有奠基意义。后梁方仲在前稿基础上增补再刊,增加了“清查及保管费用”一节。考证了明代黄册的保管、清查经费的来源由南直隶应天府上元、江宁两县出办的情况[57]。60年代开始,黄册研究走向系统化和全面化。1961年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一书出版,明代黄册问题又开始重新受到学术界重视。全书以黄册为中心,慎选详细史料,依靠实物资料判明重要问题,是首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58]。关于黄册的最后去向,有赵践的《记明代赋役档案——黄册的最后遭遇》一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顺治十八年户科档案给出了解释,指出明末170多万本黄册最后被清廷分批拨给地方杂用或者变卖的结局[59]。值得注意的是,栾成显从80年代以来围绕黄册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1983年出版的《明代黄册研究》一书以及《明代黄册制度起源考》和《明代黄册人口登载事项考略》等专题论文,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对黄册渊源于小黄册以及黄册制度败坏后出现的新册籍与黄册本身之关系等问题[60],都有细致而独到的研究。此外,栾成显对黄册在人口统计、政治身份划定等方面的作用也有探讨,有《明代人口统计与黄册制度的几个问题》,《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等[61]。
明代的里甲制极为复杂,不仅在同一时代诸书称谓不同,在同一史籍中相关记载又互相矛盾。这是因为里甲制从创始之初,因地理、经济等因素本身就带有地方色彩,自明后期折银之后,新旧里甲之役的概念又常常混淆不清,实为研究的一大难症。
从五六十年代起,关于里甲的轮输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对里甲制的关注。衔微的《明代的里甲制度》一文,就直接谈到“明代里甲制的内容如何,至今在有关著作中还没有给以满意的解释”,确实直至60年代还鲜有著述涉及到明代里甲制的问题[62]。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一书中旁述了明代里甲的状况,着重解释了“十甲轮输”问题,特点在于轮流应役。而衔微则认为,“十年轮输”只是规定全里百十户人家十年内充当一次里长或甲首,未必依次轮流,而“十年轮输”(即梁谈及的“十甲轮输”)应该是均徭输甲的办法。同年,梁方仲也发表《论明代里甲法和均输法的关系》及续篇一文,梳理了里甲制的几个问题,认为甲首的含义有从甲长到一般甲户的变化,十年轮输的方法在明初确实得以推行,自中期才被银差取代。均徭法和里甲法的关系在明朝建立伊始,并非并行的关系,到了正统初,才把杂役中经常性的差役划分出来,均徭才与里甲、杂役并行。经过讨论形成的这些观点,基本被学界接受并且延续了下来。[63]
80年代以后,里甲的专题论文也有所增加,主要关注里甲在基层社会运转的情况。刘伟的《明代里甲制度初探》,对明代创立里甲的渊源、特点、制度构建及其作用弊病都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64]。唐文基的《试论明代里甲制度》非常具体地分析了明代里甲两项超强制机能——政治强制机能和超经济强制机能,以管理人丁与佥派徭役为主的里甲正役,体现了明代通过里甲对全国人口土地的超强控制[65]。王兴亚《明代实施老人制度的利与弊》谈到了明代里中的老人一职,填补了里甲研究的一处空白,考证了明代里甲老人创立的时间,老人的人数及其职务,老人的职责及任期等三方面的情况[66]。此外,栾成显的《论明代甲首户》则认为明朝把一切有纳税服役能力的人户都编为甲首,明代里甲制下的甲首实质上是明代国家的编户齐民,每里甲首数应为百户。其另一篇文章《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则介绍了明代都以下建制分为两种:一为都图,以人户划分为主,属于黄册里甲系统;一为都保,以地域划分为主,属于鱼鳞图册系统[67]。王裕明的《明代总甲设置考述》认为明代总甲为一种职役,遍设于社会治安、军事建制、徭役组织、商税机构之中,其性质应该与里甲区别对待,而组织形态亦相当复杂[68]。丁慧倩《里甲、清真寺与回回家族—以山西长治回回家族为例》结合里甲赋役、清真寺建设,考察了山西长治以程氏和马氏为主线的回回家族发展历程[69],是为数不多的考察里甲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情况的代表性成果。
3.赋役制度的演进与变革
明朝从宣德开始,在江南尝试推行调整江南官民田税率的改革活动,引起了明代中后期赋役制度改革的浪潮。关于这方面研究最为突出的,是田赋货币化、一条鞭法等几个问题。
上世纪30年代,梁方仲相继发表《一条鞭的名称》、《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争论》、《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等论文,奠定了一条鞭法研究的基础[70]。这一系列的文章,详细考察了一条鞭法的内容,推行情况及其在赋役制度史中的作用。
五六十年代,除了梁方仲在继续一条鞭法的研究外,还有很多青年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中来。梁著有《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一条鞭法年表》,皆是汇集大量史料而成,详列了一条鞭法在各地的推行情况,并且探讨了一条鞭法改革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意义[71]。田继周发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一文,详细分析了一条鞭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论述了一条鞭法实施的概况、特点、作用和性质等,认为一条鞭法的实施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的实行是为了整理封建政权的财政,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策,含有专制主义政权和豪绅地主斗争的性质[72]。王方中的《明代一条鞭法的产生及其作用》,不同意万历九年以后全国各地立即实行了一条鞭法的说法,提出万历二十年以后,还有关于某些地区才开始实行一条鞭法的记载。该文还分析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及流弊,如促进农民的分化、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不编户则,还是改为按地和丁征银,或者摊丁入地,都会使负担额比从前合理些,都有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增长的作用等。其流弊在于一条鞭法施行后又出现了加派,仍然有职役和徭役[73]。
七八十年代,国内关于一条鞭法研究的文章较少,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南炳文的《一条鞭法始于何时》考证出一条鞭法的确切开始推行时间为嘉靖九年十月二十日[74]。陈世昭的《明代一条鞭法问题研究》对明代一条鞭法产生的历史条件,由创议、实行到全国推行的过程进行考察,并探讨了对一条鞭法的认识和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75]。另外还有曾唯一、沈庆生的《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柳义男的《关于一条鞭法实行的两个问题》等[76]。另外,这一时期部分明代财政史专著中也对明中期的赋役改革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如伍丹戈、唐文基、樊树志等学者。
90年代后研究视角发生折向。袁良义的《从明一条鞭法到清一条鞭法》一文,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明清两代的一条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述了明清一条鞭法的区别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77]。金钟博《从一条鞭法到地丁银》,针对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制度、一条鞭法的内容及实行、地丁银的内容与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地丁银不是一条鞭法的合并,而是一条鞭法的统一,是赋役制度的简便化,征收的基准完全改为土地亩数[78]。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以后,白银货币化这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不乏良作。万明发表了数篇水准很高的论著。《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一文依据427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指出,明代白银货币化发源于民间,成、弘以后得到官方认可。它启动了晚明社会的变迁,是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盛衰》一文分析了白银自上而下成为合法货币的过程,及由于政府没有控制白银发行和流通而对王朝发展的恶性影响。《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分析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和进程,并澄清了晚明赋役名实不符的问题。《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一文认为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和美洲,影响到当地的银矿开采,从而直接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构建,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一文指出在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明朝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赋役改革,折银是赋役改革的主线,无论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徭役以银代役,还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移,这些莫不是以银为趋向。同时这一过程也直接推动农民由纳粮当差到纳粮不当差,从而使得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由身份走向契约[79]。
除万明之外,还有李宪堂的《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赵秩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80]等文章,对当时引进中国的近代前期“东方中心论”提出不同的质疑意见,对于客观看待明代中国的世界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三、明代赋役制度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明代赋役制度史研究总体上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大致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整体研究充分,细节考察不足。梁方仲等老一辈学者确立的几个大的研究课题,比如鱼鳞册、粮长制、一条鞭法等等,诚然是明代赋役制度的总体性问题,后来学者理应不断拓深。但就现在的众多论著来看,这些宏观方面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在其他微观方面的用力略显薄弱。如明代中后期一些地区性赋役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法,未行粮长制地区的赋役情况、不同地域之间同一赋役制度执行的具体情况和差异等等问题,关注明显不够。弥补这方面短板,关键在于更多新民间文献的发现和利用,因此明代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仍然是学者们的主要致力方向。
其次,研究范围集中赋役制度本身,视野略显狭窄。纵观这方面的论著,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制度渊源——执行情况——演变及破坏过程”这样的模式来书写的,很少关注到制度变化与当时朝局政治、社会风气、人口及移民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这就使得研究稍显单一化之感。因此,融入明代不同时期和地域的社会面貌,提高赋役制度史论著的丰富性和动态感,这也是一个今后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缺乏理论提升与高度。考证辨析仍然是过往及当前研究的主要方法,这对了解和把握一项赋役制度的来龙去脉无疑是最具功效的。但一概作为研究的主要学路,不仅会产生思维惯性,而且不利于该方面研究方法的传承和延续,更不利于结合其他学科的成果实现联动发展。诸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引进到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中来,需要理论创新才能予以实现。
注释:
① 上世纪50—70年代大陆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中,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皆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密切相关。
② 方中:《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1期。
③ 赵其芳:《明代之赋役制度》,《中国经济》1935年第3卷第3期。
④ 畏人:《明开国前后赋率》,《益世报》1937年2月2日。
⑤ 梁方仲:《明代鱼鳞图册考》,《地政月刊》1933年第1卷第8期。
⑥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2—79页。
⑦ 唐文基:《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洪武元年》,《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⑧ 刘敏:《明代“鱼鳞图册”考源》,《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1期。
⑨ 栾成显:《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册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 栾成显:《洪武鱼鳞图册考实》,《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⑪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 (初探),《益世报》1935年5月28日;《明代粮长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4年第7卷第2期;《明代粮长制述要》,李光壁编:《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⑫ 洪沼:《明初的迁徙富户与粮长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⑬ 蒋兆成:《明末清初杭嘉湖的里役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⑭ 周绍泉:《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⑮ 汪庆元:《明代粮长制度在徽州的实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⑯ 谢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⑰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⑱ 左云鹏:《明代徭役制度散论》,《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⑲ 唐文基:《明初的杂役和均工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⑳ 李长弓:《试论明代驿传役由永充向轮充的转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试论明代驿传役编佥“唯粮是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4期。
㉑ 陈京:《明驿的组织管理及其特点》,《中国邮政》1987年第1期。
㉒ 吕景琳、张德信、滕新才:《论明代驿传之役》,《三峡学刊》1997年第3期。
㉓ 唐文基:《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赵毅:《铺户、商役与明代城市经济》,《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4期。
㉔ 秦佩洐:《明代赋役制度考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王毓铨:《户役田述略》,《明史研究》1991年第1辑;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㉕ 伍跃:《均工夫役浅析》,《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㉖ 伍丹戈:《明代徭役的优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张显清:《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㉗ 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㉘㉞ 清水泰次著、张锡纶译:《明代田土的估计》,《食货》 (半月刊) 1936年第3卷第10期。
㉙ 马小鹤、赵元信:《明代耕地面积析疑》,《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
㉚ 王其榘:《明初全国土田面积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㉛ 田培栋:《明代耕地面积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1982年第2辑。
㉜ 樊树志:《万历清丈述论——兼论明代耕地面积统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㉝ 戴博荣:《明代的田赋制度与垦荒政策》,《现代史学》1935年第2卷第3期。
㉟ 赖家度:《明代土地占有关系和赋税制度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组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伍丹戈:《论明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清田制札记》,《文汇报》1962年12月16日。
㊱ 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㊲ 王仲荦:《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和江南纺织业》,《文史哲》1951年第2期。
㊳ 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㊴ 林金树:《明代江南官田的由来、种类和科则》,《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关于明代江南官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明代江南民田的数量和科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㊵ 梁方仲:《明初夏税本色考》,《清华学刊》1933年第40卷第11、12期。
㊶ 清水泰次:《明初之夏税秋粮》,《史学杂志》1933年第29编第6期。
㊷ 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6年第3卷第1期。
㊸ 刘伟:《关于明代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北京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㊹ 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㊺ 梁方仲:《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第1卷第1期;《田赋输纳的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益世报》1936年1月21日。
㊻ 肖立军:《明代财政中的起运与存留》,《南开学报》1997年第2期。
㊼ 吴智和:《明代江南五府北差白粮》,《明史研究专刊》1978年第1期。
㊽ 鲍彦邦:《明代漕粮制度》,《平准学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㊾ 田培栋:《论明代的“永不起科”政策》,《晋阳学刊》1986年第6期。
㊿ 风良:《明代永不起科令实施时间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
[51] 周致元:《明代永免凤阳临淮二县徭赋考辨》,《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明代对凤阳府的灾蠲和灾折》,《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52] 冯尔康:《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
[53] 张志斌:《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松辽学刊》 (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54] 卞利:《明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55] 陈学文:《明代户帖制度的建立和户帖格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56] 栾成显:《明清户籍制度的演变及其所造文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集。
[57] 梁方仲:《明代的黄册》,《中央日报》1936年8月6日;《明代的黄册》,《岭南学报》1950年第2期。
[58]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
[59] 赵践:《记明代赋役档案——黄册的最后遭遇》,《文献》1986年第4期。
[60]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明代黄册制度起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明代黄册人口登载事项考略》,《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61] 栾成显:《明代人口统计与黄册制度的几个问题》,《明史研究论丛》2007年第7辑;《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1期。
[62] 衔微:《明代的里甲制度》,《历史教学》1963年第4期。
[63] 梁方仲:《论明代里甲法和均输法的关系》,《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
[64] 刘伟:《明代里甲制度初探》,《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65] 唐文基:《试论明代里甲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66] 王兴亚:《明代实施老人制度的利与弊》,《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67] 栾成显:《论明代甲首户》,《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
[68] 王裕明:《明代总甲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69] 丁慧倩:《里甲、清真寺与回回家族——以山西长治回回家族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第1期。
[70] 梁方仲:《一条鞭法的名称》,《中央日报》1936年4月23日;《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一条鞭法的争论》,《益世报》1936年9月13日;《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地方建设》1941年第2卷第1、2期。
[71] 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1期;《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岭南学报》1952年第1期。
[72] 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73] 王方中:《明代一条鞭法的产生及其作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74] 南炳文:《一条鞭法始于何时》,《南开学报》1981年第3期。
[75] 陈世昭:《明代一条鞭法问题研究》,《江汉论坛》1987年第7期。
[76] 曾唯一、沈庆生:《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柳义男:《关于一条鞭法实行的两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77] 袁良义:《从明一条鞭法到清一条鞭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93年第3期。
[78] [韩]金钟博:《从一条鞭法到地丁银》,《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
[79]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盛衰》,《明史研究论丛》2004年第6辑;《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2004年第2辑;《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
[80] 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赵秩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