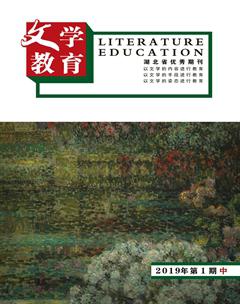试论李辉早期传记创作的特征
陈欣 张文一
内容摘要:李辉写作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作品,从他早期的传记文学创作中不难看出:他在写作初期就认识到传记文学“历史性”与“文学性”并非是不相容的,而是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他是一个书写历史的人,通过自己客观的历史感、注重搜集历史材料和运用虚构性叙事方式,他将手中的笔变成了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的命运在他的笔下融化为一体,凝固成厚重的历史。
关键词:李辉 历史真实 虚构性叙事
李辉在《监狱阴影下的人生》的自序中说道:“我说过我是拙劣的跳舞者,意思是说什么舞都跳得不伦不类,写的传也是同样。文学性与资料性如何结合好,即使在写这一本传时,依然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事,看来只要继续写,头会永远痛下去。”[1]可见,李辉当时面临着如何处理传记文学写作中“真实性”与“虚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其他传记家和批评家争论的焦点。
中国传统的传记观强调传记的历史属性,把“真实性”当作传记写作的唯一准则。随着西方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传记家和批评家们开始强调传记的“虚构性”。中国传记文学也受到其影响,从20世纪开始进行革新,进入新时期以后,虽然传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对于其文体特征,论者们并未取得共识。“有的以史学为参照系,因而强调传记文学的真实品格,甚而把它列为史学门类;有的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系,因而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品格,进而指出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非文学化倾向。强调真实品格的坚持传记文学必须严格恪守事实的真实,强调文学品格的则坚持传记文学应当允许虚构。”[2]
《监狱阴影下的人生》写于一九八七年,李辉没有执其一端,而是承认了两种截然对立观点各自的合理性,他既不满足于简单的历史材料的静态排列,也并未运用小说的技巧虚构人物情节。他在为刘尊棋作传的过程中,将“真实”与“虚构”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很恰当。我想,这与他具有客观的历史感,注重史料的挖掘,运用虚构性的叙述方式不无关系。
一.客观的历史感
传记文学写的是历史的人物或者是人物的历史,记叙的事件都发生在过去的时间和空间里。只有运用历史的眼光,将人物放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只有在时代背景的映照下,才能显示人物的经历、心理、思想及其发展变化。《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主要叙写了传主刘尊棋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四个事件:(一)青年时期因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虽在狱中处境艰难,但仍斗志昂扬,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战斗中,后因王卓然的帮助得以无条件出狱。可由于国民党的一纸假“退党启示”,他被狱中的同志们误认为是叛党出狱,被开除了党籍。这使得他的人生笼罩上了“叛徒之雾”。(二)出狱后的刘尊棋,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开除了党籍,他急切地与组织取得联系,并利用自己在新闻界的条件,巧妙地打破了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封锁,为党作了大量重要工作。皖南事变之后,被敌人注意到的刘尊棋需要尽快撤离前往新加坡,在获取出境证的过程中,他身不由己的赴了特务头子戴笠的宴请,致使他的人生腾起了“特务之雾”。(三)建国后,“叛徒”、“特务”的身份嫌疑令他难逃劫难,他先是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后又被囚禁于洞庭湖,生活苦不堪言。(四)进入新时期,刘尊棋在出狱后,先是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后经过他努力地申诉、中央进一步的调查和党内同志的作证,证实了他“叛徒”和“特务”的罪名都是历史误会,他终于得偿所愿,可以光明正大的生存了。
李辉通过对刘尊棋人生经历的选取、剪裁,勾勒出传主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八〇年间的生活图景,虽然他有一颗“再创造”的雄心,但他从未脱离历史实际,而是尽力地还原历史场景,为事件的发展营造历史的氛围,使人物的形象立体化。他写刘尊棋第一次被捕时,先插叙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围剿,沪商务印书馆彭家煌被捕的事件,烘托出当时恐怖、紧张的局势,刘尊棋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被诱捕入狱也就显得更为自然合理了。在介绍刘尊棋的妻子“郑绮红”时,李辉简略的叙写了与她相关的“女师大风潮”,以及她在“三·一八”惨案中幸免于难而后赴苏联留学的经历,寥寥几笔就让这个出场次数并不多的女政治活动家在读者心中留下了聪敏、进取、勇敢、不畏生死的形象。
二.史料的挖掘应用
胡适认为“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3],的确,传记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特征要求传记作家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存在,但历史的不可逆性注定了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历史的叙述是有限的。李辉很明白这一点,他并不追求完整的还原真相,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历史叙述,让人们能多了解历史。
《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一书中集合了大量的旧报纸信息、特讯、信件、报告等历史资料。李辉注重历史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又最能揭示历史的深刻与复杂,他正是通过这种收集历史材料,文献档案的方式,尽量客观的多角度的揭开人物历史的真相,展现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刘尊棋第一次被捕入狱后,作为狱中青年的代表,写信向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呼吁援救,却引起了一场政坛风波,胡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也因此发生分歧乃至决裂。胡适等人都是现代文坛、政坛上有威望的名人,他们究竟孰是孰非,李辉并没有情绪化的下判断,而是冷静地将双方的通信编排进文中,既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历史真实事件发生的原因与经过,也让我们看到了蔡元培等人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迫状态时,一心搭救抗日青年的“热忱”与胡适为人处世的严谨和思虑周全。
三.虚构性的叙事方式
李辉的传记文学创作在重要的人与事件上是严格遵循史实的,而一些次要的人物和事件,是進行过一定范围内的虚构性艺术加工的。《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中的虚构性叙事方式主要体现在:
(一)自然环境的描摹。“环境包含了三大要素:自然环境、社会背景、物质产品。”[4]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历史叙述的重点,环境描写只是一种交代社会背景的方式,而李辉擅于构造充满浪漫气息且与人物命运相关的场景。他时常以隐含作者的身份出现,通过传主的视角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观照,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但是景与情,却是他根据与传主的交谈和搜集的资料作出的设定。也许这景与情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他据实联想创造的。李辉在《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中多次描写景山的自然风景,刘尊棋与郑绮红曾经在景山的松林间谈天说地,夏日的景山成为了刘尊棋内心“似火激情”的映照,郑绮红被捕后,刘尊棋登上景山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景山的树木、草地都是他情感变化的见证者。
(二)心理虚构。传统的传记文学写作为了保证传记的真实客观,主要描写人物的外在行为,几乎不涉及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使得传主的个性被忽视。随着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传记家在事实的基础上开始将人物的心理穿插在叙事中,从心理的角度再现特定环境下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使塑造的人物形象闪现着人性的光彩。
李辉在作品中以叙述者的身份介入,为刘尊棋内心的独白提供向导。在刘尊棋镣铐加身,被押往北京的途中,由于空间狭小、压力过大,他晕倒了,被救醒之后,“他真想哭了。多少天以来他何曾听到过如此温柔的问候呵!他没有哭,眼泪流入心底,涌起阵阵温暖。他转而一想,如果她和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关心吗?”[5]李辉运用间接的心理虚构在刘尊棋和读者之间搭建一座虚构和现实的桥梁,让读者体会到传主在动荡时代下内心的惶惶不安。
(三)对话虚构。人物的对话原先主要运用于小说创作,它既能反映时代环境氛围、显示人物性格特征,又能推动情节发展。后来在现代传记转型的大背景下,传记家也开始对人物对话进行选择和合理的虚构。这种虚构对话以不损害事实真相为前提,建构起一个可供自由表达的虚构空间,使读者不仅能从平铺直叙的故事中获取信息,还能通过人物间的对话更深入地感受传主的个性和人物的性格魅力。刘尊棋当时受党组织的派遣,需前往新加坡,但办不到出境证,这时他遇到了朱啸谷,并且朱啸谷主动提出要为他解决这个难题。两天后他们二人有这样一段对话:“‘你是一位记者,找别人也不行,只有找戴笠。他同意你出去,要替你办出境证。‘我不要他帮忙。刘尊棋执意说。‘不行呀,他已经知道了你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决定了的事,是绝不能更改的。”透过这短短几句,我们了解到当时情况的特殊:作为记者的刘尊棋,出境是很困难的;对于需要求助于戴笠这件事,刘尊棋内心是极其抵触的;戴笠为人十分专制霸道,刘尊棋注定无法拒绝。这就使我们更能理解他当时的无奈,体会他后来被冠上“特务”的称号时内心的委屈。
李辉在创作《监狱阴影下的人生》时,虽然能以自己的方式将“文学”与“历史”权衡得当,但还是在创作初期,艺术手法的运用能力稍有欠缺,技法还不那么成熟,叙述语言也不够精炼,在描写环境时,他喜欢选取一些能与人物命运联系的意象,过于刻意营造,不够自然。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持续着传记文学的写作,“相对于慷慨激昂纵横天下的宏大评判,李辉更倾心于做一位不露声色的历史叙述者。”[6]他的传记文学写作得到了文坛的广泛认可,不少专家学者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李辉.监狱阴影下的人生·自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3.
[2]张文博.写真求实 史文并重——试论传记文学的文体特征[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02).
[3]胡适.胡适传记作品全辑·第四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03.
[4]胡亞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9.
[5]李辉.监狱阴影下的人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24、203.
[6]罗屿.李辉:不露声色的历史叙述者[J].小康,2016(05):80-85.
2018校级创新计划立项,项目号2018YXJ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