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卡佛传吗
杜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在“作者已死”的时代,我们还需要作家的传记吗?这个问题早已不新鲜但依旧时髦,或许因为它带有所谓“后现代”性感的微醺和愤世嫉俗。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阅读传记,尤其是作家的传记,除了窥私癖之外,我们还能为此找到什么理由呢?

《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 美]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著 戴大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這个大胆的宣言,是希望给文本以及广义的符号系统以更大的空间和独立性,他希望把阅读和写作的活动变成永远无法穷尽的能指的游戏:没有了作者这一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巨大阴影,所有那些不符合“原意”的见解统统可以破土而出呼吸自由的空气。
罗兰·巴特的宣言尽管诱人,但在学理上更为完备地阐释文本的实质的功劳还要记在保罗·利科头上。利科认为文本同时具备内外部两个面向,内部是指语言符号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通过变形、复制、拼接、反讽、移置等玩法令它无限制地现身,这也是罗兰·巴特想要强调的;而未受巴特重视的外部面向则是指文本中的语言符号总是在指涉文本之外的世界。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文本由内外部共同构成的理解,便不难发现所谓“作者”正是环绕着文本的那个世界片段中即使不是最清晰也是最为高大的身影。
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勉强承认作家的传记即使在当今时代仍然是有意义的—它是文本与世界连结的最直接的纽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雷蒙德·卡佛本人的自传、采访甚至他的妻子玛丽安都有回忆录出版的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翻开这本《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下文简称《卡佛传》)呢?
这本传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卡佛一生的全方位覆盖,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比如卡佛一家每一笔欠款的明细:电话费八十美元、煤气公司七百零六美元等等,更别提在卡佛那不长不短的一生中大大小小的经历了。这种写法的缺点是易被批评为对传主的人格缺乏穿透力,无法将其气质和一生经历整合为容易辨识且富有美感的形象。国内读者熟知的很多优秀的传记作品,如《巨人三传》《维特根斯坦传》等都是能将传主的形象塑造得丰满动人的作品。
但《卡佛传》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塑造形象的工作已经被传主本人提前完成,甚至是有些过度完成了—与电视时代同时崛起的卡佛(及其妻子)简直有太多自我叙述的机会了。而梳理素材、描绘形象、制造合理的戏剧性,这些工作对小说作者来说自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何况人在理解自己的时候总是倾向于构造一个完整的自我(即使内部包含着结构性的冲突),而非单纯地将大量行为和言论叠加。如此,即使传记作者再别出心裁,其编织出的形象也不会比卡佛或卡佛夫人的版本更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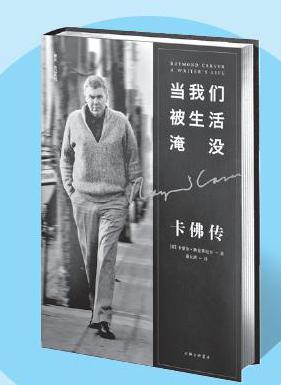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Carol Sklenicka)
然而传记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要将传主们转化为一个个文学形象,它有通过特定人物视角构建微观历史的功能,《卡佛传》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足够出色的历史性使它得以成为一本卡佛研究的字典,字典的要求当然是收录条目齐全、内容准确,关于卡佛的几乎每一桩大事小情都可以在其内部找到定位。比如,对雷蒙德·卡佛而言,父亲的酗酒对他和整个家庭的气氛都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但传记作者采访了他的兄弟詹姆斯,另一个卡佛则表示父亲确实有酗酒的问题,但整个家庭还是保持着一种和睦幸福的状态。比较之下,我们或许可以模糊地重构一个老卡佛酗酒的程度:它足以令一个敏感的少年不安但又不致于彻底摧毁一个孩子的童年。这种来自不同当事人的不同叙述视角之间的比对,广泛地存在于书中,比如卡佛妻子玛丽安和她富有魅力的上司之间的亲密程度曾令卡佛吃味,但在玛丽安的回忆录里则坚称这段同事情谊没有对她的婚姻造成影响。传记作者也直接地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玛丽安有实质性的行为,于是我们再拿起玛丽安的回忆录时会对它的可信度又多了一分理解。
《卡佛传》提供了关于卡佛一生最翔实可信的记录,其价值在于成为一把量度其他文本的标尺。就像电影《天意》中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让作家梦中的那个弗洛伊德剧场落下帷幕,戏剧演员统统换上了真实的面孔,在温暖的阳光下远离了创作者的暴力。但标尺也不反对创作和叙述,它总是和被量度对象一道存在的—没有午后,梦魇中的一切都只是想象力的自我欣赏和为赋新词强说愁;没有午夜惊醒,在草地上团聚起的只不过是又一个无聊的中产阶级家庭,其中有再俗套不过的紧张的父子关系。
传记作者也并未完全放弃对传主的人格、心理的揣摩与重构,只是在做这些尝试时相当审慎和警惕,每一处属于她个人的见解,都一定会附上“好像”“仿佛”之类的字眼来提醒读者。比如在讲述卡佛的酗酒状况在同样有酗酒问题的父亲去世后愈加严重,作者推测卡佛是在“寻找一种方式与父亲谈心”。虽然有卡佛的一位作家朋友的见解作为佐证,但作者还是放弃了在父子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下断言。
这种谦虚地避免为传主盖棺定论的态度愈来愈成为传记作品的共识,如鲍勃·迪伦的传记电影《我不在那儿》就用了相异或者说恰好相反的手法来展现同样的态度。《卡佛传》选择坚持素材的真实性而放弃给出一个完整的审美对象;《我不在那儿》的选择,是放弃完全还原自传主的亲身经历,而在审美一端用力:它将鲍勃·迪伦身份中的不同侧面进行拼接,而每个侧面以不同演员、不同影像风格呈现。无论哪种手法,它们都放弃了对传主的同一性的坚持。
丧失了同一性的传主,那个创作了无数精彩作品的作者,并不能以一个完整的真实生命的身份出现在自己的传记里。这个事实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作者已死”的训诫:作者不仅在自己的作品里已经死了,在记叙他生平的传记里也不曾活转,尽管他似乎还在那里不断地现身。因为“作者已死”从不意味着作者的彻底消失,他/她的幽灵仍然游荡在文本之中。我们当然可以携带着一部作品走过千山万水并宣称作者的亡魂始终陪伴着自己,毕竟他/她已不能出言反驳。但每个文本都有其信息上的局限,任何单一文本都不足以支撑无限的阅读和再利用,旅途终有一天会结束,作者也终有一天会入土为安。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种符号游戏的无限性,但这种无限性不存在于任何一次真实的阅读体验中,而超度作者的亡魂—平息他的不安、躁动和表达欲是真实的阅读中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说作品中保存着作者死后灵性的一面,出现在传记里的就是他肉身、质料的一面。一本好的传记要足够晶莹剔透,就像一具盛放着作者的尸体的水晶棺,纤毫毕现。厚重冰冷的晶石底下,尸体周身的血液仿佛依然温热。它沉默、驯服,不再生成危险的可能性。我可以用放大镜对准它每一寸肌肤,惊喜于发现一道不易察觉的伤疤—当我拥有“尸体”的时候我就拥有了它的一切。
现在终于可以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了:谁会需要这本《卡佛传》呢?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美] 雷蒙德·卡佛著 小二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一、卡佛小说的爱好者、模仿借鉴卡佛风格的写作者,卡佛及彼时美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中文世界中的研究者等等,总之是将理解卡佛视为自我认同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那些人,绝不会愿意错过这样一本资料最为翔实、叙述最为审慎的卡佛传记。他们是这本书得以问世的最大推动力,也将是从中获益最丰的群体。
二、那些对卡佛的作品、性情和经历等怀有知识性的兴趣,将“卡佛”视为自己头脑中的百科全书的一个词条,缺少它似有些不美,同时对“客观性”有很深的执念,贪大求全,希望能在一本书中全面、详细甚至完美地了解其人其事的读者,也会将这本传记视为他们的最佳选择,它能提供同类作品中最多的可以转化为心灵装饰物和谈资的材料。
三、这类读者则稍显特殊,他们非卡佛的忠实读者,他们可以期待的是由该书带出的一整个文本世界的复杂性。这个世界由包括小说、诗歌和自传在内的卡佛全部作品、对卡佛的采访、卡佛妻子的回忆录等组成。《卡佛传》则是一次对过往种种叙述卡佛人生经历的文本的锚定,那些曾经出现的浮光掠影将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汇聚。这不仅对卡佛研究者有致命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一个古老的问题:作者是如何进行自我书写的?卡佛在自我讲述中暴露了什么又隐瞒了什么?他那坚强而迷人的妻子又如何呢?这当然不是一种八卦小报式的跨过罗生门的渴望—因能够指出相当优秀的人物,比如一位伟大作家,身上的某种虚伪而沾沾自喜;如果说对作家或广义的创作者的传记有所期待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在于,它可能揭示一些关于创作的秘密,那么这些秘密一定会在创作者的自我叙述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如前文所说,该书作为一把标尺,在它冷峻而温情的量度下,卡佛的自我叙述的才华与力量才能够清晰地被看到,那种善于提炼生活、塑造形象、讲出好故事的能力才真正获得被赞赏的机会。
对于那些部分醉心于这种复杂性而愿意一再把玩它的读者来说,本书正是让这复杂性不致因叙述者繁多而沦为一桩无头公案,倒是可以在细致的阅读、比较中慢慢形成“原来故事的最初素材是这样一组事实”“原来故事是可以这样讲的”之类的理解。
四、对于那些既不热衷卡佛也对诸如“叙事的魔力”“文本世界的复杂性”这类蛊惑人心的大词兴致缺缺的读者,这本书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因为它足够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足够无聊。它没有过分戏剧性的波折起伏,不会消耗太多的情绪和能量,你可以让它静静地躺在枕边与你共享睡前的一点时光,慢慢被一个陌生人的生活和困意淹没,然后在另一个夜晚降临的时刻重复这种枯燥的乐趣—如果你閱读的速度不是很快的话,且有一阵子享受呢。当我们被生活淹没?这好像也无所谓了,毕竟不用再考虑上不上得了岸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