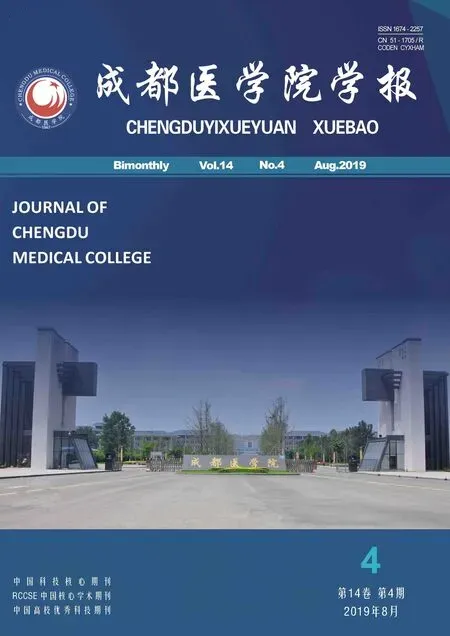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伦理的理念与原则*
江先文,唐宏川,贾伊伶
成都医学院(成都 610500)
“慢性病”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是特指某种疾病,而是对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且病情迁延不愈,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病因复杂且有些尚未完全被确认的疾病的概括性总称[1],主要包括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疾病。慢性病会造成患者内脏器官受损,严重时会导致伤残甚至威胁生命。患者的劳动能力不仅会降低,而且生活质量也会受到极大影响。防治慢性病的医疗费用十分昂贵,大大增加了家庭、社会的经济负担。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与不良的生活方式(如饮食无规律、吸烟、酗酒、运动缺乏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个人的遗传和生物及家庭,精神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慢性病已成为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类疾病,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形成重大威胁。
1 “大卫生大健康观”: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伦理的理念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方式、食品安全状况、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对健康的影响逐步显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特别是慢性病发病、患病和死亡人数明显增多,社会医疗资源和医疗费用明显增长,不少人也因病致贫。《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2]指出:“近10年来,我国主要的慢性病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以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病率为例,2012年我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为533/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86.6%,18岁及以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9.7%、高血压患病率为25.2%,而在10年前,这2个数字分别是2.6%和18.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安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要论述[3],他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大意义,有利于人们形成关注健康和关爱生命的意识,为卫生健康领域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大卫生大健康观”用更加多维的视角,整体审视健康,不仅为拓展工作领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同时也为构建健康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卫生工作者习惯以疾病为导向开展工作,强调生物学因素(如细菌、病毒)在各类疾病发生、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1997年,美国罗彻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与内科学教授恩格尔(Engel)在《科学》上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强调影响健康的因素是多维的,要以患者为中心。但在实践中,卫生工作者仍然主要关注患者的疾病,仍以疾病为中心。事实上,影响健康的因素是广泛多维的、复杂多变的,必须以生态学观点对健康进行诠释。健康领域的生态学观点有3个显著特征:“第一,多维性,无论是个体健康还是群体健康,它们均可能受到人口(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政治经济(医疗条件)因素以及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第二,交互性,以上种种因素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群体的健康,而且这些因素本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并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从而对个体健康与群体健康产生影响;第三,系统性,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显然会受到生态环境对健康的影响。”[4]这种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有时是对个体的影响,有时是对群体的影响;有的影响可能是单一的、单向的,但更多的是多重的、双向的。因此,有必要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大卫生大健康。对健康的关注不应再局限于疾病本身,而是包括躯体、心理、心灵、行为、社会、智力、道德、环境等多因素在内的“大健康”,进一步扩展健康价值的谱系,从全要素扩展到全方位(健康、亚健康、疾病、衰老、失能、残障,个体健康和群体健康,体育健身和德育修身,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危险因素的控制),再到全流程(涵盖人类生、老、病、死的全周期)[5]。对卫生的认识,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将其看做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进行辩证的把握,其不仅包括个体卫生、群体卫生(如妇幼卫生),还应包括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劳动卫生和食品卫生等在内的“大卫生”。
当前,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控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个体行为进行干预,如告知吸烟有害健康、不要吃过油过咸食品、多运动等;第二,慢性病的治疗问题,如何加大投资、扩大病房、购置诊疗设备等;第三,某些地方也在积极开展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或者展开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工作,但总体上发展极不平衡。以上这些措施,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控制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方向性、整体性和力度上的把握上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表面上看,慢性病是个体行为性疾病,但实质上却是“社会病”。社会因素为慢性病发生的“上游因素”或“原因背后的原因”,而预防慢性病最有效的方法是针对上游因素开展人群预防工作。
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思想,完善慢性病危险因素的防控体系,履行健康职责。从政府层面讲,要将健康融入全部政策,制定和改进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明确和落实各行政部门与各级地方政府应履行的健康责任,形成分工、合作的协同机制,预防和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的发生和发展;从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层面讲,应形成全民参与的健康行动格局。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不能单纯靠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及个人也须积极承担责任。如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应在全民健康管理上,发挥好医防结合的作用。新闻媒介必须加大健康宣传和健康教育的力度,不得刻意扭曲和夸大宣传不健康的食品、烟酒类以及其他增加人们静态生活方式的产品的作用,误导大众;商品生产者应坚持绿色清洁生产,改善作业环境,控制尘毒危害等;从个人层面讲,必须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开展自我健康管理。
2 预防为主: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伦理的基本原则
慢性病早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题。WHO发布的《2014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指出,慢性病仍是全球的主要死亡原因。上世纪中叶以来,各国政府以及相关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视慢性病的防控工作,不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与实践,而且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慢性病控制的基本原则,即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美国Framingham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FHS)采用“流行病学方法”,揭示了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多重危险因素,提出了综合管理心血管疾病、而非单一控制“最危险的因素”的防控指导方针[6]。类似的研究还有始于1968年并持续15年之久的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巴斯尔顿健康研究(busselton health study)、在英国进行的Caerphilly心脏病研究以及中国康奈尔牛津项目(china-cornell-oxford project)。 日本曾作为胃癌高发的亚洲国家,积极调整防治重点,采用调整饮食结构、改变生活方式、转变心态行为并辅之以早期筛查等预防手段与策略,胃癌发病率、死亡率持续降低[7]。以上研究与实践案例表明,预防对控制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遏制慢性病的有效手段,且有效的预防服务可以防止或推迟慢性病发生。因此,各国政府积极从法律和政策上为防控慢性病及其风险因素提供制度保障。美国1971年通过的“健康维护组织法”,明确将预防服务纳入医疗保险范围,2010年通过的“患者保护和可负担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PPACA),则明确要求为弱势群体(如贫困的参保人、老年人)提供减费、免费的预防服务;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立法上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规范的国家,其法定医疗保险范围非常广泛,除医疗服务外,将癌症筛查、其它慢性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早期发现以及健康咨询等纳入了法定医疗保险的范畴[8]。英国实行两级保健制度,一级保健又称为基础保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 75%的资金用于基础保健,家庭医生、社区诊所是基础保健的主体,其提供的一级预防与二级预防,对慢性病的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做法和我国卫生工作长期实践所形成的经验基础上,《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都先后明确提出,慢性病防治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是遵循慢性病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坚持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思想,把可能导致发病的机理或因素尽可能消除在发病之前,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预防为主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环节,而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是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抓手。由于慢性病的病理特点,慢性病的控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必须调整慢性病的防治策略,摒弃“治疗中心”观点,坚持预防为主,做好慢性病的三级预防工作,特别是一级预防工作(即病因预防工作)。事实上,如只采取病例筛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等临床前预防手段,虽然有助于促进机体功能恢复,但并不能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如只采取医疗干预等临床期预防手段,虽然有助于防止疾病的进一步恶化或者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但同样无助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因此,要认真抓好抓实一级预防的各项工作,通过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行个性化健康干预、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全流程健康管理、建设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等有组织的活动来降低高危人群发病几率,尽可能减少可预防的慢性病的发病、残疾和死亡,预防控制慢性病的发生流行,促进患者健康、延长寿命、提高个体生命质量。
3 健康公平: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伦理的核心要义
健康公平是指所有社会成员不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教育文化水平、职业、地域以及年龄、性别等差异,均等地享有基本医疗资源,并达到基本相同的健康水平[9]。实现健康公平,是有效推动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的客观需要,是保障弱势群体如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健康权利的需要,是推进健康中国制度伦理构建的需要,更是人们共享健康资源和共同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人人健康应该是健康的基本权利和国民待遇,国家和政府对13亿国民的健康负有重大的护佑责任。优良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制度必须有伦理关怀,以促进可持续的基本健康公平为重要目标。健康公平在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领域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健康的环境公平、福利公平和教育公平。
环境因素是导致慢性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公共因素和宏观因素,环境对于健康的影响不可忽视。正如参与了耗资870万欧元的“接触组”项目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毒理学家马丁·史密斯[10]所说:“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基因的因素与疾病的关系,而与环境因素相比,基因因素显得微不足道。”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巨大伤害是一种健康的环境不公平,不计代价、不问污染的工业化道路使国民付出了昂贵的健康代价。如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出现癌症村,而癌症村的形成主要受环境污染的影响,例如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等,尤其是水污染。现有的研究[11]结果显示,癌症村主要集中分布于河流及部分湖泊的缓冲区范围内。黑色GDP扭曲了社会发展目标,任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都是对健康的不公平。绿色GDP才能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才能从源头上控制、减少导致慢性病产生、发展的危险因素。习近平总书记[12]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因此,各级政府、各级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医疗服务机构、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自觉承担起营造可持续的生命支撑体系的伦理责任,履行好构建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的道德义务,这是促进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也是环境伦理构建的内在要求。
福利公平一般意义上包括获得健康服务、健康支出和健康资源占有三个方面。从显性角度讲,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是以城市、农村为界进行制度设计的,而城市又分为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和城镇职工在获得健康服务和占有健康资源方面有明显差异;同时,我国在卫生资源分配中还存在非正式的隐性优先规则,从而导致卫生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如果多数的、优质的公共卫生资源只是富集于小众人口,显然不符合健康的福利公平法则。健康福利公平的理想状态是最大多数人口能最大限度地平等共享基本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资源,无论穷达贵贱,都能依凭健康的国民待遇公平地享受健康的国家福利、社会福利和政府福利。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改变现有资源分布在地域间、阶层间、城乡间存在的失衡状态。首先,要加快落后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为实现健康福利公平奠定基础。其次,要把健康公平纳入所有政策,特别要关注农村、基层等重点区域,关注农民、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和就业不稳定的人员等重点人群,积极推动慢性病防治服务均等化,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机会接受基本健康服务并达到相同水平。另外,要增加健康服务的透明度,逐步减少隐性因素对健康福利公平的制约和影响,维护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促进社会公平。
健康教育是健康获得的重要路径,但目前的中国欠缺优质的、大众化的、公平性的健康教育,具体表现为:健康教育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缺乏科学性强、实用性高的慢性病防治知识和信息指南;作为肩负健康教育主体责任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农村的相关机构,并未履行好主体职责,将健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缺乏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健康教育活动组织者、实施者和管理者,服务形式不完整;没有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开展针对性强的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教育;缺乏全面、客观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有关控烟、营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主题报道居多,分别占总数的29.8%、 23.3%和21.6%,但有关口腔卫生、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卫生等领域的宣传偏少,这些方面还需要专家与媒体进一步合作[13]。
健康教育的不公平使得多数人处于健康无知的弱势之中。当前,必须加快健康教育理论研究,编撰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慢性病防治指南;增强各级各类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医疗机构及其医生的主动性,并与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新闻媒体紧密配合,协同开展健康科学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民众树立正确健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