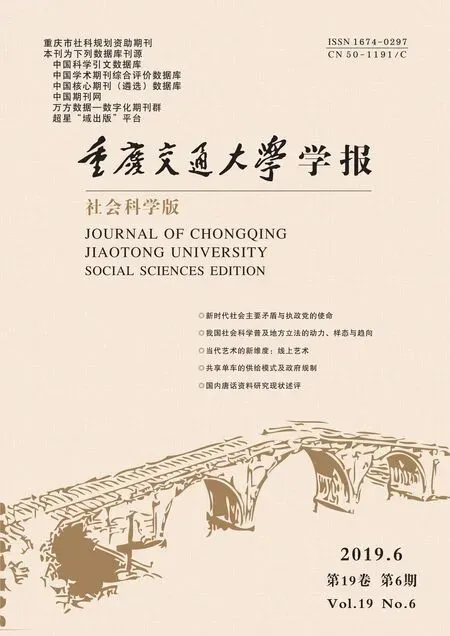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哲学思想
任江辉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言
战后初期日本社会陷入混乱局面,各种文学思潮不断涌现。战后派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思潮、民主主义文学思潮、无赖派文学思潮等不同思想潮流交相辉映,构成了战后初期日本文学思潮的体系。其中,无赖派文学思潮是“日本战败的产物,也是战后日本最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1]。该文学思潮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新奇的叙事艺术、超凡脱俗的文学理念,将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并引起了当时日本民众的共鸣。而这一文学思潮的重要旗手坂口安吾更是以著名文论《堕落论》的“堕落论调”,提倡“以堕落求生存”的口号,为战后徘徊在物质匮乏、精神荒芜的日本民众带来一阵新风,强有力地促进了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转型和发展。坂口安吾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大胆新颖的“堕落论调”,主要在于拥有独特的哲学思想内涵。这些哲学思想不仅表现在个人生活方式上,更践行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二、坂口安吾哲学思想的体现
作为无赖派文学的理论奠基者,坂口安吾哲学思想堪称战后初期日本作家群中的典范。坂口安吾的哲学思想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上,更体现在文学作品里。从其文学作品的类型观之,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小说和随笔三个方面。其一,文学评论。如《堕落论》《续堕落论》《颓废文学论》《戏作者文学论》《教祖的文学》《推理小说论》《文学的原形》等,其中《堕落论》最为出名。在《堕落论》中,坂口安吾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调:第一,强烈地抨击了日本传统的天皇制和武士道,与日本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相抵触。这一论调颠覆了长期以来日本传统的思想体系和精神信仰,引起了日本文坛的轰动。第二,指出为了生存,必须彻底地堕落。只有彻底的堕落才能够得到自我的拯救。在经济衰败和信仰崩溃的日本战后初期,只有通过堕落和颓废的方式,才能够求得人性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这些观点看似十分荒谬,但是以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历史语境而言,反而让当时的日本民众感觉合乎情理,引起了民众的共鸣。这些论调构成了坂口安吾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因此,坂口安吾的《堕落论》被盛赞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的宣言书、解脱精神桎梏的钥匙、治疗创伤的良药”[2]78。其二,小说。如《真珠》《外套和蓝天》《石头的思想》《痴女》《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为青面鬼洗兜裆布的女人》《金钱无情》《行云流水》《不连续杀人事件》《道镜》《飞鸟时代的幻影》等,其中《痴女》是其文学评论名篇《堕落论》哲学思想的践行之作。在《痴女》中,通过主人公伊泽和白痴女之间堕落的情爱叙事,将在生存极限状态下人性的本能暴露出来,将战争期间日本民众茫然、颓废、虚无、堕落的心态阐释得栩栩如生。“在巧妙地描绘人在极度孤独中蜕去精神外壳后,向原质的肉体回归的求生姿态,并展现出作者勇于向一切既有价值和观念挑战的叛逆性和立足于生存的强烈现实感。”[3]小说《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中,坂口安吾将日本传统的文化符号“樱花”描绘成阴森恐怖的象征,以隐喻叙事的艺术手法,通过山贼和美丽女人爱恨情仇的阐释,解析了“山贼是面临抉择的日本国民的象征,美丽女人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日传统道德、传统价值观的象征”[4],并以此表达对日本传统的价值体现、道德理念的批判。其三,随笔。如《日本文化之我见》《青春论》《恶妻论》《恋爱论》《利己主义小论》《关于欲望》《大阪的反叛》《不良少年与救世主》《关于闹剧》《关于男女交际》等。坂口安吾的随笔大多针对日本的社会、生活、文化、道德等层面来评论,批评指向明确,批评话语犀利,深得日本民众的好评。其中,1942年发表的《日本文化之我见》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最为深刻。文中从“日本式”“低俗”“家”“美”四个主题出发,深刻分析了所谓“日本式”的传统文化,针对日本的形式主义“美”,明确指出“仅有亮丽的外表是无法成为至善至美的东西,一切都归根于本质。为了美丽而美丽总会显得矫揉造作,终归无法成为真实。那是空洞之物。空洞之物决不能以其所谓真实的空洞打动人心,归根结底只能成为可有可无之物”[5]。文章完全否定了日本传统意义上的空洞美和形式美,坚持以“堕落的方式”来秉承实用主义美,以践行生存的需要和人性的回归。
无论从坂口安吾犀利的文学评论,还是从其巧妙构思的小说叙事,或是从其批评话语犀利的随笔阐释,均渗透着独有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内涵不仅建构了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体系,而且构成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坂口安吾哲学思想的内涵
坂口安吾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其语言犀利、风格特异,特别是其“颓废”叙事艺术颇具个性特征。其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文坛颇受文学评论家的喜爱,而且哲学思想也非常符合当时日本民众的精神意识。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层面窥之,“不管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从情节内容上的设计,均体现了坂口安吾堕落颓废的文学观”[6]。其文学作品的创作题材大多是涉及穷鬼、酒鬼、妓女、流浪汉、吸毒者、乱性者等“颓废”叙事人物形象,在叙事修辞手法上主要采用反对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文体简洁明快,富有个性。从文论思想的层面观之,坂口安吾不但秉承“颓废”意识的论调,而且大胆地树立了“无赖派文学思想”的鲜明理念。特别是在《堕落论》《日本文化私观》《堕落的文学论》《文学的故乡》等文学作品中,坂口安吾对无赖派文学思想内涵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和颇具个性的见解。这些作品中的言论对无赖派文学的确立起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为无赖派文学思潮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精确地体现了坂口安吾“颓废”叙事艺术的哲学思想。
(一)“孤独”哲学
在《文学的故乡》中,坂口安吾以举例论证的方式来探求文学的故乡,即文学本源究竟在哪里。坂口安吾用三个例证来剖析文学的根源,首先论述了法国作家查尔斯·佩罗《小红帽》中,小姑娘“小红帽”被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吃掉的故事;其次讲述了日本“狂言”片段中大名(日本诸侯)到寺庙朝拜,见到长得像自己爱妻的屋脊鬼面瓦,勾起思妻心切、痛苦流露的场面;最后描述了芥川龙之介死后留下的类似手记的遗稿中,提及农民作家杀子事件。该农民作家因贫困,为了不让大人小孩都受累,而将自己孩子杀死的事件中,坂口安吾从芥川龙之介的震惊中感受到芥川龙之介被当时社会所抛弃的虚无感和无奈。坂口安吾认为这三个故事情节都渗透着耐人寻味的孤独性,不具有道德性,仿佛让人产生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的虚无感和孤独感。这就是文学的本源,即文学的故乡。因此,他认为没有道德性和被社会所抛弃的虚无感与孤独感并不是否定文学的态度,相反,文学的建设性、道德性、社会性等都应该建立在这种故乡的情怀之上。除上述三个例证外,坂口安吾还论述了《伊势物语》中苦恋女子的男人历尽千辛万苦,求爱成功后,女子被厉鬼刺死瞬间消失的凄惨和孤独。比较和分析这一故事与上述三个例证,坂口安吾意识到生存的孤独,即文学的故乡是悲惨的、无法拯救的。跟毫无道德性自身就是一种道德性一样,在如此昏暗孤寂中的无以拯救实际上就是一种拯救,这是文学的故乡和根源。同时他指出,并非没有道德性和被社会所抛弃的虚无感与孤独感的故事才叫文学,也无法高度评价该类故事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故乡意识,没有故乡的自觉,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文学的社会性和道德性没有建立在这个故乡之上,是绝对不会被信任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7]。可见,坂口安吾认识到“颓废”叙事艺术的故乡和本源在于没有道德性,其哲学内涵在于生活的孤独感、被社会所抛弃的虚无感和堕落感。因此,“孤独”哲学思想一直镌刻在坂口安吾的文学文本中,成为其文学作品的一个基调。
(二)“反叛”哲学
坂口安吾“颓废”叙事艺术中,体现其“反叛”哲学思想内涵的理论论述在《日本文化之我见》中表现得十分透彻入里。文中他先后对日本的传统、恶俗、家、美的四个不同视角进行论述和剖析,核心内容是反叛当时日本的传统、权威,反对拘泥于形式的日本传统美,认为真正的美只存在于有内容实质的事物中。他在该文中大胆地指出:传统的美太过于形式主义,真实便利的生活比起日本传统的美更为重要和实惠。传统的寺庙和佛像即使被全部毁掉,也不会给一般民众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是如果电车停运,一般民众的生活就会变得不方便。因此,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日本传统的寺庙和佛像,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必需品。内容比形式更为重要,比起过时、迂腐的传统,现实的生存更为重要,实实在在的自由更是现今大家所期望的。可见,坂口安吾对日本传统价值观的剖析是“发自于对现实的反抗,采用逆其道而行之的做法,通过堕落摆脱旧传统、旧道德的束缚,恢复人自在的本性,发现人的真实,依靠堕落而从旧秩序中得以解脱”[8],深入批判日本传统的形式美和空洞美,显示了深刻的“反叛意识”。此外,在文学评论中,坂口安吾的“反叛”哲学思想直接鲜明,反叛意识强烈。在小说中,其“反叛”哲学思想蕴含在字里行间,提升了文学叙事的立意。在随笔中,其“反叛”哲学思想随性耿直,颇具说服力。显然,坂口安吾的“反叛”哲学思想内涵也构成了其“颓废”叙事艺术的主要内核。
(三)“堕落”哲学
“堕落”哲学思想内涵是坂口安吾“颓废”叙事艺术的灵魂。在《堕落的文学论》中,坂口安吾鲜明地提出文学应该具有颓废堕落意识,从该文的篇名就一针见血地提及“堕落”的观点,立论明确,不同凡响。文中,坂口安吾一改《文学的故乡》中提及的著名文学作品的例证做法,直接列举日本著名作家如平野谦、岛崎藤村、横光利一、夏目簌石等的文学思想论,毫不忌讳地指出堕落并不是文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作为人必然的本性和生活方式,为了不自欺欺人式地活着。
从哲学思想内涵的层面而言,《堕落论》是最能反映坂口安吾“颓废”叙事艺术的纲领性文章,“它是战后日本无赖派文学的理论性檄文,是打开精神桎梏的钥匙,是治疗创伤的良药,在战后日本人的思想解放历程中发挥过振聋发聩的作用”[2]78。首先,坂口安吾直接否定武士道,认为武士道是人性和本能的禁止准则,是反人类和反人性的东西。其次,他直截了当地批评日本天皇制,将天皇制视为日本独有的政治作品,是日本政治家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手段,是谋求权术之争的必然产物。而批判日本武士道和天皇制等传统价值观的根据在于人性,也就是作为人自然的求生天性。坂口安吾利用大量的例证来论证,如二战结束后六七十岁的将军为了求生不愿意按照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杀,而宁愿被法庭审判以求得免死,苟活于世;室町时代武士松永弹正被织田信长追得无路可走后,为了苟活仍然按照每日习惯对自己进行延命针灸治疗后才自杀身亡。为了人的求生天性,武士道和天皇制均可以抛之脑后。必须通过堕落的方式才能批判日本传统的价值观,使之崩溃,也只有通过这样理性的崩溃和堕落,才能让人性复归。这是由于人是迷惘、可怜的,是脆弱和愚昧的,才制定出所谓的武士道和天皇制。为了制定有人性的武士道和天皇制,人必须正确地有理性地堕落,才能发现自身的天性,才能得以拯救。从理性堕落的迷惘过渡到人性复归的孤独,从颓废审美的绝望发展到丑升华为美的悲壮 ,构成了坂口安吾凤凰涅槃式的叙事哲学。“他提倡不要为堕落而堕落,不要为颓废而颓废,而是在追求诚实,追求正义,探求人性。”[9]因此,《堕落论》不仅是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理论性纲领,更是坂口安吾“颓废”叙事艺术的理论性升华和哲学性体现。
从坂口安吾感同身受的“孤独”意识,到他面对物质匮乏精神荒芜的现实所采取的“反叛”主张,再到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的“堕落”行为,均体现了其独特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环境紧密相关。
四、坂口安吾哲学思想的成因
坂口安吾的哲学思想指引着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其“孤独”哲学、“反叛”哲学、“堕落”哲学等不同视域中的哲学思想构成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堕落式”的哲学思想、标新立异的思维范式为战后日本文学乃至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崭新的理念,尤其是其惊世骇俗的文论名篇《堕落论》所提倡的“人要彻底地堕落,堕落到道德的最底线才能得到重生,要否定形式主义的美德和旧秩序,要通过堕落和颓废的方式来实现人性的复归和自由的追求”[10]理念,为战后日本社会颓废的精神世界吹来一阵新风,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热烈反响。诚然,坂口安吾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当时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家庭环境造成了其特殊的个人性格和文学气质,当时激烈巨变的社会环境为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条件。
(一)坂口安吾哲学思想形成的家庭成因
坂口安吾的家庭环境深刻影响着其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和发展。坂口安吾出生在日本新潟的一个富裕且有名望的家庭,父母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教养方式。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从幼年时期他的性格就特别叛逆,逃课和吵架成为家常便饭,多个科目成绩太差而不得不成为留级生,而且他太过于叛逆和调皮,多次惹是生非,导致最终被勒令退学。此后,坂口安吾父亲病逝,家庭境况每况愈下,母亲为了生计疲于奔命,对坂口安吾的教育也疏于关心,他无法感受到母爱。同时,坂口安吾的母亲是后妻,与前妻子女的关系非常紧张,整个家庭十分不和谐,坂口安吾根本体会不到家庭的温暖。如此的家庭环境对坂口安吾的婚恋也产生了影响。他在与女作家矢田津世子四年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后以分手告终。在这四年中,坂口安吾还与其他女子同居并生活在一起,可见其私生活的混乱。由于家庭氛围的影响,坂口安吾先后得了神经衰弱症、忧郁症、安眠药中毒症等病症,最后脑溢血突发,文学生命就此划上了休止符。显然,家庭经济逐步走入窘境、家庭关系不和谐、亲情淡薄、母爱缺失的成长环境深刻影响着坂口安吾的哲学思想。
(二)坂口安吾哲学思想形成的社会成因
除家庭环境的影响外,坂口安吾所处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状况也影响着其哲学思想的形成。从坂口安吾哲学思想形成的社会成因观之,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日本的战败。二战时期,日本整个社会一直宣扬“东亚帝国”的思想,皇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潮占据社会主流,战争被极度美化,士兵被尊奉为英雄,然而“战争时期受军部为蛊惑人心宣扬的种种蒙蔽和愚弄国民的‘强国’理论影响而培养起来的大国国民意识随着战败瞬间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对一切的怀疑和否定”[11]。为此,原本对战争胜利抱有强烈希望的日本国民面对急剧出现的战败现实无法接受,他们开始质疑战时日本政府所宣扬的“效忠天皇”和“帝国主义”的真实性。与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从战时信奉日本政府的“富国强兵”理念到不得不面对“战争失败”的现实,坂口安吾逐步对战争的正义性感到迷惑,进而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质疑。这种因战争的急速变化而产生的精神信仰上的崩溃,深刻冲击着坂口安吾哲学思想的变化。其二,日本经济的急剧衰退。战争结束后,日本整个经济处于荒芜状态。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交通运输业处于瘫痪状态,生产力水平急剧下降。农业生产滞后,粮食歉收,供不应求现象日趋严峻。而且由于战争的结束,军工产业萧条,大量失业工人涌现,再加上从战争退伍回来的士兵,整个社会的失业群体迅速膨胀。同时,由于物质缺乏,物价迅速飞涨,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如此一来,由于经济衰退、工农业产品匮乏和物价高涨,日本经济陷入了瘫痪和濒临崩溃的边缘,一般民众的生活困境越发严峻。这种物资极度匮乏、生存难以为继的经济环境影响着坂口安吾哲学思想的变化,同时映射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其三,日本政治体制的变化。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了绝对主义天皇制和华族制度,将国家和神道分离开来,逐步实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战时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政体逐渐解体,“日本绝对的天皇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从根本上遭到瓦解,从二战时期以牺牲个人主义的极权军国主义转变为宣扬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肯定个人的自由、平等的生存思想,在价值观的判断和持有上,失去了原来的标准,二战时期既有的功利思想和精神价值观完全失去了主体性,民众陷入了心理上的精神虚脱状态”[12]。面对政治体制的急速崩溃,作为日本民众的坂口安吾深感原有价值观的幻灭,颓废感和虚无感油然而生。这种精神主体性的缺失和心理状态的虚脱深深地影响着坂口安吾哲学思想的形成。
五、结语
作为日本无赖派思潮的重要作家,坂口安吾的哲学思想不但表现在个人生活上,更体现在文学评论、小说、随笔等文学作品上。同时,他的哲学思想不仅构成了独立的人生价值观,而且成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孤独”哲学、“反叛”哲学、“堕落”哲学等,他鲜明大胆地提出在战后初期日本混乱的社会局势下,应以凤凰涅槃式的堕落方式才能得以生存,才能体现人性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坂口安吾之所以能提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哲学理念,与个人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因此,要真正理解坂口安吾的哲学思想,不仅应从其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入手,更应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深入探讨,才能更准确、更充分地把握其哲学思想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