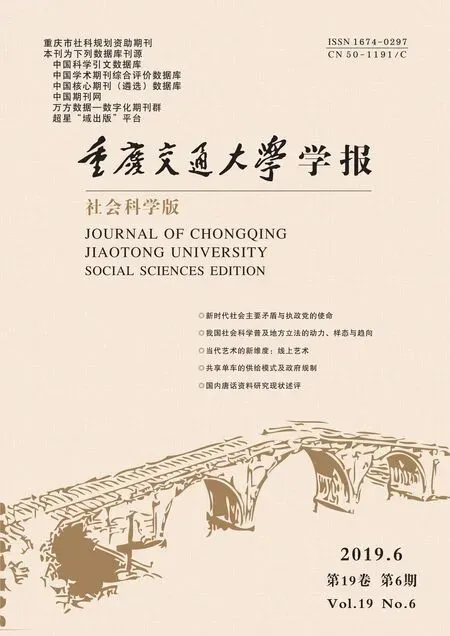超越自我之像:瑞典动画纪录片的语境及发展
米德哈特·阿扬·阿加诺瓦克(著), 郭春宁(译)
(1.西瑞典大学/特鲁尔海坦大学,瑞典;2.中国人民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2)
一、非拍摄式纪录片
人们通常的误解是,动画似乎是对现实漠不关心的非政治化艺术形式。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时代中一些最有力的故事是通过动画片讲述的。由于动画的特定方法,笔者将其定义为“加速变形”(accelerated metamorphosis)(1)参见作者的著作《动画和现实主义》(Animation and Realism,2004)。;动画是一种处理生命体诸方面的特殊艺术形式,并将存在性之抽象转化为可视。动画电影往往成功地创造关于社会和时间的“微观地貌”;借由精确和现实性,成为其所制造的、所处时空的忠实见证人,正如漫画家能够传神地呈现某人的面孔一样。在欧洲中部地区创作的大量动画片可能成为一种绝佳的范例,尤其是对动画电影中的悲观主义抵抗,在冷战时期被归纳到共产主义阵营,在反思现实中呈现政治性奇观和超越性幻想。由爱沙尼亚的皮特·帕恩(Priit Pärn)和俄罗斯影人伊果·科瓦廖夫(Igor Kovalyov)所提出的重建(perestroika)形态具有代表性。另一例子是所谓的撒切尔主义期间的英国社会与第四电视台(Channel 4)出品的社会批判性电影之间的联系。这些动画纪录片大都在社会政治语境中关切人类生存的情景和心理状况。
虽然动画纪录片(2)当然这个名字比较特殊,就如最初“电影”“漫画”和“视频游戏”那样,好消息是人们往往很容易习惯不寻常的名称,昨天视为特殊的名字在今日会变得寻常。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混合概念,但这种类型的命名已经在电影制作和研究中得以确立。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动画纪录片获得了强劲的动力,从以前不起眼的子类型成为近来重要的现象类型。随着电影进入数字时代,动画纪录片也在逐年增长。
简单说,动画纪录片可以定义为借鉴纪录片制作的标准和惯例所创作的动画电影。安娜贝尔·霍内斯·罗伊 (Annabelle Honess Roe)的著作是极少数关于动画纪录片的综合性书籍之一,其中,作者引用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的解释,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动画称为纪录片,因为“它是关于世界的,而非世界”[1]。她还提出了几个类别,如模仿(mimetic)、替代(substitution)、记忆(mnemic)、召唤(evocation)等。
动画纪录片的出现源自电影制作者永恒的渴望,以可信的方式呈现摄像机无法拍摄的事件,因为:它们发生在电影发明之前;它们如同抽象空间或细菌,或者让·米特里(Jean Mitry)称之的“虚构现实”,是不可通过拍摄呈现的;或者在某个平常或重要事件中没有相机在场。第一类形式例如可以被称为“dinocumentaries”的整个子类型,从温瑟·麦凯(Winsor McCay)的《恐龙葛蒂》(Gertie,TrainedDinosaur,1914)和威利斯·奥布莱恩(Willis O’Brien)的《恐龙和失踪链接》(TheDinosaurandtheMissingLink,1915),到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Park,1993)、BBC制作的迷你剧《与恐龙同行》(WalkingwithDinosaurs,1999)及其后作品。
电影“派系”的倾向在法国早期的电影中已经非常突出,其中包括乔治·梅里斯(Georges Méliès)。对于宗教世界的物化,描绘女神、天使、魔鬼、仙女和其他无形的各个宗教人物类型,法国电影制片人以特效和动画超越电影摄影的限制——在光学和化学上的限制。当动画用于可视化各种科学理论或重建历史事件时,这种动画在教育电影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不同的动画技术的帮助下,物理现实中一些不可见部分和不可拍摄性被完全补偿,因此电影制作者得以用他们的动画相机“记录”与“显示”微生物和病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弗莱舍(Fleischer)兄弟制作了动画教育电影,以有趣的漫画形式解释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
可能最有趣的是第三种形式,通常是对现实中发生了但未被记录的一些事件的再现。凭借电影《路易斯塔尼亚号的沉没》(TheLinkingoftheLusitania,1918),温瑟·麦凯为这类动画电影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部电影是一部“纪录片”,由手绘的动画图像组成,令人信服地重建了一个真实的事件,从而创造了一个目击者报告的幻像。在这种情况下,动画弥补了德国潜艇击沉客船“路易斯塔尼亚号”这一历史事件中摄像机的缺失。
实际上,自“路易斯塔尼亚号”事件之后甚至之前,有不少动画作品重建了未被摄像记录的事件。例如由科尔(Cohl)开创的《奥兹特里茨战役》(LaBatailled’Austerlitz,1909)对古老战役进行可视化,同样,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工作团队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什么战斗》(WhyWeFight,1942—1945)的动画部分再现了“闪电战”(Blietz Krig)。科林·劳尔(Collin Low)、沃尔夫·科尼格(Wolf Koenig)、罗曼·克罗迪尔(Roman Kroiter)和汤姆·戴利 (Tom Daly)导演的《加拿大交通发展史》(TransportationinCanada,1953)以及《大水河》(TheMightyRiver,FrédéricBack,1993)都是以动画电影的形式来叙述加拿大历史。
木下莲三(Renzo Kinoshita)指导的《广岛之歌》(ASongforHiroshima,1978)也是历史性的动画书写,揭示广岛的惨剧。麦洛克·米克罗(Melocco Miklós)导演的《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Mansfeld,2007)则是关于1956年苏联干预匈牙利背景中对于一个年轻男孩的诬告和错误裁决。这与布莱特·摩根(Brett Morgen)使用三维动画方式创作的长篇电影《芝加哥10》(Chichago10,2007)异曲同工,重新检验1968年针对美国反战活动家的审判及期间所做的证词。奥利·亚丁(Orly Yadin)和斯列维·布林格斯(Silvie Bringas)导演的影片《沉默》(Silence,1998),基于诗人和大屠杀幸存者塔娜·罗斯(Tana Ross)的证词,敏锐地捕捉到人性的黑暗面。
这类动画纪录片最近的一个范例是《破碎:霍恩克的妇女监狱》(TheWomen’sPrisonatHoheneck,2016),是一部强有力的电影,揭示了前东德女子监狱的丑恶。电影制作人加布里埃尔·斯多茨(Gabriele Stötzer)和贝吉塔·维尔舒茨(Birgit Willschütz)冷静地陈述了监狱中的日常生活,女囚犯像奴隶一样工作,生产出口产品。虽然这部电影所陈述的独裁统治下的人的遭遇已时过境迁,但动画讲述提醒我们即使在如今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仍会发生。
二、视觉传记
我们能够非常频繁地看到,动画纪录片这一子类型呈现从电影制作者个人经历中获取的叙事视角和历史观。这些电影通常因基于日常现实主义和自传体叙事的特征而被归纳。
我们拥有脑海中的记忆——这一不完美时间机器提供的影像,此外,描述的可信度通过使用真实材料而得到加强,例如私人日记、证词、文件、照片和真人录像。譬如《从记忆而来》(DrawnFromMemory,1995)是由杰出的动画师兼漫画家保罗·菲尔林格(Paul Fierlinger)创作的一部电影,电影梳理了他的中欧犹太家庭设法摆脱大屠杀之后在美国作为难民成长的记忆。导演劳伦特·波利(Laurent Boile)和比利时艺术家荣(Jung)在电影《批准收养》(Approvedforadoption,2012)中处理了类似的社会议题。作为朝鲜战争期间收养的一个孩子,荣通过图画小说和以此为基础的电影创作来寻找自己的身份。马贾内·斯特拉比(Marjane Strapi)和文森特·帕兰德(Vincent Paronnaud)创作的《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2007)以斯特拉比的图画小说为基础,用一种古老波斯细密画风格描绘了“我”在伊朗动荡岁月中的童年记忆。另一部基于图画小说的长篇动画自传是《辰巳》(Tatsumi),讲述的是漫画家辰巳喜弘(Yoshiro Tatsumi)在战后日本社会情境中的生活和事业。
安卡·达米安 (Anca Damian)凭借《超越之路》(Crulic,2011)和《魔山》(TheMagicMountain,2015)两部动画纪录长片脱颖而出,她恰当地使用剪纸动画来重构和描绘跌宕起伏的命运。
艾伦·乌格托(Alain Ughetto)创作的《茉莉花》(Jasmine,2013)是基于自传材料的建构,为该领域贡献最大的艺术成就。在第一个层面上,这部精彩作品呈现的是在几个时空中同时发生的事件,是对西方政权的微妙批评,西方政权帮助聚集于霍梅尼(Khomeini)周围的势力得以在伊朗掌权。但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是一部热烈的爱情故事,强烈而真实地阐释了时间并不能治愈一切。时过境迁,但灵魂中深深的创伤难以愈合。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动画师爱上了一位来自伊朗的戏剧学生。他们两人在德黑兰时,由青年人发起的革命、对民主和正义的灼热追求却转变为残酷的独裁统治。作为外国人,法国动画师被迫离开这个国家,伊朗女学生却决定留在家乡。这个故事主要是通过乌格托在相机前塑造粘土角色结合真实照片图片来讲述的。通过使用复杂的视觉语言、象征性的粘土人物和不断脉动的移动雕塑,整部电影感觉就像一个专门奉献心爱之人的温柔爱情和感情手信。任何形式和类型的电影能达到如此高度的抒情都是非常罕见的。《茉莉花》是关于世界的电影,同时它自身也成为一个世界,就像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
三、动画采访
采访是纪录片经常采用的形式之一,能提供最强烈的真实印象,已被应用于动画之中。通常采访会被用作对电影中心人物的见证,或是通过采访表达电影的实际主题。大多数动画纪录片都是作为一种拟像——一个从未拍摄过的现实副本的重构,通过个体的采访电影与我们分享关于这个世界的借鉴。我们正在看一个人说话,与同时听到他/她的话的事实提供了极高的可信度。采访的电影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技术可以将声音复制到电影胶片上并与之对位同步(3)早在华纳兄弟1926年8月6日电影新闻《维塔有声影像介绍》(Introduction of Vitaphone Sound Pictures)中,我们能看到一些初级的采访技巧。威尔·海斯(Will Hays)用“亲爱的朋友们”向观众展示了有声电影。同年的第二个有声电影案例是《银幕之声》(The Voice from the Screen),爱德华·克拉夫特(Edward B. Craft)使用了一些剪辑技巧,我们甚至还能看到他的助手询问他问题。。例如《房屋问题》(HousingProblems,1935)(4)此片由安斯蒂(E. Anstey)和埃尔顿(A. Elton)导演,英国出品。——译者注等电影,人们在摄像机前谈论的生活加强了将运动影像作为生活现实反映的观念。这种方法后来被电视采用,成为电视新闻和纪录片节目的主导表达方式。除纪录片和采访电影外,这一类型也在动画领域内发展——起初是滑稽的模仿,其中声音起着关键作用。例如华纳兄弟的动画研究漫画家将著名人物的漫画图像与该人高辨识度的声音相结合,声音有时是原声有时是模仿配音。
阿德曼工作室(Aardman)制作的许多电影采用了将纪录声音与动画结合的方式,呈现讽刺风格,如尼克·帕克(Nick Park)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动物舒适》(CreatureComforts,1990)。帕克在学生家中采访了几位外国学生,了解他们的生活,借助各种粘土动画角色发表评论,呈现为有趣的动物如何抱怨它们在伦敦动物园的生活条件。关于动画如何通过采访方法切入“虚构现实”的另一个例子是保罗·韦斯特(Paul Vester)的《诱拐》(Abductees,1995)。作品将各种动画手法和真实声音结合,将真实人物遭遇外星人的经历可视化。希拉·索菲安(Sheila M. Sofian)根据一位随家人移民至美国的波斯尼亚男孩哈里斯·阿里奇(Haris Ali)的访谈,创作了关于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战争的电影《与哈里斯的对话》(AConversationwithHaris,2002),影片令人印象深刻。
该类型下一步的演进计划是重新制作实拍影像,从而超越其表象。人们普遍认为动画的虚幻运动并不对应实时的动作,这是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之间的根本区别。动画被视为一种动态图像,不受现实或物理定律(例如重力)的影响。然而,我们还有对拍摄素材重新绘制的方法,替代创作新的动态图像,由于数字媒体的技术创新,这种动画越来越常见。
在这一语境中,一部至关重要的电影是加拿大动画家克里斯·兰德雷斯(Chris Landreth)创作的《拯救动画大师瑞恩》(Ryan,2004)。兰德雷斯借助的是与主角瑞恩·拉金(Ryan Larkin)的一系列拍摄对话。瑞恩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创作,成功地制作了他的动画电影,以“意识流”图像进行系列动态作品创作,手工绘制着色呈现迷幻嬉皮风格,而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技术如胶片动画、剪纸或木偶动画,他获得了国际声誉和业界认可。瑞恩创作的电影《漫步》(Walking,1968)大胆地展现了大都市的生活,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和背景描绘了人们走路的各种方式,使得年仅26岁的瑞恩成为这种动画形式领军的主要艺术家。随后瑞恩的生活和事业突然转向,并没有特别的原因,他开始滥用毒品和酒精。瑞恩在蒙特利尔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隐姓埋名,度过了30年。兰德雷斯的想法是以特定类型制作一部简短的传记电影,即基于对瑞恩采访创作的动画纪录片。《拯救动画大师瑞恩》成为一部关于酒精滥用的电影,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强调艺术家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让这部电影与众不同的是兰德雷斯处理影像的方式。在三维数字动画的帮助下,兰德雷斯在视觉上切掉了瑞恩的脸的绝大部分,使其面貌变得支离破碎。当然,这背后的想法是展示酒精如何摧毁了一位曾经受人尊敬的艺术家。这部作品获得了2005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以及60多个其他国际奖项。
另一部重要的奥斯卡奖获奖电影是动画长篇《与巴士尔跳华尔兹》(WaltzwithBashir,2008),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知动画纪录片。这是一部由阿里·福尔曼创作的自传式作品,此前他是纪录片制片人。影片中,1982年在莎布拉(Sabra)和莎缇拉(Shatila)发生臭名昭著的屠杀事件时,福尔曼作为一名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电影中的主要角色——福尔曼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每晚都被噩梦折磨。因为与曾经的战友相遇,开始与战友交流这一噩梦,并搜寻失去的记忆。通过采访,噩梦的描述借由类似描片的动画方式呈现。动画将采访场景相互联系,直到在最终场景中主角的记忆被唤起,场景是基于真实的屠杀及尸体纪录图像而重新描绘的,会引发观众生理上的不适。
除少数情况外,采访是瑞典动画纪录片的主要方法。我们拟重点介绍瑞典电影和动画历史的一些细节。
四、伯格戴尔和基于事实的动画
维克特·伯格戴尔(Victor Bergdahl)是一名水手、画家、漫画家、记者,也是一位作家。 最重要的是,作为动画师,他应该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10年代早期,他第一次涉足动画,当时他巧合地看到埃米尔·科尔(Emile Cohl)和温瑟·麦凯制作的早期动画电影,让伯格戴尔有了自己尝试动画的冲动(5)当然他没有技术经验,但电影院老板用以下的话“揭示”了动画的秘密:“魔力就在于让照片以书的形状串联在一起,借助拇指在镜头前方翻动,运动图像被捕获于赛璐璐胶片上,从而产生视错觉。”[2]在这一解释之后,Bergdahl选择了开发自己的技术。而这正是他所做的。为了避免一遍又一遍地绘制相同背景,Bergdahl将背景印刷成数百份,他在印刷纸上标记数字。他用下方打光的方式构建了自己发明的动画桌,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还创新了剪切方法、纸偶和用切割的部件组合可移动场景。。值得注意的是,维克特·伯格戴尔对基于事实的动画的兴趣,凭借他的方法,他可以更快地制作广告和教育电影,这是伯格戴尔电影制作的另一个先驱领域。实际上,他的最后一部动画片正是关于女性性器官和胎儿发育的科教电影。
和伯格戴尔一起,他的同事埃米尔·阿伯格(Emil Åberg)和利耶奎斯特(M.R. Liljeqvist)也为瑞典动画贡献了惊人的开端。 漫画家罗伯特·胡菲尔德(Robert Högfeldt)和埃纳尔·诺雷利乌斯(Einar Norelius)从伯格戴尔那里学习动画,他们在早期取得了另一项巨大成功(6)在1934年制作了一部迪士尼风格的电影《Bam-Bam和驯服巨魔》(Bam-Bam and Taming the Trolls)。同期声音及柔和流畅的动画为瑞典动画中的第一个主流类型——动画儿童电影奠定了基础。 不久之后,诺雷利乌斯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新项目——一部基于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的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Nils Holgersson Adventures through Sweden)创作的长篇动画电影,但战争终结了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动画生产恢复,儿童电影蓬勃发展以来,即使在今天,这个国家也存在着一种将动画视为“为儿童而作”的想法。。
五、动画儿童长篇、动画广告和第一批基于事实的动画
伯格戴尔培养了阿维德·奥尔森(Arvid Olsson)这一不同寻常的接班人,他是1930年代至1950年代以来瑞典最多产的电影动画师。1930年代还是一名身在巴黎的年轻学生时,奥尔森就对动画产生了兴趣。回到瑞典后,他投身商业动画创作。奥尔森创作了瑞典第一部有声动画电影,1931年的《克朗的月食》(TheLunarEclipseoftheKrona)是一部关于瑞典货币(克朗)价值的幽默广告。1934年,奥尔森成为瑞典第一位以专业方式使用彩色胶片的电影人。除数百部商业广告外,他还为中央党(The Centre)和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 Party)制作了一些竞选影片,并创作了一些教育和信息型动画。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儿童文学中的流行角色成为电视剧和动画片的英雄。与前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瑞典实际上是制作最多二维赛璐璐手绘动画长片的欧洲国家之一。如此大规模的制作归功于动画家甘纳·卡尔森(Gunnar Karlsson)、施蒂格·拉斯比(Stig Lasseby)、奥利·哈尔伯格(Olle Hallberg)、托埃里克·弗莱特(Tor-Erik Flyght)、鲁内·安德烈亚松(Rune Andréasson),让吉斯伯格(Jan Gissberg)和坡·安林(Per Åhlin)作为第二代专业动画师的领导人物。
坡·安林制作了许多短片和动画广告,也许是最多产的欧洲动画家,他作为漫画家的主要风格是精确地描绘人物和坡·安林典型的抖动性与曲线(仿佛是他坐在转椅打转时画的)。他的动画和绘画风格完全符合当代动画世界中最为现代性的潮流,充满了鲜明的纳维亚特质和感受。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安林有机会在各种电视节目中制作动画短片,他开始同流行作家和脱口秀喜剧演员哈西·阿尔弗雷德森 (Hasse Alfredson)与泰治·丹尼尔森(Tage Danielsson)合作。他们是《老人头脑中》(IntheHeadofanOldMan,1968)的幕后团队,这并不是一个为儿童创作的动画片,是对瑞典这一福利国家的委婉讽刺,创作中凸显了幽默和善意。影片设定于一名老人家中,以动画结合影像呈现了来自养老金领取者约翰(Johan)的记忆。即便这部电影不能被归类为动画纪录片,但该部动画作品与现实和时代精神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才华横溢的女动画师在瑞典动画界中争取性别平等。与其他动画文化一样,瑞典女性动画家表现出倾向于实验和使用赛璐璐动画之外的其他技术。伯吉塔·詹森(Birgitta Jansson)正是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崭露头角,她是一位在大学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坡·安林一起制作动画,然后以独立动画方式创作。詹森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动画家,受到威尔·云顿(Will Vinton)的启发,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使用了粘土技术。她意识到与使用赛璐璐画相比,粘土可以提供角色手臂和腿部更好的弹性、柔韧性,以及更强的表现力。她创作了瑞典第一部粘土动画和第一部动画纪录片,这部长达13分钟的获奖作品名为《度假屋》(HolidayHome,1981),以詹森特有的动画纪录风格获得了成功,也受益于瑞典本身的实拍纪录片优势。《度假屋》中的动画呈现了在养老院录制的对话,租户们讲述了他们的生活故事。令人惊讶的角色造型、时间节奏,尤其是电影的结尾可被视作是一种后现代性的质疑——如何区分现实和幻觉,使得这部电影至今仍令人着迷。 詹森并没有忘记向坡·安林致敬,她在影片中通过一个安林成功的长篇动画故事《胆小鬼拉班》(Dunderklumpen,1974)中的角色来怀念坡·安林。《度假屋》的纪录片特性为整个类型奠定了基础。通过这部电影,詹森开创了这一纪录片类型,并成为瑞典动画纪录片的重要特征。此外,由于这部电影的诞生,纪录片将纪录录制的音频与动画相结合的方法变得普遍。
六、《人民之家》和批判性纪录片
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瑞典制作了如此多的动画纪录片?原因之一其实很乏味——即瑞典电影协会并不将动画电影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提供资金,也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动画的专员(konsulent),而其他形式和电影类型包括纪录片有专门负责委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动画师会将其项目作为纪录片申请。另一个原因是,笔者认为与纪录片的本质有关。纪录片从不仅仅用于娱乐,他们要么是教育性的,要么总是涉及真理这一动态影像的古老信条。
电影出现后被宣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反映世界真实和准确形象的媒体,但政治权力一直努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揭示真相。就像奥尔罕·帕穆克(Orhan Pamuk)的小说《雪》(Snow)所描述的一种发号施令的力量,气象学家预告以每日提升五到六度的温度来“滋养”人们,电影经常被用来美化现实。不幸的是,才华和道德并不总是相伴相随,一些最引人入胜的纪录片是为政治宣传服务创作的。然而,还有很多有天赋的纪录片制片人积极观察和评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也就是说,不可设想和不可预测的思维过程,以及摄影师手中的相机,被证明是不被操控的。因此,纪录片的历史特征总被权力的“真理”与独立电影人的真理之间的冲突所界定。
瑞典有着强烈的民主传统,瑞典纪录片的关键特质在于对瑞典社会民主党模式被普遍接受的假设及其自我形象的质疑。社会民主党在国外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声称以团结和平等为特征的人民之家(7)我们是否还能继续谈论人民之家是个问题。由于公共财产的大规模私有化,在失去了右翼联盟的两次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自身滑向左翼。即使是瑞典著名的中立性现在也可能受到质疑,因为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美国海关对乘客的控制,以及瑞典军队在其军事任务和演习中经常是北约的一部分。(folkhemmet)。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瑞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热切地走向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但许多瑞典人仍然相信自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时代以来瑞典国内和国外没有任何改变。然而,纪录片为主流媒体和政治中很少讨论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大量证据,社会结构性不平等中的一些隐蔽的方面,如政治腐败、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比如否认大屠杀(holocoust denyal)(是2002年杰安·洛夫斯泰特Johan Löfstedt创作的伪纪录片《阴谋58》涉及的议题之一)这样的家庭暴力和类似的事情仍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中悄然上演。《瑞典爱情理论》(TheSwedishTheoryofLove,2016)是一部典型的瑞典纪录片,其中公认的电影制片人埃里克·甘迪尼(Erik Gandini)根据1970年的政治宣言《家庭的未来》(FamilyoftheFuture),检视人们相互独立的观念。该项目致力于社会中个体的独立,这是人们相互之间保有自由的系统制度。在社会实现了“舒适的生活、高水准的生活,进步和现代思维”之后,20世纪70年代是向前迈出一步,让人们摆脱“老旧思维方式”的时候。和其他发达国家关注家庭不同,富裕的瑞典关注个体,即“为自己工作的人”。正如这部电影所证明的,这项计划导致了巨大的比例异化,瑞典超过40%的人口独居,这一比例居世界之首。
实际上,瑞典纪录片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奠基人是艾恩·萨克斯福德(Arne Sucksdorf)。他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30年代,凭借1949年的《城市交响乐》(SymphonyoftheCity)成为第一位赢得奥斯卡奖的瑞典人。他还创作了瑞典第一部纪录片长片《大冒险》(TheGreatAdventure,1953)。由于萨克斯福德的纪录片在商业和国际上所获得的成功,他为瑞典电影业取得了更多的优惠待遇。
最重要的瑞典纪录片制片人或许是斯特凡·贾尔(Stefan Jarl),他的职业生涯始于给萨克斯福德当助手。虽然是萨克斯福德的弟子,但贾尔从未接受过萨克斯福德的审美概念和类似迪士尼的方法。在英国 “自由电影”(Free Cinema)运动之后,贾尔爱上了摆拍或“表演”式纪录片,采用了一些典型的真人电影和声音同步的方法。贾尔主要对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体感兴趣,尤其关注年轻一代。他的纪录片长篇《他们称我们异类》(TheyCallusMisfits,1968)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和影片的成功,作品中关注年轻一代面临着缺乏目标、无目的性和行动无果,相比老一代人受到精神和道德滑坡的指责。影片中悲观描述并残酷揭示了对年轻人的成见和缺乏理解所造成的代沟。贾尔为这种批判性纪录片设定了标准,这些纪录片将在未来几年蓬勃发展,并成为其引领的主要创作力量。
在瑞典纪录片《反对现实》(FightforReality)中,英格丽德·埃斯平(Ingrid Esping)描述了研究纪录片与审查之间冲突的长久历史[3],但纪录片制片人仍持续审视人民之家的阴暗之处。
实际上,当涉及要解决社会问题和对其进行批判检视时,实拍电影和动画纪录片之间并没有区别,除了后者涉及更多幽默和讽刺元素。
七、动画纪录片最重要的实践者
无论动画或纪录片,当它们是好作品时,总是提供解释、评论,而不是致力复制现实。如上所述,大部分瑞典动画纪录片正是如此,揭示了人类存在情景中社会和心理状态的一些隐秘方面,如公共性传播未被讲述的故事。这些电影通常是个人的、有争议的,有时是黑暗的和悲观的,甚或呈现阶级观点。
20世纪90年代,瑞典动画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这是数字媒体取代电影技术的时期。数字化意味着生产和分销的民主化。虽然此时动画生产并没有降低成本,但动画变得更容易被更多人接受,尤其是年轻人将这种媒介作为表达自己声音的一种方式。数字化也增加了动画纪录片的可能性,这无疑成为新千年中最突出的艺术类型。另一个同期发生的重要事件是,瑞典工艺美术与设计大学(Konstfack)成立了动画培训部。除教育活动外,该部还尽力开展学术研究,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启动动画节和电影动画的区域资源中心,在世界各地展示和推荐学生及其作品。最重要的是,有120多名学生由此部毕业,改变了瑞典动画。自从第一代受教的动画师,许多毕业生选择创作基于事实的动画,开展他们的职业生涯。
作为瑞典动画中纪录片方法的典型案例,《蓝卡玛老虎》(Blu-Karma-Tiger,2006)的副标题为“关于涂鸦的纪录片”,由电影制片人米亚·哈尔伯斯坦(Mia Hulterstam)和塞西莉亚·阿克蒂斯 (Cecilia Actis)搭档创作。追随伯吉塔·詹森的脚步,他们结合涂鸦艺术家的真实声音,使用了粘土动画。另一对成功的合作伙伴是汉娜·费尔伯恩(Hanna Heilborn)和大卫·安诺维奇(David Aronowitsch),他们制作了电影《隐藏》(Hidden,2002)。通过动画图像和纪录片声音,讲述了12岁的吉安卡洛(Giancarlo)的故事。他是一名无证移民,躲藏在瑞典,似乎感觉每个人都在追踪他。费尔伯恩和安诺维奇制作的另一部动画纪录片《奴隶》(Slaves,2008),揭示了苏丹南部内战期间两个孩子的悲惨命运,他们成功赢得了法国安纳西的动画大奖,这也是瑞典动画迄今为止获取的最大的国际奖项。除了审美原因,动画纪录片还能隐藏演员的真实身份,因为真人实拍影片会披露他们的形象名字,将其置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马贾·林德斯特伦(Maja Lindström)使用三维数字动画方式制作了基于现实的电影,令人惊叹的视觉风格动画《丁粤》(TheLidingo,2009),这是一部基于电影创作者童年时期在斯德哥尔摩郊区成长的自传故事。这部电影发出了强烈声明,瑞典这一人民之家已经成为两极分化的社会,一方面强烈支持福利制度,一方面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坚持私有化、全球化、低税收和放松管制。影片通过儿童的视角,观察以意识形态和阶级划分为特征的现代政治与社会环境。
动画纪录片中讨论的主题常与人们的性习惯有关。在电影《胚胎》(Embryo,2013)中,艾玛·索姗德(Emma Thorsander)使用采访来揭示堕胎的年轻女性的心态。特蕾莎·格拉德(Teresa Glad)在《丑陋情感》(Uglyfeelings,2008)中探讨了现代青少年对性和爱的态度,这也是基于预先录制的采访。格拉德也是系列动画教育影片《性爱地图》(Sexonthemap,2013)背后的主要创作力量,由于涉及性主题和场景,在公共服务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强烈争议。
乔纳斯·奥德尔(Jonas Odell)无论是在电影数量还是电影艺术质量方面,都是这种类型最重要的实践者,他迄今为止最好的电影《从未像第一次那样》(Neverlikethefirsttime,2005)中也将性作为主题。
1981年,奥德尔与拉尔斯·奥尔森(Lars Ohlson)、施蒂格·伯格奎斯特(Stig Bergquist)、马蒂·埃克斯特兰(Marti Ekstrand)一起组建了瑞典Filmtecknarna动画工作室(意为“电影卡通家”)。他们开始制作独立电影,但也制作商业动画和音乐视频。《左轮手枪》(Revolver,1993)是他们的突破性作品。这部关于时间流逝的悲喜剧是由几部短片动画构成的音乐性拼贴。在奥德尔的其他电影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拼贴结构,这些电影是他自己创作的动画纪录片,是他专注的一种类型。
在奥德尔的所有电影中,技术的精湛、视觉的丰富性与清晰的叙事相结合。他采用了一种碎片化的视觉叙述模式,建立在采访或对文献的研究基础之上,以创造现代瑞典的微观地貌图像。通过富有想象力的视觉词汇,他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现实,他的作品光照了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关注那些边缘人及他们的生活形态。
最有趣的是《从未像第一次那样》,是基于对四个人的记录采访,每个人都回忆他们最初的性体验。这部电影不仅是基于访谈和研究的伟大艺术作品,也是对现代瑞典人状况的敏感洞察。这部电影以个人的方式凸显了从远古就有的肉体欲望与现代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爱这一词汇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对于其中三个年轻人来说,显然是独立个体的一代,性的初体验是一种暴力、可怕或无情的事情。最后,他们的经历与一位80岁老人的回忆相交融,他清楚地记得那个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用美丽的诗歌语言描述它。记忆得以巧妙地呈现,通过重现1930年代斯德哥尔摩报纸上的广告及不断变化的图案,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强化和聚焦其意义,融合细微差别。正如乌格托在《茉莉花》中所做到的,奥德尔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动画如何能够深入人类心灵,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动画还可以通达真人实拍电影不能实现的抒情境地。电影《从未像第一次那样》成为柏林电影节的主要国际热门和获奖者。
在他的其他项目《谎言》(Lies,2008)和《末路黄花》(Tusilago,2010)中,奥德尔继续探索展示真实之人的体验经历。特别成功的是《末路黄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灵感来自女性A的真实传记,她是20世纪70年代西德恐怖分子诺伯特·库尔瑟(Norbert Kröcher)的女友。这部电影的出发点是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法庭案件。以纪录片的特质强调无辜的女人为她不应负责的事情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动画和实拍影像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女主角A的内心世界。
奥德尔的最新电影是《我是一个胜利者》(IWasaWinner,2016),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三维数字动画,强调了另一个在公共讨论中被降格的重要问题——游戏成瘾。正如他以前在电影中使用的隐喻意象,用三个化身代表真实世界中的游戏成瘾者,讲述当代社会中最被疏离者的故事。
作为这种非同寻常类型的最稳定的创作者之一,奥德尔已经证明了动画纪录片并将流传于瑞典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