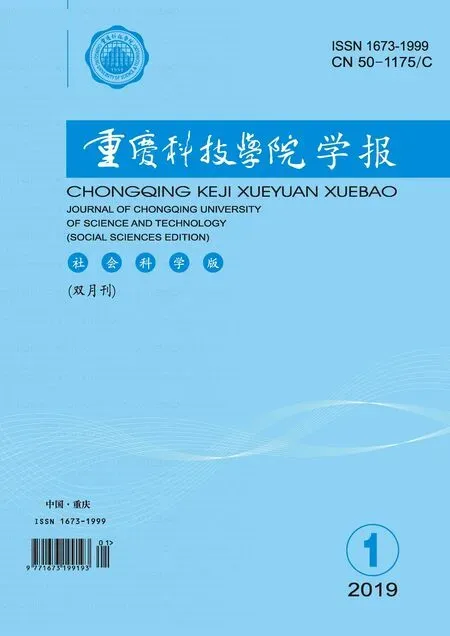意识形态安全与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刘成兴,邓国彬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我国的互联网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并已基本融入互联网“地球村”大家庭。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开放性、虚拟性等特征的网络已成为网民表达意见的窗口,并成为他们捍卫权益的重要手段。当发生社会矛盾时,网络必然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争论的平台,社会批判言论、不满情绪等在网络上迅速聚集,而这种争论在特定因素的诱导下极易演化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利益群体在网络上的意见表达是所在阶层将其观点经过加工后的产物,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产生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被看作是不同阶层意识形态争论的产物。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其事关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及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增强,因此,在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探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在虚拟社会的表现,虽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其实质仍然是受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媒体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网络群体也日益复杂,这些都给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挑战。而且,虚拟社会的高度开放性特征也给西方培育的舆论代言人和社会杂音提供了发声的机会,并给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网络媒体的多样性增加了管控难度
“媒介是影响公民政治表达的重要因素。”[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逐渐演变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外的“第四媒介”,而基于网络这一传播媒介发展起来的网络媒体如天涯社区、微博、微信等已成为网民参与网络政治的主要平台。网络媒体在其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兼具互联网以及传统媒体的一些特征,其多样化发展对政府管控网络意识形态带来了一定困难。首先,网络媒体具有易逝性,这种易逝性特征增加了政府管控的难度。网络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平台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深入人心的“博客热”还未消散时,“微博热”已经在网民中火了起来,如今网络媒体已经发展成为以“两微一端”为主的多种社交媒体融合发展的格局。其次,网络社交媒体的多样性拓宽了网民参与利益表达的渠道,丰富了网民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而网络社交媒体还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它们属于不同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司管理的网络社交媒体必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其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必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效益的实现”[2],并且,在实际传播中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媒体的控制权一旦被特定的利益集团所掌握,这时的媒体必然具有一定的利益倾向性,当这种倾向背离了主流意识形态时,就会影响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最后,网络媒体的多样性往往伴随着网络信息的复杂性,网络谣言的传播往往经过多种途径转换,这给政府追踪、查询谣言制造者带来了困难,也必然影响政府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管控。
(二)网落群体的复杂性增加了治理难度
根据2017年6月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目前中国网民规模已达7.51亿人,伴随着网民规模的迅速扩大而产生的后果是网民群体的复杂性。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是,作为网络主体的网民却是客观存在的人,其被现实社会所包容,网络只是虚化人格的存在,他们在网络上的活动仍然是基于自身的社会现实利益而进行的。而网络群体则是网民在网络中自发形成的,其形成基础是群体中的网民具有一定的思想共识,实质是基于共同的社会现实利益。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存在严重分化,这直接导致了网络群体的复杂性。网络群体的复杂性必然给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增加难度,其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群体的复杂性带来的是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在多种利益诉求下很难找到平衡点。网络相当于社会利益的放大器,给各种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在现实社会中缺乏表达渠道或者诉求未满足的个人必然会选择在网络上表达,使得网络上的声音纷繁复杂,主流声音被削弱而不利于治理。另一方面,群体的复杂性带来的是价值观的复杂性。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由于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必然会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并产生出不同的意识形态。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催生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诉求,多样化的价值观必然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3]。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能有一种,而作为社会基础的群体,其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则必然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开放的网络把这种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在虚拟社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多种声音的出现必然影响主流声音的发出,而个人在群体中往往具有麻木性和失去主体意识,这就更是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难度。
(三)虚拟社会的开放性增加了风险程度
互联网带给网民极大的自由权,便捷的互动以及身份的虚拟都间接保障了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自由。网络社会是虚拟社会,每个网民都可以借助虚拟的身份在网络空间中生存,他们摒弃了现实社会的身份关系。身份在现实社会中是个人的象征,它是个人在现实社会的通行证,虽然限制了个人的自由表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人性恶的一面。而虚拟社会则没有这些限制,它使网民表现自我的欲望得到极大的满足,也使人性恶的一面在自我以及他人的诱导下得到充分展现。“近年来,从公安机关破获的众多案件中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大V’‘公知’‘意见领袖’实际上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培育的舆论代理人。互联网和舆论代理人的结合使得意识形态渗透风险不断增加。”[4]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虚拟社会高度开放的基础之上,网民身份的虚拟性掩盖了他们的现实身份,使得他们失去了现实规则的限制。从根本上说,西方社会所培育的舆论代理人正是借助了虚拟社会高度开放性这一特征,掩盖自己的现实身份,积极在网络上制造杂音,诱导网民进行感性思考,极大地提升了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程度。
二、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意识形态分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说到底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其论战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追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变过程,意识形态争论是其产生的基本条件,体现为利益观念的不统一;西方话语的诱导是其演化失衡的主要原因,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变过程极易受到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西方话语的诱导;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是平息争论的重要手段,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引导力和凝聚力,因此,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能够统一不同的意见,实现和谐共处。
(一)事件产生:意识形态争论的产物
“网络凭借着其简单、便捷、匿名等特点,轻易就能召集起大量网民,聚集起海量的、具有明显偏向性的民意,成为了群体性事件的策源地。”[5]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也逐渐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其影响的范围日益扩大、程度日益加深。追根溯源,是海量的、具有明显偏向性的“民意”引起群体性事件,而这种“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一特定社会利益阶层的意识形态表现。在网络世界中,人们可以对信息进行选择,看自己喜欢看的信息,了解和自己价值观相符的意见,并可以对所关注的事物进行自我视角的评价。总的来说,网络的虚拟性极大地增强了网民参与政治的自主性,以及自我选择、自我表达的自由性。但我们也可以认知,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各方所表达的意见也必然是他们的自我选择。个人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他们在网络中的自我选择必然受社会现实的影响,受本阶层的利益关系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思想观念上突出表现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各种观念的集合,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各方在网络上聚集的海量声音必然是代表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讲,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由各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引起的。
(二)演化失衡: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诱导
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初是各种利益观念的表达,这种表达还不具有破坏性,随着事件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开始介入其中,借助其培育的舆论代理人所具有的影响力诱使网民的意见表达开始转向,逐渐呈现出破坏性趋势。在事件的演变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所培育的舆论代理人不断利用互联网技术设置媒介议程、引导网络舆论等,将西方的价值观不断灌输给广大网民,使网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西方的话语表达。在网络空间中,争夺话语的主导权十分重要,由于首因效应的作用,人们对事物的态度总是偏向最先获知的信息,而西方社会占据着话语的优势地位,往往能争夺到事件的首先发布权,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态度传递给网民,使网民深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因而使其价值取向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在现实社会中,西方社会从未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而网络群体性事件则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巨大,西方敌对势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不断在其中发出他们的声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往往带有突发性,但这种突发性又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某种利益支撑,使其更具有不可控性。加之政府的监管不可能面面俱到,使得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有缝可钻,不断在网络空间中诱导网民对事件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使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失控。
(三)恢复平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经过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诱导,虽然会偏离一定的价值取向,但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并不会放弃这块阵地,两者之间必然产生论战,而这场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发的论战说到底其本质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从表面上看,论战的开展是我国民主政治推进的结果,但很多观点已经不限于突发事件解决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不是单纯的网民不满情绪的发泄,而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有的甚至高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否定政府的正确做法[6]。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从矛盾事件逐步演化为意识形态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掩匿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使网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逐渐认可非主流的意识形态观点。这时就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作用,控制网络舆论的走向,消除价值分歧,形成思想共识。网络群体性事件说到底是现实社会的矛盾在网络空间中的呈现,要使其恢复平息就需要从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同时入手。首先在现实社会中通过与矛盾方的协商切实化解利益冲突,使其丧失再传播的现实基础;其次,要加强网络空间中的正面舆论宣传,增强主流声音,不回避问题,切实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策略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局部体现,主要体现在网络治理的意识形态方面,它需要主流声音的传播,需要现实利益的平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变具有现实利益支撑,其背后是多种意识形态观念之争。为了有效管控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需要搭建好主流平台,传播好主流声音;积极培育意见领袖,敢于主动抢夺话语权;加强网络立法,为其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一)搭建主流平台,传播主流声音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网民接触和传播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但在当前的网络话语平台上,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网络话语表达的回应机制,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7]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解决之道是矛盾各方的利益协商,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实现利益平衡。其中,弱势方的利益表达回应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双方达成共识的前提。只有互相知晓对方的意图才能真正协商,因此,有必要搭建网络平台进行有效的回应。首先,搭建意见发表平台,为弱势群体一方提供利益表达之地,并将意见表达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其次,搭建网络协商平台,为矛盾双方提供协商场所,通过矛盾双方的有效互动,逐步形成利益共识,为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奠定基础;最后,搭建宣传回应平台,主流平台的搭建也是为贯彻网络群众路线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政府通过网络平台增强主流声音的传播,通过话语加工真实、有效地传递事件的缘由和发展脉络,不回避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网民所关注的矛盾焦点,用真实的主流声音掩盖刺耳的嘈杂声,使网络话语的发展趋向和谐。由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是话语失衡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主流平台的搭建重新掌握话语权,用主流声音去恢复平息和消除话语分歧,使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呈现的话语趋向主流。
(二)培育意见领袖,敢于主动亮剑
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和便捷性等特点给网民提供了快速获取信息的条件,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和信息受众增加,人们不再处于信息的盲区,但由于信息的复杂性使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只是冰山一角,因此,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尤为重要。所谓意见领袖,是指在网络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评论,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其在网络信息传播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对舆情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中,要重视培育意见领袖,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一是加强对已有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意见领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二是做好新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培育工作,培育一批政治觉悟高、理论修养好,懂网络、会用网络的专业人才,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队伍;三是做好意见领袖的选育工作,网络发展瞬息万变,意见领袖必须要跟上网络发展的步伐,紧跟时代练好基本功,加强业务学习,增强网络意识。意见领袖不仅要培育好,还要敢于主动发出声音,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初见端倪的时候,意见领袖要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用最真实的声音回应广大网民,扩大正面音、削弱负面音,让主流声音占领网络空间,加强舆论引导。
(三)加强网络立法,提供法律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8]。由于网民身份的虚拟性,现实社会的道德约束力在网络空间中普遍被削弱,这使得网络空间治理尤其需要法治建设的支撑。首先,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相关部门要积极推动网络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网络管理部门能依法执法和网民能依法上网,确保网络空间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其次,要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依法管理,互联网企业作为推动网络空间发展的主体,其直接管理着网络平台。做好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工作,有助于管控网络舆论发展的平台和源头,通过引导相关企业增强责任意识,能有效避免负面信息的发酵。最后,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在当前情况下,建设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道德机制,要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建立对道德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制度,从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共同避免网络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