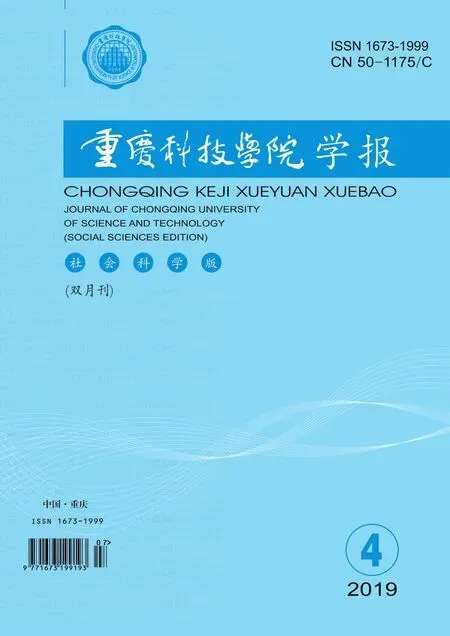试析小说《赎罪》中的现代婚姻伦理困境
陶丽丽
英国当代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自2001年问世以来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先建构后瓦解”“将历史、真实、虚构穿插交织”[1]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模式之下,小说围绕二战前后英国“奥斯汀式”庄园里一个中产家庭的爱情与婚姻故事展开,呈现了一部20世纪的“乡间庄园小说”[2]。在非线性及多重叙事主体交织的叙事中,书写了女作家布里奥妮·塔利斯追悔少年时作伪证指控罗比强奸而断送了罗比和姐姐幸福人生的故事。小说以“赎罪”为主题,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爱情与婚姻观的历史流变。婚姻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组织的重要方式,除了是社会学和法律概念外,也是重要的伦理概念,更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3]85,“婚姻的基础是道德与伦理,情感是婚姻结合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4]。解构《赎罪》中没有爱情的婚姻——塔利斯夫妇的婚姻和马歇尔夫妇的婚姻,以及没有婚姻的爱情——罗比与塞西莉亚的婚姻,分析两种爱情悲剧带来的婚姻伦理困境,有助于探索婚姻伦理选择的密码。
一、男性“缺失”的夫妻伦理关系
夫妻的两性伦理关系是婚姻状况的主要内容。塔利斯家的夫妻关系没有温情,婚姻状况糟糕。首先,杰克的常年“缺席”导致家庭秩序的混乱与丧失。塔利斯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通常意义上,“杰克是这个家的保护人,守护着这个家的宁静”[5]125,但他始终没有回归家庭,而是仅存在于人们的谈话、感知或琐碎的意识联想中。两人的互动仅局限于电话里的只言片语,试图掩盖夫妻关系的破裂和婚外情。男主人常年缺席不仅破坏了夫妻情感,也使受挫的艾米莉无法进行正常的家庭事务管理。家庭权威的丧失,使她无法得到女仆的敬畏,连晚餐做烤土豆还是土豆沙拉的简单日常问题都遭到“惊心动魄”[5]87的挑战。艾米莉在家庭秩序构建中再次受挫,家庭伦理关系不再和谐。丈夫角色的缺失,使家庭秩序失去了监督和监管,因而才会产生双胞胎离席、罗拉遭强奸、罗比遭布里奥妮诬陷成为替罪羊等一系列伦理秩序被颠覆的情况。 因为在传统意义上,“男人是家长”[3]89,能够有效地建构家庭秩序。正如布里奥妮的描述,即使不下任何命令,父亲也能不怒自威,父亲的在场,会使家庭秩序化变得轻而易举。不幸的是,男主人的长期缺席使家庭关系产生裂痕,使妻子处于无助和崩溃的边缘,从而导致传统伦理秩序的土崩瓦解。
其次,杰克的“婚外情”使婚姻内的爱情缺失,导致了情感绝望与婚姻困境。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夫妻原本应该互爱、互敬、互信、互学、互助、互让、互慰、互谅、互勉,从而共同担负起维护家庭共同体的责任”,而“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健全的、幸福的婚姻”[6]。杰克的长期缺席打破了传统的婚姻模式,使婚姻变成了“孩子没有父亲疼,妻子没有丈夫爱”[5]123的状态。因为感情出轨破坏了婚姻的基本要求即一夫一妻制,丧失了婚姻的“真理性和真挚性”[3]90,夫妻间爱情的纽带撕裂了,婚姻的基础也就丧失了。勉强维持的婚姻只能依靠人际交往中一些“常用的虚伪之道”,处于“表面的维持”状态[5]123。 感情受伤的艾米莉还没有勇气打破习以为常的婚姻,并试图从“房子、花园……最重要的是孩子身上获得满足”[5]123。 然而,在“失爱的”婚姻中,努力维持的艾米莉因婚姻痛苦变得冷漠和麻木,看似平静的她却像飞蛾一样扑向光源,明知道最终“会被吞噬”,但“不得不听命于本能的驱使,在光亮的另一头寻找最为黑暗的地方”[5]124,在无助与无奈中慢慢地走向自我的精神涅槃。作品采用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式的意识流写作手法,通过她常年犯头疼病,静卧在床却不能入眠的敏感神经展示了她的心灵创伤,揭开了她空虚、迷茫、无奈、痛苦的内心世界,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与伦理关怀。婚外情导致的婚姻残缺给两性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与痛苦,表现了作家对传统婚姻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弱者地位的理解与同情。塔利斯夫妇的婚姻是不幸福、不健全的,男性沉浸在极端的个人主义、男性罗格斯中心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之中,致使婚姻中以爱情为基础的忠贞与互助的重要伦理意识和观念缺失,婚姻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从而导致了婚姻的伦理困境和选择。
二、情感“错位”的亲子伦理关系
塔利斯家的婚姻伦理模式,不仅使女性受到了伤害,还影响了亲子关系。“家庭中的子女有被抚养和受教育的权利”[3]88,父母应该“在儿童心中培养伦理原则”,使“他们在父母的爱和信任的环境中逐渐成长”,“使子女逐步摆脱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并日益强大起来”[3]89。缺席的杰克逃避了养育子女的职责。迷恋秩序、顺从秩序的小女儿布里奥妮只有13岁,她按照男权文化秩序的构建,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在男性身上,对现实世界秩序的构建却缺乏实际经验。她终日沉浸在文学想象中不能自拔,用“稚嫩的非黑即白的是非观”[7]创作单一化、脸谱化的戏剧形象,并像自己剧本中的女主人公最终需要一位王子来拯救她的磨难一样,期盼男性角色对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但在现实中永远缺席的父亲却连基本的亲子情感沟通都做不到,父爱变得陌生而荒芜。
一般来说,当父亲失职时,母亲就会被迫担当起维护家庭秩序的“隐形父亲”角色,可是艾米莉却并不胜任。“不是闹偏头疼,就是非常冷漠,甚至不通情理”[5]18的母亲常年卧床休息,不仅不能亲力亲为家庭事务,而且沉迷于丈夫出轨带给她的苦楚与困境,不能设身处地为子女着想,并经常误读子女的所作所为,母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彼此的失望越来越多,连“亲密地说说话”[5]18的机会都丧失了。由于父爱母爱的双双缺失,因此,亲子关系就变得既疏离又冷漠。
在这样的家庭中,年幼的布里奥妮必然会在心理上寻找替代性的“母亲”和“父亲”,造成家庭伦理关系错位的现象。由于与已经成年的姐姐塞西莉亚和洗衣女仆的儿子罗比常年生活在一起,感情深厚,布里奥妮把两人看成了自己精神上的父母。男性角色的缺失使陪伴自己成长的罗比在她心里形象高大,值得依靠,充当了她“陪伴型”“保护型”的精神父兄角色。他们关系亲密而自然,从8岁开始,布里奥妮就喋喋不休地向他倾诉,甚至还拉着罗比的手。10岁时去跟罗比学游泳,布里奥妮甚至为了看到罗比舍身救她,任性地跳入了水池。尽管遭到了罗比的怒斥,她依然开心于罗比对自己的关心与照顾。布里奥妮对罗比的情感达到了完全信赖的程度,连生命都可以托付给他。童年的布里奥妮对成年的罗比这种毫无保留的情感依恋,是把他看作生命中最亲密的男性角色,精神上的“替身”父兄,不容许别人干涉与抢夺。所以,13岁的布里奥妮偷看罗比写给姐姐的“色情”情书时,“她惊呆了,不仅仅被信中的某一用词”[5]196使她感到害怕,害怕失去“替身父亲”的情感寄托。对罗比错位的爱使她感到受了欺骗与背叛,面对情感误读和情感焦虑的困境,在怨恨与冲动之下将他诬告为强奸表姐的凶手,铸成了悔恨终身、难以赎罪的大错。尽管后来布里奥妮也试图找回长久、冷漠的“父爱”,但是,她的努力失败了,除了在电话里“接到了一个让人心底燃起希望的鼻音”,再也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沟通与帮助。父爱的疏导永远缺席,最终在婚姻伦理困境中,错位的情感酿成了“不可饶恕”的悲剧。
除了父亲的失职,母亲对孩子也放任自流,姐姐事实上担当了“隐形母亲”的角色。塞西莉亚对家庭的态度是矛盾的,由于父母的原因,她对家庭很失望,可同时又对家庭异常迷恋,因为她明白自己在家庭中“隐形母亲”的职责。塞西莉亚“告诉自己,她是为了布里奥妮才留下来的,或者为了帮帮母亲”[5]19,这使她成为了家庭里的“精神”女主人。每天,塞西莉亚除了阅读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外,还试图整理出父亲这一支的家谱,这说明她不仅维护传统的完美女性形象和美德,还努力维持父系秩序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并在心理上试图成为传统女性的代言人。事实上,她关心照顾妹妹,从小“就喜欢搂抱这个家中的宝宝”[5]36,会在夜晚来到布里奥妮的房间,叫醒噩梦中的妹妹,把她抱到自己床上去;她会安慰妹妹,当她哭泣生气发脾气的时候,用爱抚和亲切的言语帮布里奥妮解决问题,并不止一次地“把布里奥妮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回来”,姐妹间的日常互动超出了寻常的姐妹情。而且,塞西莉亚还替母亲照顾表姐弟,当母亲和仆人之间出现争吵时,她及时并有技巧地解决他们的争端和化解危机。可以说,在父母之爱荒芜的情况下,长女塞西莉亚勇敢地承担了塔利斯家母亲和女主人的双重职责。可见,父爱的缺失使“替身”父亲深陷伦理悲剧之中,母爱的残缺也会促使“替身”母亲的出现,在婚姻中产生父母伦理失范和亲子关系疏离的现象,最终导致家庭伦理关系的错位与迷失。
三、价值“异化”的婚姻伦理观念
20世纪上半期,典型的英国中产家庭陷入了婚姻伦理困境的泥沼:家庭形态与传统家庭有所不同,家庭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运作模式、传统角色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伦理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缺失与疏离,可以说是传统婚姻的“失败”例证。马歇尔和罗拉的婚姻却与此相反,是一段“社会公认的长久而成功的婚姻”[8],具有讽刺意味。
罗拉作为强暴案的受害者与强暴罪犯马歇尔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直到年老依然夫妇相随,活跃在上流社会和慈善界,他们作为勋爵和勋爵夫人成为了社会的楷模与榜样。这种隐藏了罪恶秘密的结合,与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大不相同,反而成就了“成功”的婚姻,表现了现代婚姻价值的荒诞。首先,他们的婚姻以掩盖马歇尔的“罪恶”为基础。与罗拉结婚,马歇尔从性侵者身份转变为丈夫身份,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罪恶,相反,成为他掩盖罪行和违反司法公正的另一场阴谋和罪行。他们的结合意味达成了不正当的利益联盟,婚后无论罗拉是否了解马歇尔的犯罪真相,但作为妻子也不会向自己的丈夫提起“性侵”诉讼,这就掩盖了事实真相。其次,他们的婚姻是罗拉虚伪和势利的产物。过早精明成熟的“受害人”罗拉,并不是单纯的不知情者。当布里奥妮不请自来,独自来参加她与马歇尔在教堂的婚礼时,罗拉无意间瞥见布里奥妮时,在目光交接瞬间的条件反射是“颦眉”以待,“脸上分明闪过一丝不悦”“撅了撅嘴,将目光投向前方,然后,走了”[5]278。 这些不满和不快的心理反应,暗示了她对强暴案件的知情与隐匿,以及她促成这桩违背伦理道德婚姻的主观愿意。因为案发当年,“罗拉肩上和马歇尔的脸上抓痕累累”[5]276,证据明显,“罗拉(却)一脸沉默,让那热切、滑稽、古板、连现实与她脑中的故事都不能分辨的表妹送施暴者安全脱身”[5]276。在某种程度上,马歇尔、罗拉和布里奥妮三人“无声密谋,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了监狱”[5]277。在这场闹剧中,年轻的罗拉受物欲横流、享乐主义盛行的英国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影响,早就学会了审时度势,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选择了走进马歇尔的“名利场”,因为奢华的生活满足了她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最后,他们的婚姻还是一个利益联盟。联盟中的罗拉当年没有揭发马歇尔,婚后更不会还原或者澄清当年的事件真相,毕竟,对抗马歇尔并不能给她带来更多的利益。而且,“家庭中的每个成员的个别需求(在婚后)就会转变成共同的需求,进而家庭成员就会关怀这一共同体”[3]89,有权有势的马歇尔夫妇作为婚姻共同体,分享了共同的社会名声,“他们不惜血本,坚决捍卫自己良好的声誉”[5]317,所以,被诬陷的罗比冤屈难伸,最终,“只有马歇尔与他的新娘知道最初的真相,早就被稳妥地围筑在他们婚姻的陵墓里了”[5]277。强暴者与被强暴者不顾蒙冤者的死活,他们勾结在一起,在这场以罪恶、虚伪和利益为基础的婚姻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彻底被颠覆,伦理道德尽失,却成为了“理想”婚姻的代言,反映了二战后社会变迁中伦理道德观的异化与荒诞。
悲剧的是,无论是牢狱之灾还是战争磨难都不能摧毁塞西莉亚和罗比的爱情,但是,他们却丧生于战争而不能结合。这使布里奥妮连赎罪的最后机会都丧失了,倍感遗憾的她在垂垂老矣时渴望看到“罗比和塞西莉亚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5]319。残酷的现实和无声的哀怨道出了20世纪英国社会的婚姻伦理价值观的虚无与困惑。
四、结语
《赎罪》清晰而真实地展现了20世纪英国社会的婚姻伦理困境与价值选择,发人深思。解构《赎罪》中的婚姻伦理现象和观念,对探讨两性婚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的婚姻关系有利于子女的健康伦理身份建构,而婚姻伦理的丧失则会带来精神的危机、人性弱点的暴露和罪恶的难赎。作品中隐匿着许多复杂的情感,“赎罪”主题不仅仅是指布里奥妮诬告罗比的“罪”难赎,也不仅仅是大规模战争的毁灭性之“罪”难赎,更包括婚姻伦理失范和变异之“罪”难赎。对待新时代的婚姻伦理困境,或许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摆脱束缚,以增强实质性的新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