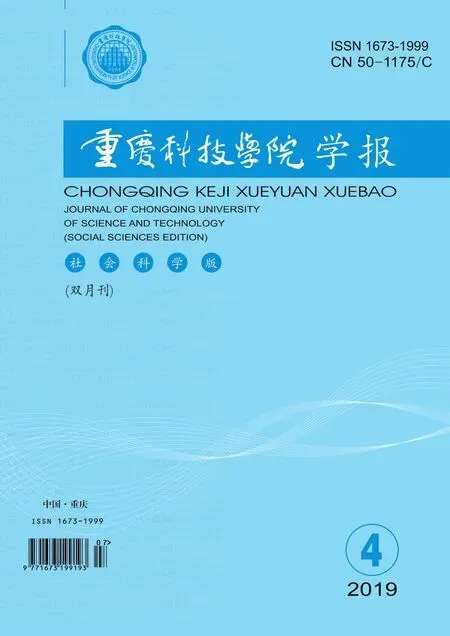论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择偶空间
刘玉梅,方莎
简·奥斯汀的小说往往与女性主义、女性意识、婚姻观、道德观等关键词相关联。现实主义成为了奥斯汀作品的代名词。奥斯汀的小说在她所处的时代盛极一时,无人能够取代,迎合了人们的时代心理,符合当时的婚恋、道德、风尚等标准。婚姻是必然之事的观点盛行于当时的英国社会,正如《傲慢与偏见》的开篇语所说:“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1]1因为“一个没有相当年纪或者足够好的、或者没有资历的女性来管理家务的家庭是不幸的”[2]18。对于现实中仍然附庸于男性的女性,婚姻和家庭是她们的唯一出路和能够经营的唯一事业,择偶也就成了影响女性一生的事业,理想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是衡量她们成功的标准。奥斯汀的作品正是在当时的历史、社会和宗教维度下,把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开放与保守、理性与浪漫共存的择偶标准、坚固壁垒式而又充满功利流动的择偶圈子和受理性运动支配的择偶场所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是一个体现不列颠式的贵族精神的时代空间。
一、择偶标准:理性的开放与浪漫的保守
“门当户对”一向是贵族维持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经济实力,缔结政治同门的重要社会标准。早在7世纪,教会贵族的出现,排他性就是贵族圈子的显著特征:他们修建城堡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来;他们生活奢华,把自己和其他阶层区别开来;他们蔑视其他阶层的人群,把社交圈子局限在本阶层。在英国的历史长河中,贵族一直为自己与生俱来的“蓝血”骄傲,为维持自己在上层社会的物质和社会地位处心积虑。在这历史的长河中,贵族父母和长辈成了年轻一代婚恋的“把关者”。《傲慢与偏见》中的凯瑟琳姨妈百般阻挠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傲慢地对待伊丽莎白,不择手段地撮合自己女儿和达西的婚姻。《理智与情感》中的费拉斯太太始终从财产继承权的赋予上掌控着自己两个儿子的情感和婚姻的抉择,最终因爱德华要迎娶地位卑微的露西而愤怒地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在《爱玛》中更是没有一桩超越门第的婚姻,私生女哈丽特最终嫁给了富有的佃农罗伯特,乡绅的女儿爱玛嫁给了富有的地方法官奈特利,继子弗兰克娶了同样寄养于上校家庭的费尔法克斯。
然而,自16世纪清教运动后,妇女地位问题已经被占当时英国人口一半的女性所关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促使妇女在陈情书中提到了“男女精神平等”。妇女在这个战争年代有机会摆脱丈夫的束缚,较自由地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生产,使她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快乐[3]。19世纪早期席卷英国的福音运动形成了与整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女性至上”非常相似的女性观:女性具有高于男性的道德水平,要求她们成为家庭以及社会的道德航标。从此,女性至少在精神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甚至高于男性的地位。同时,开始于18世纪末,由欧洲工人阶级发起的“浪漫的革命”在19世纪初向各阶层和整个社会传播。奥斯汀的作品中也处处体现出凡是父母要求的“门当户对”终将输给“自由真爱的感情”。例如,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埃莉诺对爱德华爱情的坚持;简与宾利历经磨难重拾爱情;玛丽安认识到真正爱情的内涵,最终和布兰登上校结合在一起。幸福美满的结局是奥斯汀小说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奥斯汀小说盛极一时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不列颠式贵族的理性开放性气质在两性爱情的理性执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4]206。
虽然经历了一场国内革命,但是,不列颠贵族从未在19世纪中期以前失势。攀附权贵在英国历史上一直是国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就连资产阶级激进派理查德·科布登都哀叹“我们是一个奴性十足的眷恋贵族制度并受贵族驾驭的民族”。尊贵、时髦、闲适是上流社会的代名词,追求财富、权力和享乐是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社会风尚[5]。富商和乡绅虽然在财富上有了大量增长,但是,在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上仍然被排除在贵族圈子和上流社会之外。要得到贵族圈子的接受,与贵族通婚无疑是最快速的捷径。班内特一家虽然是乡绅出生,却因为没有儿子,按照当时的惯例法,财产在父亲去世后由家族同辈的男性表亲继承。通过嫁女跻身上流社会或者至少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也就成为了班内特一家的首要任务。富有的、年轻的单身贵族宾利成为择婿的首选;有雄厚财力的贵族太太作为靠山的表亲柯林斯将要继承家族财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财富积累的潜力都显而易见,也成为班内特太太给女儿们挑中的如意郎君之一。贵族的财富和魅力更是在莉迪亚和威克姆的私奔事件中得到展现。失去了家族的财富,但拥有贵族血统的露西为了重新进入令人羡慕的贵族圈子,一向削尖脑袋要嫁给一位既有财富又有地位的真正贵族。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社会道德底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唯利是图的导向愈发明显。同时,福音运动和浪漫革命更使适婚青年渴望信任和需要幸福,从而导致了爱情与金钱、浪漫与门第、幸福与物质的交锋成为了奥斯汀小说的创作素材。不难看出奥斯汀坚持的是物质、地位、爱情三者皆得的婚姻幸福观,除这三者之外,其他择偶因素如相貌、年龄、健康和性格等都微乎其微。例如,夏洛特选择了相貌平庸、身材矮小、性格执拗的柯林斯;痴心的埃莉诺最终守候得到了体质虚弱、性格懦弱的爱德华;玛丽安最终嫁给了比自己年龄大上一轮的布兰登上校。在所有的幸福婚姻中,男性无一例外都非常富足,或者足以养家。女性都不必为物质生活奔波,与自己的伴侣都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她们能够互爱、尊重、理解,相互支持,与自己的伴侣对婚姻幸福的标准有共同的认知或者最终达成了共识。可见,奥斯汀身处当时的历史环境,她不可能跳出幸福的婚姻是由爱情和财产共同构成的观念[6]。女性在择偶过程中一味强调爱情或者异性的性吸引是危险和不幸的[2]46,玛丽安和莉迪亚就是典型的例证。这无疑正是福音派所提倡的所谓“道德盔甲”——女性贞洁至上,男性生殖器是“撒旦看得见的肉欲大本营”,性行为有罪的教义的体现[7]。它充分体现了英国从17世纪至19世纪初婚姻标准的实质——披着浪漫和真爱外衣的世俗保守。
二、择偶圈子:往上层社会去的“好女孩”
近代英国贵族群体是一个身份意识非常强的圈子。为保持群体身份的纯洁,“门当户对”的婚姻尤其重要。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男性贵族尤其是长子的婚姻往往担负着维持家族地位和光大门楣的重任。因此,他们的婚配对象往往首先考虑本圈子内的成员,女性贵族的想法颇为相似[4]286。奥斯汀小说中的女主角多出生于有世袭爵位的贵族、没落贵族或者乡绅家庭一类的中产阶级,因此,后两类按照“门当户对”这个亘古的原则,是要被排斥在贵族圈子之外的。《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和简就是小乡绅的女儿,显然不是达西和宾利恋爱成婚的首选对象。但是,无论是当时的福音派教旨,还是时下盛行的“银叉小说”都让人们笃信只有“好女孩”才能成为“好妻子”,无论她来自哪个阶层。“好女孩”除了美丽的容貌外,更重要的是得有贤淑的个性、坚强的理性、营造温馨家庭的能力、自我牺牲的精神,她们是家庭和社会的“道德风标”,男人的“精神归宿”[2]15。 “一位女孩的高尚行为就是缔结一门能增长家庭财富的美满婚姻,至于新郎的年龄、品质及知识才能都与亲事毫无关系。 ”[8]
为了让伊丽莎白和简顺利进入贵族圈子,奥斯汀刻画了一批来自不同阶层的“坏女孩”,伊丽莎白和简的妹妹们:放荡不羁的莉迪亚、跟着胡闹的基蒂、自恃有才却表现得愚蠢不堪的玛丽。她们无一不突破了当时“好女孩”“好妻子”应该恪守的底线——禁欲、无私、克己、审慎。因此,她们的情感结局都不尽如人意,或者嫁得不体面,或者擦肩如意婚姻,或者干脆没有获得任何男性的青睐。这些结局对于以婚姻为唯一出路、家庭为唯一事业的女性来说无疑是惨败的。伊丽莎白和简与自己的妹妹们相比,她们品貌出众;与宾利小姐相比,她们温柔体贴。她们的德行、品格、才貌超越了乡绅家庭的俗气,拥有贵族小姐所不具备的素质和品质,近乎完美地符合当时贵族对“好女孩”的衡量标准,因此能够打动贵族出生的达西和宾利,他们在贵族圈子里择得佳偶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跨越阶层等级的贵族择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以鲜明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为导向的时代,注定不能一帆风顺。“父权制和家长制直接影响着贵族子弟的婚姻,他们在包办婚姻中为子女挑选配偶的时候,只会考虑是否有利于家族爵位的提升,或者从经济利益出发,几乎完全忽视了子女的意愿和自由。”[9]50中产阶级则以贵族的悠闲生活为榜样,有着和贵族一样的婚恋观,因此攀附之风盛行,往往想要通过一桩婚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自己的阶层。无论是贵族还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爱情和婚姻,父母、朋友、长辈通常都不会作壁上观,而是通过帮助他们建立或者限制他们的社交圈,达到获得符合期待的婚姻的目的。例如,班内特太太一打听到附近搬来了一位每年收入有四五千磅的阔少爷时,便认为女儿们的福气来了,忙着催促班内特先生前去拜访,为女儿们提供接触贵族少爷,打入贵族圈子的好机会。凯瑟琳夫人在听到外甥达西与伊丽莎白私下订婚的传闻时,千里迢迢来到朗伯恩家谴责伊丽莎白,认为达西与自己的女儿才是“门当户对”的。
工业革命虽然把英国经济推上了世界首位,但是,肮脏的人际关系、卑劣的交易手段、虚伪堕落的道德等人性恶的一面也随着滋生蔓延。独自面对人性恶的男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渴求一个纯净、平静、融洽的家园。图佩尔描绘了一幅中产阶级家庭其乐融融的家庭图画:“他注视着他的孩子们,孩子们绽开笑颜……他的至交皆人中俊杰;他的府第一尘不染,洁净幽雅。”这是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男性理想的家庭生活图景[10]。男性对幸福家庭的期待决定了他们对婚姻伴侣的选择标准,同时也限制了在男性择偶标准之下女性的择偶圈子。这时日益流行的福音派信奉“幸福的家”的家庭观也因势利导地深入各个阶层的人心。因此,有能力为疲惫的男性营造融洽和睦的家庭氛围,胜任男性精神家园的女性更有可能突破阶级的限制而进入到上层社会男性的择偶圈子。反过来,这意味着“能力突出”的女性的择偶圈子也能够不断向上触及上层社会。例如,《理智与情感》中的露西无疑是一个典型,要想在上流社会中继续保持自己的一席之地,对于一位女孩来说只能是一桩理想的婚姻。她凭着娇美的容貌和精明的算计,先使罗伯特陷入了窘境,而后又解救了他。她在婆婆面前的恭顺谦卑、刻意殷勤和无止境的谄媚言行,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家庭天使”般的“好妻子”形象。使费拉斯太太对寄托着唯一希望的儿子选中这样一位妻子完全没有异议。这使罗伯特又重新成为了宠儿,获得了全部财产的继承权,露西也从一位没落的贵族小姐成为了真正的贵族夫人。
奥斯汀对由“门当户对”原则所限制的择偶圈子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往上层社会去”的乡绅思想决定了中产阶级以上社会阶层女性的择偶圈子是社会精英圈子的狭小范围,这同样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得到了丰富多彩的展现和浓墨重彩的刻画。但是,对于女性想要拥有符合家庭、朋友和自身期待的理想的择偶圈子,获得一桩幸福的婚姻,她必须是一位在时下标准中可以成为“好妻子”的“好女孩”。因此,在择偶圈子里,女性必须首先具有足够的理性,然后才能获得期待的情感。“在西方,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女人和孩子是感性的,男人是理性的,并且除了大脑,任何同感知和情感相关的事物,都被看作是没有必要的副产品。”[11]但是,奥斯汀笔下女性的择偶观几乎完全颠覆了这一认知。
三、择偶场所:阶层壁垒里的理性休闲和情感活跃
如果说奥斯汀小说中的择偶标准和择偶圈子是完全受英国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宗教革命、时尚小说的影响,是贵族坚守自身的社会地位需求的反映,那么,女性的择偶场所不仅是当时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理性、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和社交生活的展示台,更是身份、地位和社会风尚的标志。择偶场所是由择偶标准和择偶圈子决定的,实际就是为顺利实现一定标准下的择偶期待,集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特定空间。奥斯汀小说中的择偶场所通常有两类:较私密的家庭和本阶层专属的场所。单从分类就已经说明其极具个性化和排他性的特质。
奥斯汀的小说中,人们总是在盘算和期待一次次的家庭聚会和舞会从如何筹备、出席人员、活动内容等,甚至如何迎来送往、酒水食材、交流信息等细节都有十分到位的描写。家庭聚会耗资较大,如果再有舞会,那么就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负担的,家庭聚会和舞会本身就是对一种财力的展示和“门当户对”的说明,以及为择偶提供亲密交谈和交往的空间。班内特太太在宾利先生再次回到内色菲尔德庄园时就邀请他来家里吃便饭。这次家庭聚餐后,宾利先生和简又重新激发了爱意,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也再次重逢了。爱玛总是想在聚餐时,促成哈丽特和牧师埃尔顿的婚姻。弗兰克总在聚餐时,与费尔法克斯小姐暗中传情。约翰爵士夏天户外请客,冬天举办舞会,无疑要为年轻人寻求理想伴侣提供场所。舞会的舞池就是婚姻市场的核心地带[9]57。 《傲慢与偏见》中说:“喜欢跳舞是坠入爱河的必不可少的一步”[1]10。舞会上的言谈举止是评判一个人素养高低的重要参数。简和宾利先生的初次见面就是在舞会上,相互倾慕也是在当时的舞池里。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初次见面也是在舞会上,在舞会过程中达西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与伊丽莎白对贵族的偏见使他们之间的爱情一波三折,最终达西对伊丽莎白渐生爱慕之心。弗兰克和费尔法克斯默契优雅的舞姿,让他们的地下恋情表露无遗。女孩出入舞会由女性家长引领,表面上是礼仪,实际是为了直接把关女儿的婚恋对象。
弹琴、唱歌、阅读、闲聊常常作为餐后娱乐,让有择偶需求的年轻人进一步相互了解。她们也往往借此机会大展“才艺”,博取异性的注目。费尔法克斯高超的琴技和清亮的歌声获得了众多异性的青睐,弗兰克也因此对她无法自拔,甚至送钢琴表达情意。玛丽的琴声和歌声都让人感到乏味生厌,她因此被认定为是婚恋的困难户。柯林斯先生初次来到朗伯恩家,茶后被班内特先生邀请为太太小姐们朗诵。他选择的《布道集》内容正统刻板,朗诵的腔调单调呆板。柯林斯的无聊乏味,在让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被排除在姐妹们的择偶圈外了。然而,宾利的谈吐得体、举止得当,深受班内特一家的喜爱,深深打动了简和伊丽莎白。聚餐后的娱乐消遣在当时的中上层社会绝对不是随意而为,而是费尽心机的自我展现和潜心细致的相互观察。
狩猎刚开始是贵族专属的休闲活动,后来乡绅和地主也争相效仿[9]59。这是上层社会男子展示体魄、智慧和魅力的场所,但是,只有拥有相当土地者才可能开展这项活动。因此,狩猎场又是一个具有鲜明等级标志的择偶场所。宾利再次回到内色菲尔德庄园时,班内特太太邀请他到庄园来猎鸟,以此为大女儿简创造见面相处的机会。威洛比爱好打猎,还养有专门的猎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上层社会人士高贵的身份象征。而狩猎时的威洛比更有男子汉的魅力和风度,玛丽安为之倾倒。
乡村之所以能够成为择偶的重要场所,是因为在19世纪初,贵族大多都在乡村有自己的居所。直至1811年的人口普查,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伦敦[12]。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仍然不高,人们大多都居住在乡村。乡间宽阔的领地为贵族们的聚餐、舞会、散步、郊游、狩猎等提供了条件。另外,当时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中产阶级所遵循的生活宗旨与福音派的教旨都是以“理性”为核心,因此,中产阶级式的“理性休闲”,散步、阅读为传统贵族所接受。英格兰传统贵族也想以此来扭转在民众心目中的傲慢形象,但是,在这里最为方便、惬意的活动都以择偶为目的的社交形式存在是有阶级渊源的,因为择偶场所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就是尊贵的标志。它既是择偶标准下的择偶活动空间,具有私密性和专属性,也是理性主导下的情感活跃的空间。
四、结语
劳伦斯·斯通认为,在婚姻择偶的标准和动机上有四种形式:一是为了家族的经济政治巩固;二是强调个人感情、伴侣关系及友谊;三是性吸引;四是小说中及舞台上描述的浪漫爱情[13]。奥斯汀小说中提倡的五种形式涵盖了以上四种形式,那就是物质和爱情的完美结合。因为生活得体面优雅,以此区别于其他阶级,这是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对家庭幸福的成功人士的衡量标准。择偶标准决定择偶圈子,也决定择偶场所的择偶活动。由于择偶标准本身就是阶层理性的表达,因此,择偶圈子和择偶场所的择偶活动无论流露出多么真爱和热情洋溢,都不能离开历史背景下阶层的客观现实。因此,女性的择偶空间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并非只有浪漫,更多的是隐匿在浪漫爱情背后的道德束缚、阶层规约和宗教观念,从而注定女性从幼年开始就要接受相关的教育和面对成年人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