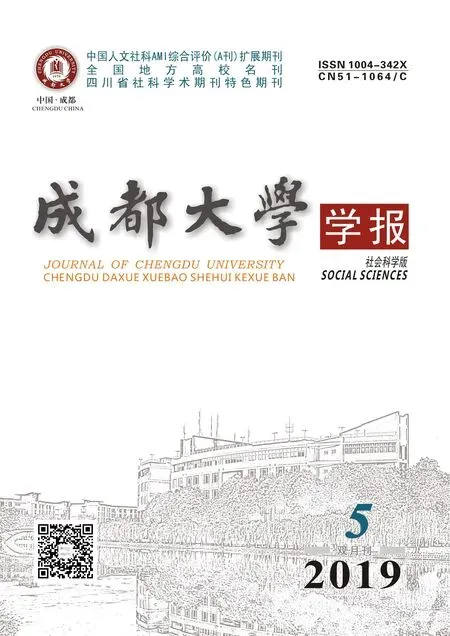《幽灵的困境》中双重他者的身份认同研究*
黄 坚 王冬方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5)
加纳著名的戏剧家、诗人、小说家和教育家阿玛·阿塔·艾杜曾旅居多国,其丰富的游学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众多素材。这位女性戏剧家一生致力于为加纳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民族自由解放发声。她不但关注泛非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还特别重视非洲妇女的自由平等、身份认同。在非洲传统文学中,尤其是对非洲文化再现以及对非洲传统妇女形象再造方面,艾杜有着重要贡献。“作为被殖民过的土地上的一员,艾杜的作品大多反映非洲世界观和西方世界观之间的对抗关系”[1]。早在大学时期,艾杜就出版了《幽灵的困境》[2]。凭借这部作品,她成为了非洲历史上首位出版剧作的女性。该剧讲述了一位非裔美籍女大学生尤拉莉亚毕业后满怀憧憬地与加纳籍丈夫阿托返回故土生活,却痛苦地发现自己无法融入阿托族人,成为“文化他者”的尴尬。“由于大多数后殖民论者本身大都来自第三世界,或者有着这样那样的第三世界背景和渊源……这些后殖民论者常常比白人知识分子有着更多地文化焦虑,更多地体悟到认同上的尴尬和痛楚。”[3]因此,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艾杜对黑人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境地可谓是感同身受,而《幽灵的困境》中女主人公的塑造恰恰反映了艾杜在面对双重“他者”身份困境时,对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思索与探究。
一、双重“他者”成因概述
“他者”这一概念的哲学渊源可追溯至柏拉图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论述。“在柏拉图哲学中,‘他者’被认为是具有从属性或次要性的低一级事物,即相对于‘存在’的‘非存在’。”[4]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中的“他者”概念主要源于萨特和黑格尔的阐述。在《存在与虚无》与《精神现象学》中,萨特和黑格尔均认为他者对自我意识的形成必不可少,且冲突对立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待他者的态度是冲突而不是对话。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他者”所“强调的是其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断、差异等特质,以显示其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5]。“他者”的存在既显示出了与“本土”的差异性,又成为“本土”的参照,并和“本土”形成互文的关系。
关于“他者”的属性,W.E.B杜波依斯曾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认为在美国的黑人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种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通过周围的充满轻蔑和同情的人群来衡量自己的灵魂的感觉。每个黑人都能感到他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黑人的二重性——每个黑人都有两个灵魂、两种思维、两种难以调和的竞争和在一个黑色躯体内的两种思想的斗争”[6]。根据杜波依斯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社会性和群体性导致“他者”问题的存在成为必然,而且“他者”属性的累加,即双重或多重他者性将给人的生活和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后果,而这恰恰是艾杜笔下尤拉莉亚的真实写照。她虽然生长在美国,但是黑皮肤注定她不能为白人主流社会所容。于是,她跟随丈夫去了非洲,认为自己能够在那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然而,女主人公特殊的身份、与族人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对族裔文化的不认可态度让她再一次成为了阿托族人排斥的“他者”。究其缘由,可归属为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差异。纵观人类发展史,殖民即意味着入侵和掠夺,给被殖民地人民带来的不仅是失去家园的悲伤和痛苦,更多的时候是残酷的杀戮和罪恶的奴隶贸易。“近代殖民主义最早窜入非洲大陆(1415年),几乎最晚退出这块大陆。然而在15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四百多年时间中……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运了至少1600万黑奴到美洲,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奴隶贩子。”[7]因为黄金矿藏丰富,加纳曾先后遭受过葡萄牙、荷兰及英国的侵略和殖民。加纳人民为反对殖民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艾杜的祖辈和父辈们被英国殖民者监禁,折磨甚至是残忍杀害……”[8]这样的悲惨遭遇是当时整个加纳人民命运的缩影。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背景影响下,老一辈加纳人民自然而然对来自西方世界的任何事物——即便是黑皮肤的尤拉莉亚,亦是抱着谨慎和不欢迎态度,视其为不同于加纳本地人的“他者”。
不仅如此,美国与加纳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也是造成尤拉莉亚成为双重“他者”的重要原因。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下,尤拉莉亚与阿托族人的相处举步维艰。她虽是非洲后裔,却自小接受了美国文化教育,对加纳文化一无所知。在多元的美国价值观中,“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个人是体现一切价值的中心和主体……从道义上来讲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9]。美国人的这种个人主义几乎贯穿在其文化风俗的各个方面,如婚俗、喜好、宗教、追求、权利、隐私、择业等。他们注重男女平等的权利,追求物质享受,注重个人感受,在婚姻与生育上遵从自我意愿,正如剧中女主人公在加纳生活时所追求和体现的一样。
反观剧中背景地加纳,情况却大相径庭。虽经历过较长的殖民统治,但传统习俗和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在老一辈加纳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以集体和部落文化为中心,认为每个人应当有自己的部落,无宗族之人就像“无根之树”;认为生育之事皆由上帝决定,而女人不能生育则是因为身边有邪灵,需要举行祭典活动并用汤药驱除;信奉家族中男性地位高于女性,象征着吉祥与尊贵的椅子一般会让男性就座;奉行婚姻是家族中的大事,通常由父母慎重决定并且隆重操办等等。很显然,美国文化及价值观与注重以集体、以部落文化为出发点的加纳文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些文化价值上的差异为尤拉莉亚与阿托族人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置身于非洲加纳却处处以美国文化价值观处事及生活的女主人公无时不刻地陷入到双重“他者”的尴尬:黑皮肤的她是美国白人眼中的他者;持异域文化观则让她成为了加纳族人眼中的他者。
二、迷失——双重他者不可避免的尴尬
虽然艾杜未多费笔墨描写尤拉莉亚在美国的境遇,但观众仍可以从第二幕女主人公与母亲冥冥之中的对话看出端倪。“约瑟夫、玛丽,最终我还是来到了非洲……我希望我所做的是对的。我将会在这儿生活得很开心啊!……不得不承认,这儿的一切都好可爱”。[2]初来乍到的尤拉莉亚坐在阶梯上啜着可乐,脑海里一个声音不知不觉地跳了出来。她记忆中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美国黑人只能生活在贫穷脏乱的黑人住宅区,他们喝不起可乐,她的母亲四处打工,以微薄的薪水供她上大学。总而言之,黑人群体的生活可谓举步维艰。
由于长期受到白人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压迫,相当一部分美国黑人开始屈服于白人文化并试图掩盖自己身上的黑色印记。“亲爱的,每当你清晨醒来看到镜中黑色的自己时,请不要责怪我和你爸爸。不要做那些傻女孩才会做的白日梦,期待着某个清晨醒来发现自己与那些好莱坞女郎一样,拥有着奶白的肌肤和柔软的金发。亲爱的,神圣的上帝给与了你黑色的躯体,你除了接受别无选择。”[2]尤拉莉亚母亲的这几句话看似是在安慰她,实则是对白色文化霸权的控诉。“生活在一个以白人文化占绝对优势、对黑人充满偏见和歧视的社会中,身份认同是黑人面临的最大挑战。”[10]由于受到白人文化的浸淫,不少黑人渴望改变,渴望由外到内被主流文化所接纳。然而无论怎么努力,黑人后代“置身于美国社会之内但同时又被排斥在美国以盎格鲁—萨克逊主流社会之外,这种若即若离的‘二重性’成为黑人身份认同最大的烦恼和困惑”[11]。
于是,迷惘于身份认同的尤拉莉亚寄希望于回到“根源之地”,期望在非洲找到合适的位置,获得身份认同。在剧本序幕中,她向丈夫阿托吐露了心声:“能够再次回归故土……当然,这是一件极其幸福之事……哇!那些棕榈树、蔚蓝的大海、阳光和金色的沙滩……”[2]而后她又独白道:“妈,我已经来到了根源之地。我已经回到了非洲,不管您在哪,我都希望您知道并能支持。”[2]这些表述无不体现了尤拉莉亚对非洲故土的向往。可实际情况却与她的憧憬相去甚远,因为她没有被当作族人来看待。
当阿托在第一幕中告知族人自己的婚事时,全族上下无一不震惊且难过。妈妈埃希责备自己没有管教好儿子,让他娶了一个白种女人;婶婶艾耶瑞也责怪阿托做的一切,认为自己族人对白人世界一无所知,接纳了这样一个外来者会遭到别人笑话。即使当阿托告诉族人尤拉莉亚并非白种人而是个在美国生活的非洲后裔,族人仍然沉浸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悲痛中。在与阿托族人相处的过程中,尤拉莉亚渐渐发现,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抽烟饮酒、用现代化机器协助做家务——这些在美国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方式也会遭致族人非议,就连因为采用现代避孕手段没有生育,也被族人误认为是邪灵缠身所致。在阿托族人的眼中,尤拉莉亚是无根之木,是来自白人世界的“他者”。于是,尤拉莉亚被奶奶称为“来自西方世界的奴隶的女儿”,被阿托姐姐曼卡称为“来自白人世界的尤物”,被村中妇女称为“陌生人和奴隶”或“怪异的女人”。如此种种,印证了尤拉莉亚的回归之路不会那么简单顺利。
同样,虽然尤拉莉亚期盼回到非洲,但深受白人文化侵蚀的她很难真正理解阿托家族并融入其中。剧中第二幕有这样一个场景:尤拉莉亚被阵阵鼓声吓得惊慌失措。由于缺乏对非洲音乐的了解,她误以为这是族人在追捕女巫时发出的号令。实际上,非洲的鼓声就如美国的爵士乐或西班牙的曼波音乐一样,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元素。由此可见,尤拉莉亚脑中储备的关于非洲的知识全来自于西方固有的认知。在第三幕中,母亲埃希来到儿子儿媳的住处,送上了在旱季极难找到的蜗牛。不明就里的尤拉莉亚称蜗牛为“可怕的生物”,打算扔掉这一在非洲人看来珍贵无比的礼物。当阿托质疑尤拉莉亚难道从来没见过蜗牛时,她反驳道:“亲爱的,在美国时,你可曾在纽约街头看到过这样一直在爬行的蜗牛?不管怎么说,看见蜗牛和吃蜗牛完全是两回事!”[2]此次事件深深地挫伤了婆婆,成为了日后她们产生矛盾的导火索。最终尤拉莉亚拒绝前往宗教感恩活动以及清晨饮酒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夫妻二人的激烈争吵,将剧情的发展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尤拉莉亚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及价值观与阿托族人所代表的非洲加纳文化及价值观相互碰撞是两者产生冲突的原因,那么尤拉莉亚在面对这种冲突时表现的态度则是加剧矛盾的重要因素。在与阿托家人见面过程中,她很少和族人主动接触和对话,一直都通过阿托传达,在与阿托交流时,她也频繁说出“非洲妇女”“一个美国人的方式”“本地男孩”“你的族人”等话语来区分自己与加纳族人。对于族裔举办的祭祖活动,尤拉莉亚虽未彻底否定,却也从神情和言语中表露出了不屑和厌恶。尤拉莉亚不顾阿托家庭负债累累的实情,刻意复制西方生活模式——喜好烟酒,购买各种昂贵的家用电器。当族人误以为她不能生育特地召开家族集会时,她因不满只有男人可以坐椅子的习俗而直接离场,留下了所有的族人在原地瞠目结舌。甚至在与阿托争吵时,尤拉莉亚将加纳称为“腐朽的土地”,说阿托的族人除了知道他们自己野蛮的习俗和标准之外,其他的什么也不懂……尤拉莉亚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和态度与她自己渴望回归非洲获得身份认同自相矛盾。
女主人公对身份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她“只能在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进行自己的身份认同,结果是身陷文化撕扯与身份焦虑之中。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而且不得不与白人主流文化相认同”[12]。白人文化对尤拉莉亚的思想和言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其全盘复制成了一个黑皮肤的“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尤拉莉亚与阿托族人在相处过程中矛盾冲突不断,渴望回归非洲找寻自我身份的她无所适从、痛苦不堪。
三、改变——双重他者的身份重构之路
如果说,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每位黑人的成长如影随形,那么谋求改变则是他们探寻并重建自我身份的必由之路。美国黑人尤拉莉亚在经历了身份模糊和不确定后,决定改变自己的处境。她选择嫁给“最黑的男孩”阿托并追随他回到黑人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开始真正接触和了解非洲族裔文化传统的内涵和精髓的举动,即是她努力探寻以及重建自我身份之路的开始。
尤拉莉亚无法避免与阿托族人相处时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对立。然而这种冲突对立也并非不能缓解与消除。事实上,她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尤拉莉亚扔掉婆婆准备的珍贵蜗牛这一事件中,若她肯改变态度,理解加纳食用蜗牛这一习俗,能在矛盾产生后主动安抚婆婆并向她解释这其中的文化差异,她们的冲突也不会进一步加深。面对族人们的祭祖活动以及族中只有男人能坐椅子这类传统,若尤拉莉亚能给予尊重,并予以认同,她和族人们的关系也会更近一步。
除了尤拉莉亚自身原因,阿托的态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作为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阿托,在面对妻子与族人的冲突时,多次犹豫不决、徘徊不定,并没有直接主动指出文化差异并解释差异性乃造成冲突的根源。而这无疑间接增加了尤拉莉亚回归族裔、重建自我身份的阻力。
消除文化对立并非易事。在经历了多次碰撞与磨合后,该剧演绎到了最后一幕。阿托与尤拉莉亚因教堂事件发生剧烈争吵后,各自负气离家出走。直到半夜阿托悲伤地回到母亲埃希住处,主动向她诉清他和妻子吵架的原因以及背后隐藏的种种误解。明事理的母亲对尤拉莉亚有了更多理解和认同,责备道:“我的儿子,在这件事上你没有处理好,没有给我们和你的妻子一个很好的交代。明天我将会把这一切告知你的祖母、叔叔和婶婶们……”[2]俩人言谈之际,尤拉莉亚也跌跌撞撞赶到现场。婆婆埃希看到尤拉莉亚后“赶紧冲上前去扶住”,并慈爱地称她为“我的孩子”,全然没有了当初的排斥。此时的尤拉莉亚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在主动来到阿托族裔的住处后,从来都不和族人直接接触的她在婆婆的搀扶下,顺从地走进了象征着黑人族裔文化的祖屋。
剧本到此已近尾声。艾杜虽并没有进一步描述尤拉莉亚与婆婆埃希进入族裔祖屋之后的情况,但两者的亲近之举无疑是一种暗示,象征着两种文化妥协甚至包容的开始。换言之,阿托族人对尤拉莉亚的逐步接受和后者从抵触到回归的过程,印证了文化冲突中“他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所持态度的重要性。
四、结语
艾杜通过塑造美国黑人女性尤拉莉亚这一戏剧人物,揭示了她在重返非洲故土生活时所遭遇的重重困境和身份认同尴尬,探讨了女主人公重建自我身份的必由之路。在她看来,重建自我身份需从转变态度和价值观开始。虽然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平坦,甚至充满着各种曲折和痛苦,但是正确的文化定位以及积极的态度能够帮助“他者”摆脱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尴尬,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获得群体的认可。这个过程不仅适用于黑人民族,同样也适用于在后殖民语境下遭受主流文化排挤而无法建构自我身份的其他少数族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