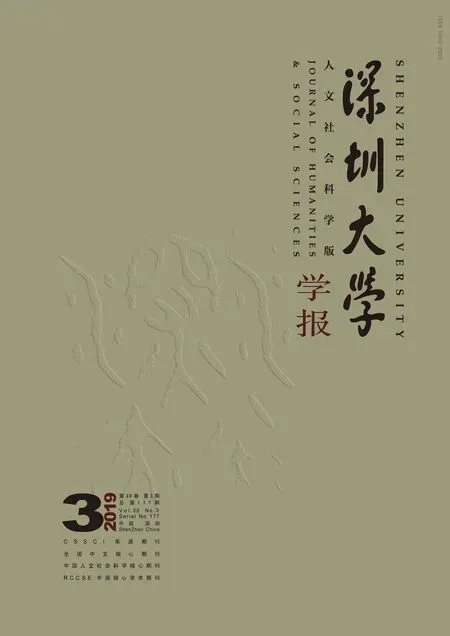太山遍雨:明清时期东亚国家“家礼”文献的刊刻与影响
彭卫民
(1.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2.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重庆 408100)
明代理学家邱濬在《文公家礼仪节》序言中说“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1]这意味着,对先王礼制的认知、运用乃至解释是区分“文明”与“蛮貊”、“华夏”与“夷狄”、“中心”与“周边”的重要标准①。明清之际,朱子学声教讫于四海。随着《家礼》一书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广为流布,华夏礼教文明以一种“太山遍雨、河润千里”的姿态泽及海外、辐射周边②,对东亚文明秩序、国家认同以及基层伦理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认为“礼让之厚,刑政之美,非他外国之所可及者,故中国之人皆以 ‘礼义之邦’称之,或以‘小中华’目之。此不同道而归于治也。”[2]日本强调“中国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夷狄亦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天宁有厚薄爱憎于其间?所以此道只是一贯。”[3]越南则宣称“同文之治,则有日本、朝鲜诸邦,而安南为尤盛。……略如中华,风俗所趋,蔚为文采。”[4](P44)这似乎意味着,东亚周边各区域间本土意识自我强化的过程与华夏礼教文明体系的东亚化具有某种内在的契合性。换言之,放眼明清时期整个东亚地区,华夏文明的“雨露均沾”、纲常道统的“四海一同”打破了以地缘与种族来划分“夷夏”身份的固化思维,文明播迁与吸收的过程必然导致族群主体意识涌动的后果。有鉴于此,本文重在考察“家礼”文献在明清之际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刊刻流传情况,初步讨论“四礼”学在东亚播迁过程中族群彼此认知认同以及周边国家在儒教文明的浸润之下如何建构自身礼法体系的问题。
一、明清中国:“家礼”卷次多样化与“礼俗共治”的格局
宋乾道己丑年(1169),朱熹为母丁忧,草成《家礼》的丧、葬、祭礼部分,后补足冠、昏礼,成五篇。朱熹死后,其门人后学将《家礼》加以注疏、校订、增补,刊刻出“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多种不分卷的版本,但这些版本都已散佚。后世学者将《家礼》的卷次、目次重新加以整理,区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等多种版本系统。在目前已知且存世的刊本中仅存两种宋刊本,即“五卷本”系统中的《宋刻杨注附图本》以及“十卷本”系统中的《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前者为“余杭本”与“广州本”基础上的翻刻本,卷首有门人黃榦 《书晦庵先生家礼》以及《木主全式》《程颐语》《潘时举识语》等,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刻钞配本,为存世孤本;后者即加入了门人杨复、刘垓孙的附、补注本,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该书的第三、第四卷,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第六、第七卷,上海图书馆藏有第五卷,亦为世所罕见的孤本。
明清之际,《家礼》一书被广为刊刻。其中“五卷本”系统中,有明刊《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清雍正十年(1732)寿昌讲堂(拙修斋)刊本、同治四年(1865)盱眙吴氏望三益斋刊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六年(1880)洪氏公善堂影宋本、光绪十七年(1891)长沙思贤讲舍刊郭嵩焘校订本、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三原西京《清麓丛书编本》(马杂货铺藏西安省城重刊本)等。“十卷本”系统中,有景泰元年(1450)金陵汤氏执中堂刊本、嘉庆六年(1801)重刊本、嘉庆十四年(1809)麟经阁重刊本、清通德堂重刊本等。“八卷本”系统中,有成化甲午(1474)邱濬序刊本、弘治三年(1490)顺德知县吴廷举刊本、正德十二年(1517)应天府、直隶太平府刻本、正德十三年(1518)常州府重刊本、嘉靖元年至五年间(1522-1526)广西刊本、陈锡仁重订《文公家礼仪节》本、嘉靖九年(1514)序刊本(天启、崇祯间刻本)、万历二十七年(1599)闽书林自新斋余明吴刻本、万历三十六年(1608)常州府推官钱时刊本、万历四十年(1612)刊本、万历四十六年(1618)何士晋刊本、康熙四十一年(1701)紫阳书院本、雍正元年(1723)善成堂书坊刊汪郊校刻本、乾隆十二年(1747)刊本、乾隆三十五年(1770)宝敕楼重修本、嘉庆元年(1796)重刊本、咸丰六年(1856)翻刻本、同治八年(1869)重刊本、光绪七年(1881)何国桢翻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江左书林影宋原刻本等。
明清时期中国“家礼”文献的著述形式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体现《家礼》典制化与国法化的文献,如《大明集礼》《大清通礼》《大清通礼品官士庶人丧礼传》《吾学录》等,这些官修礼书中所规定的婚丧祭礼体现了《家礼》的典章化,即通过国家权威来规定官民士庶人的礼仪规范。比如吴荣光在其《吾学录》中说,“荒陬辟壤于冠婚丧祭之礼,尚有沿前明之旧、徇时俗之陋者,盖以官民礼制,具载《大清会典》而卷帙浩繁,不能家有其书,以为率循之准。……取《大清会典》《通礼》《刑部律例》《五部则例》《学政全书》等书,于人心风俗之所关政教伦常之众者,手自节录。”[5]第二是理学家或汉学家对“四礼”的考订之学,如朱廷立的《家礼节要》、武先慎的《家礼集议》、毛奇龄的《丧礼吾说》、毛先舒的《丧礼杂录》、张履祥的《丧葬杂录》、王廷相的《丧礼备纂》、林伯桐的《士人家礼考》、张汝诚的《家礼会通》、赵执信的《礼俗权衡》、张大翎的《时俗丧祭便览》等③。清代考订之学大兴,礼学研究重在“三礼”的笺释,呈现出“以博为能,以复古为高”的特征,《家礼》似乎并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世不多行,学士亦往往不肯求观,而坊间所看率皆俗本,《丘氏仪节》尚难其得,是以无以正其是非。”[6]第三是民间社会刊行的日用类书,如《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新刻群书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等,这些类书所收录的诸如“冠礼指南”“婚礼附仪”“丧礼品节”“治丧仪制”“丧祭款式”等条目与仪节基本上全部沿袭自《家礼》。
明清礼学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是礼学家对经典的“群体失忆”或“沉默”造成的,但作为考订的礼学是普世而绝非仅仅是埋首故纸堆的学问,家礼研究便是明证。明清以来,关于家内仪式考订与发挥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礼学家们俱以所见、各记旧闻,至于各家、宗、族谱所载的冠昏丧祭程序与条目,更是不尽枚举。一方面,学者们素知礼学考证繁复,让蒙学之士开卷了然,仓促之间有所考据而无失尚且困难,更何况让贩夫走卒、乡野草莽之流本一家之说而通礼学精义,更需要反复揣测古经本义,才能有所发明。另一方面,明清之际的家礼学虽有司马光与朱熹之说为蓝本,但能做到确守家法而无一言出入者甚寡。学者们为求盖棺之论,为让各家尊己之说而反复考索、左右征引,最终反而使得家礼之学无头无绪、混乱不堪。且明清时期的家礼学已经抛弃了先秦“固所自尽”的基准,民俗多为僧侣诳诱,认为须世道轮回而大兴水陆道场,斥巨资开堂找僧演剧,宴请宾朋,使民风凋零而尽失哀丧本义。
二、李氏朝鲜:“家礼”研究体系化与“小中华”观的形成
韩国学者对“家礼”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以金长生《家礼辑览》、李縡《四礼便览》、李瀷《家礼疾书》等为代表的朝鲜礼书对《家礼》的学理阐释以及《家礼》在李氏朝鲜前、中、后期对国制的影响,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韩国所藏“家礼”文献的著录散见于 《镂板考》《古鲜册谱》《朝鲜图书解题》《五州衍文长笺散稿》等文献提要中。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看,韩国学者卢仁淑除考订《家礼》成书真伪外,并率先著录李氏朝鲜时期的“家礼”文献[7]。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张东宇在其《朝鲜时代的〈朱子家礼〉研究》一文中,详尽列举了 15~16世纪(合计62种,其中散佚31种)、17世纪(合计82种,其中散佚39种)、18世纪(合计97种,其中散佚42种)、19世纪(合计102种,其中散佚33种)的所有“家礼”研究成果总计 343种[8]。从文献集成的角度来看,庆星大学韩国学研究所于2011年编辑出版了《韩国礼学丛书》,该丛书分前(60卷48种)、中(62卷102种)、后(16卷22种)三编,分别收录李氏朝鲜不同时期的礼学汉籍总计138卷172种,这是迄今为止东亚礼学文献整理规模最庞大、收录种类最丰富的一项重要成果。
结合《韩国礼学丛书》已出书目中的“家礼”汉籍以及笔者的补遗,依刊行先后顺序,可将李氏朝鲜“家礼”文献(不含佚本)目录著录如下④:李孟宗《家礼增解》、李彦迪《奉先杂仪》、李滉《退溪先生丧祭礼问答》《溪书礼辑》、朴枝华《四礼集说》、宋翼弼《家礼注说》、李珥《祭仪钞》、金诚一《丧礼考证》《奉先诸规》、李德弘《家礼注解》、柳成龙《慎终录》《丧礼考证》、郑逑《五服沿革图》《寒冈先生四礼问答汇类》《五先生礼说分类》、申渫《仪礼考览》《丧礼通载》《五服通考》、申湜《家礼谚解》、曹好益《家礼考证》、金长生《家礼辑览》《家礼辑览图说》《丧礼备要》《疑礼问解》《疑礼问解拾遗》、张显光《丧礼手录》《旅轩先生礼说》、李恒福《四礼训蒙》《礼学纂要》、安泛《家礼附赘》、佚名《五礼仪抄》、李久澄《家礼疏义》、金尚宪《读礼随钞》、权得己《家礼僭疑》、金集 《疑礼问解续》《古今丧礼异同议》、姜硕期《疑礼问解》、李植《家礼剥解》、赵任道《奉先抄仪》、金应祖《四礼问答》、许穆《经礼类纂》、宋时烈《尤庵经礼问解》《尤庵先生礼说》、尹宣举《家礼源流》《家礼源流本末》、李惟樟《二先生礼说》、李益铨《礼疑答问分类》、李亮渊《丧祭辑笏》、尹拯《明斋先生疑礼问答》《丧祭礼遗书》、李爀《四礼纂说》、朴世采《南溪先生礼说》《六礼疑辑》《家礼要解》《三礼仪》《四礼仪》《祭仪正本》《四礼变节》、权以时《五礼辑略》、郑鍹《礼仪补遗》、权斗寅《礼仪补疑》、申梦参《家礼辑解》、俞相基《癸巳往复书》、柳庆辉《家礼辑说》、辛梦参《家礼增解》、李衡祥《家礼便考》《家礼或问》《家礼附录》、真一《释门家礼抄》、郑硕达《家礼或问》、郑万阳《改葬备要》、郑葵阳《疑礼通考》、南道振《礼书札记》、权万斗《四礼辑要》、权舜经《丧祭辑略》、徐昌载《冠礼考定》、李縡《四礼便览》《陶庵疑礼问解》、李瀷《星湖礼式》《星湖先生家礼疾书》、申近《疑礼类说》、边尚绥《礼仪讲录》、朴圣源《疑礼类辑》、安鼎福《家礼详解》《冠婚酌宜》、李周远《安陵世典》、俞彦集《五服名义》、金钟厚《家礼集考》、吴载能《礼疑类辑续编》、权思学《二礼辑略》、朴胤源《近斋礼说》、夏时赞《八礼节要》、丁若镛《丧礼外编》《丧礼四笺》、郑重器《家礼辑要》、沈宜德《家礼酌通》、洪直弼《梅山先生礼说》、佚名《先妣初终日记》、张锡愚《丧祭撮要》、朴宗乔《常变纂要》、卓钟佶《简礼汇纂》、金翊东《丧祭仪辑录》、金致珏《四礼常变纂要》、申锡愚《读礼录》、林应声《溪书礼辑》、任宪晦《全斋先生礼说》、崔祥纯《丧礼要解》、张福枢《家礼补疑》、李震相《四礼辑要》、姜鈗《丧祭辑要》、王德九《沧海家范》、李汇宁《退溪先生礼说类编》、安秉珣《四礼祝式》、黄泌《增补四礼便览》《悬吐详注丧祭类抄》、卢相益《退溪寒冈星湖三先生礼说类辑》、洪在宽《四礼要选》、韩锡斅《竹侨便览》、卢相稷《常体便览》《深衣考证》、金真斋《丧祭仪辑录》、宋来熙《礼疑问答》《礼疑问答四礼辨疑》、禹德麟《二礼祝式纂要》、金鼎柱《丧礼便览》、申泰钟《四礼常变纂要》、权必迪《常变辑略》、佚名《丧祭祝式》、佚名《四礼节要》、佚名《丧祭礼汇考》、郑基洛《家礼汇通》、佚名《丧礼备要抄》、都汉基《四礼节略》《冠服辑说》、郑载圭《四礼疑义或问》、李遂浩《四礼类会》、赵镇球《家礼证补》、李奎镇《广礼览》、朴珪寿《居家杂服考》、韩复行《古冠昏礼解》、绥山《广礼览》等。
《家礼》东传使得李氏朝鲜的礼学研究体系化、门派化,而这种经久不息的传承也支撑了李氏朝鲜“小中华”观的形成。目前已知最早传入朝鲜的《家礼》刊本应是辑于永乐十三年(1415)的《性理大全书》,该书第18卷至21卷收录了一部五卷本的《家礼》。此书大约在一百年之后传入朝鲜,朝鲜于中宗二十三年(1528)、中宗二十六年(1531)、中宗三十二年(1537)、仁祖二十一年(1644)、英祖二十年(1744)分别在庆州道、济州道、全州道等地对该书加以重刊。由于刊刻的频率与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官方与民间社会对《家礼》的需求,于是明宗十八年(1563)《家礼》得以从《性理大全书》中抽出加以单独刊行,此即朝鲜最早的《家礼》刊本——《家礼大全书》本。而最早传入朝鲜的《文公家礼仪节》应是正德十三年(1518)常州府刊本,这一刊本后于朝鲜明宗十年(1555)与仁祖四年(1626)在清州郡、灵光郡加以刊行。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家礼》在朝鲜的刊本应该还包括奎章阁藏明刊本、宣祖三十六年(1603)川谷书院本、孝宗九年(1658)三陟府刊本、朴世采《家礼》外编本、英祖三十五年(1759)艺阁校印本、西序书目草本、芸阁活字刻本、摛文院书目本、济州牧册板库抄本、正祖十九年(1795)官定铸本以及大正六年(1917)张焕舜校勘本等。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期,岭南礼学与畿湖礼学两大派系的性理学家们通过对丧、祭礼加以反复考辨,形成了“通论”(如《家礼辑览》《家礼考证》《家礼辑解》等)“诸先生礼说问答”(如《退溪先生丧祭礼问答》《寒冈先生四礼问答汇类》《五先生礼说分类》等)“常变”(如《常变纂要》《常变通考》《常变要义》等)“疑礼”(如《礼疑类辑》《疑礼类说》《疑礼问解》等)“礼式”(如《四礼祝式》《星湖礼式》《诸礼祝辑》等)“家范”(如《安陵世典》《沧海家范》《传家礼仪》等)等多种形式的文本。这些大部分都收在《韩国礼书丛书》之中,但目前尚有三类文献可以继续加以搜集整理。第一类,即收在《韩国文集丛刊》中未见单行的文献,如《家礼正传集解》《丧礼答问》《家礼讲录》等,不过这些文献都算不上“家礼”的专论,即研究主旨往往并不局限于所谓“仪章度数”的讨论,撰著体例并不严格按照冠昏丧祭四仪加以展开。第二类,在“问答”“疑礼”之外,展现出性理学家学术争鸣特征的文献,如金长生在著成《丧礼备要》之后,后世学者对其著作加以批评与发挥,著成《丧礼备要纸头私记》《丧礼备要抄》《丧礼备要疑义》等书,这些著作的整理发掘有助于为朝鲜礼学派系与思想的梳理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基础。第三类,李氏朝鲜后期未见刊行的抄本,如《四礼节要抄》《祭礼考定》《慎终要览》等,这类文献学术影响力较小,基本上都作为地方或宗族的日用参考类书。
作为明清两代的藩国,李氏朝鲜对儒学的尊奉注入了强烈的“华夷观”,尤其是在对以《家礼》为代表的朱子学的尊奉上表现出与东亚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姿态:一方面,朝鲜举国独尊朱学、摒斥异端,以“小中华”的姿态自居东亚文明之首,比如朝鲜通信使李凤焕曾对日本朱子学者上月信敬自夸道:“先王文物之盛,具在方册,我朝鲜讲而行之。所尊者,尧舜、文武、孔孟、程朱;所讲者,《诗》《书》《四子》《小学》《近思》,所致谨者,冠、昏、丧、祭……苟有执左道而务末技者,皆斥而远之。”⑤甚至,这种优越感使得李氏朝鲜在对宗主国礼制批判的同时产生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比如朝鲜使节徐有闻在评论清代丧制习俗时说,“汉人三年之丧,百日服之;汉人百日之服,二十七日后脱之;汉人二十七日之服,清人不服,闻之可痛。《孟子》所谓近于禽兽者,此之谓欤”[9]。另一方面,《家礼》同时被国家典章与士庶日用遵为不刊之典,“一遵《家礼》之训,行于家而施于国”[10],呈现出“国法化”与“士庶化”的双重特征。由于朝鲜性理学者对朱子学说的反复阐释与乡村儒学精英对“四礼”文献的不断创制,使得李氏朝鲜“谨守礼法,敦尚学教。三年之丧,自王家达于庶人,虽氓庶贱品,稍自好者,无改嫁之法,内外之分甚严。……‘四礼’岁遵《家礼》,不事浮屠,名分截严。”[11]李氏建国之初,要求王室丧葬之礼“一用朱子《家礼》”[12],并先后编纂《进经国大典》《经济六典元集续集》《六典誊录》《国朝五礼仪》《甲午经国大典》《大典续录》《大典后续录》等通典,这些典章所涉及的王室冠婚丧祭礼几乎全部来自《家礼》。而到了李氏朝鲜后期,随着律法体系不断完善,官方意识到除了礼教治国,“苟无精思巧法运用于听讼,则虽有公心直道,难以得其情实”[13],因此地方社会的司法管辖逐步被《囚徒册》《审理录》《三省推鞠听日记》等法典所支配,而《家礼》渐趋士庶化和家范化,真正回归到指导宗族与家庭内部的礼仪事务中。此一时期,“家礼”文献的创制也随之进入另一个高峰期,诸如《家礼类编》《丧礼纂要》《四礼问答》《丧礼精选》《疑礼考证》《四先生礼说分类》的编修等,不过这些文献缺乏了朝鲜前中期性理学家们那种学理探讨的精神,由于影响力较小、传播范围有限,且多数未克刊行,只能作为庶人处理各自家内礼仪事务的日用书籍。
三、日本江户时代:丧祭礼的受容与“先王道统”观的阐发
日本学界对“家礼”的整理与研究侧重于文献辨伪、刊本考证以及思想阐发。1936年,阿部吉雄率先对《家礼》的成书背景、真伪做出考订,“《文公家礼》为朱子未成之阙典,而颇视为疑问之书”[14]。此后,兼永芳之、上山春平、樋口胜、细谷惠志、近藤启吾、吾妻重二与池田温等学者对日本所藏《家礼》刊本进行整理与研究。特别是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吾妻重二的《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以及《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第1~7册),收录了和刻本《家礼》以及《家礼仪节考》《文公家礼仪节正误》《家礼训蒙疏》等日本“家礼”文献26种以及“家礼”古学系、朱子学系、阳明学系、考证学系、洋学系等文献16种,堪称日本学界“家礼”研究成果的标杆。
江户时代的“家礼”文献大致分为两大类别,即《家礼》校刊本以及儒家知识人“家礼”学相关文献。《家礼》校刊本如“五卷本”系统中的延保三年(1675)寿文堂刊本、元禄十年(1697)校勘本、后印须原屋茂兵卫刊本、宽政四年(1792)江户须原屋茂兵卫刊本、后印大阪柳原积玉圃刊本、天保二年(1831)佐土原学习馆跋刊本、嘉永五年(1852)仙台藩养贤堂刊本、明治印本等,再如“八卷本”系统中的庆安元年(1648)风月宗知刊本、庆安四年(1651)昆山馆道可处士刊本、明历二年(1656)柏屋八右卫门刊本、万治二年(1659)大和田九左卫门刊本、后印出云寺和泉椽刊本等[15]。其中,和刻“五卷本”所采用的底本——明刻《性理大全书》中的《家礼》五卷本,只是在编校时将杨复、刘垓孙、刘璋等人的补注部分全部删去,“五卷本”中最有名的当属浅见絅斋于元禄十年的校勘本。而和刻“八卷本”基本上都采用明人杨慎于明嘉靖九年(1514)修订的版本,即通礼一卷、冠礼一卷、昏礼一卷、丧礼三卷、祭礼一卷、杂录一卷。事实上,杨慎所修订的刊本篡改自邱濬成化甲午序刊本,讹误颇多[16]。在《家礼》版本校勘之外,江户时代知识人还著有多种阐发“家礼”思想的文献。这些文献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即对“祠堂、冠、昏、丧、祭”礼中整体或部分仪节阐发的文献。比如,若林强斋所著《家礼训蒙疏》对“祠堂”“深衣制度”“居家杂仪”的深入解说;大和田气求所著《大和家礼》对“神主纳龛”“大宗小宗”“冠昏服”“临终之事”“虞祭时祭”等仪节的创见。此外,这类文献还特别注重对丧、祭二礼的发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祭礼节解》《祭礼略解》《祭礼通考》《丧祭略说》《丧祭仪略》《丧祭私说》等。比如,荻生徂徕在其《祭礼略记》中答松子锦问神主制度时,对日本丧葬礼儒释杂糅的现实进行了批判,“吾邦俗间所为牌子多云首者,尺寸大小不一,从人所好,皆谓浮屠法。然浮屠但奉佛天,不奉祖先,佛天皆塑像,岂有之乎……世儒者恪守考亭法,而谓先王之礼,遂黜俗间所用者为浮屠法。”[17]
第二类即对《家礼》仪节进行考证与注疏的文献。如新井白石的《文公家礼仪节考》、猪饲敬所的《文公家礼仪节正误》、冈山蕃的《祭仪详注》、室直清的《文公家礼通考》等,此类刊本博引《周礼》《仪礼》《礼记》以及宋以前诸礼说,对《家礼》内文中所涉及的礼文术语、人物、条目、仪节加以详细考订。新井白石在解释“爱礼存羊”时引《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解释“尊祖敬宗”时引孔颖达疏,“宗是先祖正体,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祖祢之义也。”[18]这些都属于对《家礼》的补注之学。
第三类即知识人在继受、批判朱熹“四礼”学说的基础上自创的“日本化”《家礼》。比如,林鵞峰在明历二年(1656)遭母顺淑孺人丧时,依照《家礼》仪式为母举办仪式,后居丧期间著成《泣血余滴》二卷,记载母丧时的详细仪节,后又延及祭奠礼,著成《祭奠私仪》。林家丧、祭二礼的创制与运用,“损益而从事宜,示谕子孙,可以为我家之法,……后儒因程朱,然其间不能不加新意,岂其违戾程朱哉?所谓行之有时,施之有所者也”[19],这一创发对整个江户时代幕府与民间社会的丧祭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又如朱舜水“问简牍牋素质式,质深衣幅巾之制,旁及丧祭之略,裒其所闻”[20]而著成《朱氏谈绮》,书中对“棺制”“铭旌式”“神主式”“坟墓式”“碑式”等的尺寸与样式加以实证,部分地推翻了《家礼》中的成说。再如三宅尚斋的《朱子家礼笔记》更是批判了朱熹礼学“天理节文、人事仪则”的主张,而提出“其实之存于内者,恭敬辞让也;其文之著于外者,仪章疏数也”,并强调在《家礼》的受容上应当充分考量古今异宜、中日殊俗的问题,“吾邦地隔万里,俗殊时亦异矣,学者善读此篇,有得于因以斟酌之之意焉,则庶几于礼之全体,莫所失云。”[21]
结合日本学界文献整理的既有成果与笔者的补遗,依刊行先后顺序,可将江户时代“家礼”文献目录著录如下:林鹅峰《泣血余滴》《祭奠私仪》《室町家礼式》、三宅巩革斋《祭礼节解》、中村惕斋《追远疏节》《慎终疏节》《慎终疏节通考》《追远疏节通考》、中井甃庵《丧祭私说》《服忌图》《深衣图解》、大和田气求《大和家礼》、朱舜水《朱氏谈绮》《慎终日录》、德川光圀《丧祭仪略》、小柜与五卫门《祭礼略节》、加藤九皋《丧礼略私注》《丧祭式》《儒葬祭式》、若林强斋《家礼训蒙疏》、增田立轩《慎终疏节闻录》《追远疏节闻录》《慎终仪》、三宅尚斋《朱子家礼笔记》、藤井懒斋《二礼童览》、熊泽蕃山《葬祭辩论》、佚名《室町家礼式》、山本太冲校《四礼初稿》、佚名《和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乙集》、室鸠巢《文公家礼通考》、新井白石《家礼仪节》、猪饲敬所《文公家礼仪节正误》、冈山蕃《丧祭略说》《丧仪详注》、浅见絅斋《通祭小记》《和刻家礼》《家礼师说》、邱濬辑《和刻文公家礼仪节本》、小出永安《和刻性理大全本》、津阪东阳《祠堂考》、佐藤一斋《哀敬编》、佐久间象山《丧礼私说》、古屋鬲《祭礼通考》、佚名《祭礼节解》、石川济《新刻文公家礼》、荻生徂徕《葬礼考》《葬礼略考》《祭礼略记》等。
儒家生命仪式的本土化是这一时期朱子礼学的重大课题[22]。江户时代日本知识人摆脱了“寺请制度”这一佛教丧葬礼仪的束缚,他们将死生观建立在宋儒《家礼》仪式的实践上,这从侧面反映了朱子礼学在当时已经取得独尊的地位,“世人尊信程朱,过于先王仲尼,恪守其《家礼》而谓是儒者之礼也。而不复问其与先王仲尼所传之礼”[23]。但由于《家礼》所阐释的丧祭文化因日本社会结构与环境的差异,在日常礼法实践中与中国有不同之处,“俗有彼我,势有可否。《家礼》所定器服之制,起居之节,往往非我邦所宜。虽有行者,亦或类矫激,且流俗之弊,浮屠之习,有不可遽得有所为者,乃有志之士,不能不更推其意以斟酌之。”[24]家礼的“斟酌损益时措之宜”[25]成为建构道统合法性的重要出路。
所以,江户时代的知识人对《家礼》的受容表露出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即批判宋儒的家礼思想,为了使儒家生命仪式进一步本土化,并论证礼学“道统”一脉相承的合法性,江户时代的知识人批判朱熹“礼也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家礼”学说,认为礼乃是先王所作,而不能解读成“性”与“德”,“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宋儒既以天理人欲立说,亦能知礼之为先王所作,而欲引之于性,故作是言以弥缝之。其究犹之佛氏法,身偏法界之义耳。”[26]礼是三代圣王奉天道而作,而非天道自然之有,“后儒不识其意,而以为天者,自然也,谓自然有,是礼也。是其天理节文之所本自,殊不知,以天为自然者,老庄之意,而古所无焉。”[27]知识人主张从“道者统名”的角度重新理解“先王之道”与家礼中“孝弟之道”的关系。雨森芳洲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外孝弟而为说者异端也,天道也。以孝弟而为说者,圣人也,人道也。”[28]所以,寻求“先王之道”的本质就是要跳过宋儒家礼而实现“复古”,“后世礼法之废,此其最难复古者也,何况国俗久溺浮屠教,而不知有先王之礼。”[29]另一种声音即强调在回归“先王之道”的同时,建构日本与中国古义一脉相承的礼学体系。“夫生于我国,而尊异邦之道,犹不敬其亲,而敬他人。忘神明之恩,失君臣之义,不孝不忠,莫过于此矣。……今乃谓日本自有其道其教,而不资于中国圣贤大中至正直训。则天地之间,所谓道者多端,而庶邦各有其教也,然则天竺、南蛮、鞑靼、月氏之夷俗,亦皆谓之道,可乎?”[30]这个“道”即“先王之道”,践行先王孝弟之道的最佳方法,就是“身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31]实际上,这两种声音的出现客观上成就了江户时代“家礼”文献的两大鲜明特点:前者从“制礼者、传礼者、行礼者”的不同角色出发对《家礼》文本进行饾饤考证,而后者则以“秦汉以下书不读,所以为域中之雄也”[32]的复古思想对礼学道统进行“日本化”的改造。
四、越南后黎/阮朝:“家礼”仪文化及其对王朝“礼教治政”的贡献
朱子学早在南宋末年即传入越南。但《家礼》及其具体礼仪直到17~19世纪之间才被越南的知识阶层反复传颂,并普及到民间社会[33],“南宋晦庵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接洙泗之正统,至今仰之如泰山。……士大夫平日诵其诗,读其书,孰不欲歆羡景行”[34]。越南“家礼”文献的存目整理与研究在中越两国间尚未有系统的梳理,目前可知的 “家礼”文献见于越南国家图书馆所藏汉喃古籍。本世纪初,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其中列举了《黎贵惇家礼》()以及《寿梅家礼》()等十余种刊本⑥。相比于李氏朝鲜、日本江户幕府侧重于对《家礼》“礼法与天理”的哲理解读,越南朱子学者则更多地停留在仪文的整理以及运用于王朝的“礼教治政”。比如陈氏所藏《家礼略编》()记录祠堂、斋戒、祭礼仪式与祭文;《清慎家礼大全》()记录贺寿、丧礼、祭礼以及收录数十篇祭文;《丧礼备记》()在《寿梅家礼》的基础上改编了奠祭、服丧、五服图与挽祭联范文等。
目前对于越南后黎/阮朝时期“家礼”文献的著录只能从已出版的越、法两国所藏汉喃古籍文献目录中加以提炼,大致如下:胡嘉宾《寿梅家礼》、佚名《传家至宝》、佚名《三礼辑要》、佚名《清慎家礼大全》、佚名《家礼或问》、杜辉琬《文公家礼存真》、裴秀岭《四礼略集》、佚名《家礼国语》(又名:《胡相公家礼》或《胡尚书家礼》)、佚名《丧祭考疑》、黎贵惇《黎贵惇家礼》、陈氏所藏《家礼略编》、云亭斋《丧礼备记》、佚名《祭祖仪节》、集福堂《释迦正度实录》《三教正度实录》、青寥社《三教正度辑要》等。
后黎时期,《家礼》一书成为政府与民间冠婚丧祭仪式的蓝本,这得益于大儒黎贵惇在朱子礼学南传基础上所创制的一项重要成果——《黎贵惇家礼》。该书汉、喃文间杂,题黎贵惇序文,内容涉及居丧格式、送葬、祭礼等丧礼仪式,附有数篇喃文祭文,把“礼者,理也,理惟其是而已”的“礼理一体”思想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是此一时期王朝推行礼治教化的人文基础。史官吴士连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家可教,然后可以教国人。虽唐虞之治,不过是也。《书》美帝尧于变之盛,必以克亲九族为首,化行于家之谓也。……故上而仁宗称其孝,下而明宗遵其法。治底文明,俗臻福庶,非治效本于身修家齐欤?”[35](P401)景治元年(1663),玄宗发布“教化四十七条”,其中申严“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父母修身以教子,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夫子,妇人夫亡无子,居乡党者长幼相敬爱,便害相兴除,毋以强凌弱,毋唱讼而行私,男女勿为巫觋之徒,丧家勿为中元之唱。”[35](P794)保泰元年(1720),裕宗又颁布“教化十条”,其中涉及“民间服用,不可僭逾,丧家相恤,以敦救助之风”等规定,这些条目基本都是对《家礼》“居家杂仪”的一种发挥。
阮朝时期,嘉隆帝命阮文诚等依《皇清律例》而制颁《皇越律例》,《家礼》中的“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的主张遂成为《皇越律例》制刑量刑的重要参考标准,“服有五,本之五世亲疏之分而制其等,其年月之异,虽以恩之厚薄为隆杀,然皆法乎天道焉。”[36]《家礼》中的五服制度(斩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以及丧服图(丧服总图、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妻为夫族服图、妾为家长族服图、出嫁女为本宗降服图、外亲服图、妻亲服图、三父八母服图)被《皇越律例》中的礼律部分全文沿袭。此一时期,胡嘉宾所撰《寿梅家礼》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地刊刻与流传。此书在《家礼》基础上“参质诸书,依袭古礼,斟酌损益,敷演国音,及各节祭文对联,从宜增补”[37],可以称得上朱子礼学在越南社会实践的重要成果。然而,《寿梅家礼》的大量印行也暴露出此一时期越南礼学“儒释杂糅”“礼俗互参”的客观现象,杜辉琬在其所著《文公家礼存真》()中说,“《寿梅》祝文对句鄙俚无比,儒释相参,尤失礼之意者。世之贤士大夫不为不多,曾不留心为世起而正之者,何耶?盖其亲在不忍读书,及至临变,悲迷哀痛,未免付之村翁,礼之不明、不行者,以此。”[38]如嘉隆十六年(1817)和成泰九年(1897)分别刊行的《三教正度实录》()与《释迦正度实录》(,将儒、道、释三教的丧礼仪式杂录一处,发明出诸如“饭含醍醐”“取猫过尸”“安棺附移厝”“分针点穴法”等仪节,颇为不伦不类。
至于《家礼》及其思想对于整个越南家族结构与形态所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也同样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真空地带。从越南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汉喃古籍文献来看,有黎氏、阮氏、江氏、朱氏、段氏等亢宗大族,其编修的谱牒都与《家礼》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黎族大宗家谱》奉先世神主依“朱公《家礼》祠堂之制”,“我族报本反始之道,尊祖敬宗之心,诚于祠堂规法奉祀,庶得以尽其孝,以寿其传”,祭礼与“朱公《家礼》合观之”[39]。又如《朱族家谱》《段族谱》等在内文中收录祠堂祭文、初祖祭文、冬至祭文、墓祭祭文等,也参酌了《家礼》的祭礼仪节。至于其他宗族的家训、族谱也都十分强调族人对《家礼》的践行,比如“盥漱栉总、冠簪绅絇,礼有媒妁、告之鬼神,丧当尽礼、祭当尽诚”[40]“人之生本乎祖,不可不知其所由来”[41]“子孙享祖尊之德,思积累之艰,而欲为继承之地耳,岂徒志坟墓、存祭腊、叙世代次而已”[42]等思想,均是对朱子《家礼》文本与思想不同侧面的解读。
五、结 语
尽管华琛、伊佩霞等西方汉学家较早地对《家礼》进行了翻译、校勘、疏注与研究,但对东亚国家“家礼”议题做出系统整理研究的应属中、韩、日学界。尤其是在钱穆、陈来、史景南、杨志刚等学者为《家礼》成书正本清源,以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该丛书目前已出版至第五辑,合计收“家礼”汉籍21种)整理出版的基础上,近年来,国内学界注重从思想史交流、经典诠释、义理探讨、话语分析等多重角度对朱子礼学进行研究范式的革新。全面爬梳东亚儒家知识人所创制的“家礼”文献,其目的在于探讨东亚朱子礼学在建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为东亚礼学研究寻求共识点与知识增量,进而拓展东亚儒教文明交流的话语体系,为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交流寻求更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东亚儒教文明交流的学理层面来看,朱子学及《家礼》传至东亚周边国家后,对东亚文明秩序、国家认同以及基层伦理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家礼辑览》《家礼师说》《黎贵惇家礼》等为代表的“家礼”文献遗产证明了周边国家对华夏文明的仿效与服膺⑦;而华夏礼制“因人情而节文也,苟可以义起,虽礼文不载,亦圣人之不禁也”[43]的域外解读,也从侧面证明了伴随着区域间各主体“自我”意识强化的同时,“(儒学)精神博大,东亚数千年所信仰,中国之民族得以赓续延长,东方之文化日以发扬光大。”[44]从李氏朝鲜来看,以《家礼》为代表的朱子学说始终影响着“两班”社会的礼法政治主张;从日本来看,以德川家族为中心的武士集团组建“家职国家”,借助《家礼》所倡导的主从有序的伦理,建设忠孝一体的“家格阶层制”;而至于越南,在礼学的浸润下早就认为其与华夏“文胞一脉,声气相通,不待同堂聚首,风雨连床,然后为同心之契也”[4](P23)。因此,全面整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家礼”文献,既可以厘清以朱子礼学为代表的中国礼教体系与人文思想向东亚周边国家播迁的进路,也可以把握周边国家对儒教的继受与批判以及构建自身礼法体系的姿态。
从“东亚文化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角度来看,对周边国家朱子学的研究与检视,既是建构华夏文化记忆与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也是文化复兴进程中向周边国家展示“文化自信”的资本。如果说考察朱子学在东亚文明交流史中的影响,反映的是由“自我”而观“他者”的“文化中心主义”⑧,那么对东亚周边国家礼经与礼学思想的梳理,反映的则是东亚文明交流史中“揽镜自鉴”的大国气魄,这是呼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一时代主题的重要方式。
注:
①作为一种文明高下的批判形式,礼制是划分族群认同的重要依据。葛兆光说,“尽管古代文献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很明显,但是这种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而且这种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意味与文明意味常常相互冲突和混融,有时候文明高下的判断代替了空间远近的认知。”这种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的文明区分形式,同样也构成了古代“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作为本体论的真理,特定的手抄本(经典)语言是构成想象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前提,“较古老的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中国的官人们带着赞许的态度注视着千辛万苦方才学会挥毫书写中国文字的野蛮人。这些蛮人虽未入文明之室,却也总算登上文明之堂了”。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45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2、32页。
②在理解历史上东亚族群意识这一问题上,“礼”作为一种超越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的文化认同,很好地揭示了东亚“文化主义”的表达或“民族主义的原型”(proto-nationalism),因为它是一种“超越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的一种普遍认同感。”参见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4页。
③《四库全书存目丛刊》在经部第114-115册“通礼杂礼之属”中著录了如下“家礼”文献:丘濬《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吕柟《泾野先生礼问》二卷、宋纁《四礼初稿》四卷、吕坤《四礼疑》五卷《四礼翼》八卷与《丧礼余言》(四礼附疑)一卷、吕维祺《四礼约言》四卷、许三礼《读礼偶见》、李塨《学礼》五卷、王复礼《家礼辨定》十卷首一卷、王心敬《四礼宁俭编》不分卷、曹庭栋《昏礼通考》二十四卷、张文嘉《复位齐家宝要》二卷等。
④限于篇幅,本文所列举的文献信息有限。而更为详尽的著录情况,可参见拙著:《〈家礼〉思想朝鲜化》(巴蜀书社2019年版)所附录的“《韩国礼学丛书》补遗一览表”。
⑤李凤焕等:《和韩唱和录》卷下,延享五年(1748)刊本,第16页。又如,从壬辰倭乱时被日本人俘虏之后又出逃的朝鲜武臣鲁认的笔下,看出朝鲜在尊奉《家礼》这一话题中产生的自豪感:“我国凡人,一遵朱晦庵《家礼》。而况丧制三年,自天子至于庶民,无贵贱一也。”“傍有衙客三人书示曰:‘愿闻贵国风教婚丧之礼也。’答曰:‘我国凡风教,一依箕圣八政之教。而冠婚丧制,则只遵朱晦庵《家礼》。’左右叹之,更加敬待。”“早起驰向兴化府,行至北门之内……乃朱文公生祠堂。左右曰:‘尔那里人耶。’答曰:‘我本朝鲜人也,我国凡礼。一遵朱晦庵《家礼》。’左右叹之。”“‘三年之丧,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贵贱一也。我国之风,一遵朱晦庵《家礼》。……虽颠沛流离之际。岂可毁礼以遵夷狄之风哉?’左右叹息无言曰:‘贵哉!贵哉!谁谓朝鲜藩夷耶?守法知礼如是夫。’”分别参见鲁认:《锦溪日记》,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初六日、四月十一日,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影印本。
⑥参见刘春银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2004年,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又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并制成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资料库系统”,共计收录存藏于越法两国六所图书馆之珍贵汉喃古籍文献目录5023 笔。
⑦本文标题所用“太山遍雨”一词,意在说明传统中国的普遍性价值观(如“夷狄观”)并不具有“排他性”。换言之,通过教育和模仿,周边的夷狄可以成为文化中心的一部分,从而也与华夏民族一起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从东亚这一大的视角来看,礼制所内涵的文化观念等同于族群观念。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版,第59页。
⑧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帝制时代的中国与周边族群关系的维系依靠的是“文化主义”,即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要借助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且这种观念具有相当强的文化自身优越性,但是由于文化主义与种族观念纠缠在一起,使得帝制时代的中国在“我者”与“他者”之间很难建立起一个清晰的群体界定标准。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