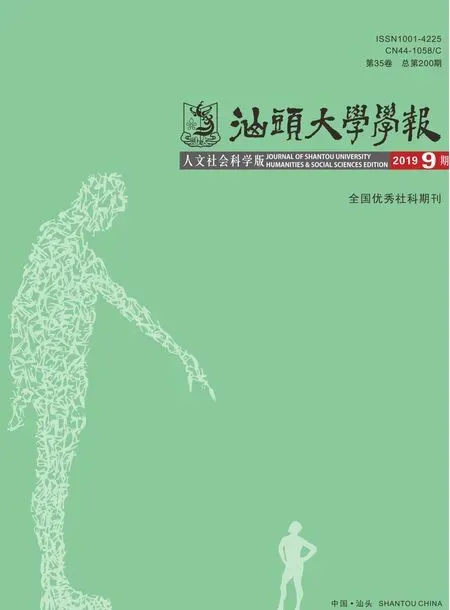“真淳之语”:论元结文学创作的内在理路
刘志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一、引言
“真淳之语”来自苏源明对元结《说楚赋》三篇的评价,孙望《元次山年谱》推测苏源明于天宝九载官河南令。其时元结“习静”[1]5于商余山①《二风诗》序云:“天宝丁亥中,元子以文辞待制阙下。……于是归于州里。后三岁(天宝九载),以多病习静于商余山。”([唐]元结撰、孙望编校《新校元次山集》,台北:世界书局,1984 年版,5 页),著《说楚赋》三篇,苏源明见而骇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语,难哉!然世自浇浮,何伤元子?”[2]35“真淳之语”,言《说楚赋》具有“真淳”的风格。“真”,有“真诚”“充实”“诚敬”“本原、本性”等意。“淳”,有“纯厚”“纯粹”“纯一”“纯大”“纯 美”等意。则“真淳”有“回归本原的纯厚”“诚实无欺的纯一”“充满元气的纯朴美好”之意,文章“真淳”的体现,表现在内容上充满真挚的感情,形式上朴实有力摒弃华丽的技巧。“《说楚赋》三篇今存,观其篇意,乃是君史借楚何荒王、何惑王、何惛王大兴工木、溺于享乐、暴虐无常从而几乎破家亡国之事讽谏梁宠王,用意在于以寓言箴戒君主,使君主弃恶从善,谨守为君之道。以“谲谏”的方式向上层统治者指出问题所在,并希望引起注意和改变,达到救治弊乱的目的,是谓“真淳”的写作。“真淳”,既有文体、文辞、文意上的,又有思想、道德上的。元结作品中,以箴劝、规谏为主题的“箴铭”类文体写作极为丰富。事实上,元结几乎所有作品都具有“真淳”的创作风格。
学界关于元结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尚缺乏从本质而非表象上探讨元结文学创作的文章,本文尝试以“真淳”为着眼点寻绎元结文学创作的内在理路。“内在理路”作为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由余英时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中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考证)自有其本身发展与转变的内在要求,不必与外缘影响息息相关。……‘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其文献上的证据是相当坚强的。”[3]2-3又言:“内在理路,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4]因此在其实际学术语境中,有“内在动力”“内在逻辑”“内在的要求”等多重涵义。本文借用此概念,用来论述元结文学创作内在动力或内在逻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元结时代“真淳”道德以及文学创作的内在要求。第二,元结自觉培养“真淳”的道德人格。第三,元结着意寻找能表现“真淳”风格的创作方法、方式。
二、元结面对浇浮之世的忧切危苦
苏源明在指出元结文章“真淳”的同时,还相对指出世态之“浇浮”。“浇浮”,有浮薄、浮泛等意。彼时的“浇浮”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上下各阶层的普遍存在。以天宝六载(747)制举为例,此次“通明一艺已上”者即可应举,是以“草野之士猥多”,此时专制朝廷的李林甫,大概是出于防范士子言论可能于己不利的原由,悉数黜落布衣之士,并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堂堂国家制度,在李林甫手里成了玩弄私人权力的工具,而唐玄宗似乎也只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野无遗贤”的谄谀之词。研究者多把这种行为归结到李林甫一人身上,其实不能算太公平。李林甫之上有手握最高决策权力的皇帝,同僚有互相制衡的三省,大臣也有上表谏诤的责任,不过竟然全体“失语”,因此这里的“浇薄”,并不只是某个人物如此而已,而是整个国家统治层面的“浇薄”。
而在应举者一方,当年元结、元结乡人以及杜甫皆在其中,虽然都是落第的结果,但落第后的表现并不相同。在元结“将东归”之时,其“乡人有苦贫贱者,欲留长安依托时权,徘徊相谋。”[1]52既然“相谋”,也许这位乡人已经打定主意要托关系、走门路,来“谋”具体办法而已。根据当时风气,乡人可能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却没有料到遭到元结的反对,乡人最后听从元结的劝说回去了[1]51-53。但乡人未做成的事,杜甫都做了。杜甫此时的表现,就是一个如何干谒请托的样本,姑引杨承祖的研究以见大概:“(杜甫)应诏自举报罢之后,欲留止长安,频游朱门,希望能得到入仕机会。其间如张垍、韦见素等,似乎并无深厚的渊源,皆呈诗乞加援手,而上京兆尹鲜于仲通的二十韵诗,更间接未意,求助于杨国忠。国忠小人,因贵妃而得宰相,其怙权纳贿、害政误国,杜甫当然知道,但为求一官,乃隐忍如此。”[5]257仇兆鳌以“邻于饿死”“姑为权宜之计”曲为少陵辩护[6]125,其实不必,杜甫呈诗乞援并非一时一地之举,在诗人生命中也可视为普遍情况。这不能不说是“浇浮”行为,不但落第后乞求权贵援手,在未曾应试之前,早已开始四处活动,宁愿忍受“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耻辱,也不会停止。品行如杜甫尚且如此,其他士人更不必说。这是本来应该最注重“气节”的“士”阶层的“浇浮”。
元结却是清醒的少数,同时对“浇浮”世道也给予坚决的批判。元结落第后曾漫游长安,“预宴于谏大夫之座”[1]53,又曾“与丐者为友”[1]54,认为“丐者今之君子”,可能并非实事,只是借题发挥对当今“浇浮”世态的不满,举世皆是苦于贪欲的“乞丐”,相比之下,真实的“乞丐”倒是守“君子之道”,值得跟随学习:“呜呼!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属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颜色于人。甚者则丐权家奴齿以售邪妄,丐权家婢颜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贫,自贵丐贱。于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时,就时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终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于仆圉,丐性命于臣妾,丐宗庙而不取,丐妻子而无辞。有如此者,不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弃衣,丐人之弃食,提罂倚杖,在于路傍,且欲与天下之人为同类耳。不然,则无颜容行于人间,夫丐衣食,贫也。以贫乞丐,心不惭。迹与人同,示无异也,此君子之道。”[1]54-55元结描述的“求乞”画面,可以看作是对苏源明“世自浇浮”说法的注解,也可以看作是“浇浮”世态的全画像。唯有对“浇浮”世态和人情保持深切、全面的认识,才能时刻保持距离和批判,并且因面对末世衰俗深感任重道远而忧切危苦。元结独挺于流俗之中并非故作姿态,而只是其内在道德人格的一个侧面。元结具有“真淳”的文学创作修养,苏源明能够辨认出这种风格,说明存在一个当时人们达成共识的道德标准或道德人格。于是元结道德人格的培养就有了追溯的必要。
三、元结道德人格的追求以及培养
首先,元结道德培养中的“非人情”观。“非人情”原是元结对德行卓著(《新唐书·卓行传》第一人即元德秀[7]5563-5565)的从兄元德秀的评价。元德秀去世后,元结撰《元鲁县墓表》曰:面对“人情所耽溺喜爱”,元德秀偏偏“如戒如惧,如憎如恶”,此“非人情”。且元德秀的一生皆是“非人情”的:“弱无所固,壮无所专,老无所存,死无所余”[1]82,好像只有小心翼翼的不被“人情”污染,才能成就“清独君子,方直之士”[1]83,挺立在“浇薄”之世,警戒“浮薄”之徒。元结作为元德秀的亲戚、门人、朋友、知音,对元德秀道德人格的赞美以及道德修行路径的揭示,也无疑是元结的夫子自道。元结自言“聱牙”“不从德于时俗,不钩加于当世”[1]113;自言“于时不争”“与世不佞”[1]81,是其自身“非人情”的表现。可以说,“人情”如何,也即是社会环境如何,个人很难脱离“人情”大网,也很难不被社会环境所改变。而“非人情”是逆当时人情、人性的行为,本身就是道德修行上难走的窄路。如果太在乎与当时“人情”的互动,往往不但不能改变世俗,还会被世俗所改变。因此当无力改变世俗时,“洁身自好”似乎成为处世的最佳选择。元结言“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1]52又言:“人生若不能师表朝廷,即当老死山谷。”[1]128“非人情”的选择,是元结道德人格培养的执著,也是清醒与自爱的表现。
元结天宝六载制举失败之后的表现,也在事实上为其“非人情”的人生态度提供了证据。天宝六载,权相李林甫弄权,布衣之士无得第者,元结亦在其中。相比于落第后杜甫积极奔走谋求入仕,元结要冷静与理性得多。在《喻友》中对李林甫“专权罔惑上下”[1]52的指责,是正直之士的不妥协和仗义执言。随后元结返乡,“习静”于商余山。天宝十一载,李林甫卒。天宝十二载,“二月,追削李林甫在身官爵。”[8]24同年,元年举进士。也就是说,元结从第一次科举失败到再次参加科举,中间隔了6 年时间,等于是6 年放弃参加科举的机会。这6 年对很多人来说是白白浪费的6 年,会错失多少机会。天宝十载,杜甫年40,奏赋3 篇,终于引起玄宗注意。而元结山谷独守,著书自娱,再三以“封包裹封”[1]63、“知命”[1]75自明心迹,警惕在权臣当道的朝廷随顺“人情”可能导致的“灭身亡家之祸,伤污毁辱之患”[1]63。元结对道德人格培养的“非人情”方法的重视,从山林“习静”中可见一斑。
其次,元结以“元气自然”为根源的道德人格观。颜真卿言元结“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2]36,无疑,“行古”“言古”的根源在于“心古”。但“古”字难免范围太大,那么具体元结之“心古”,“古”在何处?李商隐言:“次山之作,其绵远长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移易之。”[9]2256深探元结文学创作之宗旨,以“元气自然”为根本。除“元气”一词,元结还在写作中以“元化”“元极”“元和”等表述。《说文解字注》:“元,始也。《九家易曰》:‘元者,气之始也’。”[10]1大抵指一种浑厚、质朴、原本正大之气。扬雄以“浑浑若川”[11]163的比喻来形容对这种博大之气的体会。王充“天禀元气”“天道自然”交替使用,来说明万物从“元气”“自然”而生,则“元气”“自然”二者又有相似之处。“元气自然”确实如李商隐所说是元结根本创作理念,刘青海也认为,“(李商隐)评价元结文学正大而自然、具有俾补造化、与造化和人伦同工的艺术价值。作者其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教化观念,尤其是‘君君尧舜’16 句,强调一种更加纯古自然的文学特性。”[12]但元结之“元气自然”,不但是文学创作而已,应该更进一层追溯与其道德人格的联系。元结常常论及上古道德,如“上古之君,用真而耻圣,故大道清粹,滋于至德,至德蕴沦,而人自纯”[1]48、“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纯玄粹,惠和溶溶”[1]50等,并是“元气自然”论在道德观上的发挥,也是元结所追求之道德境界。
李商隐曾言元结同时代人对其的看法是:“次山不师孔氏为非。”[9]2257可以说“不师孔氏”也是元结“不从德于时俗”的一个方面,没有问题。但“为非”就难免有问题了,对此李商隐已经在为元结文集写的后序中作了充分的辩护,这里不再重复。站在元结的角度,道德呈“倒金字塔”型发展趋势:“上古之君,用真而耻圣。……其次用圣而耻明。……其次用明而耻杀。……迨乎衰世之君,先严而后杀。……继者先杀而后淫。……继者先淫而后乱。”[1]48道德水平有高下,与儒家比较,“用真”在儒家“用圣”之上。但上一级可以包涵下一级,下一级是上一级的部分。所以,“元气自然”并不是反对儒家道德,而是完全能够包涵儒家道德,是整体与部分的差别。在救世的方法上,元结却与儒家相似,先解决百姓面对的生活问题,再施以教化,渐次全面恢复“元气”,这又是一种正“金字塔”型救世图式。孔子主张“必先正名”[13]142,主张庶而后富,富而后教[13]143。元结道州刺史任上,奏免赋税、招徕流民,以恢复生产,而后发展文化教育。应该说,元结尽管崇尚“元气自然”,在“用圣”这个层次上却能与儒家达成一致。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以“元气自然”为道德追求的元结,一生的实际活动遵循的却是儒家模式。虽然现实与理想有差别,但也不能因此否定理想。
最后,元结比较注意在现实和实践中培养其道德人格。天宝六载,元结待制阙下,著《皇谟》3篇、《二风诗》10 篇,“将欲求干司匭氏以裨天监”[1]5,目的是“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1]10乾元二年,苏源明荐元结于肃宗,元结赴京师,上《时议》三篇,从君、臣、言行三方面分析形势,肃宗大悦。元结两次向政府机构献文的结果,第一次没有造成影响,第二次得到皇帝的认同,虽然有如此差异,但相同点都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深入认识和深刻分析。“非人情”的元结,却抱有对时事的热情。据杨承祖分析,元结的文章很多背后都有具体现实所指。如“《皇谟》第三篇的《系谟》……批评君王‘奢侈过制’、‘肆极侈削’、‘殚穷土木’、‘极地封占’、‘损人伤农’、‘穷黩争战’、‘耽喜靡曼’和‘甘顺奸佞’,都是玄宗当时的恶德败行。……(《二风诗》)还特别提出‘废嫡立庶,忍为祸谟’,则直接指涉李林甫处心积虑要动摇太子李亨的问题。……(《时议三篇》)所谓‘罔上惑下’的‘至奸元恶’,正指比高力士在玄宗时尤为揽权遏事的巨珰李辅国。”[5]380-384但杨承祖的分析只是在元结关注现实的层面,正面建设层面尚未论及。
积极建设层面,尤其能体现道德和实践的结合。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同年十二月,洛阳沦陷。元结大约在家乡已经沦陷的至德元载,召集邻里,举族南奔逃难,从今河南鲁山县商余山迁徙到今湖北大冶市猗玗洞。逃难本来是兵乱常事,但元结逃难规模之大,在当时即引人注目。李肇《唐国史补》载:“元结,天宝之乱,自汝濆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14]166“逃难”事件是元结道德修养和责任能力的双重体现,大概随后苏源明的推荐与肃宗的召见,也与此不无关系。而此事元结本人也在以后屡屡提及,如“臣在至德元年,举家逃难。生几于死,出自贼庭,远如海滨。”[1]102看来印象十分深刻。入仕后,在发挥更大从政能力的同时,亦亦更加注重道德修养。
四、元结“箴铭”类文体写作与“风雅”承继
言行举止包括文学创作在内,往往与其人道德修养有关。在人际交往中,元结“足不入于公卿之门,身不齿于得禄之士。”[1]91而宁愿结交“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1]101等贫贱而高尚之辈,严守君子、小人之辨。文章写作中,认为“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1]100文章写作普遍陷入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为辞流易的问题,这样的作品也不是没有价值,元结认为作为个人消遣之作还是可以的,但是让“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1]100那么能让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认可的作品,自然是“几及千岁”不传的“风雅”文章了。由此可见,元结以及同辈有着传承“风雅”精神的自觉担当。元结自己把文章创作分为两期,第一期:“径欲填陷阱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1]154,坚守“直道”,“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1]154第二期:“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文章“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以期“救时劝俗之所须”[1]155。那么,两期的共同点在:一是继承“风雅”精神,以文章写作有益于“教化”为目标。二是文章皆是元结道德人格的贯注,也是其道德人格的反映。
文章文体的使用,元结应该是有意排除一些容易出现沿袭、形似、流易,拘限声病的文体,如律诗。元结集中没有当时流行的律诗创作,但不能说不能律诗写作。天宝十三载(754),元结年三十六,擢进士第。此年几乎可以确定进士3 项考试内容必有试诗、赋一项,省试诗有严格的格律声韵要求,而元结必定是在满足此要求的情况下才得以登第,因此可以说其对律诗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入了解其弊病的基础上的。由于元结登第较晚,可以推测36 岁之前长时期在为参加科举做准备,少不得勤加练习写作进士考试要求的文体。元结17 岁跟随元德秀学习,元德秀是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开元二十一年到天宝十三载,进士三项试制的帖经、试策两项不变,但试杂文一项却有所变化[15]19-144。唐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成为定制,杂文具体文体却并没有确定。徐松在《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注解“进士试杂文两首”云:“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16]70由此可知,元知从跟从元德秀学习到登第,杂文文体中的箴、铭、论、表、诗、赋,都有大量写作的可能。而通过检读现存《元次山集》,可以发现“箴铭”类文体确实是元结写作的主要内容。
箴、铭,皆是箴劝、规戒类文体。吴承学、刘湘兰在《箴铭类文体》一文中认为箴铭类文体主要有箴、铭、规、诫、训[17]。元结创作中以“箴”为名者:《自箴》《县令箴》两篇。以“铭”为名者:《异泉铭》《瀼溪铭》《抔樽铭》等十余篇。以“规”为命者:《心规》《戏规》《处规》《出规》《时规》五篇。
虽然题目不以箴、铭、规、诫、训等命名,但主题却含有“永为世箴”“指此为箴”“欲剧为之箴于身”“全守真常规”“可为识者规”“相规”“规讽”“规谏”意图的文章数量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元结所有文体的写作。例如诗赋,有《闵荒诗》《二风诗》《系乐府》12 首、《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说楚赋》3 篇等;议论,有《元谟》《演谟》《系谟》《恶圆》《恶曲》《时化》《世化》《自述》3 篇、《订古》5 篇、《管仲论》《时议》3 篇、《自释》《化虎论》等;表状,有《元鲁县墓表》《哀丘表》《乞免官归养表》《惠公禅居表》《再谢上表》《让容州表》《再让容州表》《举处士张季秀状》等;记序,有《与吕相公书》《茅阁记》《菊圃记》《刺史厅记》《送张玄武序》《箧中集序》《送王及之容州序》《别崔曼序》《文编序》等。结合“箴铭”类文体,“真淳”在元结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以“箴铭”类文体为代表的文体、文辞、文意之“真淳”。元结反对“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反对以“拘限声病”“形似“的文体以及沿袭、流易的文辞写作,主动避开主流写作方式,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元结与同时代大多数著名诗人并无交集。杨承祖以元结诗歌中很少用颜色字和诗中直率的句法、无藻的辞采来分析其纯素、淡泊、绝去雕饰的特色[5]390-391固然准确,但评论“元结诗的句法,尤其直率,往往不但是‘押韵之文耳’,甚至几乎如同白话,也不避造语重复之忌,又常以虚字足句,而不顾诗法所讲求的精密。”[5]391却仍然拿来与精密的近体诗相比较,不知元结是对“风雅”古体的师法,且“师其意不师其辞”,是别开生面之作。而辞意尤其明白晓畅,元结作品往往有序,详述写作之原因和目的,这也是有意识地让文章主题更加显明,此亦是“真淳”之一面目。“箴铭”皆是能上溯到“三代”,也能体现“矢言之道”的“远大”[18]140文体,元结擅长写作“箴铭”文,不但内容上意蕴丰厚,形式上也多用四言句,起到一种如碑文体一般浑厚、朴质、严正的效果。
其二,以继承“风雅”精神为写作目的之“真淳”。元结列举的“时俗”文学弊病有沿袭、形似、流易、拘限声病、烦杂等等,还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不知丧于雅正”[1]100。本来任何文体都未必不可以表现“雅正”,但因为越来越偏向艺术形式与技巧,导致“雅正”精神荡然无存。“雅正”精神也即儒家“风雅”精神,“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19]269“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19]272以“诗言志”为诗发生学,以成“教化”为最终目的,达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创作效果和“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9]270的社会效果。“老于儒家”[1]111的元结不但有“文章道丧久矣”“(今之作者)系之风雅,谁道是邪”[1]37以及“风雅不兴,几及千岁”的呐喊,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忠实继承儒家“风雅”精神,“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1]37,在“儒《雅》道将废”的时候,与“二三子,旦夕相勉励。”[1]42在具体诗歌创作中,“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1]35,多伤世悯民的写作篇章。元结不但提倡“风雅”文学观——“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19]271而且有着连续一贯的写作实践,在文学精神上师法“风雅”,写作实践上传承“风雅”。
其三,“文道合一”之“真淳”。“时俗”文学创作丧于“雅正”,一方面可能是太过于注重艺术形式与技巧的追求,忽略了精神追求而陷于烦杂,而另一方面,直接忽然道德人格与文章创作的关系,使文学创作全面功利、工具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时俗浇薄化、文章淫靡化。而元结“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的救治之方也相应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创作上有意避免容易导致“淫靡”的文体写作。而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道德人格培养上。元结持“元气自然”道德观,期望达到一种德充于内而浑然无迹的“元化”状态,拥有这种道德人格的人可名为“大雅君子”,元结曾在《吕公表》中如是描写这种“盛德”:“公明不尽人之私,惠不取人之爱,威不致人之惧,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直不指人之耻,故名不异俗,迹不矫时,内含端明,外与常规,其大雅君子全于终始者耶!公所以进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颂元化者,谁预颂乎?于戏!公将用于人而不见其用;人将得于公而公忘其所得乎?”[1]109这无疑仍然是元结的夫子之道,或者是元结期望达到的道德修养高度。在人格修养过程中,元结以“不从德于时俗”“聱牙”“非人情”的态度与世俗保持距离,并在日常中作道德上严格的自我要求和反省,更能结合现实实践培养言而能行的道德能力。道德人格化的元结,一切言、行无不带有自身道德色彩,文学创作自然不会例外,除了大量“箴铭”类作品,其它描写山、林、泉、石的作品同样丰富,这些其实也是其退让、淡泊、隐逸人格的外在体现,对奔竞之徒和急功近利之辈,亦是一味清凉剂。
五、结语
元结文学创作具有“真淳”的特色,不但一篇、一种文体、一时如此,几乎全部作品皆是如此。尝试讨论其写作的内在理路,首先注意到元结鲜明的道德人格,面对“浇浮”之世既充满危机感,也充满救时拯世的自觉使命感。其次在元结道德人格的自我培养上,既追求“元气自然”的道德高度,又重视在现实实践中完善自我。最后认为元结创作达到“文道合一”的高度,是道德人格和文章写作的融合。“文道合一”的创作观,决定元结文章写作排斥烦杂、淫靡的内容以及拘限声病的文体,“箴铭”类文体是其主要写作对象,尤其是“箴戒”主题写作体现在各种文体中。“风雅”精神是元结的文学追求,其文学创作是对“风雅”精神的接受和继承。元结作品,无论文辞、文意以及文学精神,无不体现出“真淳”的创作特色。另外,立足内在理路分析元结文学创作,并非排除或者说没有外缘影响。家庭和社会环境等都会对元结文学创作、道德人格培养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这属于另一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