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外一篇)
曹洁
大片大片的芭蕉叶,依窗而绿,一盘樱桃正红;一只蜻蜓,自由自在,飞来飞去;桌子上,一本摊开的书上闲放着一支燃着的香烟,青烟袅袅。午后,主人依窗读书,倦了,起身走走。或者在床榻上躺躺,一回头,看着如此闲境,兴笔所至,成就了这幅生活情景特写。
这是丰子恺的漫画《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素净而有韵味,出离了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的苍凉:
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很久很久以前,某年某月某日,蒋捷乘船,水过吴江,一舟飘摇,岸上酒旗,迎风招摇,诱惑着,他却无法止步。那是故乡的味道,却不是故乡。恍惚间,舟子已过秋娘渡,再过泰娘桥,风也潇潇,雨也潇潇。樱桃红了,芭蕉绿了,不知归去何时,一洗羁旅之风尘?
古人蒋捷,却以现代蒙太奇手法,巧妙剪辑了一组意象,点细节,染背景,点染结合,写尽伤春的惆怅以及久别思归的怅惘。他感慨岁月无情,年华易逝,眼见时光的妙手催红了樱桃,染绿了芭蕉,把韶华人生远远抛后,自己却长年客居异乡,不得归去。
蒋捷词大多凄清,只为客袍风尘太过沉重,压得他撑不起生命的向度。一曲《虞美人·听雨》是他孤寂一生颠沛流离的真实写照: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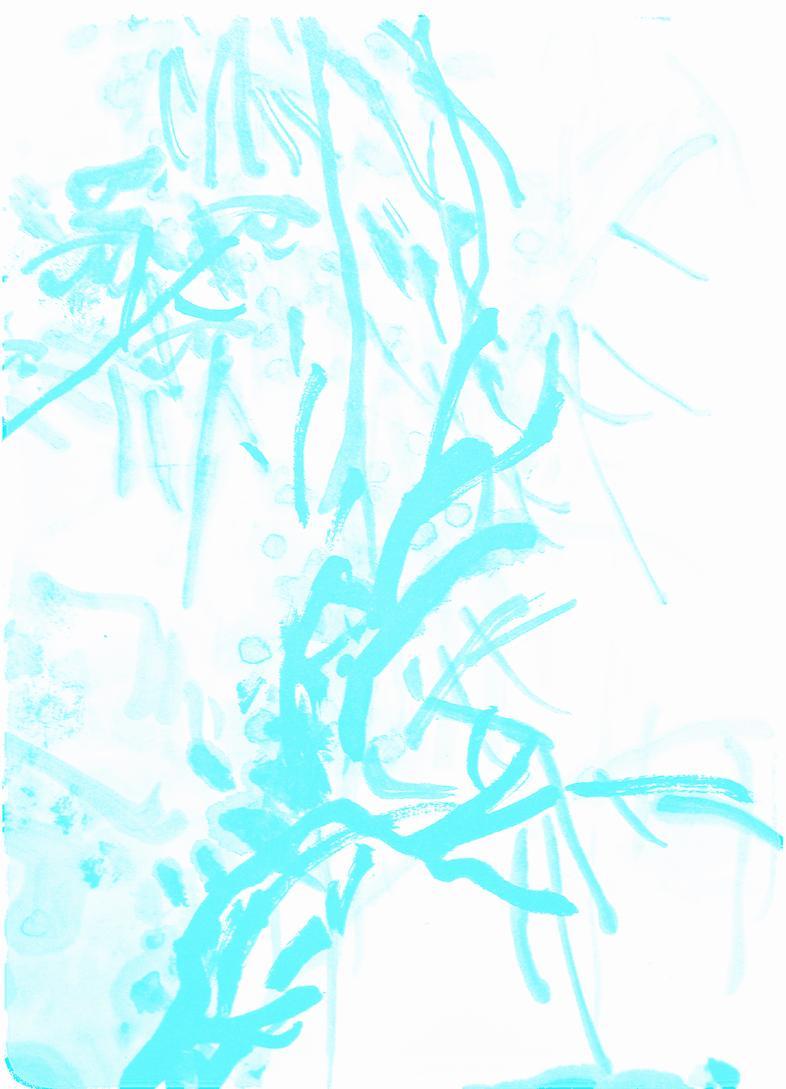
这阕词以三幅象征性画面,概括了一个人从少到老,在环境、生活、心情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三个时期、三个场景、三种心境,读来倍感凄然。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年少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连听雨都浪漫与悠闲,红罗帐中,轻软细雨温柔乡;“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壮年漂泊,客舟听雨,水天辽阔,暗云低沉,西风骤急,孤雁哀啼,一腔旅恨,万种离愁,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老年衰微,鬓发星星,寄居僧庐,深听夜雨,裘冷心寒,处境之萧索、心境之凄凉、思绪之木然,如秋窗寒雨,点点滴滴,细细数过,难耐天明。
当然,这不只是蒋捷一生颠沛流离的真实写照,也是每个人生命阅历的收纳总结,没有谁能够逃脱这个轨迹。这是上苍赋予人的权力和责任,抑或责难,让你在安享幸福的同时接纳与之俱来的悲怆和苍凉;这也是人赋予文学的审美体验和社会功用,那一场又一场雨,下了,又停了,又下了,当某一日雨不在的时候,蒋捷为我们留下了淅淅沥沥的雨声。
大概这就是文学能够赋予生命的唯一真正意义。
抛却意境凄清,这两阙词给我们同样的惊醒:“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以实落笔,不仅仅是眼前景,更沉淀着作者对故园的美好回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樱桃红,芭蕉绿,客袍湿,游子客居,家园难归。诗中既有对故土风物的怀念、对孤旅生涯的怅惘,更有对时光易逝的感叹,一切意味,尽在一红一绿。
“流光容易把人抛”,以虚言实,直抒人生苦短的无奈。似乎人活一场,其实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旅程,出歌楼、下江岸、上渡船、宿僧庐,庐下听雨,风雨兼程。那一场生命中的雨从未停息,自我年华却已走过最要紧、最美好的一段。
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蒋捷之词对生命意境的概括无端凄凉,令人悲伤沮丧,但在珍惜流光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记取。听雨固然凄然,但也是平常事,也是好事,不失为一种人生意趣。其实,读书、听雨、看阳光,都是一种境遇、一种心境、一种况味,阳光和霜雨都是快乐与幸福。有一位朋友说他家的院子里盛满了阳光。院子盛满阳光,真是好,一个人若有心境去感受阳光、倾听阳光、造设阳光,更是生命的美遇。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说:“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看看阳光。”为了看看阳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听听雨,又有何妨?倘若生命之树根植大地,背负苍天,向着阳光,世风冰霜再怎么冷,也不会冷彻心骨。
丰子恺先生走出凄冷词境,只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即便时光如流水,人在水上漂,瞬间无影无踪,我们也要尽享水中温柔,倾心守护真善的温度。任它芭蕉绿、樱桃红,只要每一个日子都柔软着韶光的味道,有如水仙的花瓣,温柔而伸展。
一个人活着,总会在某些时刻遇见美好,好人、好事、好书、好风景。那些时代、那些人,已然远去,但樱桃在红,芭蕉也绿,人生美意,何处更寻?蒋捷与丰子恺留给我们的,远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外。
松间的音乐队
明代倪允昌《光明藏》曰:“听瀑布,可涤蒙气。听松声,可豁烦襟。听檐雨,可止劳虑。听鸣禽,可息机营。听琴弦,可消躁念。听晨钟,可醒溃肠。听书声,可束游想。听梵音,可清尘根。”这段话有疏淡清凉的意味。瀑布、松声、檐雨、鸣禽,乃自然之音;琴弦、晨钟、书声,乃人类之声;梵音,则是超越凡尘之上的佛音。
自然造化,人生七窍,大概就是为了与自然之间交相呼应。我们的眼、耳、鼻、口,一定不是只停留在感官知觉,而是需要打开通道,呼出吸纳,与万物生灵,彼此安生。如此,才能做到——瀑布荡涤蒙气,松声穿透烦襟,檐雨流走劳虑,鸣禽止息机营,琴弦可消躁念,晨钟可醒溃肠,书声可束游想,梵音可清尘根。从这个意义上说,倪允昌不只是在讲听觉,而是在说天籁,说性灵,说礼乐。
古语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音乐的规律与宇宙的规律是相通的,自然界本身含有音乐所具有的许多因子,诸如节奏、韵律、和谐等等。庄子是极懂得音乐艺术规律的人,他说“至乐无乐”,把整个宇宙自然、天体运行、万物互动,看成是完美和谐的乐曲。在庄子看来,音乐是以大自然为蓝本而创造出来的,蓝本必定模仿于模本,自然美必定胜过人为美,无声之乐必定高于有声之乐。大约这就是“至乐无乐”之深义所在。广袤的自然舞台上,序幕徐徐开启,鸟鸣、水流、风声、云影,天乐舒缓而起。没有庞大的阵容,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高级指挥,只有饱满的庄严,万物伴着无形而有韵的节奏各自生发,演奏着浑然天成的旋律。
这神秘的声音组合被人类称作“天籁”。
生而为人,音乐对心灵的征服是彻底的,有时候,音乐对我们只是一种性灵释放的契机;更多时候,聆听音乐是对美的虔诚与臣服,我们必须以极低的姿态,仰望和观照一种极致之美。艺术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丰子恺先生作过一幅画《松间的音乐队》:一弯流水、一道疏离、两间瓦舍、三棵松树,树上鸟窝,有参天的古意。春天来了,天地是静的,松树是静的,房屋是静的,流水和飞鸟是动的。鸟儿飞翔着、盘旋着、繁衍着,勃勃生机,唱和不息。静的屋安慰了累的人,静的树栖息了飞的鸟,流水则隔出远离尘嚣的空灵。人与物,物与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詩画合一,这画就是好诗,不只好在物象背后隐藏了夕阳、流水、老屋、松树、窝巢、春禽等活泼泼的意象,更好在物象之间淙淙而动的乐流。读着这幅画,宛如聆听天籁,世界没有芜杂,没有掠夺,无须夸饰,不用炫耀;万类物动,秩序井然,该放则放,该收就收,收敛自如,张弛有度。
人生最好光景,莫过如此。
一个草原之夜,旺旺的篝火旁,我听过最美的声音——呼麦。呼麦,图瓦文的中文音译,原指“喉咙”,借指“喉音”,是一种借由喉咙紧缩而唱出“双声”的泛音咏唱技法,即一个人在演唱时同时发出两个高低不同的声音。这种古老的吟唱艺术已有数千年历史,声乐专家之“高如登苍穹之巅,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据说远古时期,先民在深山中活动,溪水湍流,瀑布飞洒,山鸣谷应,声闻数里,动人心魄。他们便出声模仿,以波浪起伏之声,模拟动物形象,赞美骏马草原,歌咏自然风光,“呼麦”诞生了。
呼麦,那是一种无法以语言描述的天籁,抑或是伤怀之美。那声音在演唱者胸腔内蕴藏许久,再从喉底发出,悠悠远远地,似乎往一个幽深幽深的隧道里钻,诱你深入。那是时间的隧道,也是生命的旅程,你会不自觉地随着那声音钻进去,钻进去,回到昨日,回到童年,甚至回到前世。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无法忘怀那种摄人心魄的声音。
大道之乐源于自然之音,起于宇宙之始,从未停止,也未消失,人类却在与它同行的途中渐渐疏远了它。其实,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那是别人探不到的森林,那里只用来培植天籁。语言终止之处,就是音乐的开始,没有人的世界,音乐同样鸣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