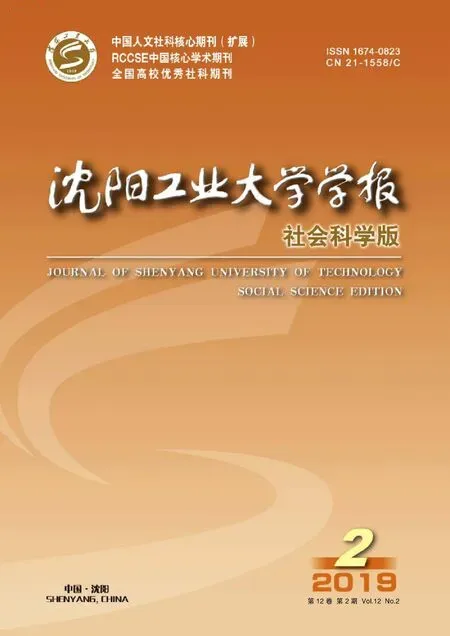基因编辑技术的制度规制路径探析*
董 妍, 夏佳慧
(天津大学 法学院, 天津 300072)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基本范畴
基因编辑技术①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成簇的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是在基因组水平上对目的基因序列进行靶向性修改的技术,通过在基因水平上实现错误DNA序列的矫正,彻底治愈遗传疾病。在医学应用以及微生物和动植物的经济性状改良以及农业育种、医学治疗、环境保护和工业微生物改造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
目前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有三种:基础研究、体细胞基因编辑、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基础研究,即研究者在实验室对体细胞、干细胞系、人类胚胎的基因组编辑所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试验,通过实验室研究可以从分子层面上了解疾病的形成原因及发展过程,也为很多疾病的治疗或预防找到新的途径和方法,对生物技术及医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细胞基因编辑,即在临床实践中运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体细胞进行修饰改变,这种编辑方式只会对个体的基因及性状产生影响,不会遗传给后代。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可直接干预生殖细胞或胚胎,使其产生的变化会从一代遗传给下一代,也被称作生殖系修饰[2]。
基因编辑技术作为科学界和医疗界的交叉技术,主要应用于精准医疗与精准育种两大领域,为解决许多医学难题提供了可能。科学家们的不断创新突破往往在解决技术上“能不能”问题的同时,忽略了“该不该”的伦理思考[3]。从1978年“试管婴儿”的问世,到1997年“克隆绵羊”的出现;从2015年黄军利用CRISPR/Cas9对导致人类患β型地中海贫血症的致病基因进行编辑,再到2018年贺建奎公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些事件使得基因编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话题,而是已经涉及到法律伦理与道德的社会问题。
“基因编辑婴儿”所采用的技术并不稀奇,只是囿于脱靶风险和伦理道德的约束而未被应用于临床,这是出于对伦理的敬畏、对生命规律的遵循[3]。在人类不断追求科技进步的今天,科技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探索,更承载着人类不可知的未来发展方向。尤其是极具争议性的基因编辑领域,其“改造人类”的可能性、想象性以及不可控性,足以让每一个人忧虑。一直以来,缓解这种忧虑的关键就是科学伦理与法律[4],因此在基因编辑技术领域法律和伦理不能缺位。
二、基因编辑技术规制现状
1. 国外基因编辑的规制经验
基因编辑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无法预估的灾难。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立法迫在眉睫,如何在有效规制和促进生物技术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是立法的关键。就各国现有规范而言,鲜有国家有专门针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约束的立法,甚至在医疗临床应用领域也无直接规范文件,部分国家在其他领域规范中有所涉及。各国因人文和科技的差异,对基因编辑技术所持的态度和包容性呈现出多样化,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规制程度也有所不同。
基因编辑技术成本低,可操作性强①买一把基因编辑刀仅需150美元,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负担起的价格。,使很多“科学狂人”有机可乘。虽然基因编辑技术日趋成熟,但其脱靶风险一直未彻底解决,因而多数国家对其仍持相对保守态度,仅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科学家们进行基因编辑活动,对凡是涉及人类伦理以及安全的问题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欧美国家在基因编辑技术医疗临床应用中一贯重视伦理审查制度,美国作为科技领先国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第一大国,更是对伦理问题尤为慎重。生物医学的伦理和监管问题由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主管,主要通过财政制约方式约束可能危及伦理的生物医学研究及治疗行为。早在1994年美国政府签署了人类胚胎研究禁令,禁止财政收入用于公共部门进行任何有关胚胎的研究;1998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专门制订了《关于人类多能干细胞研究伦理规则》,表明政府对相关研究作了有限度的支持。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2016年美国众议院在财政年度开支法案中明确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使用财政收入进行与人类胚胎编辑有关的产品评估研究或临床申请[5]。此外,日本也在伦理层面对基因科技进行严格约束,绝对不允许将编辑过的人类受精卵的基因应用到临床和辅助生殖中[6]。
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有些国家为了能有效地避免基因编辑带来的问题,甚至放弃基因编辑技术广阔的前景,在法律层面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了严格的管控,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立法,甚至在刑法层面也有涉及。例如《匈牙利刑法典》在第十二章“侵害人身罪”对其进行立法约束:第二节“妨害医疗程序、医学研究秩序与有关医疗程序的自主权利罪,妨害有关人类基因结构的医疗程序罪②第173条A款:1.任何人针对人的基因结构、胎儿的基因结构或者人的胚胎的基因结构,实施一项目的在于改变这些基因结构的程序的,构成重罪,处5年以下监禁。2.如果第1款所规定的程序永远改变了人的基因结构、胎儿的基因结构或者人的胚胎的基因结构的,处2至8年监禁。”,第174条A3条款就有补充:“出于《保健法》规定的目的实施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程序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匈牙利刑法典》对人类胚胎或配子进行研究的行为也有规定罪与刑:第173条E1条款规定任何人未获得《保健法》规定的许可证或者超出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对人类的胚胎或者配子进行医学实验或者基于科学目的制造人类胚胎的,构成重罪,处5年以下监禁。第173条F1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人出于操纵某一胚胎基因结构的目的实施人类胎儿科学实验的,构成重罪,处5年以下监禁。《哥伦比亚刑法典》在第一编侵害生命和人身安全罪中就有一章是专门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立法③第八章操纵基因罪第132条规定:非出于治疗、诊断或者生物学、遗传学、医学领域的旨在减轻个人或者人类的痛苦或者改善其健康的相关科学研究之目的,以改变基因类型方式操纵人类基因的,处16个月至90个月监禁。。《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刑法典》第二十章侵害人类健康的犯罪第一百八十一条“非法移植人体器官及改变染色体组罪第五款”,行为人并非出于医学预防、医学诊断或者医学治疗之需要,试图实施或者已经实施旨在修改人类染色体组的实验活动的,或者以改变未来人类染色体组为目的,试图实施或者已经实施旨在修改人类染色体组的实验活动的,处5年以下监禁。西班牙对基因编辑也持绝对禁止的态度,且用最严厉的刑法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了管制④在《西班牙刑法典》第五编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中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为消除和减轻严重疾病和缺陷,改变人类基因的,处二年至六年徒刑,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任任务的权利七年至十年。。
除了上述国家在刑法领域予以规定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法》⑤加拿大2004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法》对违法编辑人类基因组行为给予最高10年的监禁处罚。和《禁止克隆人法案》⑥澳大利亚2002年出台的《禁止克隆人法案》明确规定,改变胚胎细胞的基因组是违法行为,违者或面临15年监禁[10]。,对违法编辑人类基因组行为给予严厉的监禁处罚[8]。
相对于上述国家,韩国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规制更为严苛。在十余年前,为挽回黄禹锡事件的影响,韩国科技政策制定了堪称严厉的生命伦理法案①2017年,被称为“基因剪刀”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也曾一度引发热议。英国《自然》杂志将一篇美国科学家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正了未被植入子宫前的人类胚胎中的、与遗传性心脏疾病“肥厚型心肌病(HCM)”有关的基因变异的论文公之于众,但随后韩国学者表示:“是韩国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导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们是因为受到韩国生命伦理相关法律的限制,研究团队只能将开发好的基因剪刀技术提供给外国同行进行实验,最终共同完成。但通过这个事件也可得知,虽然法律存在,但却无法阻断科学家们对科学探索的向往。。这些持绝对禁止态度的国家固然可以避免很多因基因编辑带来的风险,但其对科技进步的阻碍也是显而易见的。
2. 我国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态度和规制现状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层级上直接涉及基因编辑临床研究的规定只有两部,分别是《药品管理法》和《侵权责任法》[9]。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促进法》第二十九条、第五十五条也作了相关规范②第二十九条 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第五十五条 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弘扬科学精神,遵守学术规范,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不得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弄虚作假,不得参加、支持迷信活动。。但该条款仅对科学技术与研发活动和科研人员进行了一个概括性的约束,并未直接针对基因编辑技术。
在行政法规层面,与之相关的仅有《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尚未通过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送审稿)》,但从内容来看,也并未对基因编辑行为进行直接约束。
在部门规章层面,《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二十六条③第三条 干细胞临床研究必须遵循科学、规范、公开、符合伦理、充分保护受试者权益的原则。第二十六条 干细胞临床研究人员必须用通俗、清晰、准确的语言告知供者和受试者所参与的干细胞临床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内容,预期受益和潜在的风险,并在自愿原则下签署知情同意书,以确保干细胞临床研究符合伦理原则和法律规定。就干细胞临床研究及从事该研究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循的原则予以规定。《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具体规定了凡是关系到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应当符合的伦理原则,在伦理层面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约束④第十八条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应当符合以下伦理原则:(一)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和保障受试者是否参加研究的自主决定权,严格履行知情同意程序,防止使用欺骗、利诱、胁迫等手段使受试者同意参加研究,允许受试者在任何阶段无条件退出研究。(二)控制风险原则。首先将受试者人身安全、健康权益放在优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利益,研究风险与收益比例应当合理,力求使受试者尽可能避免伤害。(三)免费和补偿原则。应当公平、合理地选择受试者,对受试者参加研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对于受试者在受试过程中支出的合理费用还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四)保护隐私原则。切实保护受试者的隐私,如实将受试者个人信息的储存、使用及保密措施情况告知受试者,未经授权不得将受试者个人信息向第三方透露。(五)依法赔偿原则。受试者参加研究受到损害时,应当得到及时、免费治疗,并依据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得到赔偿。(六)特殊保护原则。对儿童、孕妇、智力低下者、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受试者,应当予以特别保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⑤第三条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六条 申请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具有与开展技术相适应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二)具有与开展技术相适应的技术和设备;(三)设有医学伦理委员会;(四)符合卫生部制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要求。第十二条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经过批准并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第十四条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当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涉及伦理问题的,应当提交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第十九条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对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人员进行医学业务和伦理学知识的培训。分别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目的、实施场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对该技术操作人员的要求进行了规定,同时该办法明文规定了几种禁止实施的技术。
在规范性文件层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规定了有利于患者的原则、知情同意的原则、保护后代的原则、伦理监督的原则、保密原则、严防商业化的原则、社会公益原则等。《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五条规定了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的4种获得方式;第六条对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进行了规定①第五条 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只能通过下列方式获得:(一)体外受精时多余的配子或囊胚; (二)自然或自愿选择流产的胎儿细胞;(三)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获得的囊胚和单性分裂囊胚;(四)自愿捐献的生殖细胞。第六条 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 (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三)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实行分级管理,基因编辑技术则属于高风险等级。
综上,我国在基因编辑方面的立法难成体系且规范层级较低,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文将进行详细阐述。
三、我国基因编辑技术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1. 存在的问题
(1) 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界定模糊
在过去的医疗法律概念中,医疗行为的定义范围往往过于狭窄,医疗行为被视为被动、消极的诊疗工作。目前,医学服务人类的范畴不仅包括治疗行为,而且还包括其他非治疗疾病或进行疾病预防医疗行为。而非治疗性医疗行为又分为“实验性医疗行为”与“其他以治疗疾病或预防疾病为目的的医疗行为”。“实验性医疗行为”又细分为“治疗性实验医疗行为”与“研究性实验医疗行为”两种[8],前者是以对病人的临床治疗为主要目的的实验性行为,后者则是对接受试验者(多为健康的自愿者)所为的基于纯科学研究目的的试验。
一般情况下,对医疗行为的法律规范应当严于非医疗行为。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一部法律对医疗行为作出准确界定,导致实践中对医疗行为与非医疗行为的边界判断不清,特别是在基因科技、干细胞研究、保健预防等前沿领域,科研与医疗常常混同,基于“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的基本原则,在上述模糊不清的地带就容易出现法律缺位和滞后的问题[9]。因此,我国法律界、医学界连同科学界急需厘清基因编辑的界限问题,并在立法层面上考虑对基因的管理。过去科研管理的监管都是侧重药品和医疗器械,今后也可以考虑将基因操作上的科研、临床技术应用的管理上升到法律层面。相关规定在成熟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层面,或许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2) 规范层级低,罚则缺失
目前,我国关于基因编辑的标准及法律规范还不完善,相关规定仅散见于卫生部1993年制定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国务院1998年制定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等。同时,我国现行规范中缺少罚则。此次基因编辑婴儿行为违反了原卫生部在2003年7月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10]。同时也违反了科技部和原卫生部2003年12月制定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的“14天法则”,该原则中规定“不能将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等技术改变了基因的胚胎细胞存活超过14天,同时,也不能将修改了基因的胚胎细胞植入人的生殖系统。”即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必须遵守“14天法则”。
另外,我国基因治疗立法严重不足,虽已制定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关于基因科技的相关规定,但并未有专设于基因治疗的法律规范,且现有规范罚则均无相关规定。这些不足已成为基因编辑技术人权和伦理保护的依据,不利于预防和控制基因治疗等尖端医疗技术的滥用,无法对其提供适当的保护。
(3) 伦理审查法制化程度不同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日益发展与成熟,它将带来的风险及伦理问题与转基因技术并无本质差别,甚至会远远超过转基因技术应用。任何严肃的科学探索行为都应把人类伦理作为第一要素加以考虑,都应以有益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作为终极使命。虽然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治疗各种医学疾病是可以得到伦理保护的,但是在新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同时更应当把技术对人类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内[5],人类应对基因编辑技术持有谨慎的态度。
2015年黄军事件中,尽管当时黄军等人获得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符合相关法律,且研究时使用的是废弃的不能正常发育的人类胚胎,并于48小时后终止实验,但该论文在投稿时仍然由于伦理道德问题被《自然》和《科学》杂志拒稿[6]。
贺建奎案的调查结果显示,贺建奎的基因编辑虽然确实通过了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但伦理委员会成员资质和报批程序均存在问题,且深圳市卫生计划委员会并未收到此项目的伦理审查报备,因此,这个项目并非通过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审查。
根据我国2018年1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凡是涉及重大伦理问题的,属于负面清单范畴的医疗技术,必须报请相关政府部门备案或批准。我国伦理审查制度存在较大漏洞,如伦理审查机构门槛较低、伦理委员会人员资质不清、审查程序不系统和审查内容不全面等问题,亟待相关立法予以明确。
2. 完善建议
(1) 尽快启动立法,提高规范层级
技术可控,人心难测。人类应用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潜在性和不可逆性决定了约束其的法律应专门化、全面化和具体化[5]。西方众多国家对基因编辑在人体的试验均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范予以禁止,我国虽然也有相关规定,但规范层级较低,强制性和威慑性较弱,亟需完善。我国对生命科技犯罪立法规制起步较晚,虽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现了从单行规章、技术规范到综合管理的过渡[11],但由于历史局限性与立法滞后性等问题,我国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规制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12],建议尽快启动生命科技立法,提高立法的规范层级,在刑法领域增设对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并且严格禁止辅助生殖范围内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同时明确惩罚措施。
(2) 设计法律规制原则与框架,涵摄更多行为
上文法律法规构成了我国目前基因编辑立法的基本法律规制框架,就此基本框架而言[13],我国对基因科技的规制不够全面,有很多行为一旦发生,我国没有相关法律对其进行事后的惩治。在实践中难以起到有效的规制作用。现有法律规定中管制范围过窄,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规范,结合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尽快完善法律,明确规制的框架,使其涵摄更多的行为。
(3) 伦理委员会应切实发挥作用,细化伦理审查程序
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层面尚未建立强有效的伦理审查制度和科学的伦理审查程序,致使伦理委员会不能切实发挥作用,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管,理应未雨绸缪,用伦理道德辅助法律法规来加以规制,建立严格的准入和审查制度[14]。因此建议在伦理审查制度中细化审查程序,完善需进行伦理审查的内容。如将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相关研究实行备案制,对研究项目的伦理评估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应以书面的方式提交伦理委员会,由更权威、更高级的医学伦理机构进行严格管理;每个研究项目都应当被提交给省级以上伦理委员会,且应当保证其中立性,对其伦理可接受性进行独立审查。通过在伦理上对其进行严格的把控,不仅可以将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可以减少法律的应用空白,节省我国的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