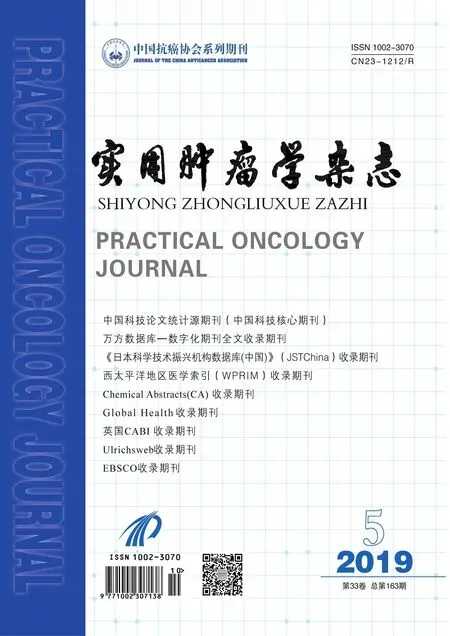乳腺癌抗肿瘤血管治疗的临床进展
李 磊 张清媛
血管生成在乳腺癌肿瘤和转移发展中的重要性已得到充分证实,阻断这个过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方向[1]。抗血管生成治疗中研究最多的是贝伐单抗(Bevacizumab,BEV)。贝伐单抗是一种重组人源化IgG1单克隆抗体,可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靶向结合,减少新生血管形成,抑制肿瘤生长。贝伐单抗于2008年获得FDA批准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此前在一线治疗中,贝伐单抗联合化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几乎是单独化疗的两倍[2]。然而,随后在其他试验中发现PFS增加不明显,更重要的是,已证实其对总生存期(OS)没有影响,导致FDA撤回批准。另一种靶向VEGF信号的策略是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如舒尼替尼和索拉菲尼)抑制信号转导,特别是VEGF受体的信号转导[3-4]。在此,本文回顾了抗血管生成治疗乳腺癌的背景和证据,并对这些治疗乳腺癌的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
1 贝伐单抗
1.1 术前新辅助治疗
NSABP B-40试验研究包括1 186例HER 2阴性乳腺癌患者,在标准新辅助治疗方案的基础上联合贝伐单抗观察治疗结果。联合贝伐单抗后,以病理完全缓解率(pCR)为主要终点的比例显著升高(34.5%vs. 28.2%),其中激素受体阳性患者的pCR影响最大(15.1%vs. 23.2%)。经过56.4个月的中位随访后,尽管预设的二级终点无病生存期(DFS)没有受到明显影响(HR=0.80,P=0.65),贝伐单抗治疗后OS升高(HR=0.65,P=0.004)。GeparQuinto试验将1 948例HER 2-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新辅助化疗方案EC-T联合/不联合贝伐单抗15 mg/kg,治疗4周期后无临床应答(稳定或进展)的患者再次随机接受紫杉醇或紫杉醇联合依维莫司治疗。联合贝伐单抗组pCR增加并不明显(18.4%vs. 14.9%),经过3.8年的中位随访后,各组DFS及OS无统计学差异,以上试验结果表明贝伐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无临床获益。
1.2 术后辅助治疗
BEATRICE试验[5]研究贝伐单抗对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主要评价终点无病生存率和总生存率(5年无病生存率:80%vs. 77%;HR=0.87,P=0.18;5年总生存率:88%vs. 88%;HR=0.93,P=0.52)无统计学差异。在评价HER 2-乳腺癌患者辅助化疗中联合贝伐单抗疗效的E 5103试验中OS(HR=0.89,P=0.41)无统计学差异[6]。
一项Ⅱ期的实验研究包含34例炎性乳腺癌(IBC),从2010年7月—2013年12月。初发/复发IBC患者每三周接受1次卡铂、紫杉醇联合化疗及环磷酰胺规律口服6个月化疗,HER 2+患者加用曲妥珠单抗,ER和/或PR≥10%患者加用内分泌治疗,术后继续口服卡培他滨和环磷酰胺6个月。主要有效终点为病理完全缓解(pCR)和客观反应(OR)。获得OR 30例(88%,95%CI:73%~97%),pCR 10例(29%,95%CI:15%~48%)。HER 2+肿瘤获得pCR比例明显高于患者三阴性或Luminal B(HER2-)乳腺癌(57%vs. 20%,P=0.019)。经过4.4年的中位随访后,5年无病生存率为58%,5年总生存率为72%,pCR的延长转化成了无病生存率(P=0.12)和OS(P=0.029)的获益[7],此研究结果表明贝伐单抗对HER 2+的IBC可能有临床获益,是否能应用于临床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证实。
1.3 转移性乳腺癌中的姑息治疗
1.3.1 贝伐单抗联合化疗治疗转移性乳腺癌 E 2100试验将673例转移性女性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紫杉醇联合/不联合贝伐单抗两组,结果显示联合贝伐单抗组患者中位PFS增加5.9个月,OS并没有明显改善。Avado50试验将736例HER 2-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按1∶1∶1的比例随机分为贝伐单抗7.5 mg/kg联合多西他赛,贝伐单抗15 mg/kg联合多西他赛和多西他赛联合安慰剂三组,经中位随访25个月后,各组中位PFS分别为9.0、10.1、8.2个月,而各组OS无统计学差异。RIBBON-1试验入组了1 237例复发或转移后尚未化疗的HER 2阴性乳腺癌患者,按2∶1的比例随机分为化疗联合/不联合贝伐单抗两组。化疗方案为卡培他滨单药或者以紫杉烷或蒽环为基础,每3周给药一次。联合贝伐单抗组患者的中位PFS较安慰剂组提高(卡培他滨方案:8.6个月vs. 5.7个月;紫杉烷或蒽环方案:9.2个月vs. 8.0个月)。与前两项研究结果一样,各组OS无统计学差异。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在一线化疗方案中联合贝伐单抗可以提高PFS,但是对OS结果无明显影响。
AVF2119G试验研究了卡培他滨在二、三线治疗时联合贝伐单抗的有效性,462例转移性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卡培他滨联合/不联合贝伐单抗15 mg/kg两组,联合贝伐单抗组中位PFS及中位OS都仅提高0.6个月。RIBBON-2试验研究比较单纯化疗与贝伐单抗联合化疗治疗HER 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随访时间中位数为15个月,联合贝伐单抗组中位PFS提高2.1个月,中位OS提高1.6个月。TANIA试验包括494例HER2-使用过贝伐单抗后出现复发或转移的患者,患者随机接受化疗联合/不联合贝伐单抗治疗,经过16个月的中位随访后,联合贝伐单抗组中位PFS提高2.1个月。以上研究表明在二、三线化疗方案中联合贝伐单抗后患者的PFS及OS无统计学差异。
1.3.2 贝伐单抗联合内分泌治疗转移性乳腺癌 在Ⅲ期CALGB 40503试验中[8],350个激素受体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随机接受来曲唑联合/不联合贝伐单抗治疗,结果显示,联合贝伐单抗治疗组患者中位PFS(15.6个月vs. 20.2个月)和中位OS(43.9个月vs. 47.2个月)都有提高。LEA试验研究了绝经后晚期乳腺癌患者使用贝伐单抗联合内分泌(来曲唑或氟维司群)与单独内分泌治疗,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提高了4.8个月和0.3个月[9]。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贝伐单抗在联合内分泌治疗时PFS有明显获益,但是OS获益不明显。
1.4 贝伐单抗药物毒性
总体来说,贝伐单抗耐受良好。贝伐单抗单药治疗时最常见的副作用是高血压和蛋白尿,但通常没有症状或可控制。罕见的严重毒性反应包括左心室功能不全、动脉血栓栓塞、大出血、颌骨坏死、胃肠道穿孔或瘘等[10]。
1.5 贝伐单抗预测生物标记物
贝伐单抗没有产生显著的临床获益,部分原因可能是没有明确的生物预测标记物可以预测药物在何种类型乳腺癌患者中可以发挥作用。上述所有报告的试验都是在没有经过特定条件筛选的乳腺癌患者中进行的,选择特定的标记物的患者是否会影响贝伐单抗的疗效需要研究加以证实。
有研究显示VEGF血浆浓度对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有一定影响,比基线VEGF血浆浓度高的患者预后较差,治疗效果可能更好[11]。MERIDIAN试验旨在评估VEGF对贝伐单抗疗效PFS的预测价值。以VEGF血浆浓度5.05 pg/mL作为基线浓度,将患者按高/低VEGF水平分为两组。研究结果显示VEGF血浆浓度对贝伐单抗治疗效果无预测价值[12]。碳酸氢酶IX(CAIX)是一种在实体肿瘤缺氧反应中过度表达的蛋白质,GeparQuinto试验的生物标记物分析表明CAIX具有预测价值[13],CAIX基线水平较低的患者在新辅助化疗后获得pCR的比率明显较低,联合贝伐单抗后显著改善(12.2%vs. 21.3%),但是DFS却没有显示出明显获益。由于表观遗传修饰可能导致血管生成的异常调节和治疗药物耐药,作者研究了DNA甲基化模式对贝伐单抗疗效的影响。根据ORR和PFS,并考虑ER的表达,将患者分为应答者(R)和无应答者(NR)。对80例贝伐单抗治疗的乳腺癌患者进行了甲基化水平(Δβ>0.15或Δβ<-0.15)强烈变化的基因位点的鉴定和进一步研究显示,9-基因和3-基因甲基化信号都可以区分R和NR,在以贝伐单抗为基础的转移性乳腺癌(MBC)治疗中,可以帮助鉴别使用贝伐单抗中有更大获益的患者[14]。
以上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寻找单一的预测生物标记物结果都不理想,考虑到乳腺癌的异质性,以及血管生成的复杂性,以后的试验研究可以尝试联合多种生物标记物观察治疗结果。
2 抗血管生成药物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2.1 舒尼替尼
舒尼替尼(Sunitinib)是一种1型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抑制多种与肿瘤增殖、血管生成和转移有关的酪氨酸激酶活性,作用靶点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血小板源生长因子受体(PDGFR),干细胞因子受体(KIT)等[15]。FDA和EMA批准苏尼替尼治疗胃肠道间质瘤、肾细胞癌和高分化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一项研究比较了舒尼替尼联合/不联合卡培他滨治疗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疗效[16],中位持续时间为14.3个月,中位PFS(5.5个月vs. 5.9个月)和中位OS(16.4个月vs. 16.5个月)在两组中均无统计学差异。另一项随机Ⅲ期试验评估多西他赛联合/不联合舒尼替尼作为晚期HER 2-乳腺癌的一线治疗,也没有显示PFS或OS的获益。此外,在这两项研究中,舒尼替尼组的3~4级不良事件导致剂量减少的频率较高。尽管Burstein等的Ⅱ期研究描述了舒尼替尼治疗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有希望的结果,但随后的其他研究没有证实这一发现[17]。最近的研究正在评估在晚期癌症中联合舒尼替尼的疗效,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示出有临床获益[18]。荟萃分析结果表明,舒尼替尼单独使用或与化疗联合使用,未显示出对晚期乳腺癌患者有益[19]。
2.2 索拉菲尼
多激酶抑制剂索拉菲尼(Sorafenib)是一种2型TKI,通过与激酶受体的ATP相应位点结合使其抑制,阻止这些激酶靶点的磷酸化。索拉菲尼是一种口服多靶点小分子,用于治疗多种恶性肿瘤,包括肾癌,肝癌和甲状腺癌。在乳腺癌中,索拉菲尼已经与化疗或内分泌疗法联合进行了研究,Ⅰ期、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的数量表明,索拉菲尼在乳腺癌中的单药活性非常有限,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时,其标准剂量应减少,因为其毒性会导致其他药物剂量减少。一项研究表明索拉菲尼可能恢复对芳香酶抑制剂的敏感性[20],然而,在已经开发了其他新近可用且具有明显的阳性结果(即依维莫司,帕博西尼,恩替诺特)的靶向药物情况下,限制了索拉菲尼的广泛应用。随机化的Ⅱ期临床试验及其荟萃分析显示,当索拉菲尼与卡培他滨、吉西他滨或紫杉醇等化学治疗药物联合使用时,PFS可能会有获益,但是OS无获益。虽然Ⅲ期RESILIENCE试验的确定结果仍有待公布,但其目前的初步结果并未说明索拉菲尼在转移性乳腺癌治疗中起任何作用。关于索拉菲尼在乳腺癌治疗方面的数据有限,一些临床试验仍在进行或正在等待最终报道。由于两项Ⅱ期试验得出结论,使用索拉菲尼单药治疗不足以达到显着的临床疗效,索拉菲尼与其他药物的联合治疗仍然是唯一的研究方法[21-22]。最后,基于临床前试验的结果,索拉菲尼与HER2阳性患者的抗HER2药物的组合可能值得研究。
2.3 帕唑帕尼
帕唑帕尼是一个多特异性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231-Br-her2脑转移模型系统上能阻止73%的大脑转移瘤过度生长。Gril评估了帕唑帕尼对大脑神经炎症微环境的影响,治疗结果显示,可减少70%的p751-PDGFRb星形胶质细胞的数量,表明其可能防止乳腺癌向脑转移发展。另外,Gril用老鼠作为实验对象,使用帕唑帕尼2倍剂量时发现,可显著降低p-PDGFRb星形胶质细胞的比例。在类似实验中,大量癌细胞的脑转移被明显阻止,在231-BR模型系统中已经测试了不同的化疗药物和分子治疗药物,发现帕唑帕尼一直是最有效的预防乳腺癌细胞转移的药物[23]。帕唑帕尼与拉帕替尼联合应用于晚期HER 2+炎性乳腺癌的II期试验中,结果显示PFS没有获益,与单独使用拉帕替尼相比毒性增加[24-25]。
3 抗VEGFR抗体
雷莫芦单抗是一种人单克隆抗体(IgG 1),与VEGFR 2结合,从而阻断VEGF受体与其配体的结合。目前雷莫芦单抗已获得EPA和FDA的批准,可用于晚期胃癌、转移性结直肠癌和晚期非小细胞肺癌[26-27]。ROSE/TRIO-12试验为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纳入1 144例HER2-无法手术切除的局部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旨在评价一线化疗方案雷莫芦单抗联合多西他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患者随机分组后分别给予雷莫芦单抗(8 mg/kg)联合/不联合多西他赛治疗,均为每3周给药1次。结果显示,联用组和单药组的主要终点中位PFS(9.5个月vs. 8.2个月)以及次要终点中位OS(27.3个月vs. 27.2个月)均无明显获益[28]。而雷莫芦单抗组3级或以上级毒性反应,如疲劳、高血压、口腔炎、手足综合征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更高[29]。
阿帕替尼可以竞争性地结合VEGFR-2胞内酪氨酸ATP结合位点,抑制VEGFR-2的磷酸化及其酪氨酸激酶活性,阻断VEGF-VEGFR-2信号转导通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30]。阿帕替尼在乳腺癌中的临床研究有很多,其中一项临床研究:Hu等研究发现阿帕替尼可为乳腺癌患者带来益处[31]。另一项临床研究:Hu等[32]研究了经激素受体评估后符合激素受体(HR)阳性、HER-2阳性表达,曾经至少有一类激素或抗HER-2药物治疗失败的患者,其结果表明,不论是mPFS、mOS还是CR、PR、SD、ORR均高于常规化疗。鉴于以上阿帕替尼Ⅱ期研究结果提示给予阿帕替尼治疗可使得晚期乳腺癌患者获益[33]。
4 小结与展望
以往的抗血管生成药物研究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作为单药治疗,还是与化疗或内分泌治疗联合应用,或作为维持治疗,在转移以及早期环境中均未显示出具有临床意义的益处。尽管贝伐单抗治疗后pCR和PFS小幅增加,但这并没有转化为长期生存状况(如DFS和OS)的改善。因此,当在其他抗癌药中添加抗血管生成药物时,所报告的毒性增加以及较高的成本不会被预后改善所抵消,甚至可能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贝伐单抗应仅在个案基础上考虑,主要作为转移性乳腺癌的一线或二线治疗,并且仅与化疗联合使用,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已证实某些PFS获益。最后,我们目前不建议使用贝伐单抗辅助治疗,至少在发现一种特异性标志物来预测哪些患者可能获得足够的获益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