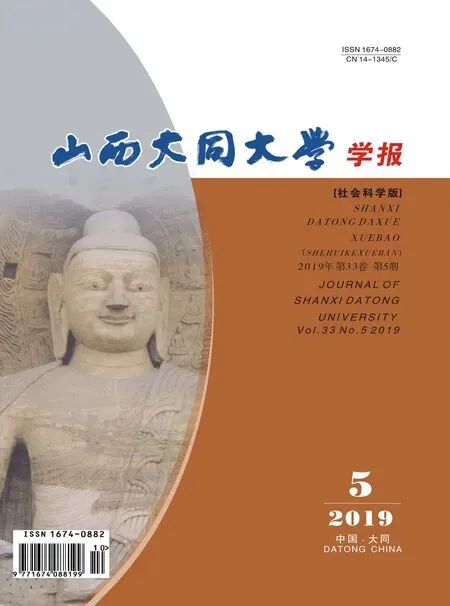重温译介路 求索无止尽
——评《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1906-1949)》
寇福明
(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一、引言
中国传统语言学就是训诂、文字、音韵构成的“小学”,始于汉代,兴于唐代,至清朝达到鼎盛。黄侃曾说,中国传统语言学是“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1](P179)但是,从学科史角度看,“语言文字之学”乃章太炎避难日本期间受到国外语言学影响,于1906年在《国粹学报》提出的现代学科称谓。从思想传播史、载意符号的转换本质来看,章太炎将国外语言学融入中国传统语言学并提出现代学科称谓,其实就是语言学层面的译介行为。凭借译介行为,胡以鲁、乐嗣炳、王古鲁、张世禄、王力、傅懋勣等学者,在20 世纪上半叶将国外普通语言学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的语言研究理论、方法和语言事实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语言学,也即中国的现代语言学。
考察中国早期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译介的历史,研究这些译介的普通语言学文献,具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述往事、思来者、明道理”的作用和意义。贾洪伟的《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1906-1949)》[2]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宗旨而写作的。以下即对这部著作的内容、特色以及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内容与特色
《汉译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研究(1906-1949)》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西方普通语言学典籍汉译(1906-1949)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而成。该书以史—论—法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方法为指导原则,以1906年章太炎受国外语言学影响提出的“语言文字之学”至1949年期间中国引进的国外普通语言学为主线,“以引进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的方法和途径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该段时期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思想的历史”,[2](前言)以期廓清中外语言学之间的源流关系。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选题目标与意义、研究问题与范围、历史与现状综述、语言学典籍译介史研究的特点与方法、译介的概念界定、本书布局结构;第二章为语言学典籍译介研究概述与分期,阐述典籍译介的历史综述和历史分期;第三章为20 世纪上半叶普通语言学典籍译介文本分析,分析译述、编译、直译、转译文本,归纳引进的术语、阐述语言学术语的流变与译介过程的走向,梳理写作出版规范的演变;第四章为典籍译介对中国现代语言学本体及其分支的影响,从语言学本体和语言学分支学科两个层面,阐述典籍译介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产生的影响;第五章为典籍译介对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归纳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梳理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译介,分析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存在的差异,指出引进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意义;第六章为余论,阐述20 世纪上半叶国外语言学典籍汉译的历史成因,分析影响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的因素,总结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的作用,归纳语言学典籍译介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指出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带来的启示,指出研究中的新发现与存在的不足。
从内容分布看,正文可分为三部分,即第一章与第二章构成的宏观文本分析,第三章独立构成的微观文本分析,第四至六章构成的宏观总结、归纳与深度分析。
正文前有代序和作者前言两部分。《代序一》以中国语文学的内容和历史价值为切入点,联系20世纪“西学东渐”中的现代语言学以及中国引入现代语言学的历史状况,引入该书的学科史意义,归纳该书所具有的历史时段选择、述史框架、中外结合的研究视角,以典籍为切入点分析史实等特点,认为该书不但是一部断代语言学史,还是一部学科史和学术史。《代序二》以古希腊和先秦的语言学思想为切入点,阐述中国语言学从无到有,从萌芽思想到体系发展的脉络,指出当前的语言学发展有必要从学科史的角度探究中国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语义学、中国现代句法学等领域的发端问题,以及国外语言学的传播路径、国外语言学的影响程度、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阶段性特征等问题,认为现有语言学断代史作品虽然提及1906-1949年期间的语言学断代史问题,但“用力不足”“文献不全”“发展脉络不完整”“分期差异大”“重大事件、重大变革、重要思想、重要术语、影响与启示等方面不够细致和系统”,指出该书以史—论—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该时间段的语言学断代史具有彰显“述往事、思来者、明道理”的史学精神。《前言》部分以当前国内语言学断代史的研究状况为切入点,勾勒该书的研究框架,交代该书的研究任务和各章节的内容,阐述该书的创新点,总结该书的研究发现。
附录部分录入了此前作者发表的《论苏联语言学汉译历史分期》《苏联语义学思想在中国:历史反思》两篇论文,以及《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译介国外语言学典籍分布表》《20 世纪上半叶语言学典籍译介者信息》《语言类型划分术语译介表》《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法研究方法演变表》《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译介大事记(1906-1949)》五篇辅助性文献,“不但能有效地与该书正文建立互动关系,联系1949年后中国现代语言学和语义学的发展动向,还能有效地说明社会文化氛围与学科发展的关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代序二)。
三、地位和意义
该书的地位和意义可从翻译学、语言学和学科史三方面加以归纳。
(一)翻译学 从翻译学的视角来看,该书属于语言学典籍译介性质,可丰富翻译学文本研究,引进科学术语,助推中国语言学发展,推进了科学译介的进程。从译介学角度看,该书打破了以文学译介为主导的局面,丰富了中国译介学的文本范畴,还丰富了中国译介学的理论建构。从实践层面看,该书为中国科学领域的早期译介提供了文献基础,可对后期的科学译介提供经验教训,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二)语言学 从语言学的视角看,该书是从译介角度考察中国现代语言学萌芽期的一部断代史,考察了语音学、音韵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以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传入路径和接受程度,呈现出中国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进程,以及训诂学与现代语义学本土化融合的脉络与成果。从这一角度上看,该书实在是一部中国现代语言学萌芽期的断代史著作。从功能上讲,该书不但为读者提供有关早期中国译介国外普通语言学的史实,还呈现了现代语言学传播的路线、路径、方式、接受度,反映了社会文化氛围对语言学典籍译介产生的制约作用,从这一角度讲该书又是一部语言文化史和语言学学术史。
(三)学科史 一般来说,学科史学或以时间为发展主线,以学术大事件或重要思想为分期标准;或以专题发展为主线,呈现相关思想更替与演变的脉络;或以区域学术思想的发展史实为根据,呈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然而,该书另辟蹊径,从译介角度呈现国外普通语言学传入的路径、方式、脉络、接受度和影响力,这是此前少见的。从学科史的写作和发展看,该书不但提供了译介的研究视角,还提供了中外文化交流角度的研究范式,更提供了国外语言学影响力研究的启示。
从上述三个方面看,该书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该书还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就该时期语言学断代史而言,该书掌握的相关文献是比较充分的,文本分析也是比较细致、系统而透彻的。最后,该书以译介角度,融合史论法相结合的方法和方式,呈现该时期的语言学断代史,可谓是一种学术创新。
四、不足之处
综合来看,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以译介为切入点,呈现1906-1949年的普通语言学断代史,忽略了非译介方式出现的史籍文献,不免存在遗漏之嫌。其次,该书论述范围虽然比以往同类著作全面系统,但也没有包罗所有的同期文献。最后,文后附录的国外普通语言学典籍译介大事记有所缺漏,反倒不如换个角度将1906-1949年所有的语言学重要事件网罗其中,似乎参考价值会更大,如果能以该期国外普通语言学的影响力为线索,续写1949年以后中国语言学论文引用数据为主导的大事记,势必会更有价值。还可使用期刊网的参考文献功能,统计该期文献在现当代语言学文献中的出现频次,作为该期国外普通语言学影响力的统计论据。
尽管该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之处还不至于影响史实内容的传达,也不至于影响该书在译介、语言学、学科史等领域的参考价值,更不会影响该书作为语言学译介史的断代史地位。
五、结语
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研究方法的建设,再到研究领域的分化和研究内容的转向,以及分支学科的出现,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较快,从1906年章太炎提出“语言文字学”这一学科称谓开始,到1912年胡以鲁写作第一部理论语言学作品,同时引进国外现代语言学思想,尤其是索绪尔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观点,再到1930年王古鲁引进语义学理论,1937年张世禄等引进英国弗斯的语言学观点等,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几十部著作和译作。如今,有关中国语言学学科的论文不计其数,专著也有数百部之多,语言学工具书亦有数十部,还分化出了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哲学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可见中国语言学已经逐步走向学科化、系统化和信息化。
这部专研语言学典籍译介的断代史的出版可谓是填补了一项空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读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