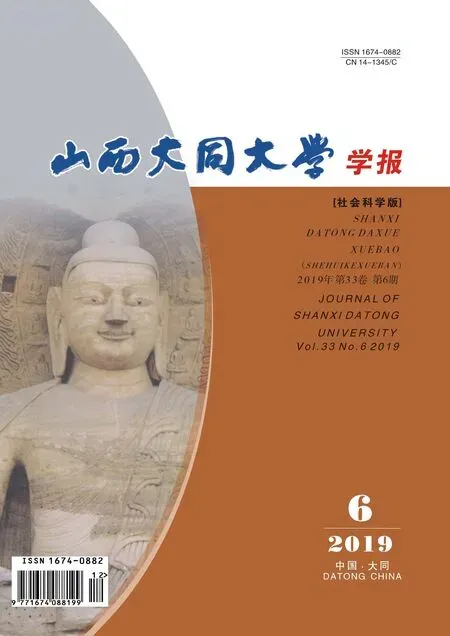通过JoanHaste译本对比反思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魏学敏,牛谷芳
(晋中学院外国语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引言
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1967)和《天涯沦落人》(1965)两部作品影响下,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开始了对此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并被尊称为后殖民主义的“三剑客”。罗宾逊、巴斯奈特、韦努蒂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翻译结合起来,成就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翻译不再是单纯的翻译过程,而是涉及到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文化纠葛,通过强国翻译将文化输入到弱国以实现其文化霸权。在中国,后殖民主义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王东风[1]、费小平[2]、王宁[3]、潘文国[4]等都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论文逐渐增多,但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作为一门新兴领域,虽然被广泛研究应用,但鲜有对后殖民理论的可行性进行反思。一方面集中于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理论性研究,如任一鸣[5]、赵稀方[6]、康孝云[7]等;另一方面是通过后殖民主义视角或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译本。
《迦因(茵)小传》是英国作家哈葛德发表的一部小说,在中国于1901年和1905年分别出现了由包天笑、杨紫麟翻译的和林纾、魏易翻译的两个译本。笔者结合《迦因(茵)小传》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两译本的研究,分析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几位代表人物的代表性理论并对其进行反思。
一、《迦因(茵)小传》两文本的异同
《迦因(茵)小传》原文是一部英文小说,由英国作家哈葛德在1895年于伦敦发表。1901年,包天笑和杨紫麟将原版的“半部”翻译为中文《迦因小传》。1905年,林纾在魏易的帮助下将整版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标明该译本为足译本,林纾将包天笑版中的主人公迦因改为迦茵,该译本也定名为《足本迦茵小传》。虽然两译本仅相隔四年,但是两译本的差异使得当时的学者和士大夫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两文本的相似点 包天笑、杨紫麟的文本与林纾、魏易的文本虽然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二者还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第一,两文本是处于同一时代背景,而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意识形态相同。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状态。所以当时的文人对于西方国家,一方面痛恨其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另一方面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林纾曾写到“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鸟,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郑振铎,1981:7)第二,两文本都对原文进行补充修改,插入译者的言论。例如,在包天笑的译本中,经常有类似“天笑生曰”的译者评论出现。而林纾的译本中常有译者“善意”的提醒:如“此盖补述之言”,“此章复述迦因矣”。其实,对于翻译作品的任意删改是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的主要特点。例如,当时著名文学家梁启超在翻译时对原文本进行大幅度删改,形成独到的翻译风格即“豪杰译”。在如此背景之下,也难怪包天笑和林纾二人的翻译文本都有删改的特色。第三,两译本语言都采用文言文。在当时,文言文译西方小说作品是一种风尚。包天笑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那时候的风气,白话小说,不甚为读者所欢迎,还是以文言文为贵,这不免受了林译小说的熏陶。”[8]曾驻英的外交大使郭嵩焘也说,“英国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9]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文言文备受推崇。
(二)两文本的差异 这两个译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两文本的内容差异造成迦因(茵)在读者心中的不同形象。包天笑把原文中关于迦因的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情节全部删改成为一个合乎礼仪、表现得体的纯洁的迦因形象。而林纾的翻译将原文本的情节尽可能忠实地翻译在译本中,尤其关于迦因(茵)未婚先孕的情节以及迦因(茵)当时的犹豫痛楚都详细地刻画出来,还原了原文本中的真实的迦因(茵)。也正是对于原文本内容的不同处理,引起了近代关于该译本的持久的讨论与争执。第二,林纾的翻译本中引入了西洋的写作技巧。传统中国文学作品直接叙述情节,对于环境、心理、外貌、动作等描写少之又少。林纾在翻译《迦茵小传》时充分利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等描述出各个时期的人物性格特点及人物的内心活动,使译本更加生动活泼。[10]包、杨二人的译本却将诸如此类的描写方法大幅删除,只保留原故事情节的内容。因此,林纾引进的新的写作手法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写作方法,对于中国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两译本的语言风格不同。虽然两个文本都使用文言文作为翻译的语言,但是林纾的语言更加浅显易懂。此外,林纾的语言更加幽默风趣。林纾在他的翻译中,通过迦因(茵)姨夫醉酒后被骂的情节将迦因(茵)姨妈的这一世俗性格描写的活灵活现。总之,两个不同的译本中林纾的翻译版本更加忠实原文的故事情节,而且超越了传统了中国文学形式,给中国的文学代入了新鲜的西方写作技巧。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反思
(一)斯皮瓦克的“属下”其实可以言说 斯皮瓦克作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理论家与印度庶民研究小组对于“属下”的研究,使她成为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她于1988年发表的文章《属下可以说吗?》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斯皮瓦克指出,“属下”不仅仅是指被殖民过的第三世界国家,“属下”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指处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底层的农民等无产阶级。斯皮瓦克进一步探讨说这些真正的“属下”即第三世界的最底层人民,一直都被第三世界国家当地的精英所取代,是“属下”中的“属下”,而这些当地的精英却被理所应当的认为是所说的“属下”,所以真正的第三世界的最底层人民完全被忽略了。第三世界的“属下”一直都被西方国家所赋予的诸如落后、堕落、野蛮等负面形象所笼罩,却一直都没有机会言说真实的自己,而这些真正的“属下”也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自己的权利。[11]
林纾和包天笑两译本发表所处的半殖民半封建时代,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形象一直充满鄙夷与嘲讽: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很有偏见地描绘中国人为“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天生眼睛小,鼻梁矮,额头低,胡须稀,耳朵大,肚子大”。[12]斯皮瓦克也在1976年发表的《翻译的政治》中指出,第一世界的译者在翻译第三世界文本时,故意使用相对落后的语言例如古英语展示他们的落后愚昧形象。在包、林二人的译本中,二人对于西方的殖民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并让中国人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言说。例如在林纾的译本中,迦茵的外貌描写如“樱桃小嘴”“双波”“秋水”“双蛾”都是典型的中国美女形象。改动西方的形象,并将中国形象融入其中,更好地展示了中国的美女形象。此外,斯皮瓦克提到西方译者故意使用落后的语言来表现第三世界的落后形象,而林纾和包天笑的译本中都选用的是以文字优雅,语言凝练著称的传统的文言文。将我国的语言形象置于西方文本之中,对于改善中国形象,同时利用中国语言进行言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斯皮瓦克质疑的真正的“属下”是否能够言说,中国近代的革命事例充分展示了我国底层劳动人民“翻身把歌唱”的过程。
(二)萨义德和韦努蒂的抵抗理论的扩充 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对西方在殖民主义时期的入侵以及之后的文化霸权进行揭露和批评,提出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抵抗。[13]韦努蒂在他的专著《译者的隐身》中指出,在传统的通顺翻译的原则下,译者努力迎合目的语文化即强势文化避免显露出翻译的痕迹,将自己隐身;他还深入地探讨了英美强国使用归化策略宣传英美文化,最终实现文化霸权的现象,并提出了通过异化策略对这一强权阴谋进行抵抗。[14]
萨义德的不足是在抵抗中没有注意到翻译过程中同样需要抵抗西方的文化霸权;而韦努蒂却是将翻译中的抵抗更多的依赖于异化策略,殊不知作为第三世界的译者在将西方文本译入第三世界国家时同样需要使用归化策略。因为在翻译强国文本进入本国文化时,强国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无疑将同时被引入弱国,并对弱国的文化造成影响,所以,在将强国文本译入弱国时更需要对西方文化进行抵抗。这时,归化策略将会对进行抵抗的第三世界的译者起到积极作用。
《迦因(茵)小传》两文本正是出现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时期,两个译本中都有对西方文本的抵抗现象。韦努蒂提出在翻译中可以采用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格式来进行写作,从而制造出一种陌生感,同时宣传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包天笑和林纾在语言选择上,使用传统的中国文言文,这一蕴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语言帮助读者在阅读外国文本的时候仍时刻提醒自己是中国人,不忘国耻。二人将翻译时的语言归化为中国传统特色的语言,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了积极的抵抗。此外,韦努蒂批判的译者隐身的现象,在林纾和包天笑两个译本中得到很成功的抵抗。包天笑在翻译中经常性的点评让读者不断看到译者的身份,尤其当包天笑评语中出现“欧西妇人”等字眼更加让读者意识到国人与西方国家的区别。林纾的译本中对读者的提醒“此盖补述之言”,“此章复述迦因矣”等也充分展现了西方文本与中国传统文本的差异,试图以译者的身份引导读者去理解阅读文本。两译本都充分展现了译者的身份,同时将文本归化到我国的角度来进行翻译,所以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不断意识到我国与“欧西”的差异,从而彰显各自的特色并对西方文化霸权展开抵抗。
萨义德在抵抗中提出,译者需要注意本土主义的问题,在翻译的抵抗中同样需要注意本土主义,过度归化无疑将会导致本土主义。包天笑的译本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包天笑的译本将原作的故事情节进行大幅度删改,使原文本故事与译本的故事出入很大。包天笑任意篡改故事情节,将原文中迦因怀孕的事实完全掩盖,并将原文中关于早产婴儿的情节完全删除,使译本脱离原文本。林纾与包天笑译本关于内容情节的差异引发的如此长久的争执,是因为类似包天笑这样努力迎合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仍然不乏其数,这样过度抵抗西方文化甚至随意删改外来文本的本土主义情节同样需要提防,这也是在抵抗西方文化霸权时译者应当注意的问题。
(三)霍米巴巴杂合的“度”太模糊 霍米巴巴对殖民以及后殖民时期的文化转变及权利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杂合”这一概念引入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并提出了“第三空间”等理论。霍米巴巴反对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相反,他提出其相互依赖的一面。殖民者只有通过贬低他人来提高自我,通过否定他人从而肯定自己。他进一步指出殖民者只有通过这样的歧视才能保持他们的权威形象。而杂合理论正是对殖民者这一行为进行的一项积极的阻挠。通过杂合制造出来一种既不是殖民者所表述的“他者”也非被殖民者本身的状况,而是一个有着殖民者特点的“他者”,是对殖民者的一个模仿与嘲讽,从而使殖民者对于自身的形象也产生了陌生感和危机感,进而破坏了殖民者的权威形象。[15]
但是,霍米巴巴杂合理论的“度”很模糊。翻译是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杂合是不可避免的,翻译总归是两种文化的杂合。翻译文本的杂合总共分三个层面,语言层面,文化层面以及文学层面。[16]例如:包天笑的译本中“密司脱”、“咖啡”、“雪茄”、“磅”等的欧洲词汇的引入,林纾译本中“密尔华德”、“礼拜堂”、“男爵”等西欧词汇的运用,以及这个西方文本本身新鲜的文化背景和情感故事;同时,二人都利用了中国的传统文言文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叙述方式对原文本进行了删改,形成了兼有西方文本特色与中国特色的两个新译本。所以,依照霍米巴巴的理论,二人通过“杂合”的方法对西方的文化霸权都做出了积极的抵抗。然而,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包天笑的译本与林纾的译本有着很大的差异:正如上文所说,原文中迦因的未婚先孕以及早逝女婴的情节都被包天笑完全篡改,是典型的本土主义情节;而林纾在他的译本中全面介绍了迦茵的可悲命运,给当时封建的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鼓励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此外,林纾引入了大量西方的写作技巧,例如详细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等等,西洋写作手法的积极引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坛文学的表达形式。可见,林纾与包天笑的两译本虽同为通过杂合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但是抵抗的程度却又很大差别。二人译本的杂合程度不同,再次证明了霍米巴巴杂合理论的缺陷:包括杂合过多弱国特色后可能会出现的本土主义情节,甚至消极杂合后的其他不良影响。
结论
《迦因(茵)小传》两文本的对比分析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提供了实际的研究事例,包天笑译本和林纾译本的异同之处帮助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的“属下”说理论、萨义德和韦努蒂的抵抗理论以及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事实上,斯皮瓦克所探讨的“属下”其实可以言说,即使是最底层的人民也终会翻身做主开始言说他们自己的权利;而萨义德与韦努蒂对于抵抗理论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扩充,在翻译中同样可以需要运用抵抗策略,而归化策略也会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抵抗方法;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对于杂合的程度太过模糊,这样容易导致极端的本土主义情节甚至是消极的抵抗态度。所以,我们需要更加客观地认识并反思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