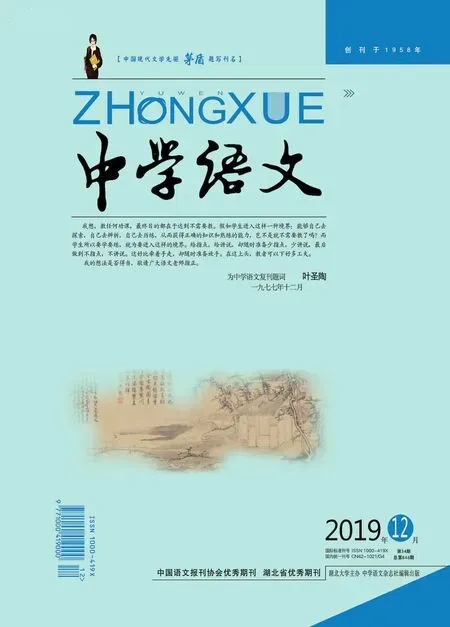比较研究:现代诗歌教学的突破口
张毛毛
现代诗歌是高中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版块,但因为其有着文体上的特殊性,带来解读和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尝试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给现代诗歌教学寻找一个切入口,寻找一些可以操作的方法,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诗教之路。
一、在语法层面比较诗化语言和非诗化语言
现代诗歌在教学初期,我们一般要给学生界定诗化语言和非诗化语言,但是又困难重重,似乎难以摹状。语言离不开语法规则,我们就从语法入手,比较诗化语言和非诗化语言(当然在这个命题下,我们讨论的都是现代诗的语言,古典诗歌暂且不论)。
首先,诗化语言常常打破语法规则。现代诗歌主谓宾的搭配比较奇特,如果我们用现代汉语语法的条条框框来衡量这些句子,恐怕大半是病句。比如:多多《春之舞》“雪锹铲平了冬天的额头”,“雪锹”怎么能“铲平额头”呢?白桦《李后主》“你摸过的栏杆,已变成一首诗的细节或珍珠/你用刀割着酒、割着衣袖”,“用刀割着衣袖”的搭配尚可,而“用刀割着酒”的搭配是不是很奇怪。再看海子的《日记》“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这里,语法是缺位的,缺位到我们看不懂了。但是,恰恰是语法的混乱,解放了语言,这就是现代诗歌的魅力。它一边挣脱格律对声音的束缚,一边踢掉现代汉语语法的种种限制,它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大地上,带给我们千变万化的语言组合,带给我们奇妙的审美体验。
其次,诗化语常常不合逻辑。在改病句版块中,不合逻辑属于病句的一种。我们想说,在现代诗歌教学中,不合逻辑和因主谓宾搭配不当产生的奇妙效果有时是一样的,或者说,为什么会判定搭配不当,因为它不符合事理逻辑,故而我们放在一起讨论。法国诗人伊夫·博纳福瓦写过一首诗,叫《雪》,开头是“她来自比道路更遥远的地方,她触摸草原,花朵的赭石色”,什么叫做“比道路更遥远的地方”,实在不合逻辑,但是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产生了奇妙的效果,比路还要远,那就是说明雪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宇宙的幽深处,人无法到达,甚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瞬间增加了雪的神秘色彩。台湾诗人门罗《流浪人》中“把酒喝成故乡的月色,空酒瓶望成一座荒岛”,怎么可以把酒喝成月色呢?但在这种错乱中,我们感受到主人公的寂寞和对家乡的思念。张枣《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想起后悔的事,梅花怎么会落呢?违背自然科学,可是诗人就是可以这样表达,这份后悔一定是浪漫的,美的,香的。此外,卡尔维诺有一篇小说《迷失在雪中的城市》,开篇语:“那个早上是寂静把他叫醒的”,“寂静”怎么能“叫醒”人,吵闹的声音才能叫醒人啊,但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我们说这个句子是诗歌,是诗化语言。我们在指导学生写散文、小说的时候,不也经常说,要写一点有诗歌味道的句子吗?怎么写,就是要“破”,突破语法,突破逻辑。
我们在教学生创作现代诗歌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抓手,或者说起步点,就是让学生比较一般的句子和诗化的句子,比什么呢?比语法。当然,写诗讲究天赋、灵感,这不假,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尝试创作,就一定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在比较中,琢磨诗化语言的无拘无束,奇妙炫丽。
二、在艺术效果层面比较诗化语言和非诗化语言
我们刚谈完诗化语言与非诗化语言在语法层面的不同,但这仍然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技术,把“我欣赏太阳”写成“我吃了一口阳光”,有点意思了,但意思还不够,还缺少艺术感染力。下面,我们还是用比较的方法,初步研究诗歌应该具有的艺术效果。
首先,“同修辞不同艺术效果的比较”。洛夫《生活》“黄昏,落叶挂来冬天的电话”,这就是一个拟人,我可以说,秋天打来电话。但诗人选取的是“落叶”,你是可以看见的,有形象感,那么多弥漫天际的落叶,是否有很多的电话呢?落叶紧跟着的是“冬天”,冬天的脚步多快啊,随着落叶,马不停蹄地跑来了。再看看诗歌的题目《生活》,悲伤就在心底散开了,季节之秋冬,生活之秋冬,生命之秋冬啊。罗门 《流浪人》“被海的辽阔整得好累的一条船在港里,他用灯拴自己的影子在咖啡桌的旁边”,若论修辞,好简单,就是拟人,但“拴”字让意境出来了,好像不拴住,连影子会跑掉一样,可见流浪人的孤独。如果我说“船像受伤的孩子,孤单地停靠”是不是味道少了许多。现代诗歌使用修辞,一定用得非常出新,而这种出新的基础是想象力。余光中《枫和雪》“想起这已是第十七个秋了/在大陆,该堆积十七层的枫叶/十七阵的红泪,悯地,悲天/落在易水,落在吴江/落在我少年的梦想里/也落在宋,也落在唐/也落在岳飞的墓上”,修辞就是排比,但“落”字,落古落今,落实落虚,弥漫天地,萦绕不去,让我们感到诗人深挚的家国情感。
其次,“同物不同艺术效果的比较”。现代诗歌,特别是当代诗歌,像“梨花体”“羊羔体”的诗歌多为今人诟病,只有物,没有境。但我们认为,这不是问题关键,关键是前者的诗歌缺乏思想的深度。比如写云,有一个作家写的,“傍晚,山上有一朵白云/披着夕阳的金纱/在山间轻舞/远处,吹来几丝微风/是否带着你的多情?”语言很美,但少了思想的光辉。辛波斯卡是这样写云的,“动作得十分快速——/转瞬间/它们就幻化成别的东西……一遇到事情,便溃向四方。和云朵相比,生活牢固多了,经久不变,近乎永恒……它们壮丽地游行而过/它们没有义务陪我们死去/它们飘动时,也不一定要人看见。”此时的云朵不再是自由漂浮的物象,而凝聚了诗人的精神——以上帝的视角看世界,死亡对于她而言,是完成了某种秩序。
可见,如果我们想写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诗歌,想象是双翼,思想是根基。
三、在文体层面比较现代诗歌和现代散文
在现代诗歌教学进入到创作阶段的时候,学生分不清,什么是散文,什么是诗歌,学生简单的认为诗歌就是短的散文,要分行的散文。首先,我们进行作家“同题不同体的比较”。我们先比较郁达夫《故都的秋》和维亚泽姆斯基《秋》,同样是对秋景的赞美,前者繁复,后者凝练;前者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明朗,后者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模糊,意象之间跳跃得很厉害。又举例闻一多《秋日之末》,“和西风酗了一夜的酒,醉得颠头跌脑,洒了金子扯了锦绣,还呼呼地吼个不休。”闻一多用了拟人的手法,秋天竟然和西风喝酒呢,多大胆,多离奇,多让人意想不到。这种拟人一定是别人没有用过的。诗歌讲究语言的“新”,新就是他人未用,我首用。关于这一点,文章第二部分已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接下来,我们进行“同体不同效果的比较”,把学生写的诗歌和类似物象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现代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它该具有怎样的特点。
先展示学生写的诗歌:《蝶》
当一只蝴蝶真的停歇在我的指尖,
我却为生命的柔韧而惊喜。
它的翅膀这样柔软,仿佛一触即碎,
它分明如此脆弱,可却拥有完全信任人类的勇气。
我不禁为自己先前的肤浅无知感到羞愧,
更为这一刻蝴蝶对我片刻的偏爱,
为生命的勇敢和无畏。
……
语言缺少诗化语,姑且不表,但除了分行之外,这真的是一篇小散文。我们选取了德国诗人冯塔纳的《两只乌鸦》“我独自走过荒野的沼地/听到有两只乌鸦在凄啼/一只乌鸦向另一只叫道:我们的午餐往哪里去找?有一个骑士,昨夜被杀死,没有人看守,躺在树林里”,饥饿的两只乌鸦在讨论午餐,它们看到一个死去的骑士,无人理睬,只剩下一具风水日晒的尸骸。这两只乌鸦充当的是“解构”的角色,诗歌充满了现实批判色彩。散文和诗歌虽然都强调对生命的观照,但现代诗歌的表达要更浓缩一点,也就是常说的凝练,构思也要更为精妙。这位同学看蝴蝶进而引发对生命的感慨,构思上没有独特之处。后者,作者设计两只乌鸦的对话,设计特殊的场景,原诗后半部分乌鸦说“他的情人跟情郎跑掉了——我们可以去安心吃个饱”,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结局,读者的心情是沉痛的。散文讲究布局谋篇,但诗歌更讲究布局谋篇,因为简短更要精彩。不过,对“物”的观照要上升到一定境界,达到一定效果,实现对更广阔人生、社会的观照,确实很难,学生不易达到,但通过多维度的比较,学生至少可以分辨什么是诗,什么是散文。
现代诗歌教学一直处于放逐状态,其一,高考不考,其二,教起来难觅固定的法则。我们尝试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语法层面比较诗化语言和非诗化语言,在艺术效果层面比较诗化语言和非诗化语言,在文体层面比较现代诗歌和现代散文,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比较,给学生一个大致印象,一些欣赏和创作现代诗歌的方法。我们更希望在中学阶段能播撒诗意的种子,让现代诗歌回归青青校园。
“语言建构与运用”由“语言建构”与“语言运用”组合而成,两个短语是什么关系可能让不少教师感到困惑,因此也值得加以辨析。
从逻辑关系的角度分析,两个概念或事物如果属于同一层面(即非包含关系),可能会构成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同质关系,即两个概念名称虽然不同,所指的其实是同一个事物,比如作为课程名称的“语文”与“国文”;第二种是并列关系,即两者类型相同,但基本上互不相属,例如诗歌与小说;第三种是因果关系,即两者有内在联系,如学习活动和学习目标。一般情况下,一组相对的两个概念之间往往只存在一种关系,才不容易造成理解的困难,但问题是,“语言建构”与“语言运用”这两个短语恰恰在上述三种关系上似乎都有点沾边。
按照建构主义原理,人这一认知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主体认知能力的建构过程,一个人的语文学习过程,就是语言运用过程,同时也是其语言素养的建构过程。或者说,在认知哲学层面,语言运用与语言建构属于一种“同质”关系,二者是不可区隔的。(郑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