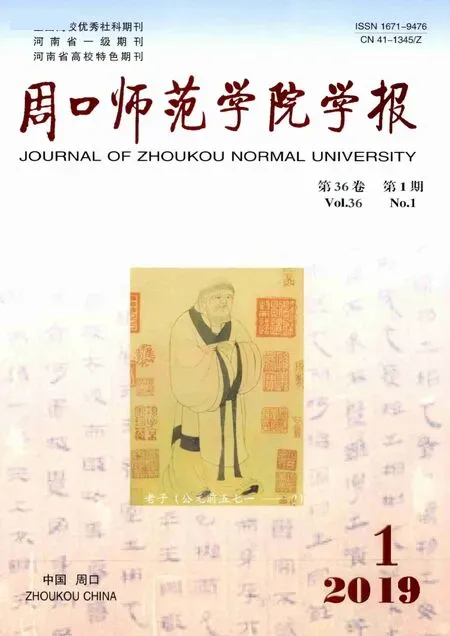论林纾对韩愈之认同与接受
王 婷
(兰州大学 文学院 国学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言“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法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1]137林纾之文在当时能有此称誉,与他对韩愈的认可与接受是密切相关的。林纾将左、马、班、韩并称为“四氏精英”,把韩愈之文集当作自己的枕边书,晚年担任教师的他,更是循着韩文而传道,足见对韩愈其人其文之痴迷。事实上,晚清士人对韩愈之推崇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的情形,“吴挚甫先生案头日置韩文一卷,时时读之”,“曾文正亦力主桐城者,乃日抱韩文不去手”[2]6335。因此,透过林纾这个个体,从而发掘晚清时期在西学思潮的压迫下,此类士人于历史的旋涡当中,期以文化复兴进而使国家复兴,为回归传统秩序所做的努力。
一、儒道式微之背景
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学在社会文化当中大多占据主流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儒学理论的不断完善,更是逐步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立身处世之准则。这一思想学说在正宗儒学之士心中不可撼动。
到唐代以后,自武则天起,佛教在唐代日渐兴盛。统治阶层一系列崇佛兴佛之举措,必然会对传统儒学产生极大冲击。面对此种境况,陈子昂曾上疏言“陛下方欲兴崇大化,而不知国家太学之废,积以岁月久矣。学堂芜秽,略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3]633。到了中唐时期每况愈下,大批佛教徒占有田产,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官吏与僧侣之间的勾结也使得政教衰颓、吏治腐败。韩愈是此时反佛的典型代表,其诗文往往直斥佛教之弊。于他而言,大兴佛教对社会有极大危害,甚至是对传统秩序与伦理的亵渎,“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4]3。他总结说:“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5]83在唐宪宗派人大迎佛骨之际,“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6]7880。然,韩愈上表,且反复陈说此中利害,“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2905。他也因此被贬至潮州当刺史。即便遭此贬谪,他依然声言“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5]268。
而到了晚清,随着帝国主义入侵,武力征伐下所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引发的不但是国家领土主权的丢失,更是西学对传统文化的蚕食。这时期的西学无疑同当初佛教盛行那般,在社会中铺展开来。林纾在前期未曾反对过西学,反而有一系列推进西学进程之举。最具代表性的是他致力于与友人一同翻译西方小说,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民俗与文学艺术,“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7]657。他也因此名声大噪,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如鲁迅、郑振铎、郭沫若等人,这些后起之秀大都通过阅读林译小说而汲取养分。郭沫若就曾在《少年时代》一文中称林纾的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对其后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性的影响。除此,林纾还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学习“外间之新法、新理、新政、新学”[8]卷上:39。这中间,又特别注重对西人实业之学习,认为实业乃“强国之粮储也”[9]卷1:34;对一味守旧不变之腐儒也进行了批判,他用大儒张载的“守旧无功”一语进行反驳,称“明知有宜悟之理,顾泥守师说,执滞己见,终不以为是”[8]卷上:39。支持变法,希望国家学习西方立宪政体,且“每闻青年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9]卷1:31。于此种种,我们很难说他是个卫道者。
考察林纾前期之经历,不难发现,他不仅算不上落伍,甚至可以称得上开拓者。既如此,为何后来又被冠以“封建余孽”之名了呢?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之“新道德”“新文学”与传统儒道相背。这场运动所刮起的自由、民主、平等之风,与传统社会纲纪伦理相左,青年以争言父母于己无恩为先进,又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势在必行之举,传统文化在他们眼中被看作阻碍国家进步的糟粕,一无是处,而西方则样样俱佳,希望能够全盘西化,以求国家进步。胡适在给青年学子的演说中就有“百事不如人”一说,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0]295。这对“志在古道”且以传统文化为傲的林纾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坚定地站在反对的一面,言“此风一扇,人人目不知书;又引掖以背叛伦常为自由,何人不逐流而逝,争趣禽兽一路”[11]85。后来同青年后生展开数次论战,又发表作品《荆生》《妖梦》怒斥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由此可见林纾的态度——西学当学,而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任何想要颠覆中学的行径与思想是坚决不能容忍的。为此,他甘愿孤军奋战,抱残守缺,且“至死不易其操”。
“不知敬人则必不重人伦,不重人伦则上下无以分,上下不分,则天下之乱其能已哉。”[12]17对士大夫而言,儒学乃安身立命之本,儒学正则纲纪正。事实上,从韩愈和林纾言行来看,无论是反佛学还是反西学,都始终是基于儒道式微的时代境遇,欲匡正儒学,以重申儒学而力图回归亲亲、孝友之道而言的。
二、卫道济世之信念
除上所提及的佛教盛行,韩愈所生活的时代事实上早已危机四伏,李唐王朝的辉煌杳如黄鹤,眼所能见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农民起义。且主上昏聩,用人不当。宪宗时,黄甫镈、程异为迎合圣意“数进羡馀以供其费,由是有宠”。一跃显职,致使“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6]7874。而在文坛上,六朝遗留下来的浮靡之风仍占主流,轻视经学,反对儒家章句之学,且科举也多以繁缛雕琢的骈文取士,不利于人才选拔。早在唐建国初期,很多文人就已经发现其中弊端,魏征就是一例,“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3]1730经过陈子昂、萧颖士、元结等人的推进,文体变革实乃势在必行之举。当此之际,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提倡取法先秦、西汉,以复古之文,倡言古道。他称自己是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这里的道即为儒家之道,是维护社会秩序与礼义纲常之道,故而要求创作具有思想性与现实性的作品。
科举制度到了清代僵化不堪,八股文已然成为“世之腐物”,社会动荡、纲纪废弛,与中唐不可同日而语,“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趋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暗然而熸”[7]617。且时人多“不省中国四千年继绍之绝学……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7]615。桐城派方苞认为韩氏所倡言之“古文”,为“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14]127。林纾既被称作桐城派的古文殿军,韩愈所提倡的这种复古,对他来说无疑有借鉴意义,言“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7]612。明知古文已不适于用,仍“力延古文之一线”[7]617。
由此,对韩愈所倡之儒道,林纾首肯心折。在他看来,韩愈之文之所以流传甚广,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对儒道之笃定。正是这种信念上的坚定,为文自然不流于俗。同样,正是因为林纾将韩文的思想确定在了儒家道统以内,自然是不能同意秦观论韩文“能钩《庄》、《列》,挟苏、张”之语了。他驳斥道:“昌黎学术极正,辟老矣,胡至乎钩《庄》、《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焉肯拾苏、张之余唾?”[2]6442在他看来,韩文之奇崛,是《庄子》《列子》一类无法比拟的,故而不会拾人牙慧,且先秦时期的纵横家之巧言令色,与儒家提倡之道也是不相吻合的。这种对正道的坚守所焕发出的文气,林纾极为推崇。
关于文章写作缘起,二人皆立足“道统”。韩愈深谙于道,提倡“文以明道”的文道观,将文章作为贯道之器,“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4]1109。认为文章有明道之重任,以文为载体,力主恢复三纲五常、亲亲之道。林纾继承了韩愈的文道观,有“敷文明道”一语,言“古文惟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于无穷”[7]566。“古文一道,非学不足以造其樊,非道不足以立其干。”[2]6389“不由于学,则出之无本,不衷于道,则言之寡要。”[2]6389
既然重提古道,必然要通过阅读经典来践行,所读之书也是要有所选择的。韩愈要求深入阅读儒家经书,“其文《诗》、《书》、《易》、《春秋》”[4]4,并告诫学者一定要“慎其所道”,断不可“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4]1114。当明白为学之方向,方向正确,终究会抵达自己想要抵达的目的地。张僖同林纾一起于兴化校阅试卷时,见其行李中所携书为《诗》《礼》《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及韩愈文集等,其推崇传统经书及昌黎之心,可见一斑。“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15]726且圣人之言,可以“抗万辩”“铸伟辞”。阅读首先要“宗经”,而经典之本,正在于明道。
对经书的重视,是要通过读圣贤之书,求圣人之志,以此而提高个人的德行与学养,这也是维护社会纲纪秩序的必由之路。二人对仁义道德的修养极为重视。韩愈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4]1,“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4]1074,要“行之于仁义之途”[4]700,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力”[4]700。林纾对仁义的推崇更是到了极致,不仅要求大德与小德皆不可忽视、不可放松,常怀一颗谦卑之心,向德行高尚之人靠近,连国家的军队都想要铸造成“仁义之师”,士兵“必识字而向学,日耸之以爱国之诚”[7]609。
要之,心怀儒学、阅读经典、修养德行便可得“道”。二人对儒道理论的阐述与接受,无疑为当时社会竖起一面旗帜,对稳固社会秩序、反拨时文之弊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更使得一大批士大夫由此而坚守古道,捍卫道统,坚定操守,守住儒学,为心灵留得一方净土,以实现其济世之志。
三、文以明道之实践
当此儒道衰颓之时,林纾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韩愈的所言之道,在实践上,也力图循着韩文明道之轨迹。昌黎之“不平则鸣”说,要求表达“感激怨怼”之情。在这里,“‘鸣’并非被动地反映,而是主动地干预现实,对不合理的境况和现实进行抗争”[16]82。这就要求创作主体立足社会现实进行创作,将眼所能见之社会痼疾迸发于诗文当中。于士大夫而言,手中的笔就是他们强有力的武器。
韩愈生于“安史之乱”后五年,亲历战乱之苦,社会矛盾丛生的现实,使其以极大之热忱参与到斗争当中,且仕途坎壈,“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终无成”[4]646,“二十五年而擢第于春宫”[4]842。在此期间,长期身居微职,声言自己于“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4]842。笔触之细微与表现内容之广可见一斑:“孔丘殁已远,仁义路久荒”[5]51,言儒道之萧索;“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仁义饰其躬,巧奸败群伦”[5]272,讽刺官吏对朝廷之荼毒;“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5]60,言自然灾害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又,《送李愿归盘古序》借友人之口刻画了三类形象,以此对士大夫之间的人情世故进行揭露;《谏天旱人饥状》则直陈民间饥困;《送许郢州序》批判地方官敛赋现象。
在危难的现实面前,积极寻求救国之路,而非如一帮腐儒般一味粉饰太平,韩愈主张向君王直谏,力陈时事,侧面反映出了士大夫内心救国之急切。郑余庆是韩愈的上司,曾对他有恩,而韩愈则直言其失,“事大君子当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悦,故于事未尝敢疑惑,宜行则行,宜止则止,受容受察,不复进谢,自以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4]635-636,体现出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之风。
林纾出生寒门,家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这使得他对社会现实的体认与感知更为明晰。虽未曾为官,以大清举人身份终其身,但他深谙政府腐败与官场黑暗风气,以文明道的意识强烈之至。
光绪二十三年“著《闽中新乐府》五十首,都三十二篇,皆由愤念国仇、忧悯败俗之情,发而为讽刺之言、亢激之音”[9]卷1:19。“富贵人居安乐窝,日斜未起如陈痾。”[17]296言鸦片对社会的危害,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量巨大,且不论贫富贵贱。精神上的萎靡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惰性,为民荒于耕作、为兵柔弱无力、为官荒淫懈怠,这一切必然带来更大的社会危机。“欧洲克日兵皆动,我华犹把文章重。廷旨教将时事陈,发策试官无一人。”[17]269针砭朝廷酸腐之辈,诚如在《与魏季渚太守序》中言“盖上有积疑之心,下有分功之思”[7]569。此时清政府上下相互蒙蔽,内外隔绝,早已腐朽不堪。“边事凄凉无一言,别裁伪体先文字。”[13]287刺官吏之贪腐。“奈何大老官,一谈外国先冲冠。”[17]271用“渴睡汉”来形容与列强谈判的外交者,在国家利益前丧失应有之原则。此时,林纾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列强欲瓜分中国之心和生民之艰难,这就更强化了他内心的抱负与追求,以愤慨之心、犀利之言鞭挞社会之疾,以期实现变革。
“怀国家之想者,视国家之事,己事也。”[18]9这是士大夫身上固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浓重社会责任感。针对慈禧太后用筹备北洋军舰之资大修颐和园,言“土木者,天下不祥之物;人君而好土木,天下犹不祥者也”[7]568。他希望人君能够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对钱财物尽其用,不追求奢靡享乐的生活。戊戌之年,德国强占胶州湾,进而出兵进犯即墨等地,林纾以清醒的判断认为中国兵力必不能与之抗衡,且变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他三进都察院,想要呈上自己的救国之策,欲求皇上下责己诏以激励士气,同时又提出“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希望朝廷采纳。这些意见以各种理由被驳回,从侧面看出清政府的腐朽已达到无可挽回之地步。
除此,林纾所译的外文作品,更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中皆名人救世之言”,经过渲染,“求和于中国之可行者”——《孝女耐儿传》之类,以教孝也;《英孝子火山报仇》,则奋国人报仇雪耻之志也;《爱国二童子》,极言实业之宜速兴也;《块肉余生述》,则揭英伦弊俗,而诚无醉心西风,但实力加以教育,社会亦可改良也……[9]卷2:22-23
“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通过诗文广泛反映社会生活,揭露时弊,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二人目的所在。
四、古文创作之艺术
明道之文非为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一类,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在艺术手法及美学上都有一定要求,而不同之人又别具个人特色。林纾自言读韩文25年,“说其义,玩其辞”,故而对韩文自有其见解:相比于宋代程朱一类的道学家只一味目于道,重道而轻文,所作论道之文少有人传习,韩文实为理蕴其中又兼有文采。《文心雕龙》所谓“精理为文,秀气成采”[15]17是也,学者创作古文当可以此为文之法度,而他本人的作品也正是以韩文为范。
艺术创作贵在情真。情感所生大抵有两种途径:对于国家及社会的情感与因个人遭际而生的喜怒哀乐之情。韩愈称“穷苦之言易好”[4]1122,足见其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而言,历经沧桑与悲痛所生发之文,其内容真切,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林纾的“叙悲之作”最为人所称道,高梦旦言“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7]642。此类文章正是林纾眼见国家领土与主权的丧失,以及个人命途多舛,历“丧葬接踵”之果。这些呕心沥血之作,情感之真,足见其赤子之心。无怪乎姚永概在《畏庐续集序》言为文当有性情寓于其中,而“世士涂饰以为工,征引以炫博,固无性情之真……若畏庐者,殆余所谓可信者也”[7]605。这正是对林纾为文情真之极大肯定。
“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4]700韩愈认为文章创作不应有陈词滥调,讲求为文之奇,甚至因此而大力称誉樊宗师艰涩之文。而韩愈文章之奇,奇在构思立意,奇在艺术创造力的发挥。“韩文于人之不留意处留意,于人留意处,转吞言咽理,为不尽之词,耐人寻味,读者但见其辞之恬退,而不知其悲;但见其意之幽曲,而莫名其愤。此昌黎之身世使然,往往成为至文。”[9]卷2:11林纾以此来解释韩文之奇,算是深解韩文“文心之妙”矣。他在《春觉斋论文·论文十六忌》一章中列《忌陈腐》一则,认为当世很多文人“述政事,则不离官文书气;辨道学,则不离语录气;著经说,则不离高头章气”[2]6402。因而要求为文当“精醇”——“唯醇故不陈,唯精故不腐”[2]6403。他仍然要求将所读经书与圣贤之言论消化吸收,储于胸中,临文时,“以简语制断之,务协于事理”[2]6403。值得注意的是,林纾是反对险怪之文的,非其不喜此类文章,而且认为后生没有如韩氏般深厚之底蕴,往往只在字句上求奇,则易流入险怪僻涩一途。
为文要有气势,韩愈讲“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4]701。林纾同样有“积理养气”一说。其《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中《气势》篇,论“文之雄健,全在气势”。要“敛气而蓄势”。这里的“气”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正是出于士大夫对儒道之自信,亦是在积淀了数千年的儒学与礼教的感染下所产生的文化自信。
林纾对韩愈之古文可谓到了视若珍宝的地步,不仅单独创作《韩文研究法》,还对其文章加以评点研究,以期为后进之人创作古文而树立向导与纲领。在其《春觉斋论文》当中,我们发现,其论文体往往以韩文为例,且加以精到客观之评语。林纾为弟子授课时,为了让他们能够体悟韩文之章法,甚至给弟子列出了书单,言“欲作昌黎文章,须读《法言》、柳文、《诗经·二雅》”[2]6536。其言“蔽掩,昌黎之长技也……能于蔽掩中有渊然之光,苍然之色,所以成为昌黎耳”[2]6441。当桐城派吴挚甫初见林纾之文时,亦称“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7]620。故而其为文,显然是循着韩愈的风格了。
当然,林纾也是位理性追随者,对韩文的个别篇目和文体也会加以批评否定。如对韩愈“谀墓”之文的批判,认为其缺乏真情实感;与书一体,当同先辈“辨析学问”,而“昌黎集中与书颇多,然多吞言咽理之作,有时文法同于赠序”[2]6359。认为此多作于韩愈不遇之时,且文中多有抑郁无聊之气;论体包括范围极广,且贵在能够“破理”,而“《昌黎集·燕子不贰过论》则应试之文,味同嚼蜡”[2]6351。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15]521,社会与时代的变革,总以文化为承载。于士大夫而言,儒道是不可废的。历经“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佛寺林立、动乱频仍,韩愈于此时反对骈文,提倡复古,以道统来打破割据混乱的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同时别开生面,尽洗文坛骈俪浮靡之习;到了晚清时期,列强侵略,人民起义不断,在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下,青年倡言之全盘西化又对传统文化造成极大损害。于此时,林纾重提韩愈复古之道,从传统的儒道中寻求出路,进而维护君臣父子之纲纪,力图重建已然崩塌的社会秩序,从历史当中寻求方法,不失为此类坚守儒道的士人可选择之路,自然有其合理之处。而在提倡白话文的社会风气中,林纾力守古文阵地,其对韩文的再研究与传播,更是为当时青年学子学习古文、创作古文指明了切实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