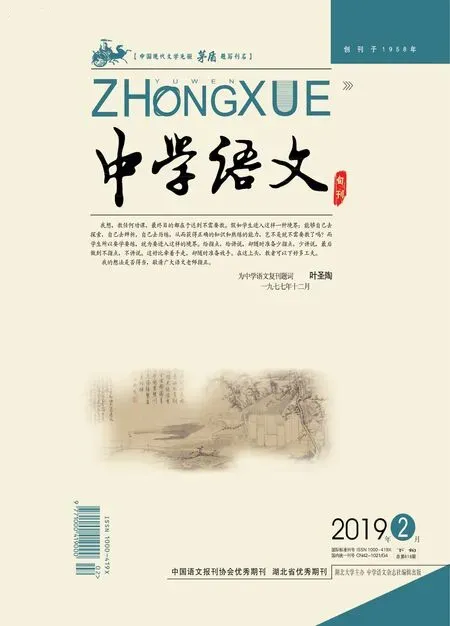棠棣:一个不容忽视的意象解读
——质疑韦凤娟老师《〈采薇〉赏析》
张茂香
《采薇》是《诗经》里的名篇,其丰富隽永的人文内涵,言之不尽的诗情画意,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让人赞不绝口。特别是诗中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感:对家园国土的思念交织着对贼寇强敌的愤恨,艰难征战的苦涩蕴含着保家卫国的豪迈,明媚乐景中蕴含隐喻的哀伤,阴晦哀景中寄寓喜悦,这一切都给人无穷的想像与回味,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魅力。
教读《采薇》的重点,就是进入诗歌的语言世界,不断地涵泳,引领学生去品味这些复杂的情感。纵观全文,《采薇》的复杂情感其实是靠三个典型的意象建构起来的,作者借“薇草”起兴,通过对“薇草”由“作”到“柔”,再由“柔”到“刚”的隐喻来表达战士思家的痛苦,集中表达的是对故土家园的思念和对强敌贼寇的愤恨。结尾的“杨柳”意象使上面的情感得以强化,并让全文笼罩着悲喜交加的美好意境。“棠棣”这一意象则折射出兄弟同袍、保家卫国的豪迈,三个意象使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思想感情意蕴丰富,令人回味。
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忽略或误读了棠棣这一意象,致使《采薇》的解读片面而肤浅。人教版语文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里收录了韦凤娟老师《<采薇>赏析》,其中有诗歌四五小节的歌唱中“还透露出对苦乐不均的怨恨情绪”的理解表述,韦老师通过第四节后面马儿“业业”“骙骙”与文中的士卒进行对比,又引申出士卒与将帅的对比,从而证明此节中揭示的等级差异所造成的苦乐不均的状况。韦老师引述了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中关于《采薇》第四节前几句的解释“什么花开得繁华?那都是棠棣的花;什么车高高大大?还不是贵人的车”加以证实。余冠英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造诣毋庸置疑,《诗经选》出版于1979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余冠英先生《诗经》的解析亦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时代的烙印。当我们跳出当年的时代,站在当代的视角来审视作品的时候,应该对作品有更加全面的解读和理解。韦凤娟老师在对 《采薇》的理解上延续余冠英先生的解读思路并得出第四小节透露出“苦乐不均”的阶级对立情绪。笔者认为,这样的解读可能有失偏颇。纵观《采薇》全文,产生片面解读的原因是没有挖掘“棠棣”这一意象在文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理解三个意象在建构全文情感上的相互联系。
一、疏漏了“棠棣”意象的传统意义和内涵
众所周知,《采薇》节选自《诗经·小雅》,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本文前三章以“薇草”比兴是毫无疑义的,在四五章的解读中,韦老师把“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四句解释为“什么花开得繁华?那都是棠棣的花;什么车高高大大?还不是贵人的车”非常勉强,如果前两句只是表达对那些将帅的讽刺,那为何偏偏选择“棠棣”这一意象?如果仅仅是为了表达花繁华的样子,用“常棣”未必最佳。常棣的花朵并不算鲜艳,或红或白,两三朵成一缀,不大,茎很长而花下垂,可见棠棣花并非繁盛之花的典型。其实,作者选择“棠棣”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诗经·小雅》中有《常棣》一诗,其中的“常棣”就是棠棣花,《毛序》中说:“常棣,周公燕兄弟也。”燕,通宴,说明《常棣》这首诗写的是周人宴请兄弟的故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本诗的主旨句,后来,很多文人就以常棣或棠棣指兄弟情谊。况且,就行文表达来看,并读不出明显的讽刺意味。不管是从意象使用的延续性来看,还是从《采薇》的整体语境来看,把“棠棣”理解为兄弟情谊合情合理。
二、割裂了“棠棣”意象与后文的联系
《诗经》特别讲究章节的谋篇布局,从结构上看,前三章采用了比兴手法,此章借棠棣花比兴也顺理成章。既隐喻将帅与士兵之间情同兄弟的感情,为下文抒发同仇敌忾的豪壮情感做好铺垫。“兴”主要起渲染气氛,奠定基调的作用,“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已奠定了本段昂扬向上的基调,“彼路斯何?君子之车”就应顺应这样的基调解读。“比”是比喻,是对本体和喻体意义的界定,既然“棠棣”象征着兄弟情意,那喻体所代表的将帅与士兵的关系自然是袍泽之谊。
如果理解了“棠棣”作为比兴手法与后文的关系,就能顺畅地把握四五两节作者要表达的感情。第四章说“戎车既驾,四牡业业”,第五章又说“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四牡翼翼,象弭鱼服”,诗歌用了回环复沓的手法,反复强调了战马的强壮。用现代汉语解释为“战车已经上路了,我们的战马是多么的雄壮”“驾着那四匹马拉的战车,四匹马是多么的魁梧”,多读几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四牡业业,象弭鱼服”使这种自豪感进一步增强。两章的最后一句分别是“岂敢定居,一日三捷”“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是总结句,强调了这两章表达的主体情感,原来,主人公有个强烈的愿望,不管多么的艰辛,一定要竭尽全力把玁狁之敌赶出境土。可见,四五两章描写战马的雄壮表达的是战争装备精良的自豪感和战争必胜的自信心。由此可见,“常棣”这一意象与表达苦乐不均的情感没有关系,表达的是“与子同袍”、同仇敌忾的战斗情怀。
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既然《小雅》是贵族宴会时的音乐,说明《小雅》中的作品是被贵族们所接受的,如果理解为“透露出对苦乐不均的怨恨情绪”似乎有些矛盾。《小雅》中确实有从士卒视角描写战争的作品,诗中虽透露出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家园的思念,但士卒并不表示反对战争,也不指斥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因为,从国家立场而言,出征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的。《采薇》中的情绪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怨恨和愤怒。如果有,也只表现在对侵扰他们生活的“玁狁”上,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孔子评价《诗经》中的《关雎》一篇,说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应该说,《诗经》中的作品大都表现了这样的中庸之美。
三、忽视了“棠棣”意象构建下的时代风貌
《毛序》曰:“《采薇》,遣戍役也。 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可见,《采薇》中所描述之事有其时代背景。就目前史书记载而言,《采薇》的创作时间说法不一,但创作于春秋中叶以前是毫无疑议的,因为整部《诗经》收集的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民间歌谣。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很明显。从史书记载看,春秋时期能参战是一种荣耀,参加战争的都是贵族,最低也必需是一个“士”,“战士”这个名称也由此而来。直到春秋后期,秦国实施征兵制度,奴隶和贫民开始有资格参争,并以建立战功而取得荣华富贵并以此封妻荫子,改变家族命运。从这个角度看,《采薇》里面的士兵,至少是一个“士”以上的贵族。再者,春秋前期重礼法,“士”以上有尊卑次序理所当然,也为大众认可接受,所以,《采薇》中的士兵和将帅并没有非常尖锐的阶级对立,相反,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期许,就是为国家而战,为荣誉而战,从这个角度分析,“棠棣”意象的意义恰恰印证了这样的历史事实。
就作战方式来看,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步兵少且地位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可以作为车战的佐证。春秋时代的散文及史书把实力强大的国家称为 “千乘之国”,可见,战车的装备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采薇》中反复强调战马的魁梧就找到了依据,整段内容所表达“同仇敌忾”的情感就顺理成章了。
可见,“棠棣”这一意象使全文的情感得以升华,也使文中的主人公形象更为丰满而感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一个普通的士兵,经过长久的征战,身心俱疲,还要忍受思家念亲的苦痛。即便如此,却还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战斗,以同仇敌忾的赤子情怀抵御外敌,这不能不令人感动。《采薇》中的意象解读,多重视“薇草”和“杨柳”的分析,却忽略了“棠棣”对于主题表达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教学参考书中所选韦凤娟老师的解读,给很多老师以借鉴意义,但其对“棠棣”意象内涵的忽略,也可能影响到很多年轻教师对《采薇》一文的理解,年轻教师往往把教学参考奉为圭臬,如果教参选择的文章不严密,恐怕对教师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