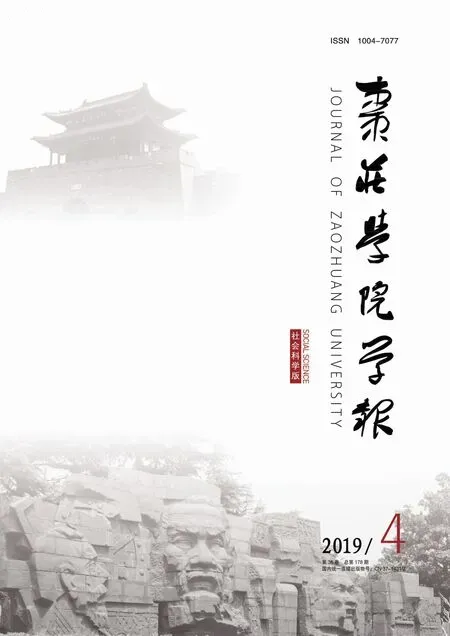论徐则臣中短篇小说中的谜题叙事
高媛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徐则臣是中国大陆“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曾写作《耶路撒冷》《北上》等多部较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与此同时,他笔耕数十年,创作大量中短篇小说,在真假参半、虚实兼备的北京、花街、鹅桥、左山以及小葫芦街等文学地理空间中,展现不同人物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在其诸多中短篇作品中,“设谜”是作者常用的情节叙述手法,谜团既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亦是吸引读者阅读的重要内容。
一般说来,通俗小说会把“提出问题,延缓提供答案”作为结构文本的重要手段。问题主要包含两类,亦催生出对应的两种小说类型: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诸如“谁干的”是传统侦探故事的内核,涉及时间的问题,诸如“后来会怎样”则是探险故事的核心问题。[1](P14)徐则臣的中短篇写作,也借鉴了这一艺术手段,以“谜”入文,使文本中的谜题呈现为两种不同形态。
一、得解之谜:言在此而意在彼
在多数小说写作中,谜题设置对应着解谜行为的发生,它一方面统摄表层情节结构发展,使其在设谜——解谜的深层叙事逻辑中顺叙进行,另一方面则赋予小说神秘的悬疑色彩。徐则臣的中短篇小说,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带有细节性的谜题,以此剥落笼罩在生活世事之上的平淡面纱,再现复杂的人物过往经历。平静的花街上,修鞋的老默孤独死去,在众人的平淡生活里掀起波澜。在遗书中,他把仅有的两万元存款留给豆腐店老板的儿子良生,透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秘意味(《花街》)。海陵镇上,老迈得已被人忘却姓名的七奶奶,在近乎失智的状态中,听人转述丈夫的侄子汝方死前念叨着“秦娥”一词,突然抽搐,似乎要发病,让人惊异(《忆秦娥》)。
在现实的谜题叙事之余,作者的笔触一转,将人物的旧日经历写入小说。良生的母亲麻婆孤身带着他来到花街,随后被豆腐店老板蓝麻子接纳组建家庭。七奶奶与汝方的婶侄关系,中间隔着长期在外做生意、一回家即暴毙的叔叔徐七。在历史的故事追溯中,人物的谜样行为似乎早已获得答案。随着良生与母亲争吵,母亲早年的妓女身份以及父亲的不义抛弃都得以显露,他与老默之间可能存在的父子血缘正是确凿的谜底。经历了回光返照的七奶奶,念叨着“我等了七十一年,他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2]离世,重演了《伏羲伏羲》中王菊豆和杨天青的悲剧,亦为人生中最后的谜画上句号。小说以谜题结构作品,在揭示谜底之余,更多将其思想意蕴置于人物的现实行为表现之中,老默来到花街后,日日光顾豆腐店,将早年的抛弃行为转化为无言的痴守忏悔,七奶奶与汝方相互爱恋却囿于宗法及世俗压力难以相守,只能在独处时回忆过往。
徐则臣作品中的谜题设置多关涉事物的因果联系,设置方式因文本内容产生差异,谜题既可能是草蛇灰线的伏笔,亦会成为旁逸斜出的点缀,部分甚至仅存在小说中的某个细节里。在对谜题进行处理时,作者并非事无巨细地交待前因后果,而是有意在作品中减少关涉谜题的描写,将其转换为“隐藏的材料或曰省略的叙述”,以意味深长的沉默,“对故事的明晰部分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并且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希望和想象”[3](P95)。
在贯穿小说始终的伏笔式谜题中,《长途》一篇颇为典型。小说开端处,叙述者“我”带着DV准备拍摄叔叔的长途跑车生活,却发现他已成为水上运送货物的船老大。“叔叔为何放弃心爱的汽车”,是小说起始预留的一个不起眼的谜题。运货途中,叔叔搭载了一位瘸腿女性秦来,二人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近至叔叔宁愿放弃拉货也要搭载秦来,远则为双方沟通寥寥,“我”对秦来的试探亦使叔叔如临大敌。双方的关系在这种亦亲亦疏的状态中成为新的谜题。除此之外,小说中还穿插着叔叔讲述的六个长途跑车故事,既与人物的水上经历应和,也暗藏着叔叔的心机,最后一个故事将谜题全部揭破。在这段被他转嫁到别人身上的肇事逃逸经历中,秦来即是被撞瘸的陌生女孩,也成为叔叔此后放弃开车、主动搭载的直接原因。小说将一个陆上的车祸故事包裹成谜,转移到水中飘摇的货船之上,以叔叔隐秘的忏悔和赎罪行为,完成两场融合在一起的长途故事讲述,也寄寓着“再坚硬的仇恨和报复都会被时间打磨掉寒光,石头失去棱角,终成为暖玉”[4](P141)的希望。
《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刑具制造者》等作品亦采用同样的伏笔式谜题设置方式。在前者中,年午的“鸭子飞上天”故事似乎对“我”的鸭子丢失做出合理解释,但他一次次送到“我”家的野鸭以及最终跻身为“我”爸爸的事实,反而为鸭子失踪提供了新的答案。作品中孩童的孤独无措以及无力抵抗压抑现实的悲剧颇为典型。后者里一出场即三天没睡觉“做生意”的大班,最终在一众戴着父亲潜心研制的新枷锁的反贼中出现,“生意”的真面目——革命得以彰显,父亲间接将其送上断头台的人生荒诞感更难以言喻。
旁逸斜出的点缀式谜题,看似是小说的情节插曲,发生在次要人物身上,却都在最终暗合了主要人物的命运际遇,强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表达。《如果大雪封门》《石头、剪刀、布》以及《一号投递线和忧伤》都包含这类谜题设置。在《如果大雪封门》中,离乡的养鸽少年林慧聪留在北京的最后愿望即是看一场大雪,可是在等雪的过程中,他的鸽子不时失踪与死亡,成为难以破解的谜题。同住的行健与米萝虽有嫌疑,却从未露出马脚,直到“我”发现他们偷偷把鸽子送给一位陌生女性。真相大白的轻松并未如期而至,随之而来的大雪以及鸽子死亡也带来陌生女性无钱医治重病被迫还乡的消息,与看完雪即回乡的林慧聪殊途同归。底层“京漂”人物的残酷生活境遇借助“鸽子”意象得到完整还原,其生计选择(贴小广告、养鸽)、生活细节以及京郊环境,都在养鸽、丢鸽、收鸽、送鸽的故事中体现。
与此类似的还有《石头、剪刀、布》,饭店老板老吉的长期住院不归之谜背后,隐藏着这个男人的不告而别真相,做出同样选择的,也包括老板娘小田的前几任恋人兼合伙人。小说结尾处,“我”作为小田的新希望,享受过女性的柔情蜜意后,仍走上了前几位男性的老路,在关键时刻背弃老板娘,回归自己的旧日生活。部分男性的贪图享乐、不负责任等劣根性成为小说着力批判的内容。《一号投递线和忧伤》之中,身为投递员的“我”努力探究单身女性陈禾的生活状态之谜,毫不留情地揭穿她自己给自己寄信的把戏,戳破她所营造的“有人在关心我”心理幻想,却未料到在触及他人的痛苦时,自己以及其他都市人的孤独感同样强烈。
同时,小说中的部分谜题,体现在部分仅为叙述者“我”所知的细节中:《弃婴》中如玉丢弃的男婴,正是她与村长不正当关系的佐证;《大水》中,沉禾的妻子不帮丈夫拉架,与邻居年五似乎交往过密的行为之谜,都在最终她与年五私奔的结局中得到验证;《失声》中丈夫过失致人死亡的姚丹,拒绝邻居好意仍要维持家庭生计,等在黑暗中门口的明灭烟头,在“我”的眼中,即是对其选择的无声证明。
除了对因果关系的谜题运用,徐则臣还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时间谜题,将小说的情节推进动力转化为“然后发生了什么”这一读者阅读诉求。《纸马》里的叙述者“我”,因手艺出众,也为了家庭生计,在邻居葬礼上摇纸马。但在送葬途中,承诺在家陪伴病重母亲的侏儒哥哥却出现了,使我开始担心“家中母亲如何”这一问题,也在无形中将其转化为小说的情节谜题。紧随其后,哥哥心爱的唢呐、“我”怀中的纸马、母亲的病症表现以及葬礼的过程描写等内容交错且重复出现,既写出光棍兄弟俩的贫寒家境以及仅存乐趣,也不断强化“母亲在家如何”这一谜题所产生的悬念。小说结尾处,哥哥受送葬人群中怂恿,即将碰触身边的女孩达到人生“高峰”“我”却听到报信孩子带来的母亲倒地不起的消息,谜题的结局昭然若揭,也将兄弟二人拉回残酷的现实。
除此之外,在北京这一地域空间的文学叙事中,寻找恋人胡方域的女孩居延面临着“能否找到”的人生谜题(《居延》),有着八旗血统的上海女孩王琦瑶也在思索着能否见到“富豪爷爷”的重要问题(《浮世绘》)。前者中的寻找,因为居延的逐步成长与独立变得无足轻重。谜题让位于人物的经历叙述,虽获得破解,但只是为完成人物的心理转变书写。较之于谜的结果,人物努力破解谜题的过程及其中的人情冷暖,反而成为小说着力描写的内容。后者的同名主人公王琦瑶,复刻了《长恨歌》中女性的选择和命运,在与多位男性产生身体以及情感纠葛后,错过了似谜一般的爷爷的真实境况——常年卧床且贫苦无依,也彻底失去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希望。
E·M·福斯特曾指出:“情节属于小说那个讲求逻辑、诉诸智识的层面;它需要谜团,不过这些谜团在后文中一定要解决”[4](P85)。这些在后文得以解答的各异谜题,存在于徐则臣的中短篇小说之中,不再像其在侦探小说等类型文本中,聚焦于“人物如何通过努力破解谜题”的过程,而多以水到渠成的方式被人物获知答案,并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中产生令读者回味的艺术魅力。其原因即在于,小说中谜底的揭破,并非单纯实现“真相大白”的叙事目的,从而满足读者对于事实的简单探求,而是逸出谜题本身,暗示人物的行为,影响人物的命运,透射出现实社会中的都市底层人群、村镇街道居民的人生百味体验。基于此,得解的谜题在完成小说常规设谜——解谜情节模式之余,更多促成了“言此意彼”的效果达成。
二、悬置之谜:言有尽而意无穷
与文本中已获确定性解答的谜题相比,始终处于无解状态的谜题也在徐则臣的多部作品中出现。它们如同前者,扮演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角色,却在关涉真相的时刻被悬置,使小说留有“空白”。这些谜题以单一或交错的形态,产生于情节发展的不同阶段,虽可供读者进行多重读解,仍赋予作品独特的神秘韵味。
单一形态的悬置之谜可能出现在情节链条的任意一环,在徐则臣笔下,最为典型的是开端以及结尾部分。开端部分的未解谜题,本应类似于前文所述的伏笔式谜题,统摄整篇作品,但在逐步产生裂隙的文本叙述中,其位置和导向都发生偏移,最终促使无解状态的生成。
小说《西夏》为投奔“我”的陌生哑女西夏设置了谜一样的身份,以大量篇幅表现“我”为了探究西夏经历所尝试的种种努力。但临近结尾处,西夏即将自陈身份,真相马上可以大白,“我”却主动放弃为其医治哑疾的机会。因为“我”内心的恐惧作祟,担心西夏的未知过往会导致双方的分离结局,只能采取拒斥态度逃避现实。“我”的人为干预终止了真相显露的进程,使小说重点从“西夏是谁”这一谜题,转移到都市生活中陌生人共处“同一屋檐下”的可能性探究,也暴露出部分现代人在熟悉状态中拒绝改变和失去的脆弱心理状态。
《六耳猕猴》以冯年化身为六耳猕猴、被耍猴人玩弄的重复梦境,在开端设谜——冯年为什么总做同样的梦?虽则主人公及其身边人物提供不同解释,诸如工作压力、异性渴求、家庭幻想等,但并无确定性结论。看似多解的谜题在本质上仍处于无解状态,反而体现出“京漂”小人物的现实生活处境以及多重心理压力。
出现在结尾部分的悬置之谜,失去破解可能,只能将人物命运和情节进程定格在特定瞬间,小说叙述亦戛然而止。这类谜题使小说形成一种“没有结局的结尾”[5](P145),也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一个短篇小说来说,故事的确切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蕴的结局”,基于此,创作者“可以对故事保持必要的沉默”[6](P115)。
《我们的老海》中,前去海边看望情人的“我”,被情人的丈夫海生发现私情,受到其不断升级的报复,几乎要殒命于大海。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终海生将“我”推上游泳圈,然后自己消失在大海之中。“海生为何要救我”变成无解谜题。《容小莲》里的女性容小莲,生活被异地丈夫、年幼儿子、周末情人、苛刻婆婆以及天真小叔子包围,既要解决家中小叔子误杀致人死亡的危机,又要面对单位查账引发的情人失踪问题。在小叔子伏法、情人被查后,人物从琐事中抽身,却发现儿子失踪了。“儿子去哪儿了”是人物必须面对的现实谜题,在小说未能给出答案的情况下,极易导致人物生活支离破碎。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人生际遇都呈现出同样的下滑态势,却在小说结尾处,一反弹,一坠落,被悬置的谜题决定命运。
不同于上述设置单一谜题的作品,《最后一个猎人》《古代的黄昏》等作品采取“谜中谜”的方式,以旧谜题引发新谜题、新谜题解决/影响旧谜题等手段结构情节。需要注意的是,作品中的部分谜题并未获得解答。正是因为这种未解状态,人物命运及情节发展“留白”,为小说营造丰厚悠远的审美意蕴。
身为“最后一个猎人”的杜老枪,在禁枪期间被人举报用枪,面临牢狱之灾。“是谁举报”是小说的核心谜题,多次出现于作品之中。他需要缴纳足额罚款,在“借钱比赚钱还难”的现实境况中,女儿袖袖如何筹措钱财是暗藏的新谜题。直到以物质换取袖袖身体的男子前来“要债”,新谜题在杜家得解。男子被愤怒的杜老枪打死,又在“我”父亲的言语掩饰中“变成”“举报的人”。于不知情的旁观者而言,杜老枪成功找到举报者加以报复,破解了小说中的唯一谜题。但对少数知情者来说,得解的新谜题与未解的旧谜题被并置在一起,却未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举报者未知又搭上了袖袖。戛然而止的结尾所留下的空白,按照现实逻辑发展,极有可能是杜老枪继续服刑,袖袖为筹措钱财的努力付诸东流,更有可能还要继续。人物在无解的谜题影响下,陷入新的悲剧境地。
《古代的黄昏》是一部多重谜题相套的作品。鹅桥的大户林家已经渐趋衰败,宅里潜藏着各色谜题,远至几年前的少爷被毒身亡之谜,近到刚发生的太太白猫被害之谜。种种迹象暗示谜题复杂交错:家中管家与少奶奶曾有私情,管家毒打“不能生育”的妻子,为少爷看病的医生杳无音讯,管家之妻偷买砒霜……多重矛盾爆发后,真相得以显露:管家为了家产和少奶奶毒杀少爷,继而暗害太太未果,管家之妻为了子嗣给少奶奶下毒,却在无意中害死丈夫。看似清晰的叙事在结尾时产生新的谜题:少奶奶讲述的小少爷身世真假难辨,在少爷与管家两个当事人已死的境况中,“父亲是谁”的答案,更像是少奶奶自保的护身符,可靠性大打折扣。未解的身世谜题在真假、是非乃至实虚之间游移,使小说保持一种神秘且混沌的风味。
与这类无解的谜题不同,徐则臣的部分中短篇小说中的谜题,呈现出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它们贯穿情节发展始终,表现为晦暗不明的悬置状态,确证或消解小说中已经发生过的情节内容,使小说一直保持着谜样氛围。在以这类谜题为主的作品中,人物的缺席、情节的断裂时有发生,意义的无从探究亦是常态,类似于叙事充满“空缺”[7](P116)的新潮小说。
《鹅桥》一篇中,带着已逝父亲“回到鹅桥”的嘱托,“我”百般寻找终于抵达,却发现当地人对“我”这个“水中影子是直的”外乡人带有冷漠的敌意,只有小水姑娘友好热情。“我”向当地人打听父亲在此的经历,多数鹅桥人不自然地否定他的存在,唯有精神有问题的“神经七”言语错乱地还原“父亲年少到此随即拐跑当地姑娘”的事实。但细究人物的精神状态,故事本身更像是不可靠叙事,“父亲在鹅桥经历了什么”这一问题变成“父亲是否到过鹅桥”“我”也在探究未果的情况下离开鹅桥。谜底固然可被解读为“外乡青年带走本地姑娘,引发当地人愤怒以致讳莫如深”,但当地人的“影子说”“神经七”的疯癫言行,又使这一结论含混且暧昧不清。
同样具有谜样氛围的《养蜂场旅馆》,表现“我”的记忆与经历差异谜题。“我”在左山散心时住进陌生的养蜂场旅馆,却发现房间似曾相识,老板娘小艾也认识“我”。她以种种举动不断提醒“我”8年前的故事:“我”倾心于她,把她从女孩变成母亲。这与“我”的前女友摇摇的言说不谋而合,但丝毫没有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她还拿出录音带证明自己话语的可靠性,在她的诱导下,“我”试图相信8年前确有其事,并与她鸳梦重温。在这一过程中,老板在门口亲眼目睹二人亲热,发出一声“啊”,与录音带中那声不知道是谁发出的“啊”重合。“旧事是否发生”是“我”到左山时即存在的谜。如果像两位女性言之凿凿那般发生,那“我”的记忆空白,其实正呼应了《褐色鸟群》中“记忆是靠不住的”论断。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问题,那摇摇与小艾二人近乎一致的话语,以及“我”莫名的熟悉感,又能够将一个谜题拆解为多个,并具多重解释。
作为创作者曾计划的《虚构的旅程》[8](P3)系列中的作品,两篇小说都以人物探访某地为情节线索,借助似是而非的谜题连缀起人物的过去和现在。《鹅桥》中“我”与父亲重叠在一起,离开时,“神经七”误以为“我”又把小水带走,《养蜂场旅馆》中时隔8年重演的场景及“啊”声。重复的意象、事件将线性时间置换为循环时间,与谜题共同营造神秘的小说氛围。
无解、多解乃至意味不明的悬置谜题,在小说文本中留下待解的“空白”,为作品提供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些没有明确答案的谜题,给予读者多重读解的机会,使他们寻找存在于文本中的“蛛丝马迹”,揣度可能的谜底,最终得出多样的结论。与此同时,个体的生活经验、特定地域的变迁故事乃至社会历史的转折进程等内容,被包含于小说的谜题叙事中,也会随读解被读者强化,凸显小说中悬置谜题“言不尽意”的特点。
得解谜题与悬置谜题二者并存于徐则臣的小说之中,既以现实谜题的揭示反映生活的不同形态,亦以日常谜题的无解将“人世的榫隙和断层”以及“可以发现和言说之外的沉默部分”[9](P2)公之于众。
——论徐则臣文学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