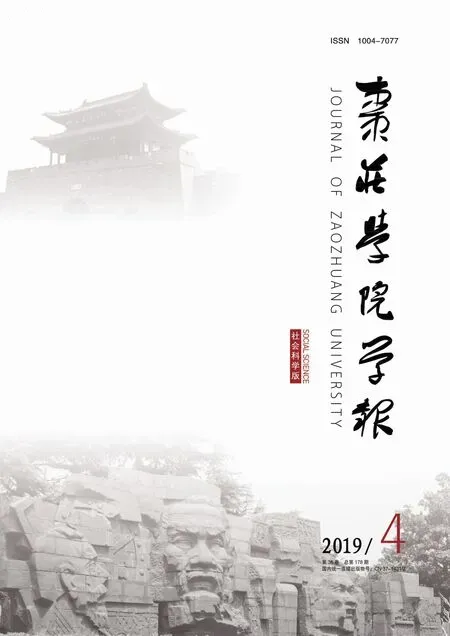徐则臣创作综论
张相宽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自1997年开始小说创作以来,徐则臣在文学道路上已然走过22年的时光,他共创作《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6部长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居延》《我们在北京相遇》《花街》《如果大雪封门》《人间烟火》《大水》《我们的老海》《养蜂场旅馆》等中短篇小说60余篇,散文集多部,《青云谷童话》1部,总计约300万字。其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红楼梦奖”决审团奖,其中有3部入围茅盾文学奖题名,《耶路撒冷》更是进入第9届茅盾文学奖评审最后前10名。由于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突出的创作成绩,兼及1978年出生,又有“70后作家的光荣”“‘70代’作家的代表和骄傲”等美誉,徐则臣已经成为当下最为出色的作家之一。
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取材特征,学界习惯于将徐则臣的创作分为“花街系列”“京漂系列”“谜团系列”“校园系列”等。自然,这些分类显然还不能完全涵盖徐则臣的所有作品,有时甚至还遮蔽了他的创作的更为深层的艺术特质,但大致还是能够反映徐则臣创作的主要特征。事实上,单就“花街系列”而言,徐则臣的创作有着逐步递进的过程。对此,徐则臣曾说:“今年是我写作的第22年,有20年我都在写运河,过去是中短篇小说,长篇《耶路撒冷》里涉及一部分,但运河主要还是作为故事背景。这次《北上》是大规模的、彻底地写运河,我盯着这条大河20年了,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了,感觉到了。我一直想认认真真地把运河当成主人公来写一次。”①“花街”是淮安运河边上的一条街,生在运河边,学在运河边,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其实也可以称为“运河系列”或“故乡系列”。《北上》写了4年,出版于2018年12月,无疑是徐则臣创作道路上的又一界碑,这一作品的出现对于认识他的“花街系列”及其整体创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北上》出版这一时间节点上对徐则臣的创作来一番回顾和总结是极其必要的。
一、从二元对立到和解共融的“故乡”与“世界”
徐则臣缘何会选择“花街”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并将之熔铸为独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地标?而且由于这一地标的日渐拓展和成长,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地理标记。人们是如何由“花街系列”认识徐则臣创作的“出走”主题的?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徐则臣笔下的故乡与都市、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虽然徐则臣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花街系列”“京漂系列”“校园系列”“谜团系列”等几种题材类型,但毫无疑问,“花街系列”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徐则臣最为重要的创作实绩。“花街系列”是徐则臣创作的起点,“花街”也是徐则臣抵达创作理想境界最为重要的目的地。目前,“花街”几乎可以和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文学原乡相提并论,徐则臣也以“花街”向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发起正面强攻。这也许隐含着徐则臣的创作策略和创作野心,但“花街”的确标示了徐则臣创作的主要领地并将赋予他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一方面,作家之所以想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独辟一个富有特色的文学地理坐标,是希望将自己的创作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并且独特地理坐标的发现,也的确能够帮助作家寻找到独特的自己;另一方面,文学地理坐标的构建也是文学创作与人生经验之间关系的客观反映,作家要创作出情感充沛、意蕴深广的作品,往往要从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入手。而一个作家最为重要的人生经验,莫过于自己的出生及成长经历,于是,“童年”“故乡”等也成为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和重要写作对象。
对徐则臣来说,“花街”还和一般作家的“故乡”有所区别。“花街”本为江苏淮安运河边上一条长约200米的街道,甚至于徐则臣刚开始写作时其原型是他上大学做家教时所经过的一条街,与现在的“花街”本无多大联系。而徐则臣1978年出生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直到他18岁上大学时才来到淮安并与“花街”结缘。所以,徐则臣的写作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现实故乡”和“文学故乡”的密切联系及其本质区别。
徐则臣18岁时离家到淮安读书两年,又到南京师范大学进修两年完成本科教育,大学毕业后留他在淮安高校做教师,两年后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任编辑,但是由于编制得不到解决,2009年到上海作协从事专业写作,2012年又回到《人民文学》工作至今。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徐则臣的求学和工作历程,是为了说明他创造“花街”这一文学王国的来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出走”和“寻找”会成为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也为了说明为什么他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处于“漂泊”状态。徐则臣本人的经历和人生追求、世界观、人生观和写作理念都促使他将“花街”作为文学的起点并且不断地让他小说中的人物“到世界去”。
从故乡到世界,从“花街”到“北京”,在认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徐则臣的观念是不断变迁的。他说:“‘到世界去’是我很多作品中都贯穿的主题之一,这些年我也在自身的写作中持久地探讨这个问题。我对‘到世界去’充满了探究的欲望。如果说此前的作品中,我对‘到世界去’的理解是远离故乡的‘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那么在《耶路撒冷》中,我突然意识到,‘回故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乃至更高层面上的‘到世界去’。我们总认为世界在故乡之外,但当我们心智成熟到一定程度,当我们的阅历和见解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对故乡、尤其是心灵之故乡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世界为什么就不能在故乡之中呢?于坚守故乡者而言,世界在故乡之外;对身居世界的游子,故乡可能就成为真正的世界。故乡和世界并非二元对立、格格不入。”②从徐则臣的6部长篇小说来看,有5部(《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耶路撒冷》《北上》)是以“花街”为背景或者就是以花街人事为主要内容的。即使是《王城如海》这部主要描写北京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长篇,里面的人物也有着从乡下(海陵县兰水乡余家庄)到都市的人生经历。这些小说正反映了徐则臣从“故乡”和“世界”的二元对立到和解共融的观念变迁。当人生经验日渐丰富,创作观念日渐成熟,他的人生观日渐通达,无论“出走”还是“回归”,徐则臣对“世界”的看法已经有了根本上的改变,“故乡”也有了“世界”的意义。
二、“故乡”与“世界”的性质及其形式
那么,徐则臣笔下的“故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他的表达又有何特点?
认识和认可“故乡就是世界”,是建立在对生活、人生、世界的深刻体验的基础之上,由此,徐则臣的小说也体现出鲜明的日常性和烟火气。相比黑塞的《悉达多》,徐则臣更喜欢菲利普·罗斯的《凡人》,原因是后者具有“小说应有的丰沛的人间烟火和日常细节”③。徐则臣曾经漂泊的人生经历和呈现生活原生态的写作观念使他更重视表现小说的日常性和细节,充分认可和欣赏浓郁鲜明的人间烟火气。徐则臣小说的代入感强,当我们看到水汽氤氲的运河、湿漉漉的青石板街道、喧嚷热闹的石码头、夜色笼罩下挂着红灯笼的小门楼,往往会沉浸其中,使读者能够深切体会小说中摹写的生活。这种生活描写也透露出徐则臣宽厚谦和的个性和日渐豁达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出他不紧不慢、轻松舒缓、自由自在的写作态度,同时也体现出他对生活其中的怀揣梦想而又命运多舛的人们的悲悯同情。所以,我们看到徐则臣小说大多为悲剧,但又充满着温情和理解。
我们通常将江苏理解为江南地域,但徐则臣又生在苏北,这一地区是南北搭界,不南不北,既南又北。后来徐则臣又在苏北与北京求学,再后来又在北京定居,所以有时候徐则臣也自认为是北方人。但是,一旦进入写作境界,徐则臣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人,其语言风格、人情风俗、意境氛围、审美意蕴都充溢着鲜明的南方蕴味。这是由徐则臣自觉地写作追求所决定的。谈到自己小说的语言,徐则臣说:“我希望文字里有水的感觉,湿润、丰沛,又有点黏稠,还有就是稍微灰暗和颓败,像浪漫主义对夜的感觉。”④这种感觉让人想起苏童的小说,但由于徐则臣独特的生平经历,他的小说又有北方语言的某些特征,这就将两者的小说区分开来。
徐则臣笔下的“故乡”“花街”还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不断拓展的“世界”,徐则臣试图将“花街”写成“世界”的缩影。对此,徐则臣曾说:“有人说花街很短,才两百米左右,但是它原来很长,在小说里更长,长到什么程度?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都可以塞到花街里,这个世界有多广阔,花街就有多漫长;这个世界有多复杂,花街就有多丰富。可以说,全世界的东西我都能塞到花街里,花街己成为一个背景。”“花街写得越来越长,写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朋友开玩笑说,写的都是古典的,能不能写点洋的?比如说里面出现一个教堂,我说没问题,我在《耶路撒冷》里而就写了一座教堂。朋友又说这个地方能不能搞一些现代的,比如我们说的名牌店,麦当劳、肯德基,我说只要是你认为可能出现在一条街上的,我都能把它搬到这条街上。”⑤徐则臣已经有了构建和福克纳、马尔克斯、沈从文、贾平凹等笔下同样出色的文学原乡的野心。说到这里,不能不谈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对于“高密东北乡”,莫言曾经说过和徐则臣上面所说的几乎同样的话,他说,“高密东北乡只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但它实际上是无边的,是完全突破地理界限的”⑥,“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⑦,“最终将特殊中的普遍凸现出来”,从而“获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⑧。徐则臣并没有说过莫言“高密东北乡”对他“花街”“故乡”营构的启发和意义,但从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上来看,两者的确有相通的地方。徐则臣也希望能够将“花街”置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所以,对于徐则臣的小说而言,“故乡就是世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从价值观上“故乡”和“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是统一互融的;二是从地域范围,从写作地理观念上,“故乡”是无限大的,无限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从一隅反映整个世界。
从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来讲,徐则臣的小说强调故事的重要性和叙事技巧的探索。小说形态学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重叙事,一个重抒情。越是古典小说,特别是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由于受到传统说书艺术的影响,更是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进入现代之后,从五四开始,小说的抒情传统得到充分发扬,周作人曾经大力提倡小说的抒情性与散文化,废名、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更是以其小说实绩显示了小说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的并驾齐驱。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世界范围来看,小说的写作越来越走向多元化。一方面有的小说的写作对象越来越向内转,日益摆脱故事情节的设置和讲述,越发重视小说的情绪表达与意蕴象征;从另一方面来看,小说的叙事传统从未断绝,总有一些作家顽强坚守故事的讲述并将之与现代小说技巧相融合。当然,也许是物极必反,也有些“先锋”作家从小说的实验性写作中开始向“传统”回归,比如余华与莫言等。先锋作家的创作特点在于从关注“小说讲什么故事”到“小说怎样讲故事”的转变,如张志忠所说:“关于小说要不要讲故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中国文坛的一个争论热点。当马原、格非、余华、孙甘露等新潮小说家先后崛起,给文坛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时间,论者认为这就是真正的现代小说,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性之一。小说可以不必全力以赴地讲故事,而去关注故事的叙述方式乃至讲故事的那个人。”⑨先锋时期的余华也曾热衷于“虚伪的形式”的探索,喜欢采用超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和并置式的碎片式结构,直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的小说开始出现了向现实和故事的转向。他曾经“粗暴地认为人物都是作者意图的符号”⑩,现在他终于“听到了人物的声音”,在写作中也开始肯定“贴着人物写”的重要性。莫言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则提出要“大踏步撤退”,从极力推崇欧化风格到主张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
徐则臣的小说与莫言的小说在故事的讲述方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他希望自己的小说“在形式上回归古典,在意蕴上趋于现代”。“从形式上回归古典”,使得徐则臣的小说具有一定的传统性与通俗性,这主要体现在徐则臣的小说故事性强,并且和莫言一样,也从传统说书艺术汲取了讲述技巧。我们知道,莫言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一个“当代说书人”,他曾宣称“我把说书人当成我的祖师爷。我继承着的是说书人的传统”。莫言小说的说书特征主要体现在叙述者的说书口吻、有说有听、有说有唱、有说有评、第一人称回忆视角等方面。和莫言一样,徐则臣的小说也有一个潜在的说书人,有预想听众,也有很多第一人称,只是说书口吻不如莫言小说那么鲜明。我们会看到徐则臣的很多小说也使用了第一人称说书人身份叙事,会偶尔看到徐则臣小说中的叙述人跳出来以说书口吻与预想听众交流,并且有时会像一个说书人一样对故事中的人事进行评论。比如“为了免掉各位读者的猜谜之苦,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此番回故乡我是为了卖房子”(《耶路撒冷》)、“我们也没有必要替他记录一切”“现在要说的是以后的事”(《水边书》)、“接着说现在。现在,我是一个自由漂泊的人”(《伞兵与卖油郎》)、“说一个可能会让你失望的事实,那就是至今我也不知道父亲是否和高棉有过,那个,你知道的”(《梅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也能够发现徐则臣小说拟书场的存在。与莫言小说不同的是,由于语言风格及其他审美元素的不同,徐则臣的“形式上的古典”还给他的小说带来一种古意,这是莫言的小说风格所没有的。而且,莫言崇尚“快”的写作,一部50余万字的《丰乳肥臀》仅仅用了83天即告以完成,徐则臣则越写越慢,《耶路撒冷》《北上》分别耗去6年和4年的时间。莫言的小说是一鼓作气,大江大河,徐则臣是走走停停,细水长流。
三、“京漂系列”的特征、局限与可能性
“京漂系列”是徐则臣从“故乡”出走到“世界”去寻找自己的重要途径和具体体现,是徐则臣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代表作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分量还难以与“花街系列”相媲美。我们提到徐则臣的创作往往会想到这两个系列,主要源于这两个系列题材的差异度和创作主题的逻辑性。徐则臣要写出与“花街系列”相颃颉的“京漂系列”或者说“北京题材”的作品还在将来。
但无论如何,“京漂系列”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甘于“故乡”的贫乏、闭塞、无聊,为了改变自己的物质水平或者寻求自己的心灵安妥、精神信仰,一批“故乡”的年轻人纷纷到北京去,到世界去。但是北京并没有给他们理想的生活,他们成了北京办假证的、卖黄碟的、贴小广告的、做家教的、卖房子的、保姆、推销员等城市的底层边缘人。即使有《王城如海》中的海归高级知识分子,但边缘人形象依然是徐则臣“京漂系列”中最为重要的人物。由于徐则臣也有漂泊经历和落魄心境,所以,徐则臣对“京漂”一族极为熟悉,他了解他们的酸辛,对他们的不懈追求有感佩之心,对他们的坎坷命运充满悲悯和同情,所以,徐则臣写起来就显得真实、真诚,而且能够比较容易地抵达他们的内心。此外,徐则臣的“京漂系列”也写得比较温和、温暖。我们知道,这类作品往往都是悲剧结局,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从小说的艺术性或意识形态性都会做出这种设置。“京漂”一族本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奋斗的不易和道路的崎岖,另外,某些从事违法活动的人物的结局在有学院背景的徐则臣的写作观念里也大都只能是悲剧。但是,由于同情心与悲悯情怀,徐则臣的最为出色之处是写出了这些小人物之间的互相牵绊与关心,并未像某些主要关注人性之恶的,认为他人即地狱的作家的写作,徐则臣写出了小人物之间的温情,写出了人间的苍凉,而不仅仅是丑,是痛。
之所以说徐则臣还没有写出与“花街系列”相媲美的“京漂系列”,原因之一是和前者相比,除了《王城如海》之外,后者还没有出现像《午夜之门》《耶路撒冷》《北上》这样的大部头作品,《王城如海》在艺术含量上也和《耶路撒冷》《北上》相差甚远。如果再追究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徐则臣一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花街系列”,再就是徐则臣在北京毕竟是个“外来户”,和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相比,他对北京文化的了解还不能算透彻,他也没有将北京文化很好的糅合进“京漂系列”中,没有将“京漂”一族和北京文化的纠葛和冲突写深入,缺乏深刻的张力。但随着徐则臣在北京居住时间的增长,等到“花街系列”已经被充分挖掘,他就可能写出经典的以北京为题材的作品。
也许附加在他身上“70后著名作家”的标签被撕掉的时候,这一天就会到来。
注释
①http://t.yzinter.com/index.php m=News&a=listcontent&classid=192&id=704363.
②游迎亚,徐则臣:《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③徐则臣:《孤绝的火焰—重读黑塞》,《把大师挂在嘴上》,第7页.
④徐则臣:《作家应该小于其作品》,《朔方》,2009年第8期.
⑤徐则臣,刘海宁:《花街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花街”—徐则臣谈故乡与创作》,《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⑥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70页.
⑦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⑧莫言:《超越故乡》,《恐惧也希望:演讲创作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⑨张志忠:《远行人必会讲故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解》,《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⑩余华:《我的写作经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论徐则臣文学的发轫
——到壮族花街节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