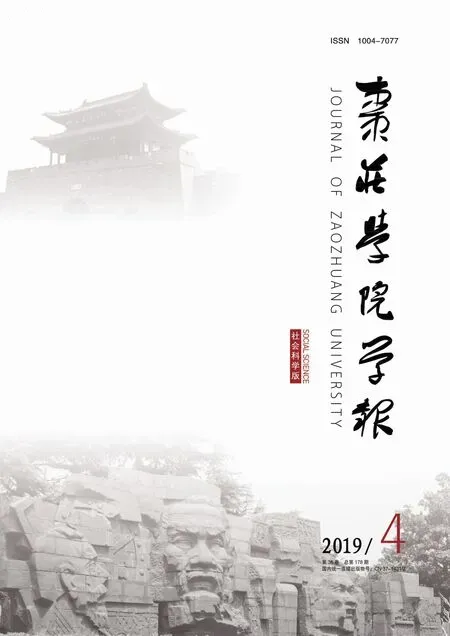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的版本学贡献
吕亚非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陆心源(1834~1894),字子稼,又字刚父、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湖州归安(今吴兴)人,清季著名藏书家,据云“得书十五万卷”[1](P1)。《仪顾堂题跋》是陆氏自撰藏书题跋的集录,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全书十六卷,收入各类题跋323篇,其中书画、碑铭48篇,书跋275篇,被潘祖荫誉为“七百年来未有之作”[2](P254),李慈铭羡称“其中可取者甚多”[3](P892)。题跋中有关版本学的论述,是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陆心源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也是一位有所成就的版本学家,所谓“版刻源流,收藏姓氏,剖析异同,如指诸掌”[2](P17)。在长期的实践中,陆心源形成的一套古籍鉴定的系统方法,还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后学积累了材料,指示了途径,兹分别加以论析,以为好学者之参考。
一、版本归属的鉴别
陆心源对于版本的鉴别颇可称道,一方面是由于他勤于读书,熟悉相关文献资料;一方面则得益于其长期经眼实物的实践。
宋刻避讳甚严,凡属讳字都要缺笔或改字,既讳本字,也讳嫌名。利用宋刻本的避讳特点,陆心源不仅识别了一些宋版书,还确定了一些书的具体刊刻时间。如卷二《新唐书》跋:“仁宗以上讳‘匡’‘胤’‘炅’‘恒’‘祯’及嫌名‘殷’‘敬’‘镜’‘贞’等字皆缺笔甚谨,不及英宗以下,盖嘉祐进书时刊本也。”[2](P45)卷六《丽泽论说集录》跋:“宋讳多缺避,至‘惇’字止,盖光宗时刊本也。”[2](P94)利用避讳也可以证明一些书非宋版或原定刊刻时间有误,如宗源瀚所藏《隋书》当时以为宋刊元修本,陆心源则以为“宋版官书于庙讳嫌名缺笔甚谨,间有疏漏,亦十之一二耳,或空其字,注‘某宗庙讳’‘某宗嫌名’及‘今上御名’‘今上嫌名’字”,而“此本于宋朝庙讳无一缺笔”[2](P44),所以定为元本;萧穆所藏《孔子家语》当时以为北宋本,陆氏跋曰:“‘瑗’字为孝宗为皇子时原名,书中‘瑗’字缺避,则非北宋刊可知。”[2](P90)利用避讳还可以考察一些抄本的源流,如卷八《乙卯避暑录话》跋:“‘慎’字注今上御名,凡遇太宗、真宗、仁宗等字,皆提行或空二格,盖从宋孝宗时刊本影写,即《津逮秘书》之祖本也。‘敦’字亦缺末笔,刊版后所刻改也。”[2](P121)卷十明抄《小畜集》跋:“语涉宋帝皆提行,盖从宋刊摹写者。”[2](P155)宋刻避讳也有特殊情况,如宗源瀚藏本《玉篇》残本书中“恒”字缺笔,“敬”“桢”“慎”“瑗”皆不缺,有人据此怀疑并非宋刻,陆心源跋曰:“不知庙讳或缺与否,官书已不能画一,周益公序《文苑英华》曾言之,况坊刻乎?不必因此质疑也。”[2](P32)卷十《王右丞文集》跋中陆心源更指出:“宋讳有缺有不缺,南宋麻沙坊本往往如此。”[2](P146)这是在利用宋刻避讳进行版本鉴别时必须要注意的特殊情况。
古籍的行款、格式、版心、木记等特征也可以作为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通过比较古籍的行款可以推断刊刻者和刊刻时间,如卷二《后汉书》跋:“蔡琪所刻尚有《前汉书》,行款悉同。吴兔床拜经楼藏有列传十四卷,珍同球璧,不能指为何本,核其款式,即蔡本也。”[2](P36)卷六《丽泽论说集录》跋:“行款与《东莱文集》同,盖同时所刊也。”[2](P94)通过一些特殊的格式可以判断古书刊刻的版本渊源,如卷六王祯《农书》跋:“凡遇‘国’‘家’等字皆顶格,当从元刊翻雕者。”[2](P100)卷十《南阳集》跋:“凡遇皇帝及陛下、先帝、太皇太后等字,或提行,或空格,当从宋本传抄者。”[2](P154)版心、木记更为古书版本的鉴定提供了方便,如宗源瀚藏本《隋书》无序跋,陆心源以版心字考之,“‘路学’者,瑞州儒学也;‘浮学’者,浮梁县学也;‘尧学’者,饶州学也,尧即饶之省文;‘番泮’者,鄱阳学也;‘余干’者,余干学也;‘乐平’者,乐平州学也,故又曰平州。元初饶州、乐平、浮梁、余干皆为州,仍隶瑞州,至元十四年,饶州始升为路。”[2](P43)遂判为元瑞州路刊本;《贾谊新书》目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一行,陆氏据此知为南宋麻沙本[2](P90);《针灸资生经》目后有“正统十二年孟夏三峰景达详咨”木记,卷末有“三峰广勤叶景达重刊”一行,陆氏由此知为明麻沙刻本。[2](P114)
序跋、衔名、卷末题字等也可以为确定古籍版本提供重要参考。利用序跋可以确定古籍的刊刻者及刊刻时间。如元刊《韩鲁齐三家诗考》与《玉海》刊本不同,无王伯厚自序及后序,而有延祐甲寅胡一桂序,则即是胡一桂所刊。[2](P27)《西溪丛语》前有嘉靖戊申俞宪序,据序可知为俞宪据西京马西玄抄本刊于武昌。《通典》前有李瀚序,一百卷后有丁未岁杪李仁伯恕甫跋,丁未为大德十一年,据此跋知为元成宗时刊本。衔名也可以为版本鉴定提供帮助,如宋椠《国语》元修之页,版心“國”字作“国”,无字数,有“监生某某”衔名,陆心源据《元史·百官志》及《秘书监志》考得至元廿四年国子监置生员二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百人,兴文署掌刻经史,皆属集贤院,推断此必南宋监版,入元不全,修补印行,所以版心才会有监生衔名。《外台秘要》每卷后或题“右从事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赵子孟校勘”,或题“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因校勘衔名皆浙东官,陆心源推为浙东刊本。[2](106)卷末题字有时可为古籍版本的辨别提供重要信息,如《黄帝内经明堂》残本跋卷末有“宽元年以相传本书写毕”一行,陆心源考宽元为日本八十六代四条年号,其元年当宋绍定六年,知此书为从七百年前抄本传录。《黄帝内经太素》每卷后仁平元年、仁安二年书写点校等字,陆心源考日本近卫仁平元年为宋绍兴二十一年,六条仁安二年为宋乾道三年,于是知此书为从八百年前抄本传录者。
字体、纸张也为鉴别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据。利用刊刻字体的特征可以推断版本,如在卷一《五经正文》跋中,陆心源总结蜀本、监本、建本、婺本的字体特点,认为该书字体与婺本重言《尚书》《周礼》相同,遂定为宋婺州刊本。陆心源又以《玉篇》残本字体,与其所见宋季三山蔡氏所刻《内简尺牍》《陆状元通鉴》相同,证以篆法、前题语,定为宋季元初闽中坊刻;《通鉴考异》因字体与三山蔡氏所刻《陆状元通鉴》相近,且多破体,陆氏定为孝宗时闽中坊本。纸张的某些特征可以为版本鉴定提供便利,例如《欧公始末》纸背乃元祐四年官册,陆氏据此判为元初印本。
前人书目的著录及一些古籍的记述、校勘、引用为古籍版本的鉴别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书目著作的著录可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重要信息,如《五经正文》,自来藏书家罕有著录,惟《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有宋刊《五经》,行密字展,与此相似。陆氏又考《景定建康志》,知诸经正文有四:监本、川本、建本、婺本,经比较各本特点最后定为宋婺州刊本。《天禄琳琅》载有宋版《新唐书》,行密字整,结构精严,于仁宗以上避讳及嫌名缺笔甚谨,不及英宗以下,卷末有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四进书衔名,及中书省奉旨下杭州镂版劄子,与陆氏藏本《新唐书》一一皆合,惟佚脱中书省劄子及进书衔名,陆氏据此知其所藏与天禄本同出一版,为《新唐书》的祖本;《宛丘先生文集》分卷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记蜀本合,陆氏知为从宋刊蜀本传录者。一些古籍中对相关图书的记述有时也可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线索,如陆氏藏本《分类夷坚志》五十一卷,据考朱国祯《湧幢小品》曾云“《夷坚志》本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删之”,知朱氏所言即指此本。[2](P140)古书的校勘记录也为古籍版本的判定提供了方便,陆氏以其藏本《千金方》校以日本覆宋治平本,发现不但编次先后迥然不同,即字句方药,几于篇鲜同章,章尠同句,但与治平本校勘记所称唐本多合,于是知其所藏北宋本“洵为孙真人之真本,非林亿既校以后所可同日而语”[2](P107)。相关图书的引用也可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参考,如大字本《通鉴》间附音义于本文之下,陆心源通过与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所引注文进行比较,发现胡三省所引费本注文与此本一一皆合,由此推定此本为蜀广都费氏进修堂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陆氏古籍版本鉴定方法多种多样。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陆心源的版本鉴别不是孤立的依据某项特征遽下断语,而是结合古籍的字体、纸张、行款等版式特征与古籍的避讳、序跋、木记等内容特征,综合考虑图书的各种信息及前人著录情况,审慎的给出自己的判断。如卷一《五经正文》跋:陆心源先考察其著录情况,“自来藏书家罕有以《五经正文》著录者,惟《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有宋刊《五经》,行密字展,与此相似,亦不言何人所刊”。又参考《景定建康志》记载知诸经正文有监、川、建、婺四种刊本,结合自己的耳识目验,进一步考察各版本的字体、版式特征, “蜀本皆大字疏行,监本比川本略小,建本字又小于监本而非巾箱,惟婺本重言《尚书》《周礼》两书款格狭小,于此书近,字体方劲,亦复相同。”陆氏以为定为婺本当不谬,继又根据宋帝讳自孝宗以前皆缺,避光宗讳,“惇”字不缺,知为孝宗时所刻。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陆心源将《五经正文》定为宋孝宗时婺州刊本。[2](P28)可见,陆氏的古籍版本鉴定,既善于抓住的古籍各方面的具体特征,又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高了古籍版本鉴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这是他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步的原因,也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
二、版刻源流的考订
一些古籍往往经过了多次的重刊与翻刻,形成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因此也越来越复杂,给使用和研究带来不便。陆心源通过考察古籍的版本源流,善于揭示各版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在古籍版本的流变中更好地确定某一版本的地位和价值。
陆心源的题跋特别重视揭示各种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卷二宋椠《汉书》跋:“绍兴初刊于湖北茶盐提举司。淳熙二年,梅世昌为提举,版已漫漶,命三山黄杲升、宜兴沈纶言重校刊二百二十七版。庆元二年,梁季祕为守,又命郭洵直重刊一百七十版。此则庆元间初印本也。”[2](P35)详细考察了湖北茶盐提举司《汉书》刊刻与补刊的具体情况。卷三元椠《战国策校注》跋:“元时已有重刊本,行款不一。成化中有坊刊小字本,嘉靖中张一鲲与《国语》同刊,皆有讹舛。此则其祖本也。”[2](P58)通过考察指出此本为以后各刊之祖本。卷九《道德真经旨归》跋:“《津逮》《学津》两本与胡刊同,盖《秘册汇函》之版,明季归毛子晋,增为《津逮秘书》,《津逮》之版,后归张海鹏,增为《学津讨原》,故与胡刻无异,皆非善本也。”[2](P142)陆心源通过校勘,发现胡震亨《秘册汇函》本与毛子晋《津逮秘书》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编次、脱误相同,由此推断书版之授受,而刊刻之源流自明。
陆氏广泛参阅各书序跋、书目、文集、史志等资料,并从各书版式、文字等内容进行比勘,以期更准确地弄清古籍各版本之间源流和内在关系。如宋板《读史管见》跋:“据大正序,淳熙以前无刊本,至大正官温陵,始刊于州治之中和堂,乃此书初刊本也。其后嘉定十一年其孙某守恒阳,刊于郡斋,并为三十卷,与《书录解题》合。有犹子大壮序,明季有重刊本,即《四库》附存其目之本也。《姚牧庵集》有此书序,谓‘宋时江南宣郡有刊板,入元,板归兴文署,学官刘安重刊之。’牧庵尝得致堂手稿数纸,今摹诸卷首。”陆氏参考了序、书目、文集资料等考察了该书版刻源流并得出了“是此书在宋凡三刊,元人又重刊之”的结论,说明了当时对此书的推重。[2](P85)影宋抄《史通》跋:“以明陆文裕本、国朝浦起龙通释本互校,浦本多与影宋本合。陆本校正固多,而妄删误改者亦不少。卢抱经所称影宋本与此本同出一源,其善处卢氏已尽录于《群书拾补》中。是书明刊,以陆本为最先,张之象又翻陆本。西江郭延之据张本重刊而加评,王维俭又据郭本而加注,国朝黄叔琳又据王本删订重刊。浦起龙通释本虽不言所自,而与宋本皆合,则当见影宋本矣。”[2](P84)陆氏通过各本内容的比较与校勘,将各本之间的脉络清晰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宋刊明补本《贾子新书》跋:“是书北宋刊本无闻,淳熙辛丑,程给事为湖南漕使,刊置潭州州学,据胡价跋,字句讹舛,以无他本可校,未能是正。正德中,陆宗相守长沙,得残板数十片,因补刊成之,见黄宝序。是其中尚有宋淳熙残版,特不多耳。正德十年,吉藩又据陆本重刊于江西。余官闽时,从杨雪沧中翰借校,与此本行款悉同。其后,何元朗、程荣、何镗诸本皆从此出,惟所据之本摹印有先后,全缺有不同耳。宋本不可见,得此亦不失为买王得羊矣。此本胜于吉藩本,吉藩本胜于程荣本,程荣本胜于何镗本,明刻诸本以何元朗为最劣。”[2](P90)通过序跋、亲身经眼,陆心源不仅详细的考订出了各版本之间的流变继承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对各个版本的价值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在整理出版《贾子新书》时被证实是合乎事实的。
三、版刻规律的总结
长期的实践、丰富的藏书,使陆心源在古籍版本的鉴定和版刻源流的考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如此,陆心源还善于对版本现象特征等进行归纳,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是对古籍刊刻避讳规律的总结。例如《隋书》跋二中说“宋版官书于庙讳嫌名缺笔维谨,间有疏漏,亦十之一二。”[2](P44)说明了宋版官书避讳严谨的一般情况。《毛诗句解》跋曰“宋讳有缺有不缺,宋季坊刊往往如此。”[2](P27)《王右丞文集》跋曰“宋讳有缺有不缺,南宋麻沙坊本往往如此。”[2](P146)两跋又点明了宋刊坊刻避讳不严的特殊情形。避讳规律的总结,为利用古籍的避讳进行版本鉴别指出了门径。
其次是对古籍刊刻版式、字体特征的一些总结。例如宋刊《五经正文》跋说“诸刻正文,今不数见,而他书之所存者尚多,以余所藏,蜀则有《春秋》杜注、《周礼》郑注、前后《汉书》、六臣《文选》,监则有单疏《尔雅》、前后《汉书》、单《吴志》《通鉴》《武经七书》《广韵》《册府元龟》《宋文鉴》,建则有十行本《诸经注疏》、杜注《左传》、许氏《说文》《纂图周礼》《纂图礼记》《北史》《新唐书》《方舆胜览》《王右丞集》《山谷诗注》《陆状元通鉴》,婺则有《尚书》《周礼》残本。蜀本皆大字疏行,监本比川本略小,建本字又小于监本而非巾箱,惟婺本重言《尚书》《周礼》两书款格狭小。”[2](P28)陆心源通过对自己所藏相关古籍的观察比较,总结出了蜀本、监本、建本、婺本各自的版式特点,为自己及后人的版本鉴别指明了方法。宋刻《玉篇》残本跋:“南宋时,蜀、浙、闽坊刻最为风行。闽刻往往于书之前后别为题识,序述刊刻原委,其末则曰‘博雅君子,幸勿忽诸’,乃书贾恶札,蜀、浙本则无此种语。”[2](P44)此处总结了闽坊刻牒文的规律,为闽刻古书的鉴别提供了方便。元瑞州路《隋书》跋二:“宋世官书,字皆极精,有颜欧笔意。坊刻稍草率,亦尚齐整。”此句总结了宋版官书与坊刻书字体的一般特征,对辨别宋版官刻与坊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又曰:“元、明人刊书,凡宋朝官牒题名,不刻则已,刻则必仍宋式,如今所行《内经》《脉经》、严州本《文鉴》、嘉靖本《金陀萃编》之类。”[2](P45)总结了元、明刻书时对于宋朝牒文、题名的一般处理方法,可资借鉴。
再次是对于古籍刊刻发行规律的总结。例如宋椠《国语补音》跋:“宋初刊书,注疏、音义皆别行,今单刊单疏、音义犹有存者,如《尚书》单疏、《仪礼》单疏、《榖梁》单疏、《尔雅》单疏、《经典释文》《汉书音义》《晋书音义》是也。至南宋而有附陆氏‘音义’于诸经各条之后者。此本别行,固宋代撰‘音义’者之通例也。”[2](P57)陆心源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了宋初刊书注疏、音义皆别行至南宋才附于本书之后的通例,有助于了解宋时刻书的格式习惯;宋椠《汉隶分韻》跋说“辽金人著述往往有南宋覆本,如辽释行均《龙龛手鉴》、金成无已《伤寒论》皆是。”[2](P33)此处揭示了辽金人著述有南宋覆本的刻书现象,使得元人所著收入《宋史》、金人所刊避宋讳的奇怪现象得到解释。《西塘集》原本二十卷,陆氏藏本经叶向高汰并,只有十卷而内容却未减少,陆氏由此想到“宋人文集往往以数页为一卷,以充卷帙。《范忠宣集》以行状一首分为卷十八、十九、二十三卷,是集想亦类此。”[2](P168)此处又点明了宋人文集多分卷帙的现象,为解决版本考察中类似的疑问提供了借鉴。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素有自觉总结文献学方法和理论的传统”[4],陆心源亦不例外。通过对一些古籍刊刻情况的总结,陆心源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为后人版本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四、版本价值的评价
在明确了古籍的版本,分析了古籍的版刻源流之后,陆心源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古籍版本的优劣和价值给出自己的评价。
陆心源主要根据刻本的纸张、墨色、字体、模印等外部情况来评价和判断古籍版本的赏鉴价值,但也兼顾文本残全等状况。总体而言,多贵宋元精刻、精抄本。例如宋椠《汉书》历经七百年,纸墨如新,完善无缺,陆心源以之史部藏书中第一等秘笈。《黄文献集》历经五百余年,纸墨如新,完善无缺,陆氏赞为皕宋楼中元板第一等。宋本《真西山读书记》为南宋初刊祖本,字画清朗,体兼颜、欧,陆氏认为非麻沙刊本所能及。宋椠《历代故事》为杨次山手书付刊,书法娟秀可喜,历经七百余年,完善如新,陆氏以为良可宝也。从以上题跋可以看出,精刻、精抄固然可宝,但陆心源更注重的是其内容是否完具、是否有讹夺,也就是其校勘价值,故不可以一般赏鉴家视之。
宋、元本往往为初刊祖本或经过详细校勘,讹夺较少,故其校雠价值为陆氏所重。例如陆氏以其所藏宋椠《汉书》与今所通行《汉书评林》、汲古阁明监本互校,发现胜处颇多并就翻阅所及,偶举一二,录于题跋中以见宋本之善。又如陆氏以崇祯中程衍刊本校其所藏北宋本《外台秘要》,发现程刊本删削几及两万字,妄改处亦复不少,考《百宋一廛赋注》知黄丕烈藏宋刊之富甲于东南,仅得目录及第廿三两卷,考《经籍访古志》知日本虽有原书,但模印在后,多糊模处,而此本宋刊初印,无一断烂,不禁赞叹“洵海内外鸿宝也”[2](P106)。
影宋本保存了宋本的原貌,所以也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陆氏以旧藏朱友鹤旧抄本《尹河南集》与影宋本互勘,知朱本讹夺甚多,于是感叹“书贵影宋,良有以也。”[2](P158)又以影宋精抄《王广陵集》校其所藏旧抄及40卷本张月霄爱日精庐旧藏,发现两本夺误甚多,于是知影宋精抄之可宝也。因为宋本、影宋本的校勘价值,所以即使是残本陆氏也非常重视,例如宋刻《玉篇》虽是残本,但陆心源以为宋本流传日少,小学书尤不易得,譬之残珪断璧,弥足珍贵。又如影宋抄《通历》原本十卷,今虽只存卷四至卷十共六卷,陆心源却认为唐人著述,传世日稀,未可以残缺见废。
从版本的内容上,陆心源注重原本、完本、精刻精抄本。原本多未经后人羼乱,例如卷四影宋抄《营造法式》跋:“《四库》所收,据天一阁范懋柱所进,缺第三十一卷,从《大典》补全,此则犹原本也。”[2](P74)卷十一《广陵集》跋:“两本皆尝插架,以校此本,诗文无所增益,盖经后人分析卷数,此则犹宋人原本也。”[2](P164)完本内容完整、少缺佚,例如《四库》所收《吴越春秋》,序存而缺徐天祐姓名,至不辨为何人所作。《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皆并为六卷,仍用天祐注,不著其名并削其序,而陆氏藏本首尾完具,模印精良,由是以为虽不及宋本,亦是书之善本。精刻精抄本讹夺较少,例如陆氏以郁氏新刊本与毛抄《杨辉算法》互校,凡校勘记所补正,毛抄本皆不缺不误,不禁叹曰:“盖毛抄之至精者,当与宋刊同观。”[2](P118)《范太史集》宋以后未见刊本,陆心源藏张立人手抄本,自始至终数十万言,无一字讹夺,陆氏以为诚善本也。
陆心源注重刊刻、存世较少的版本,例如大字本《通鉴》因卷帙繁重无人重刊,流传益罕,陆氏以为稀世之秘笈。毛抄《国语》以宋本久亡,世无二本,尤为钱大昕、段玉裁诸公所重。《书小史》宋以后无刊本,近时藏书家罕见著录,陆心源视为稀有秘笈。日本虽多藏中国古书,《经籍访古志》所载福井榕亭藏本《风科集验方》,只存卷五、六、十二、十四4卷,而陆氏藏本仅缺一卷,故他珍重自家藏本,亦见其于海内外善本之比较有清醒之认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版本有某种缺陷的书,陆心源也能以自己的眼光发现其价值。例如范晔《后汉书》本无《志》,刘昭注范书,以司马绍统《续汉书志》补其缺。宋椠蔡琪一经堂本《后汉书》不辨原委,《志》书亦题“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诚为荒谬,然因其所据底本为淳化原刻本,胜于今通行本甚多,陆氏以为“未可以一眚掩也”[2](P36)。元板《南史》虽刊手不佳,陆氏校以汲古阁本,乃知其善处。《分类夷坚志》原书四百二十卷,惟存五十一卷,出于通行八十卷及支志巾箱本之外者甚多,陆氏认为此本犹宋人所辑,当见四百二十卷全书,不但全书崖略可以考见,即宋人遗闻轶事,亦往往赖此以存,未可以删削薄之。
当然《仪顾堂题跋》在版本研究上也有其不足之处,余嘉锡在《书<仪顾堂题跋>后》指出其考证之失三:一曰辩证未确,二曰引证不详,三曰持论矛盾。虽有这些缺点,但诚如先生所说:“盖见闻或偶有不及,思虑亦容有未周……全书大体既佳,征引亦富,其精博之处,固不以一眚掩也。”[2](P677)从陆心源在题跋中对古籍版本的详细考证和阐幽释微,可以看出其识见确实非同一般。陆氏虽然以藏书闻名,但同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问家,当得起“富收藏,精鉴别”的赞誉[5](P677)。严佐之考察陆心源的一生,认为“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能不乏政绩,又能著述等身,还跻身四大藏书家,确属不易”[6](P153),对于这样的人物,其著作和学术贡献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