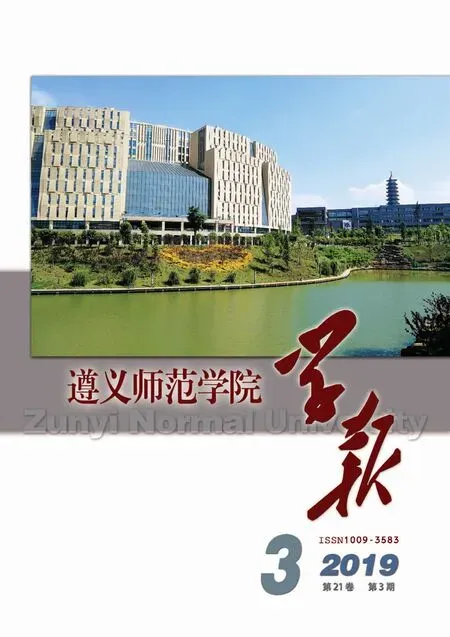莫迪亚诺小说寻找主题生成模式探微
郭昆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国内外关于莫迪亚诺的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研究范围覆盖了其二战时期的犹太记忆及后现代下的叙事策略的展现等多个方面,充分说明了莫迪亚诺小说中所蕴藏的生命力。莫迪亚诺创作初期的“占领三部曲”倾向于对自身处地定位的形而上思考,并将这种对个人的思考置身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使之能更好地凸显个人生命的本质。由于莫迪亚诺自身很特殊的犹太身份,犹太身份的书写时不时地要带进文本之中,这在其最初创作的《星形广场》(1968)、《夜巡》(1969)、《环城大道》(1972)三篇小说中都有所体现。犹太身份进入文本的途径比较细微和隐秘,比如在《夜巡》中同时受雇于总督和中尉两个互相对立的团体的“我”想从两方同时得到利益,“我”在两方的压力下识破了他们的诡计,“这些人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但早已秘密结盟要毁掉我。总督和中尉不过是一个人。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灯火。每次都烧焦点翅膀。”[1]P51因此,将来世界的命运与“我”无甚关联,只求能够无烦恼也无忧愁地随波逐流。[1]P79于是,当“我”在两方的伪装身份被揭开的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予以承认,中间充斥着无奈的感伤和命定的悲剧感,身份的无所归依在这里展露无遗。莫迪亚诺在后来的文本创作中虽然极力抹去其特殊的犹太身份,文本中却仍然充斥着无根感和漂泊感,反而更进入到了一种人生普遍意义上的身份或归属感的质询。这种对普遍意义上身份的质询在莫迪亚诺的小说,尤其是关乎小说的寻找主题有着最深切的体现。
一、寻找的契机:三种关系模式
莫迪亚诺小说主人公在寻找的初始阶段始终处于某种“关系网”之中,这里要么是关乎个人,要么是与个人有直接关系,要么凸显的就是时代的群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会像磁铁一样吸附在周围,相识、相恋、相爱和相知,但终究有一天,“每个人都在一条不同的时间走廊里”“如同两个人被鱼缸玻璃隔开那样”互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2]P116,然后关系开始破裂、分离,但分离恰好又是寻找的开始。《暗店街》(又名《寻我记》)是主人公寻找自我经历的代表作:主人公“我”十年前突然得了遗忘症,忘却了自身先前的记忆,侦探于特帮助“我”办理了一份假户籍(附带身份证和护照)——居伊·布朗。借用于特保留的年鉴、电话簿等探寻自身历史的种种,“我”的面孔在各色人物面前转换变色,“我”完全需要外人来确定“我”个人本身,自我注定不能脱离于他人对“我”的“海滩人”印象中;“我”个人的经历仍需要本人加以拼贴、组合和推演,这种选择性或间歇性记忆的方式,既有着现代主义思潮下的人无法找到自身归属的失落感,也有着个人对过去沉痛回忆的不堪回首。
而寻找与主人公有直接关系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亲人的寻找,另一类是对恋人、朋友的寻找。《环城大道》中,主人公“我”由一张照片想追寻父亲的身影或足迹,生活之父的缺失造成“我”精神之父的不在场。莫迪亚诺小说中把父母并置在一起并非是想寻求父母之间的一种绝对的对立态势,他们全然处在同一层级的地位上,在生活中的缺席致使儿女缺失家庭的温暖而走向逃逸的边缘,伴随着儿女的长大成人,这种对亲人的寻找带有自我寻根的意味。毫无疑问的是,莫迪亚诺小说主人公都很年轻、流浪和无职业,纵然有着看似牢不可破的三人家庭关系的组合,仍然暗示了家庭关系的松散。《地平线》中的主人公博斯曼斯和《青春咖啡馆》中的主人公雅克琳娜都有对母亲或亲情的逃离,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永远处于不确定、漠然和对立的边缘。《一度青春》中开头有一段诗意生活的描绘:“她和路易坐在木屋的凉棚下,远远观赏他们一对儿女:他们正同维特尔多的三个孩子在草坪上奔跑。儿子才五岁,左胳膊打了石膏,但似乎并不妨碍玩耍。”[3]路易和奥迪儿十五年前的生活是“惊心”,现在却比较“安逸”,这段安逸的场景可以说是莫迪亚诺作品中鲜有的一个亮点。可以说莫迪亚诺小说中“精神之父”的缺席让主人公像一株无根的浮萍,表面看似光鲜艳丽,内心实则已经千疮百孔。“我关注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生活在世外之人,正是要通过他们确认我父亲的不可捉摸的形象。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要编造出来。”[4]P50通过那么一种“编造”的技巧,“我”确定了自己的“精神之父”的地位,这样也才能为当下的生活找到更为坚实的基础。对朋友和恋人的寻找,既是向青春美好岁月的致敬,又是向阶段性青春的告别,个人的记忆的书写依托于对他人的记忆之上,通过对他人或与他人相交叉关联的历史来激活对自身经历的回忆,以此来确认自身生存的意义。《凄凉别墅》《多拉·布吕代》《夜半撞车》和《地平线》等即是此类代表作。《夜半撞车》在“我”即将步入成年的一天深夜,一辆轿车撞向了“我”,“我”被送往诊所,出诊所后,“我”一直追索轿车主人雅克琳娜的路程,并在寻找的过程中回忆起了事故前生活的点滴。看似这场车祸是致使“我”失却了一段时间记忆的“罪魁祸首”,但却毫无疑问地扭转了“我”车祸前萎靡颓败的生活,由此“我”开始了规划往后生活的企图,这便是这场车祸的意义。主人公通过与自己有直接关系之人的寻找,其实更大程度上在他人身上寻得了自己,重新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激活个人的生命体验。
最后,这种关系模式还有对时代群像的展示。《星形广场》《夜巡》《环城大道》《一度青春》和《地平线》等都是这方面的题材,尤其是以莫迪亚诺的“占领三部曲”为代表。莫迪亚诺的“占领三部曲”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入手来把握时代的群像,通过一种情境的书写展现历史大环境下的个人生活。《星形广场》序章说是写的“犹太人故事”,文中铺开展现二战时犹太人的历史,莫迪亚诺这里对二战存留的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记忆有着绝大的不同,莫迪亚诺本人也认为,普鲁斯特展现给我们的是本有稳定的社会,“普鲁斯特的回忆让过去在最些微的细节中重现,就像一幅活生生的画”,现在正是由于对记忆的失忆和忘却,“我们只能捕捉到一些过去的碎片、断裂的痕迹,飞逝的、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5]P67李玉民先生认为,“莫迪亚诺和普鲁斯特的文学创作,虽然都以记忆为内动力,但是一个是记忆的梦游,一个是记忆的追寻,一个呈现虚幻,一个体现真切,两者有本质的差异。”[6]这样来看,莫迪亚诺笔下不论是关乎个人经历的寻找,还是与个人有直接关系之人的寻求,都有一种展现宏阔的历史和凸显时代群像的冲动。其实,三种关系模式有时又可相互交叉和联系的,不论以何种关系模式开始主人公的寻找,都有对时代背景的展现和历史集体群像的揭示,这样才有利于主人公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坚定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对各种人及各种形式的追索,其实紧追不舍的只有我们自己。[4]P106主人公在寻找的过程中当然也充满了艰难险阻,这些阻碍正是莫迪亚诺笔下“点石成金”的时刻,其本身早已形成了一道迷雾中的风景。
二、寻找的途中:雾中的风景
主人公始终处在寻求自身生存意义的三种关系模式之中,中途往往充满着神秘和恐怖的氛围,这当然与莫迪亚诺偏爱侦探小说不无关系,但同时也反映出对先前记忆的每一步探寻可能真如在迷雾中前行并观赏的两边风景。
(一)光线、电话铃和人名
《青春咖啡馆》中侦探受雅克琳娜的丈夫让-皮埃尔·舒罗的委托寻找妻子的踪迹,两人交流完有关雅克琳娜的信息后定时开关的照明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侦探式的想象发挥出余地来。[7]P42侦探在追查雅克琳娜的过程中也有遭逢到灯光的想象,“更确切地说,我感觉到她就在这条灯火如闪烁的信号灯一样辉煌的林荫大道上,我分辨不出这些信号灯,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个远古年代发给我的。而这些灯火在土台的黑暗中显得更加璀璨夺目。既璀璨夺目又飘渺悠远。”[7]P54其实,唯有在暗处才能观察光影中的一切,思考也才能更丰富,“我是属于那种黄昏时分在池塘边停住脚步的人,是在观看死水所有的动静前,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昏暗光线的人。”[8]P85电话在互相分离的人们成了互相联系和交流的纽带,这时不论是《夜半撞车》中神秘的“帕蓝”旅馆电话铃,还是《地平线》中博斯曼斯梦见之前办公室响了许久的铃声都成为久已失联的人与人沟通的一种媒介。人名(含户籍和护照)在莫迪亚诺早期小说中只是作为作者处理的一个难题,之后人名只是作为一个代号,作者不会对人名有任何怀疑和疑虑,叙述者让读者也信以为真,人名的追索在这里失去了先前所赋予的光辉。
(二)宗教、集会等集体性的催眠
《夜半撞车》中博维埃尔“博士”聚会,《青春咖啡馆》中罗兰和雅克琳娜参加神秘学。“暗物质”才是这里想要追寻的,“在确切的事件和熟悉的面孔后面,存在着所有已变成暗物质的东西:短暂的相遇,没有赴约的约会,丢失的信件,记在以前一本通讯录里但你已忘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以及你以前曾迎面相遇的男男女女,但你却不知道有过这回事”[2]P2,而其显现的只能是冰山一角。乙醚在《夜半撞车》中既是致使主人公发生车祸事故并失忆的一个因子,当然也成为回忆的一个出发点和引起回忆的一条线索,即想要对之前模糊记忆的寻根溯源。《青春咖啡馆》中雅克琳娜偏头痛的时候有买维佳宁和乙醚,并和亚娜特吸叫“雪”的白色粉末,“过了片刻,那东西就让我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和轻松自如的感觉。我坚信在大街上侵袭我的恐惧和迷茫的感觉可能永远也不会在我身上再现。”[7]P79
正如谭立德在《夜半撞车》译者前言认为,“莫迪亚诺的小说并没有什么情节,其真正的魅力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在故事所传递和调动的氛围……故事中常常设置悬念,提出疑问,套用侦探小说的手法,紧扣读者心弦,并通过氛围的渲染,来表现作者的寓意。”伴着神秘的气息,并从中建构着莫迪亚诺个人的态度,即在一种对似是而非事实的把握中抵达回忆的终点。莫迪亚诺想在平凡的东西中,在背景材料中寻找到一种超现实的东西,认为事物的真实性反而就隐藏在这种超现实当中,“有一种磷光现象,它并非必然地来自于我,而是来自于这件事情本身。”[9]其实,莫迪亚诺认为“消失、身份、时间都和大城市的变迁密切相关”,显然,现在的城市不同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等作家笔下城市的书写,而是充满了各种神秘的可能性。[5]P66毫无疑问的是,莫迪亚诺通过对种种氛围的神秘描写既成就了莫迪亚诺创作的文学特质,同时又发现了小说的存在和书写何以可能性的问题,这种寻找途中的可能性直接伴随着所要追寻的结果。
三、寻找的结果:或此或彼的模糊书写
(一)浮动的叙述者
莫迪亚诺小说笔下叙述者常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视角出现,叙述者基本上等同于作品中主人公的视角,“叙述者和人物知道得同样多,在人物对于事件没有找到解释以前,叙述者也就不能向我们提供解释。”[10]首先是主人公家庭关系的归属问题。主人公在小说文本中大都没有确定的名字,有关家庭的线索只隐晦穿插在文本中,主人公像“海滩人”一样是不确定的、无所归依的个体,这种浮萍似的主人公带来的只能是整个寻找过程的茫然无头绪和与之相伴随的一种无所凭依的状态,这样使得“小人物”的书写成为莫迪亚诺笔下一道亮丽的风景,虽则能增加读者的认同感,但同样展现了主人公缺乏一定固定社会关系的根基。余中先先生认为,莫迪亚诺在《暗店街》中把寻找自我的主题发展到了极致,主人公丧失了姓名、履历、职业、社会关系等全部外部特征,真正成了一个飘忽的影子。[11]这样,以一个“不健全”的人的视角看待世界其实是不很确切的,处处是充满怀疑和不完满的。其次是主人公的限知视角。限知视角的使用一方面增加了寻找过程的神秘性和难度,另一方面同样也使得所追寻到的事实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状态。《环城大道》中父亲想抛弃“我”独自生活,忍心把“我”推下火车道,幸好有人拉住了“我”,在警察审问的过程中,“我应当承认明显的事实:有人要把我推下火车道,让列车把我碾成肉饼。推我的人,正是坐在我身边这个南美人模样的先生。证据:当时我感到他的戒指触到我的肩胛骨。”[4]P69他们是真正的父子关系吗?是叙述者固有的策略或者是在玩什么伎俩欺骗读者吗?……这些问题没有答案而且也不可能会有答案,读者只能进行无尽答案追索的循环。《青春咖啡馆》从学生视角、侦探视角、罗兰视角展开对雅克琳娜的点点追忆,雅克琳娜在这里就像是一个被观察者,那么雅克琳娜个人的视角又作何解释呢?《青春咖啡馆》有四个同级的叙述者,其中雅克琳娜的视角在其中处于主导作用,另外三个视角对雅克琳娜的视角所展现的内容形成辐射或佐证的作用,雅克琳娜到底是何种真身仍然值得探究。叙述者和主人公的感觉是否可靠,真实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莫迪亚诺像艾丽丝·门罗一样“……较多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她通过直接叙述或其他人物间接介绍等现实主义方式将人物的外貌、背景、职业、性格及个人经历等一一呈现,使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仿佛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随处可见。”[12]莫迪亚诺看似是一种对现实人物的真实呈现,我们仍然把握不住人物的真实形象。也许,这也就是莫迪亚诺想引领我们思考的寓意所在,而这也恰是莫迪亚诺所要引导读者注意分析的关键。
(二)模糊与精确的时空观
莫迪亚诺小说的时间观可以说是对现在时间的延续,现在时间并非是循环轮回的时间观,“我”之所处的现在是流动的现在,“我”由现在回溯至历史的记忆,过去的时间和现在时间发生重合;当“我”在追索属于过去的时间时,现在的时间又和未来的时间重合。现在便成了过去和未来进行交流的场域,回忆在这三重时间里能自由转换,记忆在这三重时间的重合中全然没有了与过去和未来的分界。因此,过去由于时间分界的消失与现在难分难解,“我”虽然能随时跨越这三重时间的记忆,但对过去的专门记忆却变得模糊而不可追寻,逝去的时间便无理由地逃遁而去。莫迪亚诺小说充满着地理空间的互文性,其空间诗学架构在对巴黎全景的整体构思上,并运用空间分割、切换主人公的经历和记忆的方式使得主人公在这种被切割空间中的逃逸变为可能,巴黎的星形广场、环城大道、香榭丽舍大街、咖啡馆等完全成了莫迪亚诺自由驰骋想象的园地,巴黎的琐细而又繁复的街道、历史与现在交汇的遗迹、光与影的变幻在莫迪亚诺的笔下展露得巨细无遗。各色人物在巴黎的时空里穿梭而相互不识,“时间走廊”和“固定点”的时空错位全然找不到一个在静处可观察的一点,充满着变化和各种存在的可能性,这与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密切相关。莫迪亚诺想通过寻找逝去的回忆抵制时代过快发展的现实,莫迪亚诺对十九世纪的小说充满着一种“怀旧的意绪”,认为十九世纪的时间过得要比今天要缓慢,十九世纪时间的那种缓慢和小说家的写作恰好是合拍的,那时的作家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和注意力搞好创作。[5]P61结合第一部分对关系模式的论述,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莫迪亚诺所盼望建构的是一个不用识辨他人的历史就能和睦相处,大家虽互相存有防备心但马上就能互相融入对方的真实理想的社会,每个人的背景关系虽则复杂,但却能相处融洽,各取所需的现实。寻找的过程既有对自己、他人等的寻找,同时又把这种寻找嵌入到有关巴黎的时空观中进行具体的展现,从而使得寻找的过程变得既具体又模糊,小说中的人物是否都寻得了自己的回忆,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并且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不仅主人公在追索,我们也在寻找的边缘,我们与主人公之间好像也在发生着某种时空的错位和置换,以此为我们指明继续生活的方向。
四、结语
莫迪亚诺在创作观念上是少有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题材形式坚持如一的作家,其笔下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寻找的漫漫长途中。无论是对自我的寻找,亲朋的寻找,还是对时代群像的考察,都是想定位自己的位置,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途中经历的像是在欣赏着迷雾中的风景,并极力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吴岳添先生认为,莫迪亚诺小说中虚实相间的创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小说吸取现代小说的结果,“他的小说以虽然虚构却真实可信的故事来表现生活的不安和危险,由此形成了一个既确实存在又变幻不定的世界。”[13]但莫迪亚诺笔下展现的难道真正是所想要展现给我们的真实?昆德拉在对海明威进行分析时发现了“现在”,认为人只在过去的时间才能认识现实(记忆中的现实),回忆并非是遗忘的对立面,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14]“现在”具体的情境由于时间的退场或缺席转变成为过去被讲述的抽象,寻找失去的时间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变成了对抗遗忘的方式,这种碎片化的叙事很难让人想到是具体的现实回忆,这就像“莫里森的小说充满着分裂的故事片断,她的叙事者从不连贯地讲述故事,而是偶尔进行插话,随后便消失在小说的进程中,读者所要做的是积极参与到小说的碎片叙事中,与作者一起建构。”[15]
《夜半撞车》中披露主人公追寻的原因:尽管“我”出身卑微,但追寻或许能让“我”发现“并不了解的自己生命中的整整一个部分,一个在流沙下面的坚实的基础”[8]P104,认为生活要比想得要简单的多。个人通过回忆发现了未来,意味着寻找的并不仅仅在于结果的扑朔迷离和这个不确实的世界本身,更重要的是可以重新激活个人的生命体验,然后能让人们恢复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