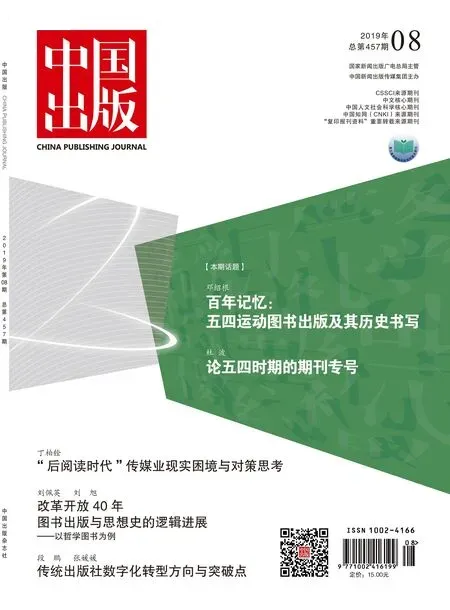五四时期新闻学遗产与近代中国重大自然灾害报道模式流变*
□文│王 华
晚清以来,水、旱、蝗、疫等一些重大自然灾害给国民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损失,文学作品与媒介新闻对此皆有反映。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就是众多灾难书写之一。这些文字总体性地铺展了多灾多难的旧中国社会诸多面向。1936-1937 年,四川发生特大旱灾,持续时间长,影响面积广,受灾程度重,百年罕见。1937 年4 月,范长江奔赴四川进行了采访。《川灾勘察记》就是范长江当时所写的一篇重要的自然灾害通讯,发表于1937 年5 月30 日《大公报》第3 版。
一、早期自然灾害报道与新闻观念的关系
可以说,重大自然灾害报道是随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而产生的,将自然灾害新闻研究视野拓展到1949 年以前,自是情理之中,也利于全面、完整地认识灾害新闻。《川灾勘察记》是1949 年以前灾害报道的一个典型文本,它既对公厕产妇、求助老农、夜市评书、路边饥民等灾情事实进行了细致呈现,又批评了旱灾时期利用灾情致富、强派鸦片、强验地契等社会不良现象,对灾害成因、救灾工作、川政情况、社会影响都进行了宏观性评议。[1]《川灾勘察记》还大量引入历史、地理、饮食文化等知识,运用白话文叙事,故事性、可读性强,显示了记者宽阔的知识视野和文字能力。那么,灾难通讯逼近灾害事实,尽力展现丰富的社会底层情状,并敢于批评时政,这种灾害新闻报道观念是如何诞生的呢?究竟是个案秉性的独特性体现,还是那个时代一批记者的职业追求呢?
1.早期灾害报道指导和“以新闻为本位”
1923 年,对于灾害新闻采写问题,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谈到了记者在采访具体新闻事件时候应该记录和报道的项目,其中包括失火、地震、暴风雪雨、煤矿爆发等“突发之天灾地变”,这应该是国内最早详细地为灾害或突发新闻实践所做的指导,比如其对“地震”如是所述:①震动之时刻(何时)、时间(多少时)、范围,②地震之性质强弱,③震源及地震之方向,④损害(家屋及其他建筑物之倒坏、半坏、人畜之死伤),⑤罹灾民之救护,⑥悲惨之罹灾者,⑦罹灾者避难之光景,⑧在同地方前次震灾之回顾,⑨山崩、龟裂、海啸、余震,⑩有无前兆。[2]
这些报道项目反映了邵飘萍的新闻报道原则。邵飘萍称,“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3]新闻学者陈力丹认为,“以新闻为本位”恰当地表达五四时期新闻思想特点。不论是《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著作,还是具体新闻实践,它们都深受西方新闻思想影响,把新闻作为构成报纸的第一材料,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新闻事业作用第一位。[4]此外,萧乾在报道1935 年山东黄河水灾时,分别从“鲁西难民”“大明湖畔啼哭声”“宿羊山麓之哀鸿”“从兖州到济宁”四大方面,进行了灾情和民生记录。当然,除关注信息本身之外,早期灾害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入阐释了灾害原因、社会影响、民间应对、官方赈灾等等。
2.文人议政的延续与记者服务社会精神
中国文人心怀天下、勤于议政,自古有之。“整体上,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由士大夫阶级践履不决的公共批评的潮流,只不过这样的事实不为中国新闻与舆论史专业的学生所知罢了。”[5]这种批评精神在20 世纪30 年代的中国新闻事业中有所体现,例如《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以及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进行西部考察临行前,总经理胡政之所教导的“新闻事业是国家的公器,新闻记者应当为社会服务”,[6]一定程度上是对古已有之的公共批评精神的注释和延伸。在当时西方新闻理念(特别是“第四等级”)传入背景下,这种精神被报人们接受与放大,使中国新闻事业焕发着现代色彩。在此基础上,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范长江也发挥了个体潜质,秉承文人议政倾向和公共批评精神,以敏于观察细节和洞察社会宏大走向的智力,朴实而又大气地书写了“川灾”。
二、近代中国重大灾害新闻报道脉络与特点
如果以《川灾勘察记》为原点,考察其前后灾害记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灾害报道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闻实践中是变化着的。
1.从传统文言记史转到现代白话叙事
自古以来,中国灾荒不断,历代史籍中皆有所记录。在前代繁多、零乱的灾荒统计调查史料基础上,邓拓于1937 年曾对历代灾荒史实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并分析了灾荒成因与影响、历代救荒思想和历代救荒政策。从中可见,历代典籍对灾荒情况都进行了记录,现试举两例:
“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夏本记》)[7]
“世祖顺治五年,山东、夏津蝗。春,广州等三州县大饥,人相食。二年,邱县大雨雹。三月,海丰雨雹损麦;泾阳地震。闰三月,昆山雨雹如斗,破屋杀畜生。……八月,海丰飓风,毁庐舍无算。”(《十一朝东华录》、《清史稿》)[8]
有趣的是,在论述民国灾荒情状时候,邓拓写道,“兹就逐年政府公报,及各种新闻纸等直接材料,将历年灾荒之实况汇举如下”[9]。可见,邓拓所参照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就是报刊资料,具体如:
“吴县各乡农田,本年因为天气亢旱,三月不雨,故被灾田亩有二十余万亩之多。县政府现在分别派员赴乡实地查勘,距今一星期前,有某勘察委员会赴斜塘乡堪荒:被农民一度包围,后经区长等劝导后,始各散去。……”(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报》)[10]
于是,新兴报刊开始广泛记录社会灾害事件,与其他新闻题材一样,新生报章灾害文字多属文言文,后逐渐有文白混杂,而《川灾勘察记》则直接用的是现代白话文。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了这一转换,白话文改革促进了报纸方式和新闻语言风格变化。
2.从新闻到政治宣传
对于重大自然灾害报道,新闻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两大特征:一是视域往往置于1949 年之后;二是批判多于肯定。前者与当下新闻学研究的年代史思想、政治分期观念以及新中国特殊的历史形态紧密相连。其实,重大自然灾害报道远在1949 年前已经层出不穷,代表如萧乾的《流民图》,李蕤的《喑哑的呼声》《风沙七十里》《雨天绝粮记》《粮仓里的骨山》等形象生动的通讯。
重大自然灾害报道研究中的“批判多于肯定”,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一个争议上:“灾情”和“救灾”孰重孰轻。之所以有此争议,主要是1949 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重大自然灾害报道乏于灾情描述,而重于救灾报道。这种新闻政策直接溯源到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一段指示:
“各地对于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地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过去的灾情报道一般是有益的,但亦发生了偏向,……这种报道把个别的特殊的例子夸大为一般的现象,片面地孤立地宣传灾情的严重性,而没有和实际工作相结合,这是客观主义倾向的表象。这种报道可能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同时给予帝国主义反动派夸大我国灾情,进行挑拨造谣的藉口。”[11]
基于国内外政治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扩大救灾工作报道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在今天的灾难报道中,这种政策仍旧不能废之不理。同样,这一灾害报道策略也与当时新闻理念是一致的,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陆定一对“五四”以来传入西方的新闻学常识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确实产生了效果,人们努力抛弃‘资产阶级新闻理论’, 不再讲究新闻价值, 以及新闻时效和新闻的趣味性, 仅在形式上接受了新闻写作的‘五W’,投身到全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工作中。”[12]随后的灾害书写在此基础上模式化,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稍有好转,许多报道在这一政策下不断突围。
3.从政治宣传到信息
进入新世纪,经过商业化、娱乐化和受众本位思想影响的中国媒体灾害报道,进一步转向新闻本身,分类、分专题地全息透视灾害,分析灾害动因,注重政府主导的救灾与社会各类救助联合报道。[13]从2003 年的“非典”报道,到2008 年的汶川地震报道,再到2010 年的舟曲泥石流报道,新闻利用现代多媒体方式,及时跟踪灾情,注重救灾的多样采写。在这一变化进程下,重大自然灾害报道的模式化批评已属过时,应当超越“灾情”与“救灾”之争,其实,重大自然灾害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准确传达信息,而“救灾”也应该是新闻的一部分。新闻从业主体既不可完全夸大救灾功绩或为其歌功颂德,也不可单一地回避或者漠视政府主导的救灾行为和英雄故事宣扬。在当前复杂的社会中,救灾报道延伸出来的一个主要方向是灾后抚慰和持续关注。
改革开放前后30 年中国新闻业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 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 年的新闻本位。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推动了其他一系列变化。[14]中国灾害新闻报道同样受到这一推动,并逐渐进行了第三次转身。这一转身背后存在着中国受众素质不断提高、信息观念张扬、媒体竞争压力等多种原因。为满足受众的知情需求,掌握重大灾害报道的话语主动权,中国媒体已经逐渐回归到了信息本身层面。人们隐约地感觉到当前重大自然灾害报道又回到了范长江《川灾勘察记》报道轨迹,一致重视灾情细节,服务社会。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复现,它存在着一种超越与提升,需要进行深入地注解。
三、灾害报道需要坚持公开、人文的意识与全球视野
当然,对于中国重大自然灾害报道及其批评意见,需要全面解释。其中,重大自然灾害报道要在“灾难—人—社会”关系框架下铺展信息,形成“灾情进展—救灾工作—心理疗救”动态报道模式。灾情动态也要注重社会影响,并非完全地“按需报道”,应该在职业道德、社会关怀以及法律法规下进行权衡,以防灾难报道本身引发“次生灾害”。[15]“救灾工作”是重大自然灾害新闻报道无法回避的,对于政府救灾、抗震英雄和民众自救等信息,灾难报道是需要书写的,但要防止陷入僵化的教条境况,不能仅是从政府关怀与灾民决心上宽泛地讲述,而是要采写活生生的社会情绪、灾区表情与救济措施。例如,《川灾勘察记》在结尾即写道:“救济川灾,尚无根本办法。一方面应谋政治之刷新,军队之整理。另一方面应从大规模的工赈农贷入手。对老弱应设办收容所,普通的急赈,已没有多少用处。”[16]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主导的救灾报道依然需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如果媒体在传播事实过程中过分强调主观意识,用“宣传概念”取代或弱化事件情节和细节,受众将会失去进一步接收和参与传播的兴趣。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各类风险随时可能在我们意识内外发生,而我国幅员辽阔、地质复杂,各种自然灾害事件频发,“风险传播”和“危机传播”被高调提出。不过,“风险传播”和“危机传播”往往采纳一种社会控制和政治控制视角,多集中于对非自然性的政府、企业与传媒危机的关注。一旦这些讨论缺乏足够透明的信息、公共批评精神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诸如此类的控制性研究都将是缺乏弹性的。
追溯灾难通讯《川灾勘察记》,正是要把信息性与批评精神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既批判地继承《川灾勘察记》新闻理念,又要面对现代中国社会语境,在“人、自然和社会”关系中继续探索自然灾害新闻走向。众所周知,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早已是不争事实,全球传播技术早已得以普及,重大自然灾害报道影响早已是世界性的。因此,有关报道需要树立一种全球意识,使用人类生存、地球环境保护等视野和思维来观照灾害,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内权且传播。此外,当我国重大自然灾害报道早已突破单一的救灾新闻套路,坚持新闻性和社会责任感的时候,灾后的精神疗救性文字和影像书写应该有所张扬,以全面地审视灾难和敏锐地跟踪灾后。有研究建议,社区报纸及其从业者可以吸取公共新闻理念,践行灾害社区新闻学,通过举办社区活动和议题设置,达成社区情感营造。[17]
其实,我们可以从重大自然灾害报道流变中明显地发现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与转变。陈力丹曾在上个世纪90 年代指出,中国新闻学发展基本脉络可以用“报馆有益于国事”“以新闻为本位”和“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三大观点来形容。[18]如今过了近30 年,新时代中国新闻学发展又迈入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阶段。在这些新闻学逻辑思路下,重大自然灾害报道从《川灾勘察记》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乃至批评当时报刊灾情新闻落入“客观主义倾向的表象”,之后又转向当前灾害新闻的及时跟踪。重大自然灾害报道的思路变化深受中国新闻学理念变迁影响,这也是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当下新闻学发展阶段回顾范长江这份新闻遗产的初衷所在。
注释:
[1][16]范长江.川灾勘察记(一九三七年五月).范长江新闻文集(上)[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2][3]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J].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3)
[5]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方蒙.范长江传[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7][8][9][10]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一九五0 年四月二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12][18]陈力丹.新启蒙与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J].现代传播,2004(1)
[13]杜耀锋.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突破——5·12 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J].新闻战线,2008(7)
[14]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 年新闻媒体[J].国际新闻界,2009(9)
[15]苏虹.“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对“5·12 汶川大地震”灾难报道的一些反思[J].新闻大学,2008(4)
[17]蔡莺莺.921 地震灾后的社区报纸与培力[J].新闻学研究,201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