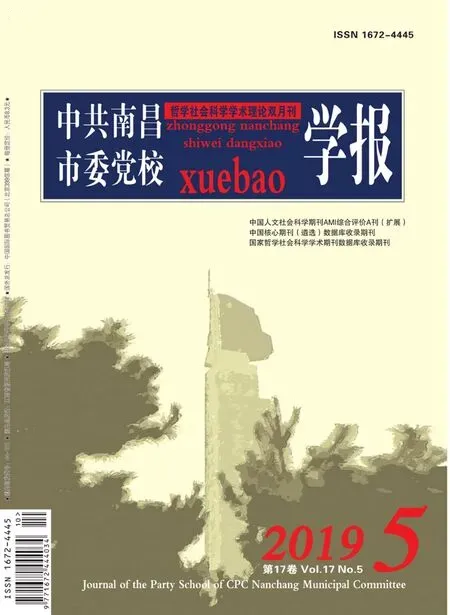马克思自然观的立论之基、核心论题及目标向度
刘歆 卢晓 苏百义
(1.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2.鲁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思考、认识和把握是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内生动力,是数千年来古圣先贤反复思考、不懈摸索和系统探赜的哲学命题,是无数仁人志士探索自然演化规律、展望人类社会命运、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向度。步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人类社会在实现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生态危机持续扩大。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下,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出发,在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弊端的基础上,为人类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枷锁”和迈向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路径,以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和解”。
一、立论之基: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人与自然的定位
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人依赖于自然”“人与自然异化”“人与自然圆融”三个阶段。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水平有限、活动空间尤为狭小、物质产品极度匮乏,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深感天道之深邃、自然之伟岸、宇宙之神秘,人类只能被动地、消极地依赖自然、屈从自然。在这时,“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P534),可以说,自然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关系和生活质量。在资本主义阶段,康德提出“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2]的哲学命题,导致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对立思维模式的泛滥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生。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稳步提升、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一方面导致人变成围绕机器工作的附庸,成为悖离本质的孤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摧毁着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诱发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在共产主义阶段,生产资料的全面占有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真正解决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恶性竞争的社会根源被消除,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活动的异化被扬弃,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协同共进和永续发展的圆融状态。
(二)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的自然观源起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复思考、深刻认识和着重把握。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共生共荣,二者“天然”地融合为“一体”,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而实现和谐统一“整体”的关键在于实践。
一方面,作为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人类能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复现于自然界,调整和控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使自然界、人类社会同历史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但这一过程必定受到自然界和自然规律的制约,因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P209);而自然界具有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主体性和本原地位,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光热、森林、空气、食物等自然条件和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桥梁”,实践是建立在人们认识自然规律基础上的物质活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自主性、参与性、创造性的物质活动,是主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在对自然的不断改造中加深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立足自然现状、掌握自然动态、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就会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最终演化为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三)人与自然的对立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极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可以说,作为物质演化的最高级形式,人类经历了无数的巧合与偶然、灾难与险阻,最终产生了自我意识,形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
人类的生存发展史是人类血和泪的历史凝练,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史。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初步确立了人类社会的理性原则;“柏拉图的理念论标志着西方文明走上了灵与肉分离的形而上学的道路”[4];从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到培根的“工具理性”,进一步强化了人类社会的理性精神;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使西方灵肉分离、二元对立的理性文明达到人类思想史的高潮。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从根本上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它以征服、称霸自然的方式来证明自我的本质力量,造成自然界真正意义上的裂变,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加剧,最终使人类文明走向万劫不复的困境。在当前生态难题凸显的大背景下,生态危机告诫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否则,“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5]。
二、核心论题: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
(一)资本逻辑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
从古希腊理性文明和希伯来信仰文明演化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在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以掠夺、控制自然为目的,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机器的广泛运用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通过机械化、化学化、设施化等技术手段从大自然中无限获取物质资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满足了人类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泛滥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单纯的主客体关系,把自然视作人类征服、改造和利用的客体,导致人与自然长期处于分离对抗和异化状态。
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积累、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就是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逻辑”[6]。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工业文明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把土地、森林、矿藏等自然资源以及一切生命都变成了自己满足欲望、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增值和增效的财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本性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本质,激化了社会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生态系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在资本疯狂趋利和扩张的运动中,资本主义企业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视为核心要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因此,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抢占、掠夺和控制自然资源,增加工厂投资、提高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逼迫工人进行最大限度的产出,以获取最丰厚的利润和最大化的剩余价值,但是这势必侵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割裂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造成人与自然分离对抗状态的进一步加剧,全球性生态难题的进一步凸显。
(二)资本扩张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
马克思曾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赜、剖析和解读,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明确使用“生态危机”一词,因为那个时代尽管隐现出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星星之火,但却未呈现生态危机的燎原之势。马克思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构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工业资本所到之处充满了扩张、剥削和杀戮,对自然界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科学预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的生态问题的全球性扩展趋势,为人类构筑了破解生态危机的智慧之光。
当人类破解自然之谜,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人类仿佛在自然面前获得了胜利,然而,每一次胜利都是迈向悲剧的一个环节。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资本盲目的自我扩张和“成本外在化、收益内在化”的逻辑造成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引起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关系,使人类社会与自然发生新陈代谢断裂,表现为生态危机在世界各地的蔓延,笃而论之,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造成人与自然紧张对立、生态危机持续扩大的重要根源。
(三)制度变革是规避生态危机的最优路径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是人类整体面临的生存条件困境,预示着人类生命活动能力的发展开始破坏自身生命存在的条件,意味着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中断,是人与自然之间张力恶化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是工具理性疯狂渗透和资本逻辑无限扩张的结果,是西方工业文明“理性万能论”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沉疴痼疾”。只有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而非“技术性修补”,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与自然分离对抗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类的真正自由和人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视角出发,指出人与自然新陈代谢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必须返还于土壤,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这种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使得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刺激市场消费,进而导致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最终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失衡。马克思在批判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弊端的基础上,强调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形态——“自由人联合体”,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解”的基础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
三、目标向度:共产主义社会两大“和解”
(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历史趋势的展望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双重维度,马克思着眼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逻辑生成、综合发展与历史演变的产物,并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阶段三大历史形态,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两大“和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正确处理“自然——人——社会”三者关系的终极目标,这为人类正确处理生态难题、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正义提供了实践指南。
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改造能力有限,人与自然之间狭隘的活动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本质力量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与他人合作才能实现,但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在这一历史时期,人们不能充分认识自然又高度依赖于自然,土地的肥沃程度、气候变化、开发方式等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关系,引发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改造能力的提升,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但此时社会财富还未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人依旧局限于对物和他人的依赖之中。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另一方面导致人愈发失去对机器的统治地位,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物与物的关系,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迷失了自己”。在“自由个性”阶段,随着人类实践深度和广度的空前提高,生产资料的全面占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彻底克服了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的局限性,消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活动的异化被彻底扬弃,人类从支配他们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其存在价值得到充分确证,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协同共进的美好状态,人类历史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状态。
(二)对不断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发展的社会状态的设计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呈现扩大态势,甚至进一步演化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这场声势浩大的危机从表面上看,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生存空间,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和生命物种的灭亡;从长远来看,它必将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乃至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走向。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以宽广的世界视野、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以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为目标,向全世界发出了“建构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最强音。
“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无限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处于分离对抗与异化状态的罪魁祸首,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技术性修补”都无法从源头上改变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才能破解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才能克服资本逻辑的扩张性、侵略性、掠夺性,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同阶级的紧张对立,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回归。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P185),只有到那时,人类才会摒弃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枷锁”,迈向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状态——“自由人联合体”。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关系一直贯穿于人类历史进程,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马克思的自然观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罪魁祸首,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全景式的批判、解构和超越,最终为人类建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和解”的“自由人联合体”,这对我国在新时代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