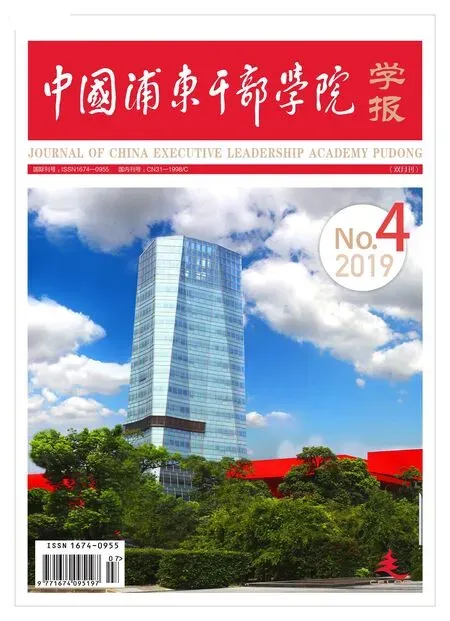中国崛起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
——兼论《资本论》的文明意蕴
张艳涛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马克思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以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破解为导向,才使得《资本论》经过150余年的沉淀依然具有穿透时空的思想力量。《资本论》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典型样态的解剖学,通过分析“资本奴役劳动控制社会”这一总问题,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提出后发现代化国家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0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既充分肯定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又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文明的限度,得出了资本主义是“承上启下”的历史性存在,开启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有鉴于此,有必要深入挖掘《资本论》的文明意蕴。
一、《资本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表达
《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文明的历史作用及其限度的理论表达。理论上,马克思在19世纪通过《资本论》科学阐明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及其限度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1]887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挤压人的生存时间与空间,历史地看,资本却“极大地张扬了资本持有者的个性,加速了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进程,为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从资本逻辑与文明进步的关系看,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比此前一切社会都更有利于打破人对自然的崇拜和人对人的依赖,有利于破除封建社会的种种桎梏,从而为现代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并建立起现代社会联系,同时为人的自由个性创造条件。在资本主义时代,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找寻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条件,探索一种不以“资本逻辑”而是以“人的逻辑”为主导的新型文明形态,就成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基本动因。
如所周知,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计划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后来马克思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当时资本主义的中心伦敦创作了《资本论》。概括起来,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动因主要有三:“动因之一是要科学地揭示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真实关系,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动因之二是要揭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言,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明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动因之三是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为解开人类历史之谜进行理论探索。”[3]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考察最终指向了“消灭私有制”,可以说“消灭私有制”这一信念构成了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石。从历史维度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封建所有制的否定;从现实层面看,现代社会依旧没有跳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理论框架;从未来视角看,消灭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则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历史地看,“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927-928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客观条件只是劳动者主体性得以实现的无机自然,二者的结合具有简单的、片面的统一性。而“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198——“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成果,破除了以前交往方式的地域局限性,使民族历史演进为世界历史,但同时也伴随着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的统摄。马克思直言:“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269无独有偶,福柯也揭示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根据它的根本法则,它必然要产生不幸。资本主义存在的目的不是要让工人挨饿,但是,如果不让工人挨饿,它就不能发展。”[5]37-38可见,以资本逻辑为本质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以占有工人劳动为前提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现实地看,当今时代依然是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因此《资本论》并未过时,依然具有巨大的理论解释力和思想穿透力。《资本论》是“剖析当代资本主义市场权力结构,进而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的最深刻理论”。[6]第二版自序虽然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出新的样态、拓展出更广阔的空间,但资本只有依靠不断占有剩余价值才能保存和实现自身的本质特征没有改变,结果是在现代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仍然是最核心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此前提下,《资本论》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从《资本论》问世的19世纪到21世纪,实际上是从大众到分众的过程。21世纪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明显增强,如何在社会“分化有余而整合不足”的形势下进一步激发资本活力,提升资本的文明作用,就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现代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现代性的文明就是资本的文明。因此‘驯服资本’的道路就是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7]221
用未来的眼光看,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历史性和过渡性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文明同样如此,人类文明最终指向的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的过渡性就体现在,大工业终结了农业文明后,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胎胞里逐步发展了生产力,同时又孕育着解决其内部对立关系的物质条件,即新的更高类型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对高级文明形态的科学预测最终指向共产主义,也就是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走向“人的自由个性”,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资本主义的必然王国,存在着多种对抗关系:资本家的自由时间与工人的剩余时间的矛盾、资本家的自由发展与工人的片面发展的矛盾、资本家能力的充分发挥与工人能力的被制约被限制的矛盾等,而且“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8]214但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4]929在真正的自由王国,必然王国的一切对抗关系都不存在了,联合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每个人充分发挥自身多方面的能力,这无疑为人类新文明开辟了新道路。
对人类新文明的探寻,还要回到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应该说,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就蕴涵着超越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对此,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74这个“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就是资本无法克服的自然限制,体现在现实中就是资本的私人占有性。如何在理论上充分认识资本的限制,并在实践中克服这一限制,在此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开启新型文明形态的重要方向。
总之,无论哪一种文明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文明形态,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文明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分娩的。资本主义文明只有充分发挥自身文明的力量之后,才能退出历史舞台。毕竟,新文明形态的产生需要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只有在充分吸收此前一切文明积极成就的滋养基础之上才会具备。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中国现代性”及其展开能否构成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超越,依然有待长时段的历史和实践来证成。
二、中国崛起: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契机
当前,人类社会整体上已经进入“后西方社会”,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人类对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方面,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中国既要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文明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要防止崇洋媚外,失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较大贡献?关键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把世界现代化模式从“单选题”变成了“多选题”,可能开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前,大国崛起通常是:在国际上,一国牺牲别国而致富;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阶层牺牲另一个阶级和阶层而致富。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页。而未来大国崛起应主动承担世界历史责任,并给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和谐,给本国人民带来福祉。从文明论的视角看,“大国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制度文明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内部深层次文明力量的外延,是文明复兴与创造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力量转移与全球秩序重构,中国发展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可以说“中国向何处去”也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向何处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所蕴涵和展现的“整体转型升级”,最终就是要在中国建构起“现代文明新秩序”。“只有在建构现代文明秩序方面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才能真正由‘大国’走向‘强国’,也才能更加赢得世界的尊敬与尊重。”[9]中国崛起的关键是,破除“贫富分化”的陈旧逻辑,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破除“强国必霸”的陈旧逻辑,跨越“塔西佗陷阱”;破除“一山容不得二虎”的陈旧逻辑,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无疑需要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
中国应当对世界文明有较大的贡献,无论从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形势看,当代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古代中国曾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以及殖民扩张,主导力量向资本和科技转移,由于近代中国没有这种力量,因此西方国家主导人类历史长达300年。这300年间资本为谋取更多利益,不断加强资本扩张、文化压制、市场垄断,逐渐暴露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世界呼吁一种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文明出场。中国作为世界几千年历史上唯一连续的文明体,诚如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0]157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曾坦言:到21世纪中叶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11]233并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和平政策,“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11]158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也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12]可见,半个多世纪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蕴涵着“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改变着世界体系的“物质力量结构”,还会带来“世界精神结构”的革新,这种世界精神结构最集中体现在“精神—文化建制”和“政治—法律建制”上。因此,中国不仅要从世界发展趋向中提炼出“现实的原则”,而且要进行“有原则的实践”,中国崛起的道路选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崛起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承载着当代中国人的雄心壮志,体现出中国人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崛起不仅要通过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打造“物质中国”与“经济中国”,更要通过生产关系的优化,打造“文化中国”与“文明中国”。中国和平崛起和文明崛起就是要改变“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等弱肉强食、倚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道路绝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模仿和重复,而是以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为指向,可能为人类发展创造新的文明形态。对比之下,“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以民族文化相对性为借口,试图以‘另类现代性’争夺全球霸权而最终自掘坟墓,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不能挑战底线,相反地,积极展开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这是赢得文明主导权的不二法门”。[13]53-54中国积极走文明崛起之路,创新人类科学发展和文明发展模式,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
中国的文明崛起之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意义。中国崛起绝不是靠打压其他文明巩固自身地位,相反,是以尊重和繁荣人类文明多样性为己任的。实际上,人类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各种文明只有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和互学互鉴,在差异和多元中寻求共识,在协商和对话中消除隔阂,才能获得共同的繁荣和进步。“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4]29为此,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一种发展模式。正是由于中国崛起及其示范效应,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认识到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关键是走对路。
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成果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为人类开辟一种新文明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就,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崛起能否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能否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强制规律,能否成为创造新文明的力量?一切的关键都在于,能否超越“现代性文明”而实现“文明型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和世界潮流,它构成了一条使人类大多数民族投身其间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需要新的解题思路,也就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建构中国现代性,其结果极有可能孕育出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
在追求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同时,如何不牺牲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个难题!如何把“社会主义的公平”和“市场经济的效率”结合起来并发挥各自优势,这同样是个难题!过去,我们过于注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直接支配作用,结果导致市场和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如今,确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主旨就是要重构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今,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法治主义的政治思想,构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新的“三位一体”。[15]388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建制?关键是建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主体和法治规范,防止“市场经济”演变为“市场社会”。事实上,“在后改革开放时代,当代中国只有超越‘资本的文明’,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一种‘超越资本’的文明”。[7]230就此而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分析仍需要进一步激活。
中国崛起,如何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这24字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市场规则为核心的“竞争型”价值导向,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型”价值体系。“三个倡导”是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确立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关键词,既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充分吸取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着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道路,孕育了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一条和平崛起与文明发展之路。现实地看,中国道路不仅对世界作出了“生存性贡献”和“发展性贡献”,而且还作出了“和平性贡献”和“文明性贡献”。可见,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问题进行中国理论建构,本质上是进行一种划时代的整体性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建构不仅具有中华民族首创意义,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三、文明的力量:文明型现代化之路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刀剑,二是思想;前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其实,思想比刀剑更有力量,正是思想成就了人的伟大,正是伟大的思想铸就了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思想就是力量,有思想才会有力量,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既要注重“物的力量”,也要注重“思想的力量”。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需要研究“轴心文明说”与现代轴心文明出现的可能性问题。轴心期文明主要包括中国(中华文明)、印度(印度文明)、以色列(犹太文明)和希腊(欧洲文明),这一时期最有可能产生人类文明新形态。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既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各种文化的反思过程。类似地,帕森斯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哲学的突破”阶段,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世界文明演化的“苗床社会”,受契约和财产制度的影响,现代西方社会成为文明进化的唯一成功者。归结起来,雅斯贝尔斯和帕森斯的观点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诚然,资本主义在短短300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加速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并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各方面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严峻的阶级斗争、严肃的伦理问题等现象,这启示我们,在多种文明形式并存的21世纪,需要以历史的眼光认清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另辟蹊径为全人类探求更文明的发展路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研究思路可以成为研究轴心时代的一个崭新视角。在《资本论》中,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揭露出资本主义文明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正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打破了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正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以及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会被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文明所取代的趋势。承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论》的伟大续篇和最新创新成果”。[6]第二版自序21世纪,我们处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时期,要将这种“新文明观”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不仅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充分了解当前世界的各种文明样态,还要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强大的信心,唯有如此,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当前,中国虽然逐渐强大,但仍不够自信,要在国际竞争中把中国发展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关键是充分发挥文明的力量。进言之,也就是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走向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
文化自觉首先是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是其对文化自觉理念的高度概括。“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6]前言文化自信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包括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在力量。从社会整体维度看,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则是体现在“四个自信”背后更为根本的力量源泉。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①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文明自觉要求我们明确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和未来趋向,文明自信则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中华文明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文明而存在。在今天坚定文明自信,不止体现在对中华文明的内化和弘扬上,更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实践上,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才有可能在世界众多文明类型的包围中开辟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建构起一种异于资本主义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新的世界秩序否定文明冲突和文明等级差异,肯定文明互鉴与文明共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后的“第五个现代化”。“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个人”的出现都需在“第五个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我们认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建立“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其核心是建构“现代心灵秩序”,也就是转统治为治理、转人治为法治,以人民为中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引导个人消除传统思维惯性,培养具备现代化思维的人。
中国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引人注目的中国奇迹,关键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一种新质的文明制度,其内在优越性在于,始终秉承人民利益本位的坚定立场,坚持从整体性构架上谋划、设计和奠定属于这一制度的价值基调和蓝图。”[17]改革开放释放了部分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中国正是将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迅速崛起。如今,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4]16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引导下,中国资本开始大量“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金砖+”模式和亚投行等为中国资本“走出去”开辟了新道路,同时也给国际合作开辟了新空间。一句话,只有借助于政府、市场和资本三者所形成的“合力”,中国才能建成“现代国家”、中国社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中国人才能成为“现代人”,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比较而言,文明的力量相比于武力和科技具有更深远更持久的影响。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自身局限性。在多种文明并存的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践证明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尊重不同文明能够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既能够建构中国自身的现代性,也能够创造多种文明共存的人类社会。
四、文明共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回答文明共存如何可能,需要对时代主题和时代潮流进行重新判定。在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世界局势中,“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8]264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根本目的就是建构“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19]这就要求世界秩序背后的文明秩序也呈现“和而不同”的样态。
不同文明得以共存且“和而不同”,首先要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狭隘视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乃是构成国际关系及其冲突的重要因素,“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20]6显然,亨氏的理论“隐藏了一种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优越性”,①《从文明冲突到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载钱永祥主编《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政治思想的探掘》,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2年版,第73页。表现出很强的美国文化的强势倾向。与之相似,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提出“历史终结论”,他通过回顾20世纪的历史,断言西方文明,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随着这种文明形式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人类历史将走向“终结”。[21]1所谓人类历史终结,并非指历史的结束,而是特指历史的真正的重大问题都已解决,历史的合理的原理与制度都已形成,从此历史不再有真正的进步和发展。这显然是一种以“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论”为归依的“文化趋同论”。反观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性,“亲诚惠容”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对“文明冲突论”和“文化趋同论”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论”的话语体系,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为文明共存提供了契机。文明的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当前,人类正经历着历史上第三次重大变迁的冲击,因此人类正处在创造一个新文明的过程之中。历史地看,第一次浪潮——农业革命,出现了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出现了工业文明;第三次浪潮——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信息革命,出现了信息文明,三种文明对应三种主要财富形式,土地贡献的是食物,资本带来的是金钱,信息给予的是自由。从个人角度看,人有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三层需要,农业社会主要满足人生存的需要,工业社会主要满足人发展的需要,信息社会主要满足人自我实现的需要。②参见姜奇平:《21世纪网络生存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根据梁漱溟的“人类三大文化路向说”,西方文化解决的主要是人的生存问题,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解决的是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是更高层次的思考。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要想在世界文明竞争中有所作为,就要做到“合而为新”,也就是说,不仅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明成果,剔除传统思维惯性和交往方式,还要充分消化吸收西方现有的文明成果,根除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弊端,攫取二者符合现代化趋势的部分,创造一种立足于中华文明根基的现代性文明。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一个新文明生产时的阵痛。正如托夫勒所提到的:人类不只在过渡,而是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且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这一“新文明有其截然分明的世界观,有其处理时间、空间、逻辑与因果关系的独特方式。并且有其对未来政治学的独特原则纲领”。[22]3-4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由谁创造。新文明与世界历史力量转移密切相关。在由体力型经济走向智能型经济的环境下,当前的很多社会问题,如能源、战争、贫穷、生态等,已经不能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得到解决,迫切需要创新型、生态型、和平型的文明形态。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过渡到创新型强国,当代中国人应自觉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的中国崛起正在创造全人类所需的新文明。这种新文明的优越性将随着中国崛起日益凸显出来。站在世界变局的十字路口和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中国崛起不是处在人类现代文明之外的发展,而是自主融入、引领世界潮流的发展,中国崛起不仅意味着文明复兴,而且还象征着新文明的创造。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的社会主义,也不等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在理论上与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续写中华文明新篇章,关键是要创造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就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他人的主体间关系以及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上进行革命性变革,建设美丽中国、平安中国、和谐中国、健康中国,从生态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意义上为世界贡献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