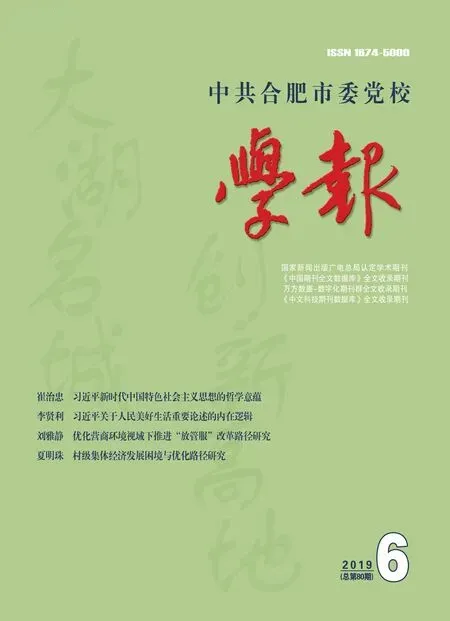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李贤利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山东 济南 250099)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报告、演讲、致辞中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思想新观点。科学理解、正确认识这些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必须充分把握贯穿其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质生活的科学论述, 是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把物质生活纳入研究范畴, 作为立论前提,设为逻辑起点,阐释了“现实的个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的客观实在性、自然社会性和重要必要性,解析了“现实的个人”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能力、 生产关系及其相互矛盾运动规律,论述了“现实的个人”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道路、形式、方法。 “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2],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资料制约人类发展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是“现实的个人”的自然、本能、生理属性,是人类肉体组织生成、活动和发展的客观、实在、具体标识,是人类生产、生存和繁殖的第一前提、基本条件。人类要想能够生活和长期生活下去,每日每时每刻都需要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等其他东西。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3]
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 再三强调“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4]“悠悠万事、 吃饭为大”“不吃饭就不能生存”[5],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统一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第一,掌握和运用了物质生活资料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6]和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告诫全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训,“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7]。 第二,掌握和运用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指出,“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8];“发展, 说到底是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9]第三,掌握和运用了物质生活发展长期性、曲折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张“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逐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0],量力而行做好民生改善工作,绝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尽力而为做好民生托底工作,绝不光喊口号、只放空炮,“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 ”[11]
(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实践决定思维认识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从客观的、 真实的物质生活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12]的客观真理,阐述了观念、思维“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3]的科学观点,强调一切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
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 一方面主张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 另一方面主张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4],掌握和运用了物质生活存在与上层建筑要素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原理。 一是把“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15]贯穿党的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 再三强调改善民生是头等大事,先后提出执政者的首要使命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6],党的历史任务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17],党的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8],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19]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维、新理念。二是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贯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部工作之中。 强调国家宪法是“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20]的最高遵循和基本准则,坚持一切法律的立、改、废、释都要为了人民生活、造福人民生活、保护人民生活。三是把“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21]贯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部工作之中。 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为人民创作、为群众立言,多感知人民生活疾苦、体察人民生活冷暖、关注人民生活偏好、反映人民生活要求、传递人民生活心声。
(三)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条件决定阶级关系的政治立场
没有私人占有,没有贫富分化,就没有贫穷、没有阶级、 没有阶级对立,“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2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系统论述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 使用和支配是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和阶级、阶级对立的真实基础,深刻批判了物质生活条件的好坏、 优劣和高下之分是反映阶级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根本因素, 科学阐明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 ”[23]
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 谋划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历史任务,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4]作为促进物质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出人民幸福最终要“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25],强调“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现实, 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奋斗”[26], 充分代表了人民利益,集中体现了人民立场。第一,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依赖主体。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灿烂的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27],以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28]第二,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享受主体。创新完善人民获得出彩人生、梦想成真的规则,切实维护人民获得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全力创造人民获得发展自我、奉献社会的机会,精心保障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公共服务,尽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9]第三,人民是美好生活的评判主体。为人民服务工作到位不到位,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30]
(四)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社会变革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批判揭露了工人阶级贫困潦倒的物质生活与资产阶级奢侈浪费的物质生活之间的直接的秘密联系: 资产阶级凭借资本特权不劳而获,直接或间接地占有、使用、支配和处分了几乎全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而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31],是生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引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无产阶级要想摆脱生活贫困, 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重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大工业生产“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32]
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 把消除贫困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重要使命,把“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33]作为心头牵挂,强调“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34],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35],吹响了脱贫攻坚冲锋号,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产业工人生活贫困的批评逻辑、批判思想和消灭贫穷的伟大设想。一是守住民生底线,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织紧织密织实社会保障网络。二是抓住教育根本,“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36]三是拧紧思想开关,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淡化贫困地区“贫困意识”,引导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四是把握关键环节,因地制宜帮扶贫困地区实现产业脱贫, 全力以赴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就业脱贫。
(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宏伟蓝图的时代内涵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最初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建立在“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37], 实现了社会占有物质生活、生产资料,全体社会成员在必须劳动的前提下“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38],过着“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 ”[39]
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 一再强调“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0]。 “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41],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伟大设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人民增添更多福祉的美好事业, 实现了人民生活从忍饥受饿到基本温饱的根本转变,即将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华丽蝶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与优秀文化传统相耦合、与时代发展潮流相一致、与人民群众命运紧密关联,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过上这样水准的生活。”[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安排。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土沃田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公共产品,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民健康、 关于民族永续,“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43],必须抓紧抓实。
二、 苏联共产党探索实现所有劳动者最美好最幸福生活的历史鉴戒, 是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待遇, 曾是苏联共产党一切活动的全部意义、最高职责、遵循路线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经营原则、发展规律、基本要求,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苏共丢掉了初心、忘记了使命、违背了规律、走错了道路、偏离了方向,没能将丰满理想落到实处,结果导致宏伟计划落空,教训十分深刻。
(一)苏联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人民生活的计划安排
列宁积极寻找俄国工人农民生活贫困的真正根源,努力探索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途径,使社会主义的生活理想变为现实。首先,恶劣的生活境况是导致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原因。 列宁号召遭受盘剥掠夺的一切无产工人密切联系和团结起来,“为改善生活条件、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而斗争”[44],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开辟一条消除剥削压迫的崭新社会道路。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主要“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45]列宁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政权要想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 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下生存下来, 关键就在于使人民群众相信“无产阶级给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资产阶级给他们的好”“布尔什维克使他们的生活更有保障。 ”[46]第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人农民生活。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指出,“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 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 ”[47]他甚至把“改善承租企业中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当地同类企业的其他工人相比),使其达到国外的中等标准”[48]列入外资租让合同,作为承租首条契约。
斯大林指出, 工人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刺激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展示社会主义优势的前提和保证, 强调苏维埃经济生产、分配的目的均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49]在他的领导下,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发布《关于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 研究部署“能够在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最大发展速度条件下提高工人阶级与贫、中农的物质生活水平”[50]这一重大核心课题。据此指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 (1938-1942 年)、 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 年)、 第五个五年计划 (1951-1955年)一脉相承地分别规定了“五年计划中的劳动问题”[51]“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的计划”[52]“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计划”[53]“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计划”[54]“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保健事业和文化水平方面的任务”[55]等内容。
赫鲁晓夫指出, 党一切活动的全部意义在于“提高人民的福利,发展和更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56],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 ”[57]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 年)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 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速发展农业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与文化水平”[58]的目标任务。仅仅过了三年,他就急躁冒进地宣布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具备了使“苏联全体人民在最近就开始过更加美满的生活”[59]的一切条件。两年过后,他又脱离实际地提出尽快实现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走在资本主义国家前头,在世界各个国家面前做出“真正充分和全面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榜样。”[60]
勃列日涅夫倡导恢复发展列宁关于科学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 引导苏联人民生活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他把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党最重要的任务, 把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福利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迫切需要和重要前提、 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和最高目的,提出了“进一步使经济建设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61]的核心命题。 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 年)一以贯之地提出了“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使全体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更充分地满足”[62]“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63]“始终不渝地实现共产党关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方针”[64]“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65]等目标任务。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改造的施政纲领,幻想在短期内解决食品短缺问题, 使每一个苏联人民、 苏联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党的领导是“保证苏联人在和平条件下过上物质和精神都丰富的、有充实社会内容的生活”[66]的先决条件。 党的经济战略的最高目标, 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 ”[67]党的纲领性方针,“就是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保证不断改善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68]党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改进居民的食品供应,特别是肉、奶、蔬菜和水果的供应,“最充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69]党的长期目标,就是“保证各阶层居民和社会集团的福利进一步提高”[70],巩固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具体实践中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鼓吹的“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反而将人民生活拖入了困境,最终毁掉了苏联社会主义。
(二)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绩效总体评价
应该肯定的是, 苏联社会主义曾经为人民群众创造了较为丰裕发达的物质生活。 一是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长。1960 年、1965 年、1970 年、1975年、1980 年、1985 年,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638 卢布、843 卢布、1199 卢布、1434 卢布、1747 卢布、2090 卢布,呈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 二是社会公共消费支出稳步增长。1940 年、1950 年、1960 年、1965 年、1970 年、1975 年、1980 年、1985 年,居民从社会消费基金中得到的各种支付和优惠分别为46 亿卢布、130 亿卢布、273 亿卢布、410 亿卢布、639 亿卢布、901 亿卢布、1170 亿卢布、1470 亿卢布,绝对值呈现长期增长态势。三是生活消费品销售量稳步增长。 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中的肉类和肉制品、奶类和奶制品、鱼类和鱼制品、糖、蔬菜和瓜类、 水果和浆果的人均消费量分别从1913 年的29 公斤、154 公斤、6.7 公斤、8.1 公斤、40 公斤、11公斤增至1985 年的61.4 公斤、323 公斤、17.7 公斤、40 公斤、102 公斤、46 公斤。 四是生活消费结构日益进步。以工业工人家庭开支构成为例,伙食开支、衣着开支、文化生活用品开支、文化生活服务开支在各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分别从1922 年的45.6%、26.1%、1.1%、7.4%调整为1985 年的29.4%、15.2%、7.6%、24.4%, 生活品质显著提升。五是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 1950 年、1960 年、1965 年、1970 年、1975 年、1980 年、1985 年,分别有530 万 人、1200 万 人、1080 万 人、1120 万 人、1100 万人、990 万人、1000 万人获得了住房或为自己建筑了私有住宅;1960 年达到顶值后, 每年改善住房条件的人基本稳定在1000 万人左右。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提高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是生活资料生产产值长期偏低。 1913 年、1928 年、1940 年、1955 年、1985 年, 生活资料生产产值比重在全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64.9%、60.5%、39%、30%、25.2%,总体呈现剧烈下跌态势,导致人民劳动分配所得远远低于国家所得和劳动创造价值,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二是生活资料生产权力高度集中。生活产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怎样生产统统依靠党和国家的行政指令,剥夺了企业消费产品生产的主体地位,抹杀了群众消费的个性需求, 扭曲了社会商品的供求关系,导致“社会需要同已经达到的生产水平之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有保证的物质供应之间的脱节。 ”[71]三是生活资料生产基础不牢。 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的农业,是人民生存之本、生命之脉,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1951-1955 年“农产品生产的五年计划任务没有全部完成。 ”[72]1959-1965 年“七年计划的农产品生产任务没有完成。 ”[73]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 年)规定的部分农业发展任务也都未能完成。四是生活资料产品供应不足。“六五”时期,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增长开始滞后。 20 世纪60 年代,某些日常生活食品特别是肉类食品“有时造成商业中的脱销现象”[74];鞋靴、缝纫品、麻织品特别是上等毛织品供应一度紧张。 20 世纪70年代,中小城市的肉、奶、黄油等普通食品供应匮乏。20 世纪80 年代后,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肉和奶制品出现经常性短缺,蔬菜、水果供应紧张,白糖需要凭票供应。五是生活资料分配不公。农业生产长期剥夺农民剩余劳动,“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75]工业生产长期实行低工资战略,导致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美国人民。 1988 年上半年,苏联工人和职员的月均工资213 卢布, 仅相当于美国普通中等收入群众月均工资的1/6。 生活艰辛的劳苦大众是不会考虑“全国的共同‘进步’的”[76],他们必然会丢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77]
三、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状况的艰苦奋斗历程, 是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实践逻辑
“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78]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担负起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历史使命,始终不渝地“为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79]。 这是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实践逻辑。
(一)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赤诚初心和崇高信念
党的创始人之一、 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号召进行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上“主张实际的多数的幸福”[80],经济上建立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 ”[81]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深刻认识到劳动阶级摆脱饥饿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社会主义, 保证人人享受“平均的供给”,获得“最大的幸福”[82]“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83]党的早期领导人李达主张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改造,“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84]这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建马克思主义组织, 酝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谋求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 ”[85]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出版《劳动周刊》,刺激无产阶级“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 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86]19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87]的声音。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1921 年—1923 年, 全国各地党组织掀起了铁路工人、海员、矿工运动高潮,组织工人罢工,要求工头普遍增加工资、 减少无理压迫和残酷剥削,并取得了部分胜利,短暂地改善了工人的悲惨生活。
1923 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苦痛及要求, 遵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决定采用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形式,“为全国民众的利益而奋斗”[88],谋求“农夫、工人之解放”[89],“增进农人生活”“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 ”[90]遗憾的是,国共合作后期,面对国民党叛变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盲目依从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 不仅目光短浅、缺乏清醒认识,而且一味退让、委曲求全,甚至主动放弃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最终导致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
(二)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与行动纲领
南昌起义打响了实现党代表平民利益主张的第一枪。毛泽东在长期的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进程中,郑重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91],一点都不能疏忽,一点都不能轻视。 他深刻指出,苏维埃要想打破国民党的“堡垒”政策和铜墙铁壁,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 ”[92]各地苏区在中央苏区的带动下,“以彻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93],制定劳动法规,明确工人劳动权利;“以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94], 颁布土地法规,打土豪、分田地,从而“使民众生活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受尽饥寒的地位,进到不但完全免除饥寒而且日益向上改良的地位。 ”[95]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 党中央果断提出“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96]的行政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立刻提出“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97]的奋斗目标和“改良人民生活”[98]的政治宣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党中央领导各敌后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统筹保障了各方财权、物权和人权,有效动员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 党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党委:“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 ”[99]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按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牲畜、农具、房屋、 粮食及其他财产,“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100]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 毛泽东告诫全党全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101]
(三)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逻辑与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连年战争和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其困难。 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积极稳定金融物价、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1953—1956 年,党组织领导了全国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扩大了人民群众生活资料供应,改善了农民生活,增加了合作社社员收入,给与私营工商业主生活出路。 其间,“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102]写入国家宪法,“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103]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了人民生活改善权利和目标。
1956 年起,我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 党和国家先后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8-1962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1976—1985 年)中相继规定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04]“保证城乡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105]“逐步改善人民生活”[106]“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07]等具体内容。 但由于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多年来“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 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108]
“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09]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前期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吹响了“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0]的时代号角。 一是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判断标准, 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111]二是把“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判断标准,强调“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12]三是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 强调社会主义虽然在本质上优越于资本主义, 能够实现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113]
(四)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是新世纪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要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2020 年之前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为他们谋利益,带领他们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114]一是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出发点,“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 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115]二是开拓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事业的落脚点,“还是发展经济,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16]“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117]三是妥善处理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118]唯有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让群众感到安心、放心和舒心,才能让百姓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汲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衰亡的教训, 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国力,“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119], 描绘了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要求全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120]“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121]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任务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平等地过上富裕幸福的美好生活。”[122]全党同志必须认真工作,“带领群众创造幸福生活。”[123]第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124]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125]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事业。 ”[126]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主要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幸福生活。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