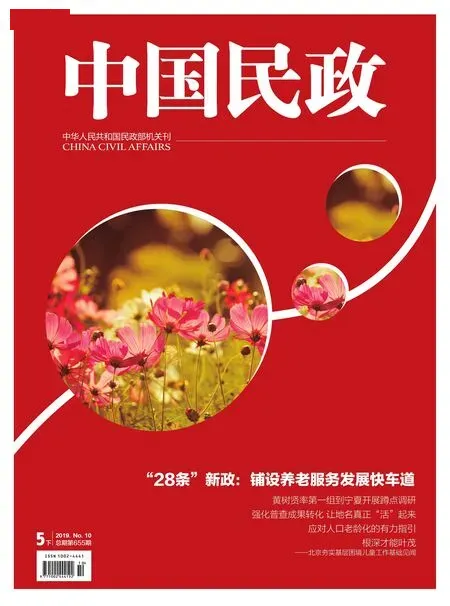根深才能叶茂 北京夯实基层困境儿童工作基础见闻
彩绘门楣,红色方柱,蓝色桌椅,整洁而温馨,几个孩子在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儿童成长驿站内玩玩具,志愿者陪伴在侧……
在丰台区和义街道和义东里第三社区,社工崔超冉和同事正在困境儿童家中走访……
中午放学后,女孩精灵回到房山区儿童福利院吃午饭,母亲入狱,姥爷体弱,这里有她的“李妈妈”“徐妈妈”,是她的另一个家……
北京有262万名儿童,其中困境儿童约2.2万名,在困境儿童工作方面一直在探索:2013年入选民政部20个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2017年9月在全国省市民政厅局层面率先成立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专门处室;但也面临着难题:基层基础能力薄弱,“尤其是基层社区作为儿童服务递送体系‘最后一公里’,缺设施平台、缺工作力量、缺工作机制。”2018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儿童保护和福利处在一份材料中提及有待解决的问题时如是说。叶茂必得根深,这一年,通过不断探索推进、总结提升,他们终于找到了破解之道。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社工,各司其职
“儿童处成立时编制4人,这次机构改革,市委社工委和市民政局合署办公,我们充实到了8个人。”北京市民政局儿童保护和福利处处长孙先礼说,机构改革为理顺和强化儿童福利工作管理机制提供了契机,区县层面实现了业务归口管理,街道“大部制”改革中强化儿童福利等民生保障部门,明确街乡、社区(村)力量配置。
与此同时,平台正在搭建,规划建设儿童福利服务指导中心、紧急庇护站以及儿童之家、儿童心理服务站;通过设立街乡儿童督导员、社区(村)儿童主任,基层工作力量逐步加强。2018年8月底,北京331个街乡、7097个社区(村)实现了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配备,并制订了队伍实施管理意见,明确队伍的来源、条件、任务、职责等等。
作为儿童福利递送最末梢,儿童主任通常由社区工作者兼任,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儿童保护和福利处副处长乔伟圣这样定义:问题发现者,政策宣传者,资源链接者。“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是一层一层的,儿童主任更多是预防,应对苗头性、初级性问题;再严重的,可能要在街乡层面解决,资源链接、政策帮扶;涉及监护侵害的突出个案,通过区级层面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保障联席会议制度解决。”
一方面,基层工作繁杂,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精力有限;另一方面,北京社工事务所500多个,做儿童工作的很多,应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政府购买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
这一年,通州区儿童福利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嵩体会到,儿童福利事业发展整体环境更好了,机制顺了,基层力量充实了,针对困境儿童的成长驿站、普惠型的社区儿童之家正在建设,“我们拿到了中央和北京市两级福彩公益金将近900万元,在每个乡镇设立儿童成长驿站,对困境儿童进行帮扶。”
会都开到高法和民政部去了
“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做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购买服务项目了,”中鼎社工事务所主任苏峰说,项目开始实施没几天,丰台区民政局转给他一个案子,“这是项目第一个案子,也是最难的一个,持续了两年,会开了十多次,都开到高法和民政部去了。”
在什刹海附近,一名女子带着个4岁的孩子,白天乞讨,晚上住窝棚。一查,女子是丰台区东高地人,因家庭矛盾出走,孩子是非婚生。社工找到他们时,天寒地冻,孩子正在破帐篷里玩,头发没几根,话也说不清;而妈妈则是精神异常。丰台区民政局和社工把母子俩接回来,街道民政工作人员帮着租房子。女子依旧每天带了孩子去乞讨,社工只能跟着了解情况。
与此同时,社工找到了女子父亲,老人年高体弱;又做孩子父亲的工作,孩子出生后脚有残疾,家里出钱给孩子做了手术,和孩子感情基础还是有的,但已经结婚;最后,社工以孩子爷爷奶奶为突破口,多次沟通,老人表示愿意抚养孙子。
但如何带走孩子,着实让丰台民政局和社工为难。此前沟通涉及母子俩流浪的西城区、孩子父母所在地朝阳区、丰台区,以及民政、公安、城管、法院、妇联,尚且能通过各种途径协调;但带走孩子不但关乎人情,还有法律。关键时刻,民政局领导给了社工很大的支持。最终在社工和律师的劝说努力下,孩子父亲愿意出面沟通安置问题,并承担了孩子的养育责任。
“2016年,孩子办了户口上了学,现在又弹琴又画画。”苏峰边说边掏出手机,“春节晚上12点,孩子父亲准会给我发孩子照片,一年比一年变化大。”
这个孩子只是丰台区1403名困境儿童中的一个,他们为困境儿童家庭建立了信息档案,对260户重点家庭进行了风险评估,并为高风险家庭提供跟踪服务;为712个家庭提供监护干预、社会救助、心理疏导、教育矫治、技能培训等服务;并形成了源头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等五大机制。
苏峰特别看重源头预防。一次,有个孩子因家暴找到社工,并报了警,苏峰希望警察可以对孩子妈妈进行训诫,警察却劝孩子“你妈多不容易”,结果从晚上6点沟通到凌晨。“儿童福利观念需要宣传,相关技能更需要学习。”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对生活的信心”
2017年4月,微弱的婴儿哭声从一间女厕传出,保洁员发现后马上报了警。2018年12月,婴儿妈妈马某因遗弃罪被判刑一年六个月。
孩子在医院完成治疗后,被送到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养育,但监护权仍旧悬而未决。事发地海淀区民政局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并找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张雪梅,她曾代理了北京市第一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
“我们要先确定孩子生父、外祖父母能不能养。”张雪梅说。调查结果是:孩子生父不明;外祖父养着马某的一个孩子,外祖母是继母,也带着一个孩子,生活压力较大。最终,法院撤销了马某的监护权,指定海淀区民政局担任监护人。
这或许不是事件的终点,儿童利益在每个阶段可能是不一样的。孩子后续的安置如何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则?在母亲身边长大无疑是最优选择,母亲是否愿意抚养孩子,恢复监护人资格是否可行?民政局和福利院正在研究,但也存在法律困境:按照《民法总则》,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不能恢复监护人资格。
其实,民政部门履行对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兜底责任,北京从2003年就开始探索了。当年,张雪梅曾承办过这样一起案件。一个又聋又哑还有肢体残疾的女人因家庭矛盾被接回娘家,后来女人丈夫去世,留下了10岁的孩子。孩子找到妈妈住处,砸门呼喊,奈何一墙之隔的妈妈根本听不到。父亲去世,母亲不具备监护能力,是否启动国家监护?经过一年多协调,民政积极作为,担任孩子的监护人,协调了福利院,落实了国家监护。
这一案例也直接推动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2003年修订时第十五条的出台,父母死亡、丧失监护能力或者监护人监护资格被依法撤销的未成年人,村居委会也不具备监护条件的,可以由民政部门依法担任监护人,2017年《民法总则》确定了这一原则。
2017年底,一个小伙子找到了张雪梅,就是十几年前那个孩子。他已经工作了,但不想离开福利院,“我的行李在那,就觉得那是我的家,我是有家的人。”一番劝解后,他决定离开福利院,“妈妈很不容易,将来我养她。”
“他走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对生活的信心,”张雪梅感叹,“国家监护及时补位了,及时保障了,使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同时还能解决妈妈监护养老问题,这是多好的循环。”
如何守住阵地、探索边界、形成合力
基层基础能力提升,为北京困境儿童工作带来了新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首先,社工能力建设还不足,他们应该熟知各部门保障政策,还需要了解孩子心理建设能力。其次,政府购买服务的标准,目前没有指导性意见,我们参照的是2017年三社联动的资金使用标准,肯定比现在低。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可能在挣很少的钱甚至不挣钱的情况下做事,不利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也不利于社工职业发展。最后就是疑难个案,基本靠专家出主意,我们和相关部门协调,特别牵扯精力,有时甚至束手无策。”刘嵩说。
实践中如何守住阵地、探索边界、形成合力,这不仅是刘嵩面临的问题,孙先礼也在思考。“儿童工作各个方面跟民政都有关系,各部门也在从不同角度做,民政作为牵头,不可能包打天下。根据民政的职能,我们的主责主业是什么,配合协同是什么?联席会议制度要发挥引导协调作用,任务如何分解、部署给谁,既各司其职又能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儿童福利从补缺到适度普惠,未来是面对所有儿童的普惠,这也是北京民政人在研究的。“究竟做什么才能体现普惠?哪些需要民政做,哪些需要其他部门做?民政应该怎么做,工作切入点在哪儿?这还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