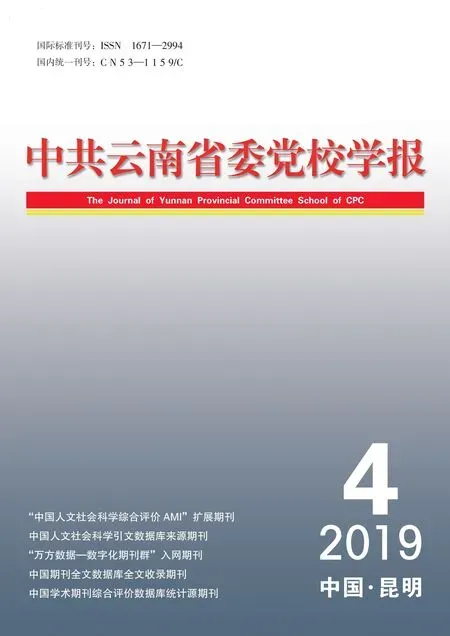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研究综述
左伟尘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的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力图梳理学界研究成果所关注的重点和争论的焦点,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一、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
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要理解矛盾必须先分析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的研究非常丰富。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拟从两个方面的思维抽象、两个方面的内涵、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三个层次来予以梳理。另外,把我党在1956年和1981年的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简称为“旧矛盾”,把2017年的论断简称为“新矛盾”。
(一)矛盾两个方面的思维抽象:“需求”和“供给”思路
1.经济学学科的“需求”和“供给”思路的主导性。学界对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理解具有多学科性视角的特征,但是,经济学学科的“需求”和“供给”思路是基础核心思维,是其他各学科研究思路的底色,即不同学科对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分析建立在“需求”和“供给”思路的基础上。
经济学学科从“需求”和“供给”思路研究社会主要矛盾是其鲜明特点。卫兴华认为,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认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2]刘少波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着眼点是人民利益及实现程度和路径,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是主要矛盾的经济学表达形式。[3]康伟认为,我国1956年、1981年、2017年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有变化,但是,矛盾的两个基本面都是“需要”和“社会生产”(或“发展”)。[4]钱智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需求和生产矛盾关系的理论演进,认为社会主义需求具有欲望和理性两种属性、生产决定理性欲望需求。[5]赵中源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矛盾两方面的内涵,认为新旧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未发生改变,仍属于“需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范畴,但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6]
2.经济学学科的“需求”和“供给”思路的渗透性。从“需求”(需要)和“供给”(生产或发展)来看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可能会使人误认为党的十九大的论断是经济主要矛盾而非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康伟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不等于经济主要矛盾”的警示,[7]但是,这种“需求”和“供给”的思路是可以超越经济学学科领域渗透至其他学科领域的,因此,它也就拓展了需求内涵和供给内涵的理解范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包含着“经济是基础”的合理性内核,同时也蕴含了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要求。因此,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延伸的广义概念。
(二)“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
学界普遍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的动态历史性概念。人民除了追求物质文明的需要之外,还有追求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需要。简言之,人民除了对经济收入这个基础和重点的需求之外,还扩展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环境等需求领域。
赵中源认为,“美好生活”具有普遍性、人民性和超越性的特点,人的全面发展是其核心要义。[8]马拥军认为,“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内部层次和结构的属性。[9]马克思把人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具有决定作用。虽然在认识上可以把人的存在划分为片面和孤立的经济人、政治人和道德人,但在实践中,现实的人却是要求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才能过上美好生活,单向度的人是不可能有美好生活的。当然,马拥军还没有指出人的生态生活,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本身的一部分,离开自然生态,人也不能存在。
(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内涵
学界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理解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以广义的理解为主流),主要原因在于学者对“发展”和“不平衡”语义的理解不同。双方认识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把城乡、区域、领域、收入等纳入“不平衡”的范围。
1.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广义理解。赵中源认为,“发展”内涵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内涵,“社会生产”包括物质、人自身、精神、社会关系四个方面的生产,又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体。[10]邱柏生认为,“发展”主要具有结构、方式、质量和效益四个变量,“不平衡不充分”要结合这四个变量来考虑,结构、方式、质量和效益四个变量中的每一个变量都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还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11]马拥军认为,“不平衡发展”除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之外,还有城乡区域领域等不平衡。[12]相对于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而言,“不充分发展”主要是指享受需要的高级供给还不充分,同时三种需要的供给在质量和效益方面也不充分。[13]赵中源认为,“不充分发展”主要是社会生产四个要素(能力、总量、质量和效益)中的质量和效益不能满足美好生活需要。[14]王中汝认为,不平衡不充分可以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去认识,[15]经济方面主要指产能过剩、产品质量不高,导致消费需求境外外溢,社会方面主要指城乡、区域、领域、收入等存在差距。
2.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狭义理解。卫兴华认为,要从主要矛盾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方面的关系来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需求侧需要的产品面临着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趋势,但是,供给侧的产品是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类不足,因此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6]虽然卫兴华也认为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生态方面的供给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反对把地区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不平衡这种会长期客观存在的结构性失衡,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侧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范围。[17]
3.广义和狭义理解之论争的系统论出路。学界更多是从广义来理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上文已经述及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需求”和“供给”是超越经济学概念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经有多样高质需求的变化,“平衡充分发展”也是要多样高质供给才能满足这种变化。这是广义理解的可取之处。
不过也要看到,在供给端的变化中,供给品的质量是最核心的。从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看,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其实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做到数量充足,化解总体短缺之后出现的新问题,即要在总体过剩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解决质量和结构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是狭义理解的可取之处。
从论争情况看,有一个是否把主要矛盾也看成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认识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同一事物具有无限侧面,无限侧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系统性;同时,无限侧面中存在多个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具有矛盾性。学界的研究表明:“需要”和“发展”本身具有很多变量,这意味着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本身各自都是一个小系统。社会主义矛盾是一个大系统,包含着主要矛盾这个小系统,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一个更小的系统,因此,分析事物要坚持系统论和矛盾论的统一。
(四)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谁为主要方面、谁为次要方面?学界普遍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生产或发展),“需求”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次要方面。
刘同舫认为,不能通过抑制人的需要来适应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而是要通过具有能动性的发展的可技术化手段来适应人的需要,因此,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18]刘少波认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应得到认可和鼓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19]胡鞍钢认为,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新时代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而“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关系中,虽然生产力发展没有达到极高水平,但“不平衡”比“不充分”更加突出。[20]贾康认为,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最关键的是不平衡问题。[21]庞元正认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22]
二、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为什么会发生转化?学界普遍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方面来研究矛盾转化的依据。
(一)转化的理论依据
学界关于理论依据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
1.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学界普遍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矛盾论中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普遍矛盾,主要矛盾是特殊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形式相同,但是,性质不同。吕普生认为,不同的地方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敌我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23]导致这种差别的关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事实。因此,两种社会的基本矛盾外化表现为主要矛盾时才会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则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2.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发生转化。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主要矛盾的“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发生了转化。从需求侧面看,吕普生认为,需求结构、需求层次以及生产力发展释放需求的节奏发生了变化,[24]这种突破物质需求转向多元需求的变化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一个理论原因。从供给侧面看,因为生产(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生产(发展)的数量、质量、结构和效益等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即数量或多或少、质量或高或低、结构或强或弱、效益或优或劣,总之,不适应不匹配需求侧。这种数量短缺供给属性基本突破之后,转向质量高、结构强和效益优供给属性的变化,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另一个理论原因。与此种认识相似,易淼认为,新的利益失衡是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动因,利益失衡不是由利益总量性矛盾激化而是由利益结构性矛盾激化而激发。[25]
(二)转化的历史依据
学界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历史原因的探讨,大多侧重在描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几次变化的史实,认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事关全局的重大认识变化。
学界普遍关注了1956年党的八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的内在延承关系。艾四林从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回顾了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和应用的经验,认为如果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党的事业就兴旺,反之就会遭受挫折。[26]李景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史的分析中也得出这个结论。[27]李忠斌粗略描述了建国近70年来我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六次判断,[28]从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变化来看大致的历史顺序是:阶级矛盾(第一次、第二次)—需要和生产矛盾(第三次)—阶级矛盾(第四次)—需要和生产矛盾(第五次、第六次)。余雷把建国以来的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划分为阶级矛盾(政治层面)、供需矛盾(经济层面) 和存续矛盾(社会层面),[29]这种划分虽然侧重点很明显,但是,冲破了新旧主要矛盾本质属性不变的理解。高文兵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的变化(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30]隐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存—从小变大—从大变强)的逻辑。
在历史分析中,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个是缺少主要矛盾与两大部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的分析。第二个是毛泽东对党的八大主要矛盾认识的改变是理论认识不清还是事实使然?换言之,1956年党的八大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受到1957年毛泽东两类矛盾理论认识或者其他理论认识的干扰更多更大,还是受到国际国内不利事件的干扰更多更大?从《毛泽东年谱》所载史实来看,这是理论认识不清和应对突发事件时经验定力不足两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或完成不久,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攻击等影响了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之后的中苏论战、苏美南北夹击中国的险恶态势,强化了毛泽东对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当然,还有一些理论上的认识,例如,毛泽东对六步不断革命论(即夺取政权、土地改革、再次“土地革命”、思想政治战线上革命、技术革命)[31]的认识越来越侧重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而偏离技术革命,进而认为我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期限不断延长,[32]在整个过渡时期必须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最后得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强化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
(三)转化的现实依据
学界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原因的分析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数据事实之类的定量分析较少。吕普生提出了判断转化的三个实践依据并进行了分析:首先,GDP总量、人均收入、社会贫困发生率表明现有生产力水平已经化解旧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是一种定量分析;其次,物质、民生、文化、政治参与、公平、法治、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变化是需求结构和层次变化;最后,通过定量分析证明发展不平衡在城乡、区域、收入分配、领域等方面表现明显,不充分在市场微观主体、经济发展方式、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公共物品和服务等方面表现明显。[33]聂辉华认为,从GDP总量、恩格尔系数、热点问题关注排名三个方面可以解释矛盾转化。[34]胡鞍钢定量实证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几个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并且认为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为严峻,后续排序是生态、文化、经济。[35]
学界研究成果的共同之处,归结到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
三、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本国情、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化,如何理解“变”与“不变”的关系?
学界普遍认为,要从质量互变规律,特别是总体量变和部分质变的统一中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两个没有变。当然,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变化的事物,虽然没有发生总体质变,但有总体量变,在这个总体量变中又包含着部分质变。
侯衍社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上升性、系统性、变动性、复杂性。[36]李君如认为,需要把主要矛盾变化与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统一起来进行理解。[3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任务不变,所以初级阶段的定位没有变。庞元正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次要矛盾取代主要矛盾的矛盾易位,也不是矛盾两个方面基本性质发生变化,主要矛盾本质属性未变,决定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8]金民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两个没有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没有变、新时代所处的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没有变。[39]
学界的研究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位阶高于新时代这个阶段,或者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强起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化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正确认识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小阶段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38年把即将到来的抗战相持阶段称为“新阶段”,按照同样的逻辑,根据实际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可以划分为不同小阶段:已经被历史发展证实的小阶段(温饱阶段、总体小康阶段、全面小康阶段)、正处于的新时代(或许又可以划分为总体富裕阶段和全面富裕阶段)。在这些小阶段中,中国发展成就巨大,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世界历史还是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在中国以社会主义国家身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必然面临资本主义力量的阻力,因此,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认识提醒我们,有所能有所不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依据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出的应对中国和平发展之外阻力的化解之策。
四、关于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
学界关于如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特点,但最主要的方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
学界认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宏观上的理念指导。孙兰英认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40]陶文昭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更加直接。[41]化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段。钱智勇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又可以表现为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之间的矛盾、需求质量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化解矛盾的手段是生产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2]贾康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这意味着从以往的强调需求管理转为供给管理,着力进行制度、产业、区域、收入分配、人文、生态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43]王中汝认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44]因此,需要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质量发展这个主攻方向。胡鞍钢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了优化结构、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两个方面的含义,并且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个方面的供给侧改革。[45]刘同舫认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最突出的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化解主要矛盾的着力点在于用分配正义解决贫富差距。[46]陈金钊认为,用法治来化解社会主要矛盾。[47]可见,学界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然,由于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内涵理解不同,卫兴华认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是从数量发展走向质量发展,[48]不能用城乡平衡、地区平衡、收入平衡之类的长期存在而又长期无法解决的话语冲淡或者挤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卫中旗认为,我国制造业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和企业利润率过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紧迫课题。[49]
(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方法之论争的辩证思维出路
学界的论争表明,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统一起来。人民美好生活肯定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生活,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发达的物质文明而要去化解其他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无异于空中楼阁。我国当前物质产品供给最重要的问题,是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效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伴随着“三去一降一补”的阵痛。当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解决其他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二者之间其实有一个演进逻辑。承认人民的主体性,就得从“现实的人”出发,承认个体的能力差异;社会要有活力,就要实行体现个体能力差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消除了绝对平均主义,但也必然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如果贫富两极分化,其本身及溢出的负面效应会危害社会和国家长远发展,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任务,既在经济建设之中,又在经济建设之外,要凝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合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因此,从辩证逻辑看,不同学科提出的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是合理的。
五、总结
(一)已有研究成果的成绩
第一,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以“需求”和“供给”思路为底色。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又是结合了数量、质量和结构三分法来进行,体现了数量与质量、内容与形式、本质和现象的内在统一。结构其实是内容的表现形式(即类型),数量、质量都有结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供给”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个方面都具有系统性的丰富内容。从总体上看,学界更多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方面多层次性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广泛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
第二,通过比较新旧主要矛盾,学界认为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有内在提升的变化,但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没有变化(仍然属于“需求”和“供给”范畴),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变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但新矛盾不是对旧矛盾的取代而是包含旧矛盾的转化和延承。
第三,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但对供给侧的理解具有多学科视角,因此,学界在具体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的优先次序上存在分歧,实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如何统一起来。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和建议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和系统论研究尚未结合起来。从系统论看,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各是一个子系统,这点虽然已经得到学界研究的事实证实,但关于主要矛盾和系统论相互融合的理论表达还比较少见。换句话说,“需要”是一个子系统,“发展”也是一个子系统。子系统内部各元素的属性(性质、数量、结构、功能)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两个子系统是如何对立统一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我们党改变或长期坚持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现象尚缺乏历史的经验分析。要从历史角度研究1956年社会主要矛盾论断没有长期坚持的原因;也要研究1981年社会主要矛盾论断36年内长期坚持的原因,因为改革开放40年能取得巨大成就,是与长期坚持这个论断密切相关的。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50]理论是经验的总结,从历史角度总结我党做出理论判断之后,处理后续各种重大事件时,如何对待原有主要矛盾论断的经验,对我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处理中美贸易战之类的重大事件时,保持定力,坚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